

□ 董国宾


在春天,总有不少让我念想的,憧憬的,踮起脚尖儿去翘望的事儿。
冬天还没像河流一样干枯的时候,春天似乎早就许诺了、答应了。等春天响起了脚步,一个个一件件,便绿鸟一样络绎不绝地飞来了。
春风穿上轻快的跑鞋,跑到哪儿,哪儿就换上新装。该绿的绿,该艳的艳,该欢的欢,该走向舞台闪亮登场的,自然没谁赖床昏睡了。
春阳甩开了温暖的手,绿柳扎上小辫子,高雀欢水歌唱起来,细弱银针的谷荻,也兴冲冲往春天挤,一溜小跑似的,唯恐掉下队。那样子天然的细,天然的小,又恬然地活在我的春梦里。
大地上跟随而来的,少不了一串串流水般的脚步声,一双双小脚丫如跃出水面的鱼儿,从一家一户的简舍篱院中走出来,相约去原野摘谷荻。
鲜亮亮的春野上,遍生一种叫茅草的植物,田边、地头、沟沿、荒地、河岸,到处布满它们的影子。茅草学名白茅,别名茅、丝茅草、白茅草。清明前后,茅草初生叶芽,恰处于花苞期的花穗,即谷荻。书上说之:“处处有之,春生芽,布地如针,俗谓之茅针。夏生白花茸茸然,至秋而枯。其根洁白,六月采之。又有菅,亦茅类也。”这谷荻如针,纤细的身姿,称为茅针。茅针可食,摘谷荻的少小儿童,食之满目童幻童趣。在不经意的阳光或月辉下,将记忆拉回锁在岁月的童年,如临春风似的,颇具怀想之美。那种美好或者说小光点,如镌刻的金边,是不褪色的,如实说,也拼成了我完完整整的人生。
春天点了下头,天就暖了,阳光给世界的边边角角,都呈上一份份春景。在追赶春意的童声童气里,自然不会遗漏我的影子。三五个,七八个,一前一后或拥堆而行的村里娃,这会儿正兴高采烈地接受春天的邀请,朝谷荻吐香的方向赶过去。天气还略带几分微寒,他们却像烤甜薯的小火炉,心思暖着呢。
浅滩上,沟渠边,田埂上,荒野里,一丛丛茅草从地层冒出来了。展露无遗的,是白白的,尖尖的,嫩嫩的,蓄势待生的一片片茅丛景观。谷荻长成了,正处于生长旺盛期,不过生长期短,仅十来天光景,过期就变老抽穗。适时来摘谷荻的小娃童,几乎同时低头弯腰,又同时睁圆小眼睛,你瞧这边,他瞅那边,专注地寻找一株株尖尖的绿芽。
“谷荻谷荻,出来打荻。鼓荡鼓荡,出来放枪。”小孩童一边放眼搜寻,一边齐声唱响快活的童谣。满脸喜悦的小孩们开始拔谷荻,谷荻嫩细若针,稍不留神会折断不出,瞧那心细如发,一门心思拔谷荻的凝神模样,个个可爱极了。“谷荻谷荻,抽筋剥皮,今年出来,明年还你。”拔谷荻是细致入微的活儿,娃娃们将拔谷荻的认真劲儿,与俏皮的儿歌捆在一块了。等细细茅针攥满小手,一个个小顽皮才舍得停下来。
寂静的高坡传来悦耳的欢笑声,如青鸟落入高枝开始了婉转的啼鸣。一群小娃娃聚拢高坡上,一阵欢喜过后,一只只紧攥的小手松展,放下,采获的谷荻濡了春天的气息,一根根欢快地滑落到地上。孩童像是也能做一次针线活一般,他们粉粉嫩嫩的巧手摘采的谷荻,谁的手心都握有十几支。小小谷荻,细小的茅针,如上天抛向舌尖上的一个美丽童话,接下来孩童开始品尝谷荻。他们先将紧裹的绿皮一点一点剥开,露出白白的嫩穗,一丝丝的,两头尖尖的,那诱人的雪白和晶莹,忽然间也破皮而出了。孩子们小心地放进嘴里,眯着眼去慢嚼细品,这轻若鸿毛之物,却让娃儿陶醉痴迷。少小时我尝惯了谷荻的春味,有点涩,丝丝的甜,淡淡的香,又柔软如棉絮,丝丝滑滑。嚼之乍然一现的,更有从感知世界中狂奔而来的浓稠的春天的味道、欢乐的味道和童年的味道。
女孩子机灵精巧,每次拔谷荻都多有收获。相比之下小时候我算手拙的一个,采摘的谷荻动几下嘴就吃完了,于是我拿橡皮跟她们进行交换,一块橡皮顶10支谷荻,先赊账回家如数偿还。我还交换过小铅笔刀,记得那次是我耍赖了,朝人家女孩子作了虚假承诺,谷荻吃进了肚子里,回到家却咬牙没认账。
谷荻,迎春而生。谷荻,长在顽皮的童年里。年少的每个春天,我心中装着甜丝丝的谷荻,呼朋唤友朝原野走去,走着走着,踩出一段人生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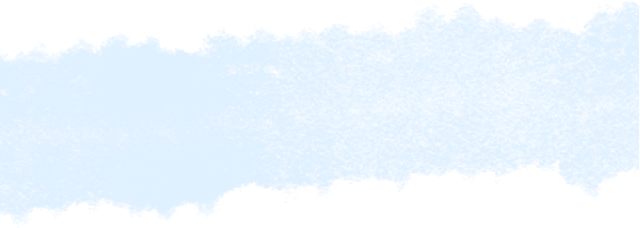

钟凡 手绘
□ 吴晓波
每年清明前后,在皖南老家一带,都有吃蒿粑的习俗。
这个时节,油菜花还在忙于吹奏金黄的喇叭,绿油油的麦苗闷着头一门心思打苞抽穗,最热闹的是空中的燕子和蜜蜂,来来回回不厌其烦地翻搅春天。此时,距离秧苗下种还有一阵时日,收割午季还早着呢,村里的农妇们完全有空闲来挑些刚出头的新鲜野菜,打点农家日子。
做蒿粑,就要用蒿。蒿有两种,一种是柴蒿,野性十足,遍地都是,最高能长到四五十公分,叶茎却不能食用,只能为柴,所以叫“柴蒿”;另一种是米蒿,大多生在田埂之上与庄稼为邻,个头长不高,叶片呈米白色,挑起放至篮子里,和野生的荠菜一样,闻起来有一股浓郁的芳香味。
小时,清明吃蒿粑,有一种“粑魂”的说法,说是吃了蒿粑,就能确保一年里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长大后,这种说法自然就不攻自破了,但皖南人爱吃蒿粑确实是有科学根据的。据《本草纲目》记载,将茵陈蒿细煮汤服,具有去眼热红肿,治伤寒头痛、风热痒疟,利小便等多种功效。米蒿属于茵陈蒿的一类,春季,乍暖还寒,血脉初开,正是各种流行病的高发期。吃蒿粑,一为美食,二为强身,可谓是一举双得,足见民间的智慧。
米蒿挑了回来,并不能马上食用。在家总见母亲把挑回洗尽的米蒿放入一石臼内,然后找块长长的鹅卵石细细地舂,直到舂得粉碎流出浓浓的汁来,然后再用清水洗尽。母亲说,这样,做出来的蒿粑就不会带有苦味了。洗尽后的蒿渣被母亲揉成几个绿莹莹的菜团子,放入盘中。
做蒿粑用的米粉,是用糯米和粘米混合磨出来的,一般是三七开,糯米不能多也不能少。
做蒿粑最关键的一道食材,就是腊肉了,最好是一块肥多瘦少的肉,切成肉丁子,大火在锅里翻炒至八分熟,直到肉里金黄粘稠的油全流了出来,此时,整个屋子都是腊肉的香味。小时家贫嘴馋,挂在梁上用来待客的腊肉没等到清明早就吃光了。等到清明,家家都在做蒿粑了。母亲就会变戏法般变出一块腊肉来。原来母亲早就留了一手,在坛子里藏下一块,上面盖上腌菜,以备做蒿粑之用。
米粉倒入面盆中,炒好的腊肉和米蒿团子也倒入,兑上温水,用筷子搅匀,母亲就开始用力地揉,直至变成一个泛着油光、青黑色的大面团。
蒿粑的美味不仅仅在于食材,更在于那一口烟火味十足的柴火大灶。离开了柴火大灶,蒿粑的美味也会大打折扣。成年后,母亲见我们一家子爱吃蒿粑,就让我们把揉好的面团带回来放入冰箱中,想吃时自己就可以做。城里的煤气灶方便是方便,可功效却远远比不上母亲乡下那土里吧唧的柴火大灶,做出来的蒿粑怎么吃也吃不出那股烟火味道来。还是母亲亲手做的蒿粑解馋过瘾。
母亲在灶下用柴火把小半锅水烧沸,便让父亲蹲在灶下续火,把手洗尽,从面盆里扯出一个个面疙瘩来,双掌合吧合吧,一个粑粑就成了,贴着锅面围上一圈,然后大火烧上十来分钟,一锅蒿粑就好了。这样做出来的蒿粑一面软,一面硬,硬的一面带着一层柴火烧出来的焦黄的壳,吃起来特别有味。
盛在碗里的蒿粑看上去很粗糙,黑不溜秋,还带着母亲瘦黑的手掌印。但腊肉的味道、米蒿的味道、大米的味道、柴火的味道,经过母亲双手的一发酵,便成了独一无二的人间美味,吃得人胃口大开,一口气来个五六个也不在话下。
皖南人爱吃蒿粑,是道解不开的情结。清明前后,除了家家做蒿粑吃蒿粑,就连大街小巷卖早点的摊子上,也会支起个炭火炉子,小铁锅上煎着滋滋冒烟的蒿粑。“蒿子粑粑呢,蒿子粑粑呢。”方言十足的叫卖声,悠长而又浑厚,如同那缕永久飘散在故乡天空的炊烟,牵扯远方游子的心。
是的,清明到了,母亲的蒿粑也熟了,现在就起程,回家。
□ 宋庆发
岭南建筑

会同村。珠海传媒集团 吴长赋摄
一脊镬耳,截图名利掠影;一檐灰瓦,见证高屋建瓴;一栊趟门,打开大湾乡愁。
所有的符号,无需标点;所有的意象,任意东西。
寺庵祠庙,何其厚重?何其绝伦?光孝寺不但有光有孝,梅庵自然源于梅岭寒梅。陈家祠述说的,何止陈家事?南海神庙祈求的,何止“海不扬波”?北帝有应之灵,感念诸庙之缘;南粤忠义之风,赓续汉宋香火。
庭院楼阁,何其轻巧?何其通透?轻巧得可以让梁家后花园昨夜的故事,今晨登上历史前台;通透得如清晖,如余荫,无粉墨,静悄悄,自带光。
市井街巷,烟火为胜。当西洋的建筑线脚缝进东方的青砖,西关小姐,便锦心绣口地步出大屋,招摇过市;东山少爷,便站在时代的潮流之上叱咤风云、尽得风流。当德庆学宫“四柱不顶”的文气,顶不住沙面列强的频频“出跳”,开平碉楼,只能让子弹飞,让离魂归。而今,粤式骑楼,又随姚黄魏紫、郁李樱桃,走入春天最深处。
岭南建筑,汇聚世界目光,纵览百越千秋。
岭南音乐
一把梦托给石头和树,山歌便气若幽兰;一把心交与波澜和鱼,水韵便质朴无华。
淘取螃蜞(蟛蜞)一串,串成一地凼凼转的月光光,小儿够无赖吧?听取雨打芭蕉一宿,仍心心念念春郊试马的小桃红,老夫够聊发吧?
唐宋遗风,旖旎不散。龙舟意气,说唱何妨?
让山再寒一些吧,甚至寒成山歌或英歌的一个歇脚;让水再瘦一些吧,甚至瘦成粤曲或潮剧的一抹顾盼。
如是,山更空,水更虚,音更清。
黄钟余韵宛在。
丝竹涛声依然。
插秧辞
(外一首)
□ 王轲
在故乡的稻田里插秧
一株秧苗下地
另一株秧苗也尾随其后
高矮不一的秧苗
是一排音协律美的钢琴键
在斜风细雨的催促下,
我们加快了步子
就像在弹奏一支曲调激昂的乐曲
有的深,有的浅
每一个节拍都有一株秧苗在生长
我的母亲在稻田里插秧
佝偻的背影是一个拉长的问号
只一眨眼,
母亲的秧苗便一望无际
我的秧苗却孤独地趴在水面上
像一支笔
在书写着幼时的力不从心
日历撕下一天再一天
秧苗长了又割,割了又长
我们在插秧与稻香之间反复往来
与东升西落的故乡有了更深的交集
耕牛辞
在广袤无垠的草海上
它们低头吃草
像一台小型的除草机
牧牛人在桑树下栖息
牛绳只拴在青草最深处
宁静祥和,如一帧古画
耕田时,有的牛个性犟
牧牛人便挥起长鞭
每一声都像抽在坚硬的岩壁上
它们背上犁耙
将土地犁出一行对偶的句子
春去秋来,农作物在土地上生长
密密麻麻的鞭痕在雨丝里巧妙缝合
它们是田间一枚沉重的动词
在作物和农人之间承前启后
像一座无怨无悔的独木桥
□ 龙建雄

珠海传媒集团程霖摄

“春事阑珊芳草歇。客里风光,又过清明节。”
读《东坡词》里这首《蝶恋花·春事阑珊芳草歇》很有似曾相识的情景切入感:春天野草芳菲,百花盛开,处处令人赏心悦目,所谓“人间四月芳菲尽”,这美好的景色一闪而过。久处异乡,又是一年清明节,只能在外地深深地思念那些远去的先人。苏仙写这首词的时候,江南春去,自己远离家人,独居黄昏小院,又值清明,看春意阑珊、落红满地,此情此刻,悲不自胜、触目伤怀,于是有感而发,至今流传千古。
我们今人比古人怀念逝者要更直接一些。“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哪个先来,珍惜当下。”但凡这世间有意想不到的偶然事件发生,涉及到苍生,涉及到普普通通的生命个体,这大概就是朋友圈最火爆,也最潸然泪下的留言。“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生命薄如纸,来去一念间。但凡好友发怀念亲人的微信,我习惯慰问朋友“逝者安息,生者坚强。”我向朋友转达一种问候,或许是因为时光交错,那些亲人只是平静地去了另一个时空世界,多维立体的某个地方。
早两年的这个时候,岳父把他在这人世间仅存的一点点余温,在我和小舅子给他穿衣服过程里慢慢消退,他和我们完成了生命的彻底交接。再早六年,我握着爷爷的手,他把生命的最后一声呼吸拉得很长很长,眼角不自主流下眼泪,他似乎在“告诉”我,这就是生命的终结。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生命最后要是体面而又有尊严,那便是永生。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算是“空中飞人”,每每航班起降,会习惯性地在微信一家人小群里发“平安登机”“安全到达”。现在回想起来,这平淡无奇的几个字,大概也是我最爱家人的佐证吧。据说金鱼有7秒的记忆,据说人在正常脑死亡后的7秒内能够听到亲人哭泣,人生时间的停止,没有人能够重新激活,剩下的只有苍白无力。
人和人相遇的概率是千千万万分之一,说一声“您好”“再见”,在岁月长河里其实都是难能可贵。人与人之间的相识相知绝非偶然,若有意,相隔千里都会不期而遇,要是无心,即便是擦肩而过而也不会有丝毫交织;人生的相遇就如那一次次花开花落,人生的别离则如同那一场场风雨雷电,一切的发生、结果,再发生、再结果,皆自然而然。所以,与他人认识就是一种幸运,此生是亲人那更值得倍加珍惜。
一回回的生死离别在不定期地发生,这些让我明白,世间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奇迹也是少之又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于是,在知晓人生无常这个常理之下,当下有什么想法大家就去勇敢地做吧。比如,好好爱一个人,感恩双亲,友爱姊妹,培育子女;又比如,专一某一项事业,追逐梦想,奉献国家;还比如,人心向善,团结周围,拯救自然……
活好是人生常态。好好地活,即当下,即时间以及生命存在的根本意义,特别是对先人们最好的怀念与回应。




□ 董国宾


在春天,总有不少让我念想的,憧憬的,踮起脚尖儿去翘望的事儿。
冬天还没像河流一样干枯的时候,春天似乎早就许诺了、答应了。等春天响起了脚步,一个个一件件,便绿鸟一样络绎不绝地飞来了。
春风穿上轻快的跑鞋,跑到哪儿,哪儿就换上新装。该绿的绿,该艳的艳,该欢的欢,该走向舞台闪亮登场的,自然没谁赖床昏睡了。
春阳甩开了温暖的手,绿柳扎上小辫子,高雀欢水歌唱起来,细弱银针的谷荻,也兴冲冲往春天挤,一溜小跑似的,唯恐掉下队。那样子天然的细,天然的小,又恬然地活在我的春梦里。
大地上跟随而来的,少不了一串串流水般的脚步声,一双双小脚丫如跃出水面的鱼儿,从一家一户的简舍篱院中走出来,相约去原野摘谷荻。
鲜亮亮的春野上,遍生一种叫茅草的植物,田边、地头、沟沿、荒地、河岸,到处布满它们的影子。茅草学名白茅,别名茅、丝茅草、白茅草。清明前后,茅草初生叶芽,恰处于花苞期的花穗,即谷荻。书上说之:“处处有之,春生芽,布地如针,俗谓之茅针。夏生白花茸茸然,至秋而枯。其根洁白,六月采之。又有菅,亦茅类也。”这谷荻如针,纤细的身姿,称为茅针。茅针可食,摘谷荻的少小儿童,食之满目童幻童趣。在不经意的阳光或月辉下,将记忆拉回锁在岁月的童年,如临春风似的,颇具怀想之美。那种美好或者说小光点,如镌刻的金边,是不褪色的,如实说,也拼成了我完完整整的人生。
春天点了下头,天就暖了,阳光给世界的边边角角,都呈上一份份春景。在追赶春意的童声童气里,自然不会遗漏我的影子。三五个,七八个,一前一后或拥堆而行的村里娃,这会儿正兴高采烈地接受春天的邀请,朝谷荻吐香的方向赶过去。天气还略带几分微寒,他们却像烤甜薯的小火炉,心思暖着呢。
浅滩上,沟渠边,田埂上,荒野里,一丛丛茅草从地层冒出来了。展露无遗的,是白白的,尖尖的,嫩嫩的,蓄势待生的一片片茅丛景观。谷荻长成了,正处于生长旺盛期,不过生长期短,仅十来天光景,过期就变老抽穗。适时来摘谷荻的小娃童,几乎同时低头弯腰,又同时睁圆小眼睛,你瞧这边,他瞅那边,专注地寻找一株株尖尖的绿芽。
“谷荻谷荻,出来打荻。鼓荡鼓荡,出来放枪。”小孩童一边放眼搜寻,一边齐声唱响快活的童谣。满脸喜悦的小孩们开始拔谷荻,谷荻嫩细若针,稍不留神会折断不出,瞧那心细如发,一门心思拔谷荻的凝神模样,个个可爱极了。“谷荻谷荻,抽筋剥皮,今年出来,明年还你。”拔谷荻是细致入微的活儿,娃娃们将拔谷荻的认真劲儿,与俏皮的儿歌捆在一块了。等细细茅针攥满小手,一个个小顽皮才舍得停下来。
寂静的高坡传来悦耳的欢笑声,如青鸟落入高枝开始了婉转的啼鸣。一群小娃娃聚拢高坡上,一阵欢喜过后,一只只紧攥的小手松展,放下,采获的谷荻濡了春天的气息,一根根欢快地滑落到地上。孩童像是也能做一次针线活一般,他们粉粉嫩嫩的巧手摘采的谷荻,谁的手心都握有十几支。小小谷荻,细小的茅针,如上天抛向舌尖上的一个美丽童话,接下来孩童开始品尝谷荻。他们先将紧裹的绿皮一点一点剥开,露出白白的嫩穗,一丝丝的,两头尖尖的,那诱人的雪白和晶莹,忽然间也破皮而出了。孩子们小心地放进嘴里,眯着眼去慢嚼细品,这轻若鸿毛之物,却让娃儿陶醉痴迷。少小时我尝惯了谷荻的春味,有点涩,丝丝的甜,淡淡的香,又柔软如棉絮,丝丝滑滑。嚼之乍然一现的,更有从感知世界中狂奔而来的浓稠的春天的味道、欢乐的味道和童年的味道。
女孩子机灵精巧,每次拔谷荻都多有收获。相比之下小时候我算手拙的一个,采摘的谷荻动几下嘴就吃完了,于是我拿橡皮跟她们进行交换,一块橡皮顶10支谷荻,先赊账回家如数偿还。我还交换过小铅笔刀,记得那次是我耍赖了,朝人家女孩子作了虚假承诺,谷荻吃进了肚子里,回到家却咬牙没认账。
谷荻,迎春而生。谷荻,长在顽皮的童年里。年少的每个春天,我心中装着甜丝丝的谷荻,呼朋唤友朝原野走去,走着走着,踩出一段人生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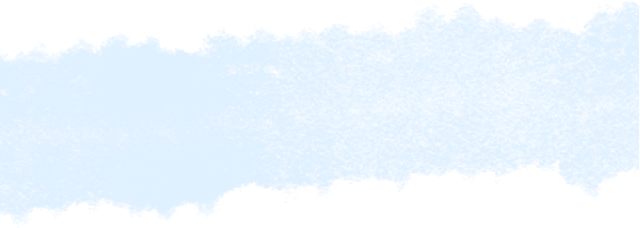

钟凡 手绘
□ 吴晓波
每年清明前后,在皖南老家一带,都有吃蒿粑的习俗。
这个时节,油菜花还在忙于吹奏金黄的喇叭,绿油油的麦苗闷着头一门心思打苞抽穗,最热闹的是空中的燕子和蜜蜂,来来回回不厌其烦地翻搅春天。此时,距离秧苗下种还有一阵时日,收割午季还早着呢,村里的农妇们完全有空闲来挑些刚出头的新鲜野菜,打点农家日子。
做蒿粑,就要用蒿。蒿有两种,一种是柴蒿,野性十足,遍地都是,最高能长到四五十公分,叶茎却不能食用,只能为柴,所以叫“柴蒿”;另一种是米蒿,大多生在田埂之上与庄稼为邻,个头长不高,叶片呈米白色,挑起放至篮子里,和野生的荠菜一样,闻起来有一股浓郁的芳香味。
小时,清明吃蒿粑,有一种“粑魂”的说法,说是吃了蒿粑,就能确保一年里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长大后,这种说法自然就不攻自破了,但皖南人爱吃蒿粑确实是有科学根据的。据《本草纲目》记载,将茵陈蒿细煮汤服,具有去眼热红肿,治伤寒头痛、风热痒疟,利小便等多种功效。米蒿属于茵陈蒿的一类,春季,乍暖还寒,血脉初开,正是各种流行病的高发期。吃蒿粑,一为美食,二为强身,可谓是一举双得,足见民间的智慧。
米蒿挑了回来,并不能马上食用。在家总见母亲把挑回洗尽的米蒿放入一石臼内,然后找块长长的鹅卵石细细地舂,直到舂得粉碎流出浓浓的汁来,然后再用清水洗尽。母亲说,这样,做出来的蒿粑就不会带有苦味了。洗尽后的蒿渣被母亲揉成几个绿莹莹的菜团子,放入盘中。
做蒿粑用的米粉,是用糯米和粘米混合磨出来的,一般是三七开,糯米不能多也不能少。
做蒿粑最关键的一道食材,就是腊肉了,最好是一块肥多瘦少的肉,切成肉丁子,大火在锅里翻炒至八分熟,直到肉里金黄粘稠的油全流了出来,此时,整个屋子都是腊肉的香味。小时家贫嘴馋,挂在梁上用来待客的腊肉没等到清明早就吃光了。等到清明,家家都在做蒿粑了。母亲就会变戏法般变出一块腊肉来。原来母亲早就留了一手,在坛子里藏下一块,上面盖上腌菜,以备做蒿粑之用。
米粉倒入面盆中,炒好的腊肉和米蒿团子也倒入,兑上温水,用筷子搅匀,母亲就开始用力地揉,直至变成一个泛着油光、青黑色的大面团。
蒿粑的美味不仅仅在于食材,更在于那一口烟火味十足的柴火大灶。离开了柴火大灶,蒿粑的美味也会大打折扣。成年后,母亲见我们一家子爱吃蒿粑,就让我们把揉好的面团带回来放入冰箱中,想吃时自己就可以做。城里的煤气灶方便是方便,可功效却远远比不上母亲乡下那土里吧唧的柴火大灶,做出来的蒿粑怎么吃也吃不出那股烟火味道来。还是母亲亲手做的蒿粑解馋过瘾。
母亲在灶下用柴火把小半锅水烧沸,便让父亲蹲在灶下续火,把手洗尽,从面盆里扯出一个个面疙瘩来,双掌合吧合吧,一个粑粑就成了,贴着锅面围上一圈,然后大火烧上十来分钟,一锅蒿粑就好了。这样做出来的蒿粑一面软,一面硬,硬的一面带着一层柴火烧出来的焦黄的壳,吃起来特别有味。
盛在碗里的蒿粑看上去很粗糙,黑不溜秋,还带着母亲瘦黑的手掌印。但腊肉的味道、米蒿的味道、大米的味道、柴火的味道,经过母亲双手的一发酵,便成了独一无二的人间美味,吃得人胃口大开,一口气来个五六个也不在话下。
皖南人爱吃蒿粑,是道解不开的情结。清明前后,除了家家做蒿粑吃蒿粑,就连大街小巷卖早点的摊子上,也会支起个炭火炉子,小铁锅上煎着滋滋冒烟的蒿粑。“蒿子粑粑呢,蒿子粑粑呢。”方言十足的叫卖声,悠长而又浑厚,如同那缕永久飘散在故乡天空的炊烟,牵扯远方游子的心。
是的,清明到了,母亲的蒿粑也熟了,现在就起程,回家。
□ 宋庆发
岭南建筑

会同村。珠海传媒集团 吴长赋摄
一脊镬耳,截图名利掠影;一檐灰瓦,见证高屋建瓴;一栊趟门,打开大湾乡愁。
所有的符号,无需标点;所有的意象,任意东西。
寺庵祠庙,何其厚重?何其绝伦?光孝寺不但有光有孝,梅庵自然源于梅岭寒梅。陈家祠述说的,何止陈家事?南海神庙祈求的,何止“海不扬波”?北帝有应之灵,感念诸庙之缘;南粤忠义之风,赓续汉宋香火。
庭院楼阁,何其轻巧?何其通透?轻巧得可以让梁家后花园昨夜的故事,今晨登上历史前台;通透得如清晖,如余荫,无粉墨,静悄悄,自带光。
市井街巷,烟火为胜。当西洋的建筑线脚缝进东方的青砖,西关小姐,便锦心绣口地步出大屋,招摇过市;东山少爷,便站在时代的潮流之上叱咤风云、尽得风流。当德庆学宫“四柱不顶”的文气,顶不住沙面列强的频频“出跳”,开平碉楼,只能让子弹飞,让离魂归。而今,粤式骑楼,又随姚黄魏紫、郁李樱桃,走入春天最深处。
岭南建筑,汇聚世界目光,纵览百越千秋。
岭南音乐
一把梦托给石头和树,山歌便气若幽兰;一把心交与波澜和鱼,水韵便质朴无华。
淘取螃蜞(蟛蜞)一串,串成一地凼凼转的月光光,小儿够无赖吧?听取雨打芭蕉一宿,仍心心念念春郊试马的小桃红,老夫够聊发吧?
唐宋遗风,旖旎不散。龙舟意气,说唱何妨?
让山再寒一些吧,甚至寒成山歌或英歌的一个歇脚;让水再瘦一些吧,甚至瘦成粤曲或潮剧的一抹顾盼。
如是,山更空,水更虚,音更清。
黄钟余韵宛在。
丝竹涛声依然。
插秧辞
(外一首)
□ 王轲
在故乡的稻田里插秧
一株秧苗下地
另一株秧苗也尾随其后
高矮不一的秧苗
是一排音协律美的钢琴键
在斜风细雨的催促下,
我们加快了步子
就像在弹奏一支曲调激昂的乐曲
有的深,有的浅
每一个节拍都有一株秧苗在生长
我的母亲在稻田里插秧
佝偻的背影是一个拉长的问号
只一眨眼,
母亲的秧苗便一望无际
我的秧苗却孤独地趴在水面上
像一支笔
在书写着幼时的力不从心
日历撕下一天再一天
秧苗长了又割,割了又长
我们在插秧与稻香之间反复往来
与东升西落的故乡有了更深的交集
耕牛辞
在广袤无垠的草海上
它们低头吃草
像一台小型的除草机
牧牛人在桑树下栖息
牛绳只拴在青草最深处
宁静祥和,如一帧古画
耕田时,有的牛个性犟
牧牛人便挥起长鞭
每一声都像抽在坚硬的岩壁上
它们背上犁耙
将土地犁出一行对偶的句子
春去秋来,农作物在土地上生长
密密麻麻的鞭痕在雨丝里巧妙缝合
它们是田间一枚沉重的动词
在作物和农人之间承前启后
像一座无怨无悔的独木桥
□ 龙建雄

珠海传媒集团程霖摄

“春事阑珊芳草歇。客里风光,又过清明节。”
读《东坡词》里这首《蝶恋花·春事阑珊芳草歇》很有似曾相识的情景切入感:春天野草芳菲,百花盛开,处处令人赏心悦目,所谓“人间四月芳菲尽”,这美好的景色一闪而过。久处异乡,又是一年清明节,只能在外地深深地思念那些远去的先人。苏仙写这首词的时候,江南春去,自己远离家人,独居黄昏小院,又值清明,看春意阑珊、落红满地,此情此刻,悲不自胜、触目伤怀,于是有感而发,至今流传千古。
我们今人比古人怀念逝者要更直接一些。“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哪个先来,珍惜当下。”但凡这世间有意想不到的偶然事件发生,涉及到苍生,涉及到普普通通的生命个体,这大概就是朋友圈最火爆,也最潸然泪下的留言。“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生命薄如纸,来去一念间。但凡好友发怀念亲人的微信,我习惯慰问朋友“逝者安息,生者坚强。”我向朋友转达一种问候,或许是因为时光交错,那些亲人只是平静地去了另一个时空世界,多维立体的某个地方。
早两年的这个时候,岳父把他在这人世间仅存的一点点余温,在我和小舅子给他穿衣服过程里慢慢消退,他和我们完成了生命的彻底交接。再早六年,我握着爷爷的手,他把生命的最后一声呼吸拉得很长很长,眼角不自主流下眼泪,他似乎在“告诉”我,这就是生命的终结。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生命最后要是体面而又有尊严,那便是永生。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算是“空中飞人”,每每航班起降,会习惯性地在微信一家人小群里发“平安登机”“安全到达”。现在回想起来,这平淡无奇的几个字,大概也是我最爱家人的佐证吧。据说金鱼有7秒的记忆,据说人在正常脑死亡后的7秒内能够听到亲人哭泣,人生时间的停止,没有人能够重新激活,剩下的只有苍白无力。
人和人相遇的概率是千千万万分之一,说一声“您好”“再见”,在岁月长河里其实都是难能可贵。人与人之间的相识相知绝非偶然,若有意,相隔千里都会不期而遇,要是无心,即便是擦肩而过而也不会有丝毫交织;人生的相遇就如那一次次花开花落,人生的别离则如同那一场场风雨雷电,一切的发生、结果,再发生、再结果,皆自然而然。所以,与他人认识就是一种幸运,此生是亲人那更值得倍加珍惜。
一回回的生死离别在不定期地发生,这些让我明白,世间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奇迹也是少之又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于是,在知晓人生无常这个常理之下,当下有什么想法大家就去勇敢地做吧。比如,好好爱一个人,感恩双亲,友爱姊妹,培育子女;又比如,专一某一项事业,追逐梦想,奉献国家;还比如,人心向善,团结周围,拯救自然……
活好是人生常态。好好地活,即当下,即时间以及生命存在的根本意义,特别是对先人们最好的怀念与回应。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