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历险和境界辽阔
——关于刘合军的诗歌

□ 陈啊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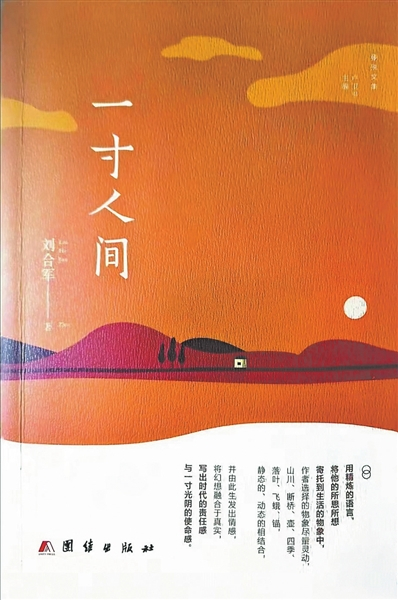
诗集《一寸人间》。 刘合军 著
从刘合军的一组近作看,他的诗歌风格悄然有了转变,其诗性的内核更坚实,而境界更为辽阔了。当然他诗歌的根基仍是建立在与自然界默默地相望和对语上,于平静中,于细微处,于空茫里,小心引发一场场“对峙”和翻转。更为清新和明晰的是,他和这个世界的“较量”基本出自越来越多的妥协和相安无事,他和万千存在,接受了时间的洗礼——这个共同的对手,所以一种“惺惺相惜”游走于文字间。也可以说,岁月蹉跎让诗人的心更为敏感,也更加细腻了,原先可作模糊处理的“空隙”和界面,已透析出更为本质的肌理。总体上,他倾向于内在的开阔掘进,力求呈现存在的本原和本性,揭开遮蔽真相的“皮”,其方法论不是哲学的或空幻臆断,而是用语言这一工具,即自有的言说方式,使存在敞开胸口,当然也只有诗歌的语言才能实现这一自觉,才能完成的美妙又彻底。
所以,我认为刘合军的诗歌,已然进入更高层次的成熟性,即对存在的深度思索与揭示。比如《微小的叙事》,写的是“平常的风”吹起“几片平常的叶子”,风和叶子是一对存在,如果不作深究和思考,就无法建立恒久、广阔并超出一般认知和美学感受的精神力量,我们尽可以去思索这一阵风从酝酿和劲吹的过程,它的力量是通过吹落几片叶子实现的,而叶子呢?它们从树枝上起飞,既是一种光辉的自由,又是曾经“盛开过的美好”的收场,诗人在这首诗的最后一节写道:“一条小道握住夕阳/一寸一寸地扎紧光阴的丝线,天空的一半/慢慢暗下来”,从低微处回到宏大处,由巴掌大的“叙事”推衍出宇宙,同样的一日辉煌与无法遏制的黯淡,就不再是简单的触景生情了,而是导入人文和生命关怀,其存在的真相毕现。
《松上日》这首诗代表了刘合军的心灵史。诗中有几个词组引起我的注意:“倾角”“弯曲的空寂”“空隙”,已简单构勒出生存状况,而一个“爱鱼的人”,“在松间闲坐”,这是另一个存在,所以:“一边接受光的喂养,一边/让密枝/空出喘息的空隙”。这不是普通的忙里偷闲,而是心灵自由放飞的逼仄与挣扎,这种看似“对抗式”的写作策略,所要揭示的并非某一变故或突发事件,是漫长而迟缓的人生。人生是需要从拥挤与淹没中脱颖而出的,是需要弯曲的,是需要沿着斜坡上行或下冲的,更需要在浓密的“耸立和满绿连成一片让微澜的光晕,躲进/弯曲的空寂里”,这就是人生的真相啊,屈身以求喘息和品赏的“自由”。很惊叹于刘合军身临水边,被环山和巨松遮掩时,心灵所产生的感应。说这首诗涉及“心灵史”,是因为生活之旅的艰辛和复杂在内心所形成的历史语境。历史在诗歌中,尤其是这类影射人生的短制中,反而能焕发出更强烈的气息,由此所产生的语言的张力,正如“按住历史的心跳”般,盎然保持了历史的也是求真求实的开阔思维体质。
我喜欢《立冬日》这首诗的原因,在于诗人将纯“中国元素”的节气“立冬”,放置到更广阔的空域,所体现的不止是语言能力,而是精神能力。我一直相信唯有自身的精神气力能够超越普世生存与存在,在精神的感召下,万物得以另一种形态生存。诗中:“鱼鹰被雪浪淹没/方言和足印被滚烫沙海拾起”,就具有精神的“法力”,如造物的上帝——谁又能说上帝不一定是真实存在,但它是精神的存在呢?刘合军诗歌在精神上的营造,反过来对他诗歌语言创化的生长,是相得益彰的,是彼此澄明与提升的。另一首《气场》,则更是将这种精神力无限扩张,气场是无形的,正如精神无法物化,但可以用心感触的:“有容乃大/可以装下宇宙的空旷,而星火在底部沉落,灿烂在万里浮荡/冬风吹响萧杀冷雪”,精神或气场要通过诗化语言来实现的,所以,“语言即存在之所”,从语言里构筑存在,包括一种精神的存在和形态功能。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写成诗歌,不是用了诗歌语言,而是以学术语言来说明一个瓶口可以“大”的程度,会被人当精神病。由这两首诗,可以说刘合军精神语言的提升与丰富,对存在的深度掘进,从而产生高迈情怀和生命力。
近观自然物是刘合军的拿手好戏,凸显的是他超常的想象力,由微小实物而打开宇宙。《旧叶子》写的是“一些放下天空的叶子”,我觉得诗人在很多场合选择“叶子”这一存在是很有讲究的,它的静雅与平淡,它的高度与低处,它的临空舞蹈与枯萎成泥,很像普通人的一生。诗人把这几片叶子放在冬日天空下观赏,当然就具有更锋利的言辞。通读全诗,诗人所营造的“荒诞”情景:“北风/把寒凉堆在门槛上,叶子不再低鸣/听说河岸以北/绽放了很多雪白的花蝴蝶,南岸与我/拾起大海初雪和落魄的旧叶子/等风吹”,所体现的也是语言的本质力量,将存在的核心要义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能力。从他的另一首诗《青花瓷鱼》中,诗人从一条观赏鱼身上,感受了一种“放逐”,一种世界的退隐,而另一种世界的蓬勃。诗人创造了另一个时空,从中“不觉顿生幻化和/一种莫名害怕,怕他洞穿/人性的厌恶”,生命的出路何在?诗中并无答案,但恍惚中的焦虑和悬疑,同样感染了读者,与人类相关联的重大问题在“我”和纯真的青花瓷鱼间展开对语,加深了人性的危机感。从中可见刘合军驾驭此类题材有活力的成熟性。
刘合军诗歌无一不体现了中年人的沉静、诚恳和细腻中潜藏着的轻盈和灵韵。他的诗歌是很准确恰切的日常口语,但又不是大白话,我觉得这种语气往往最适宜表达豁达又深刻的内在经验,能做到很松弛又适度陡峭,于坦诚中营造纯真的幻境。有如他在《走过月光走过的路》中写道:“光阴被流水打碎/良知像暮霭一样轻薄”,充满了对命运和人性的沉静反思和叹息。正如陈超说过的:“真正的诗人会深深体验到生存的阴晦和险恶,但仍然相信生存意义的可能性”,诗人并未灰心丧志,而是以亦庄亦谐的反讽语气,继续捕捉人间可贵的人性的清气和亮光:“我试着,抬起双臂和空气/一起轻轻划动/顿生/脱离陆地和拔出深渊的快愉”(《前山河看赛艇》)。总之,刘合军的诗是求真的,也是停不下来的文学追问和语言历险。
活在当下,与生活和解
——读《与尘世相爱》有感
□ 林小兵
□ 赖廷阶
好的散文不仅给人带来魅力,更让人得到精神的提醒,让人陷入沉思的散文更具有散文的深度与本质。散文的思想深度在于提醒人心、灵魂,让人得到精神的矫正,让灵魂获得光,成为光明的力量。
黄康生散文《“火水河”上流萤飞》,回忆了童年时代的捕捉萤火虫、伤害了它们,回忆起来的反省,是对人性弱点的深思,促使人回到爱里。为此,这篇作品在行文的字里行间,都有一种讲述中的深沉。
散文之美,首先在于语言美,只有雄厚语言功底的散文家才能做到这一点,读黄康生的散文,首先就被语言的魅力所捕获。
好作品,只要一读,就会被深深地吸引,好像铁遇到了磁石的吸引力一样。一读《“火水河”上流萤飞》,目光就明亮起来,开篇写道:“半江蛙声,一船渔火;满天繁星,遍地流萤——孩提时的画面,又在‘火水河’上一一浮现。”
优雅、高贵的汉语,写成散文,讲述童年遇到的萤火虫,读起来,心一下子就十分温暖,跟随作者的娓娓道来,一下子就进入了作品的魅力之中。江水,蛙声,渔火,繁星漫天,萤火虫活跃,童年的自己与一只萤火虫的带领,一下子,作品里的美引人入胜。读者的代入感很强,这都是作品吸引力的缘故,读者一下子跟随小时候的散文家进入了萤火虫的在场氛围。
魅力四射的夏天夜晚,令人陶醉的夏夜风景,尤其是作为主角的萤火虫虽然细小,却拥有不可缺少的位置。
萤河的壮观美丽明亮了童年的夜色,照亮了回忆,让人在忙忙碌碌中回忆童年的夜空、星星、萤火虫,都是难得的记忆财富。好的散文就是给人保留了记忆的财富,作品为此而成为精神珍贵的财富:“天上几多星,地上几多萤。记忆中的农村夏夜,总是漫天流萤。结伴到江边捉萤火虫则是我少年时最为有趣的一件事。”
作品铺垫写萤火虫的美丽,引发出童年对萤火虫进行捕捉的行为。
童年捕捉萤火虫,在表面上,有一个客观原因:当时,还没有电灯,因为村子里还没有通电,点煤油灯进行夜晚的照明,自然而然就会想到用透明玻璃瓶来装上它们,封住它们在容器里,进行照明、取乐。
童年的恶作剧,都是一切都觉得好玩,都是按照自我的想法去做,都是为了自我的快乐,觉得要做自己想到的事情,才会带来开心,才会有满足感。个人愿望的实现,很多都对其他生命、对其他人带来不利:“清晨醒来时,我发现囚在瓶子里的萤火虫集体遇难了。晨曦打在这些小精灵稀薄的鞘翅上,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痛。”童年的所作所为,产生的萤火虫死亡事件,唤醒了有良知的少年。
从萤火虫更大的悲剧事件里面,我们看到:人性的弱点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身上,只有良知、良心、好的道德修养、自律、父母管教教育、契约精神……才能对人的一生进行约束。小孩的成长依靠父母、社会氛围、教育、自己……融合在一起才能得到良好的效果。
作品里展示的反思、反省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力量。
人要首先活着,就得要有一个好的生态系统,人一旦作恶,生态系统变得恶劣,那么,唇亡齿寒的局面就会随之出现。
黄康生散文《“火水河”上流萤飞》是一篇超出一般性的、极其优秀的、大气厚重的散文精品力作。它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阅读它,就会被它感染、震荡阅读的情感,触及内心深处的根本,让人随着作品而深思,可见这篇作品的创作之成功,在于它能够进入人的精神内部,让人的心灵得到一股强有力的冲击。该文以小见大,作品的旨意是为了唤醒人性的美好:悔改、反省、反思的功课让人在行事为人上得到及时、积极的教育与引导。有了这样的好散文,就看到了散文对人生、对社会的积极价值。
□ 桑 子

亚洲女歌王叶丽仪演出现场。 澳门文化局供图
今届澳门艺术节的主题是:奇·遇。仅就我观赏的两场演出而言,都对应了主题,妙不可言。
5月25日,落座即看剧目册,“签约英国EMI唱片公司的首位亚洲歌手”,难怪选择“伦敦人剧场”。此外,她是《上海滩》的首唱者,关于叶丽仪,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2002年,澳门《海上续梦——蔷薇玫瑰夜来香》演唱会,我在现场,听蔡琴演绎陈蝶衣的经典,唱者波澜不惊,听者万千沟壑。4年后,《金光灿烂——徐小凤与澳门中乐团》演唱会,见识了小凤姐浑厚温婉的嗓音与金礼服、波波裙。此番听叶丽仪,也因她是女中音,仅此而已。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叶丽仪大打亲情牌,曲风转圜也因亲人的喜好随时切换、毫不违和。老母亲爱听江南曲,就唱《天涯歌女》;老爸中意爵士调,《这世界多美好》献给他;有了孙辈,大方自曝年龄,背景全家福照片叠加中,是《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深情吟唱……
76岁,身材健硕却不失柔婉,白发皑皑更时尚有范,中西夜礼服款款有致熠熠夺目。更关键的是全场撑得住、台风拎得清、情怀分得明,如是,“浪奔 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 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唱响,歌、人浑然一体之际,忽然有些明白:当年为何黄霑填好歌词便径直寻她去,所谓皮相易得、骨相难求。
出道55年,状态犹佳、气度不凡、宝刀未老,同时也拥有着完满家庭,人生赢家非叶丽仪莫属啊!然而,上网一看,即刻惊怔:
1996年,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叶丽仪罹患乳腺癌,手术切除一半乳房。翌年,她在香港回归现场作双语主持、献唱歌曲,之后即被查出抑郁症,丈夫David寸步不离全力照顾,她的抑郁症才慢慢痊愈。David曾因颈椎骨碎压迫到神经,左腿失去行动能力,好在他坚持做复健,恢复后行动自如。2008年,出生一个月的孙儿被查出脑部有肿瘤进了ICU,身上插满管子。孩子顽强地活了下来,虽然至今只能坐轮椅出入,一家人不离不弃、悉心关爱。
而所有这些,被叶丽仪淡淡称为“人生中不快的记忆”,不作刻意隐瞒,也“不需要洗掉”,她坦荡分享如何走出患病阴霾,坦荡承受整个家族遭遇的磨难,坦荡向这个世界传递着:是喜是愁,是成功是失败,就算分不清,“仍愿翻 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
勇气与担当,更深层面上的人生赢家,如此叶丽仪,如此值得回味。
再聊聊另一场戏,莎剧《马克白》。
开场,震撼即突如其来——巨大的黑暗,巨大且嘈杂的声响,昏天黑地的世界渐渐冒出,女巫们鬼祟叽叨出没,骑士彪悍纵马、蹄声得得……马克白听信三女巫预言而弑君,三女巫几乎贯穿全剧,象征着命运对人的引诱:激起欲望,许诺未来,最终却遭遇抛弃与毁灭。
1606年问世的《马克白》,全剧弥漫着阴郁可怕的氛围,许多版本的表达借助于浓墨重彩的舞美、道具、服装、化妆,意大利导演亚历山德罗·塞那的此版,则着力在声音、形体以及恢复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传统。
导演塞那2006年曾在萨丁尼亚岛拍摄狂欢节。当地人用牛铃、古老乐器、兽皮、牛角和软木等奏出低沉乐音,配以舞蹈和吟诵,以有力的声音和形体动作,祭祀酒神狄奥尼修斯。阴冷的冬日、阴沉的面具、阴郁的乐音,石头、沙尘、钢铁、鲜血,粗犷荒凉的原始力量直抵人心。他大为震撼,萌生制作《马克白》的念头。
以萨丁尼亚语演绎《马克白》,以舞者雄浑身姿表达传统舞蹈,以全男班演出致敬莎剧年代,以舞台设计极简风凸显作品本质。“无数的牛铃结集成震耳欲聋的声响,然后是深夜羊群低头吃草的静谧,女巫跳起萨丁尼亚岛民族舞蹈,卷入漩涡中消失,狂欢节面具幻化成演员轮廓分明的脸孔。”
打磨18年,塞那成功了,舞台上“所有痕迹微妙得像光环的阴影,无法言喻。杀戮,却不见一滴鲜血”。而观众,惊怵于命运之神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久久难以自拔。
从酒神祭祀介入莎氏悲剧,奇妙,却不见半分违和。

封面图;程霖编辑:唐祺珍 责任编辑:孙宁

语言历险和境界辽阔
——关于刘合军的诗歌

□ 陈啊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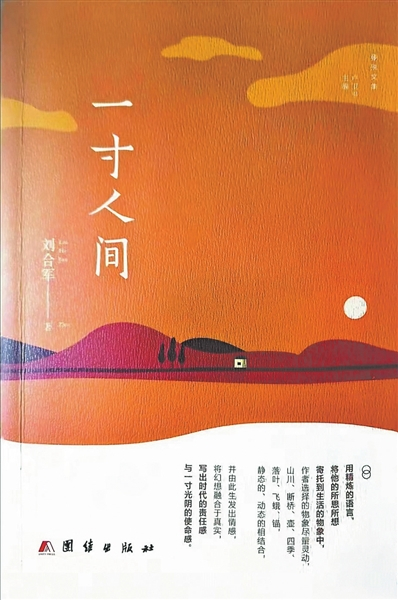
诗集《一寸人间》。 刘合军 著
从刘合军的一组近作看,他的诗歌风格悄然有了转变,其诗性的内核更坚实,而境界更为辽阔了。当然他诗歌的根基仍是建立在与自然界默默地相望和对语上,于平静中,于细微处,于空茫里,小心引发一场场“对峙”和翻转。更为清新和明晰的是,他和这个世界的“较量”基本出自越来越多的妥协和相安无事,他和万千存在,接受了时间的洗礼——这个共同的对手,所以一种“惺惺相惜”游走于文字间。也可以说,岁月蹉跎让诗人的心更为敏感,也更加细腻了,原先可作模糊处理的“空隙”和界面,已透析出更为本质的肌理。总体上,他倾向于内在的开阔掘进,力求呈现存在的本原和本性,揭开遮蔽真相的“皮”,其方法论不是哲学的或空幻臆断,而是用语言这一工具,即自有的言说方式,使存在敞开胸口,当然也只有诗歌的语言才能实现这一自觉,才能完成的美妙又彻底。
所以,我认为刘合军的诗歌,已然进入更高层次的成熟性,即对存在的深度思索与揭示。比如《微小的叙事》,写的是“平常的风”吹起“几片平常的叶子”,风和叶子是一对存在,如果不作深究和思考,就无法建立恒久、广阔并超出一般认知和美学感受的精神力量,我们尽可以去思索这一阵风从酝酿和劲吹的过程,它的力量是通过吹落几片叶子实现的,而叶子呢?它们从树枝上起飞,既是一种光辉的自由,又是曾经“盛开过的美好”的收场,诗人在这首诗的最后一节写道:“一条小道握住夕阳/一寸一寸地扎紧光阴的丝线,天空的一半/慢慢暗下来”,从低微处回到宏大处,由巴掌大的“叙事”推衍出宇宙,同样的一日辉煌与无法遏制的黯淡,就不再是简单的触景生情了,而是导入人文和生命关怀,其存在的真相毕现。
《松上日》这首诗代表了刘合军的心灵史。诗中有几个词组引起我的注意:“倾角”“弯曲的空寂”“空隙”,已简单构勒出生存状况,而一个“爱鱼的人”,“在松间闲坐”,这是另一个存在,所以:“一边接受光的喂养,一边/让密枝/空出喘息的空隙”。这不是普通的忙里偷闲,而是心灵自由放飞的逼仄与挣扎,这种看似“对抗式”的写作策略,所要揭示的并非某一变故或突发事件,是漫长而迟缓的人生。人生是需要从拥挤与淹没中脱颖而出的,是需要弯曲的,是需要沿着斜坡上行或下冲的,更需要在浓密的“耸立和满绿连成一片让微澜的光晕,躲进/弯曲的空寂里”,这就是人生的真相啊,屈身以求喘息和品赏的“自由”。很惊叹于刘合军身临水边,被环山和巨松遮掩时,心灵所产生的感应。说这首诗涉及“心灵史”,是因为生活之旅的艰辛和复杂在内心所形成的历史语境。历史在诗歌中,尤其是这类影射人生的短制中,反而能焕发出更强烈的气息,由此所产生的语言的张力,正如“按住历史的心跳”般,盎然保持了历史的也是求真求实的开阔思维体质。
我喜欢《立冬日》这首诗的原因,在于诗人将纯“中国元素”的节气“立冬”,放置到更广阔的空域,所体现的不止是语言能力,而是精神能力。我一直相信唯有自身的精神气力能够超越普世生存与存在,在精神的感召下,万物得以另一种形态生存。诗中:“鱼鹰被雪浪淹没/方言和足印被滚烫沙海拾起”,就具有精神的“法力”,如造物的上帝——谁又能说上帝不一定是真实存在,但它是精神的存在呢?刘合军诗歌在精神上的营造,反过来对他诗歌语言创化的生长,是相得益彰的,是彼此澄明与提升的。另一首《气场》,则更是将这种精神力无限扩张,气场是无形的,正如精神无法物化,但可以用心感触的:“有容乃大/可以装下宇宙的空旷,而星火在底部沉落,灿烂在万里浮荡/冬风吹响萧杀冷雪”,精神或气场要通过诗化语言来实现的,所以,“语言即存在之所”,从语言里构筑存在,包括一种精神的存在和形态功能。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写成诗歌,不是用了诗歌语言,而是以学术语言来说明一个瓶口可以“大”的程度,会被人当精神病。由这两首诗,可以说刘合军精神语言的提升与丰富,对存在的深度掘进,从而产生高迈情怀和生命力。
近观自然物是刘合军的拿手好戏,凸显的是他超常的想象力,由微小实物而打开宇宙。《旧叶子》写的是“一些放下天空的叶子”,我觉得诗人在很多场合选择“叶子”这一存在是很有讲究的,它的静雅与平淡,它的高度与低处,它的临空舞蹈与枯萎成泥,很像普通人的一生。诗人把这几片叶子放在冬日天空下观赏,当然就具有更锋利的言辞。通读全诗,诗人所营造的“荒诞”情景:“北风/把寒凉堆在门槛上,叶子不再低鸣/听说河岸以北/绽放了很多雪白的花蝴蝶,南岸与我/拾起大海初雪和落魄的旧叶子/等风吹”,所体现的也是语言的本质力量,将存在的核心要义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能力。从他的另一首诗《青花瓷鱼》中,诗人从一条观赏鱼身上,感受了一种“放逐”,一种世界的退隐,而另一种世界的蓬勃。诗人创造了另一个时空,从中“不觉顿生幻化和/一种莫名害怕,怕他洞穿/人性的厌恶”,生命的出路何在?诗中并无答案,但恍惚中的焦虑和悬疑,同样感染了读者,与人类相关联的重大问题在“我”和纯真的青花瓷鱼间展开对语,加深了人性的危机感。从中可见刘合军驾驭此类题材有活力的成熟性。
刘合军诗歌无一不体现了中年人的沉静、诚恳和细腻中潜藏着的轻盈和灵韵。他的诗歌是很准确恰切的日常口语,但又不是大白话,我觉得这种语气往往最适宜表达豁达又深刻的内在经验,能做到很松弛又适度陡峭,于坦诚中营造纯真的幻境。有如他在《走过月光走过的路》中写道:“光阴被流水打碎/良知像暮霭一样轻薄”,充满了对命运和人性的沉静反思和叹息。正如陈超说过的:“真正的诗人会深深体验到生存的阴晦和险恶,但仍然相信生存意义的可能性”,诗人并未灰心丧志,而是以亦庄亦谐的反讽语气,继续捕捉人间可贵的人性的清气和亮光:“我试着,抬起双臂和空气/一起轻轻划动/顿生/脱离陆地和拔出深渊的快愉”(《前山河看赛艇》)。总之,刘合军的诗是求真的,也是停不下来的文学追问和语言历险。
活在当下,与生活和解
——读《与尘世相爱》有感
□ 林小兵
□ 赖廷阶
好的散文不仅给人带来魅力,更让人得到精神的提醒,让人陷入沉思的散文更具有散文的深度与本质。散文的思想深度在于提醒人心、灵魂,让人得到精神的矫正,让灵魂获得光,成为光明的力量。
黄康生散文《“火水河”上流萤飞》,回忆了童年时代的捕捉萤火虫、伤害了它们,回忆起来的反省,是对人性弱点的深思,促使人回到爱里。为此,这篇作品在行文的字里行间,都有一种讲述中的深沉。
散文之美,首先在于语言美,只有雄厚语言功底的散文家才能做到这一点,读黄康生的散文,首先就被语言的魅力所捕获。
好作品,只要一读,就会被深深地吸引,好像铁遇到了磁石的吸引力一样。一读《“火水河”上流萤飞》,目光就明亮起来,开篇写道:“半江蛙声,一船渔火;满天繁星,遍地流萤——孩提时的画面,又在‘火水河’上一一浮现。”
优雅、高贵的汉语,写成散文,讲述童年遇到的萤火虫,读起来,心一下子就十分温暖,跟随作者的娓娓道来,一下子就进入了作品的魅力之中。江水,蛙声,渔火,繁星漫天,萤火虫活跃,童年的自己与一只萤火虫的带领,一下子,作品里的美引人入胜。读者的代入感很强,这都是作品吸引力的缘故,读者一下子跟随小时候的散文家进入了萤火虫的在场氛围。
魅力四射的夏天夜晚,令人陶醉的夏夜风景,尤其是作为主角的萤火虫虽然细小,却拥有不可缺少的位置。
萤河的壮观美丽明亮了童年的夜色,照亮了回忆,让人在忙忙碌碌中回忆童年的夜空、星星、萤火虫,都是难得的记忆财富。好的散文就是给人保留了记忆的财富,作品为此而成为精神珍贵的财富:“天上几多星,地上几多萤。记忆中的农村夏夜,总是漫天流萤。结伴到江边捉萤火虫则是我少年时最为有趣的一件事。”
作品铺垫写萤火虫的美丽,引发出童年对萤火虫进行捕捉的行为。
童年捕捉萤火虫,在表面上,有一个客观原因:当时,还没有电灯,因为村子里还没有通电,点煤油灯进行夜晚的照明,自然而然就会想到用透明玻璃瓶来装上它们,封住它们在容器里,进行照明、取乐。
童年的恶作剧,都是一切都觉得好玩,都是按照自我的想法去做,都是为了自我的快乐,觉得要做自己想到的事情,才会带来开心,才会有满足感。个人愿望的实现,很多都对其他生命、对其他人带来不利:“清晨醒来时,我发现囚在瓶子里的萤火虫集体遇难了。晨曦打在这些小精灵稀薄的鞘翅上,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痛。”童年的所作所为,产生的萤火虫死亡事件,唤醒了有良知的少年。
从萤火虫更大的悲剧事件里面,我们看到:人性的弱点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身上,只有良知、良心、好的道德修养、自律、父母管教教育、契约精神……才能对人的一生进行约束。小孩的成长依靠父母、社会氛围、教育、自己……融合在一起才能得到良好的效果。
作品里展示的反思、反省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力量。
人要首先活着,就得要有一个好的生态系统,人一旦作恶,生态系统变得恶劣,那么,唇亡齿寒的局面就会随之出现。
黄康生散文《“火水河”上流萤飞》是一篇超出一般性的、极其优秀的、大气厚重的散文精品力作。它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阅读它,就会被它感染、震荡阅读的情感,触及内心深处的根本,让人随着作品而深思,可见这篇作品的创作之成功,在于它能够进入人的精神内部,让人的心灵得到一股强有力的冲击。该文以小见大,作品的旨意是为了唤醒人性的美好:悔改、反省、反思的功课让人在行事为人上得到及时、积极的教育与引导。有了这样的好散文,就看到了散文对人生、对社会的积极价值。
□ 桑 子

亚洲女歌王叶丽仪演出现场。 澳门文化局供图
今届澳门艺术节的主题是:奇·遇。仅就我观赏的两场演出而言,都对应了主题,妙不可言。
5月25日,落座即看剧目册,“签约英国EMI唱片公司的首位亚洲歌手”,难怪选择“伦敦人剧场”。此外,她是《上海滩》的首唱者,关于叶丽仪,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2002年,澳门《海上续梦——蔷薇玫瑰夜来香》演唱会,我在现场,听蔡琴演绎陈蝶衣的经典,唱者波澜不惊,听者万千沟壑。4年后,《金光灿烂——徐小凤与澳门中乐团》演唱会,见识了小凤姐浑厚温婉的嗓音与金礼服、波波裙。此番听叶丽仪,也因她是女中音,仅此而已。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叶丽仪大打亲情牌,曲风转圜也因亲人的喜好随时切换、毫不违和。老母亲爱听江南曲,就唱《天涯歌女》;老爸中意爵士调,《这世界多美好》献给他;有了孙辈,大方自曝年龄,背景全家福照片叠加中,是《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深情吟唱……
76岁,身材健硕却不失柔婉,白发皑皑更时尚有范,中西夜礼服款款有致熠熠夺目。更关键的是全场撑得住、台风拎得清、情怀分得明,如是,“浪奔 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 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唱响,歌、人浑然一体之际,忽然有些明白:当年为何黄霑填好歌词便径直寻她去,所谓皮相易得、骨相难求。
出道55年,状态犹佳、气度不凡、宝刀未老,同时也拥有着完满家庭,人生赢家非叶丽仪莫属啊!然而,上网一看,即刻惊怔:
1996年,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叶丽仪罹患乳腺癌,手术切除一半乳房。翌年,她在香港回归现场作双语主持、献唱歌曲,之后即被查出抑郁症,丈夫David寸步不离全力照顾,她的抑郁症才慢慢痊愈。David曾因颈椎骨碎压迫到神经,左腿失去行动能力,好在他坚持做复健,恢复后行动自如。2008年,出生一个月的孙儿被查出脑部有肿瘤进了ICU,身上插满管子。孩子顽强地活了下来,虽然至今只能坐轮椅出入,一家人不离不弃、悉心关爱。
而所有这些,被叶丽仪淡淡称为“人生中不快的记忆”,不作刻意隐瞒,也“不需要洗掉”,她坦荡分享如何走出患病阴霾,坦荡承受整个家族遭遇的磨难,坦荡向这个世界传递着:是喜是愁,是成功是失败,就算分不清,“仍愿翻 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
勇气与担当,更深层面上的人生赢家,如此叶丽仪,如此值得回味。
再聊聊另一场戏,莎剧《马克白》。
开场,震撼即突如其来——巨大的黑暗,巨大且嘈杂的声响,昏天黑地的世界渐渐冒出,女巫们鬼祟叽叨出没,骑士彪悍纵马、蹄声得得……马克白听信三女巫预言而弑君,三女巫几乎贯穿全剧,象征着命运对人的引诱:激起欲望,许诺未来,最终却遭遇抛弃与毁灭。
1606年问世的《马克白》,全剧弥漫着阴郁可怕的氛围,许多版本的表达借助于浓墨重彩的舞美、道具、服装、化妆,意大利导演亚历山德罗·塞那的此版,则着力在声音、形体以及恢复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传统。
导演塞那2006年曾在萨丁尼亚岛拍摄狂欢节。当地人用牛铃、古老乐器、兽皮、牛角和软木等奏出低沉乐音,配以舞蹈和吟诵,以有力的声音和形体动作,祭祀酒神狄奥尼修斯。阴冷的冬日、阴沉的面具、阴郁的乐音,石头、沙尘、钢铁、鲜血,粗犷荒凉的原始力量直抵人心。他大为震撼,萌生制作《马克白》的念头。
以萨丁尼亚语演绎《马克白》,以舞者雄浑身姿表达传统舞蹈,以全男班演出致敬莎剧年代,以舞台设计极简风凸显作品本质。“无数的牛铃结集成震耳欲聋的声响,然后是深夜羊群低头吃草的静谧,女巫跳起萨丁尼亚岛民族舞蹈,卷入漩涡中消失,狂欢节面具幻化成演员轮廓分明的脸孔。”
打磨18年,塞那成功了,舞台上“所有痕迹微妙得像光环的阴影,无法言喻。杀戮,却不见一滴鲜血”。而观众,惊怵于命运之神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久久难以自拔。
从酒神祭祀介入莎氏悲剧,奇妙,却不见半分违和。

封面图;程霖编辑:唐祺珍 责任编辑:孙宁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