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维浩
岩头江村上椅子岭的道路变得不通畅的时候,到城市的路变得越来越方便。屋前是002乡道,有客车穿过,招手即停,像城市公共汽车一样方便。隆回县城的客车,则从龙江下游通到邻村娄山下,全程30里。六哥买了辆“大路易”的摩托车,周日开着送六嫂和两个孙子去隆回县城上学,半小时车程。他经常帮人主持祭祀仪式,有摩托车方便到黄桥铺采买祭祀用品。那个给父亲入土司仪的年轻师公,开着一台枣红色的广州传祺SUV到处做法事,据说他拥有大专文凭。隆回县城有只需三个多小时就直达广州的高铁。沪昆高速的隆回出口,离岩头江仅20里。
农业税曾经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税,俗称“公粮”。全国的平均农业税税率过去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这个税率真不算低。纳税人获得过什么样的服务呢?乡下人不会追问。回老家给父亲“总七”的时候,在火塘边,八十多岁的小舅舅一边添柴禾,一边兴奋地对我说:“历朝历代,哪有不交税的?俗话说皇粮国税。可现在真的取消了。这个沿用几千年的税收取消了!种田不但不缴钱,还补贴钱。政策真是好得很。你说国家怎么一下就发达成这样了?”在城市,面向企业经营者,减税或免除某些税收,不会给人这么强烈的心灵激荡。一直耕作并靠土地收成养家糊口的农民对此感恩戴德!但是,在年轻人看来,减免不减免,已经无所谓了。小舅舅的孙子不再种田,学汽车维修,在长沙的4S店摆弄汽车,每月有过万的收入。
2018年10月,84岁高龄的曾祥正从上海打来电话。我是晚辈,平时都是我主动给他老人家打电话问安。这一回,他主动给我打来电话。他说回了湖南老家一趟,心情很是沉重:很好的低保政策可能会让农民变懒。他的忧虑在岩头江得不到回应,在上海更无处诉说,只好跟我聊聊。
曾祥正已经在上海工作生活了六十年,是桥梁高级工程师,上海市高级专家委员会成员,对上海充满感情,在电话里总是邀我带老婆孩子到上海去走走。他住在浦东塘桥路,离东方明珠不远。我也邀他们来珠海看看。他参与设计的横琴大桥所通达的横琴,已不是一个荒岛,是国家级的自贸片区,高楼林立。他答应来,尤其想来看看港珠澳大桥——这是中国桥梁建设者的荣耀。我们不自觉地会讨论故乡岩头江。我已经在珠海生活三十多年。我们讨论岩头江,实际上是一个上海人与一个珠海人在讨论湘西。一个东海之滨的桥梁工程师与一位南海之滨的文字工作者在讨论湘西的留守农民。我们为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牵肠挂肚。我知道珠海请过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师,参照过许多城市的规划。我说:“整个中国乡村都需要规划。珠海已经有规划师下乡了。”岩头江实际上没有规划,都建房“占地盘”。曾祥正建议村里人把房子前面的路修好,方便走动。乡亲们说:“这个啊,政府拿钱来!”他感到非常吃惊。此前的岩头江人不是这样的,人们自力更生,任劳任怨。
四哥花了三年时间建房,一年多时间装修,四层,每层四房一厅。他还深思熟虑地在正房外留了一处柴灶房,正房内只烧煤气。我走进去,光洁的瓷地板,淡金色顶饰,富丽堂皇。难怪他怕柴火烟尘进房。四哥介绍,那些实木床3000元一张。我说:“你山上有树,自己砍树做会不会合算些?”四哥说:“自己砍树做,时间久,还没这个合算。再说了,人家机器刨磨。现在家里木匠手工哪里做得到?”四哥其实并不住岩头江,一直住武冈市城区,陪孙子读书。儿子在深圳,接单做眼镜架。四哥感叹:“我们这地方就是太偏了。要是在别的地方就好了。比如城郊有这样一个房子,想租房的人很多。”这才是建了房子的岩头江人的真实想法!若有游客,这栋房做民宿,一年收入不菲。
我探亲后返回广东,堂弟曾维圳送他刚满18岁的儿子搭便车去东莞打工。在路边,他用不无苦涩的幽默表情告诉我:“我现在一家五口人,四个吃‘国家粮’。不打工怎么办?”我仔细问才知道,农村生产责任制后,所分土地很难改动。他在结婚前分得一个人的土地,妻子和三个孩子都没有再分配土地。这是中国乡村所面对的现实。只有“世界工厂”给了岩头江人底气——只要远方的工厂没有倒闭,年轻人就不在乎有没有土地。
一场声势浩大、持久广泛的改革开放是如此地与岩头江人紧密相连息息相关,这是我和我的父老乡亲过去从未料到的。在岩头江, 60岁以上的农民每月获得103元养老金,钱很少——乡村砌砖匠的日薪已到200元,但它却是开创性的,改变长期的自耕农生活结局。年过七旬未成家的堂哥患有风湿病,干不了活,住进镇养老院。我去这个养老院探视,四个人一间房子,有电视。堂哥说,吃饭在食堂,养老院有点地,还种菜、喂猪,伙食还行,每月有点零钱。岩头江人不一定靠土地养老,也不一定靠儿女提供老年人的经济保障了。
我没有曾祥正那么悲观,一切可能会变得更好,撂荒或可以涵养土地。穿村而过的乡道上,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在夜晚它的照明十分有限。岩头江人好像也不太需要夜生活,其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实际意义。
人们筹措资金修一条路通向椅子岭。为什么要修这样一条路?是为了上山砍柴,还是种红薯?不得而知。2018年10月,我回到岩头江参加三伯母的葬礼。村民小组的负责人找到我,小声说修这条路大家得凑点份子钱,每人150元,看看我算多少人。他们反复说:“路修好,你清明节回来扫墓,车就可以开到屋后来。给你父母竖墓碑时,运石碑也能直通到屋后。你出点钱一点也不亏的。”我不在乎是否受益,但我很愿意出点钱。我把份子钱交给他时,他再次诚恳地对我说:“你不会吃亏的。”
农村在凋敝,所有的城市都在快速扩张。珠江三角洲已成世界级的大湾区城市群。长沙城区已达800万人口。无论是建设者还是管理者,一直都面对新来的乡下人。岩头江人正向这些城区进发。
千百万个岩头江顶在这儿,他的儿孙们都指望着让自己受益的改革开放深化,指着在长株潭务工,在粤港澳大湾区务工,在长江三角洲务工,所得收入用于养家糊口。解决温饱后,他们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珠江三角洲的百行百业,都与岩头江人紧密相连。
曾维浩 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弑父》、中短篇小说集《凉快》、非虚构作品《一个公民的成长笔记》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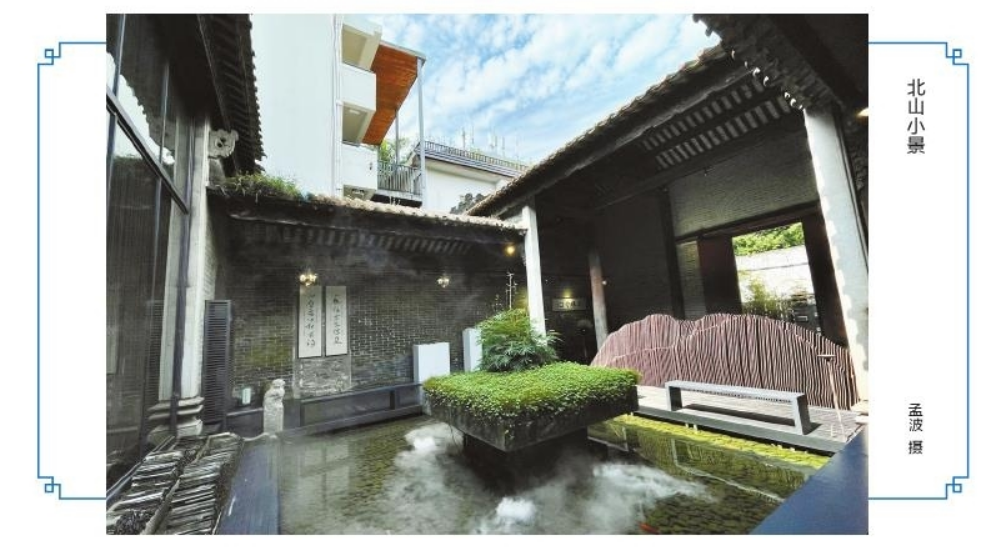
——读路文彬《当教育遇上电影》
□方守金
随笔集《当教育遇上电影》初版两年旋即再版,一本书大受欢迎,不止是国人对教育和电影两大话题格外关注所致,还在于这本书文辞中闪烁出来的火花,令人敞亮和温暖。
揽阅此书,我首先感受到了行文之美,字词句段里,充盈着高贵而独到的情操和意味。观察的细深、情致的高远,以及一语道破事物本质的睿智,更令我着迷。倘把此书的文字绵延比作清澈的河流,那河面上蓝天白云的倒影或粼粼波光,皆诗情和哲理也。顺手拈几个例句吧:其一,“瓦尔瓦拉的教育理想不求回报,因为这教育实践本身就在时刻点点滴滴地回报着。”我从这句朴素的话语里,读出了几乎所有人皆可适用的普遍意义。真想把这句话送给对子女抱怨不休的老年朋友:甭再说什么孝顺不孝顺回报不回报了好不?我们养育的孩子,不是从襁褓里睁开眼对你咧嘴一笑起,就开始点点滴滴给你回报了吗?其二,“调皮是孩子的天性,同他们的调皮为敌,其实就是同孩子为敌。”此为至理名言,可惜许多师者和父母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往往以正确和爱为名,伤害孩子的同时也伤害着自己。第三,“满眼泪花的基汀老师足可以告慰自己了,他点燃了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同时也温暖了他。”后面这两个短语,是不是比传诵千年的“教学相长”更富有人情味?还有,“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快乐是这一年龄阶段所有少年活动的灵魂”,“成功是存在,它永远不能被占有”,等等,皆为珠玑,俯拾即是。
当然,最能拨动我心弦的,还是路文彬在述评16部教育主题电影时,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情怀和教育理念。这些电影中,大学题材的仅《心灵捕手》和《三个白痴》两部,其余14部的故事内容都是中小学教育。而在这14部电影里,竟有《乡村女教师》《鲁冰花》《凤凰琴》《放牛班的春天》和《地球上的星星》5部的故事,发生在偏远封闭、贫穷落后的乡村,占到同类电影的三分之一以上。深入读下去,我还发现,除《乡村女教师》的女主角瓦尔瓦拉是个令人敬重的正面形象外,其余的老师大都是不合时宜的另类,且结局悲催:能用爱来发现并培养天才的郭云天、基汀、麦修遭到了开除,牺牲了梦想用一生的努力改变了学生改变了学校甚至还改变了社区的霍兰德被“下课”,美国的凯瑟琳和中国的张英子无奈而怅惘地别离……放眼这些电影中的学生,也少有省油的灯。不是先天有疾者如海伦、威尔、布莱德,就是劣迹斑斑的捣蛋虫、缺德鬼,或智商似乎不高成绩也不好的不受待见者。然而,就是这些师生,演绎了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脱胎换骨地变了,进而出现了天才,出现了品德高尚的人、意志坚定的人、能力超凡的人。作者令人信服地分析到,这一切才是真正的教育!我从中读到的关键词有:爱与自由、希望、快乐、个性、耐心和反抗等等。
反观当下我国基础教育的现实,不能不说契合上述关键词的少之又少。能上热搜的,至今还是我戏谑了几十年的“三点式”:重点难点知识点,以及考试、打卡、学霸、刷题、听话、秩序、提分……围绕这些热词,多少中小学师生和家长,团团转晕乎乎难知轻松快乐为何物!作为一个站了四十年讲台的退休教师,我非常怜惜现在的孩子,亦不愿指责当下的同行,更同情如今的家长。故我强烈建议老师、家长和教育官员们,读一读《当教育遇上电影》这本书,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顺应孩子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减缓他们稚嫩肩膀上的重压,进而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此外,路文彬这部随笔,还强力佐证了我的一个观点,即人在什么时候什么状况下才能称之为成功?又由谁来评价和验证你的成功?高官名利,富贵权威,孔老夫子早就说了,皆浮云尔。我倒认为,唯一能够确证你成功的,只有你兢兢业业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为之付诸的工作对象。庄稼证明农民的成功,牛羊证明牧人的成功,公民证明官员的成功,病人证明医生的成功;当然了,就教师而言,学生,唯有学生,才能证明你的成功。
方守金 文学评论家,曾发表多篇文学评论,现居珠海。
我的第一本书
□张映勤
出了校门进校门,书读了二十年,时间不算很长,也不算太短,读书的好处自不必说了,先贤圣哲的训示在耳边萦绕不绝;坏处是在不知不觉中磨灭掉了你的锐气、朝气和自信。
毕业后别无所长,就一直和文字打交道,“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接触多了便也蠢蠢欲动,产生投笔一试的欲望。
说句心里话,当年,以我之平庸才疏之辈,本不该心存著书出书的奢望。读过几本书,“文章千古事”这句古训是早就记下了,始终把写文章看作是天底下最神圣的事,虽然常年与笔墨(后来是电脑)打交道,可是轻易不敢轻举妄动,贸然下笔,一怕污了读者法眼,二怕坏了文章名声。
缺乏自信,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是我辈庸碌无为者的通病,之所以当年敢硬着头皮写一些东西,其实心里始终装着一个信念:写书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强迫自己多读书,多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系统地了解一门学问,也学会怎样去思考。
记得三十多年前在大学读书时,看过朱光潜先生的一本小册子,也许叫《与青年朋友谈美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谈到他二十多岁在法国留学写作《西方美学史》时,有一段话我牢记在心,大意是,他一边学习一边写作,写作强迫他更广泛更深入地阅读,系统地钻研学问。
正是受到朱先生的启发,我牢记在心,坚守这个信念,强迫自己多读多学,深入思考,间或练笔,充实自己。
记得二十几年前写第一本关于话剧方面的书时,心中异常兴奋,以我当时的年龄、水平、阅历而蒙人错爱,只有用加倍的努力来回报。自己才疏学浅、出校门不久,应约完成一部二十多万字的书稿,难度可想而知。正是心底的信念支撑着我、鼓动着我咬牙接下任务。清楚地记得那一年的夏天天气奇热,近四十度的高温我泡在图书馆里,一点一点地熟悉材料。冬天,我独居一处,夜里睡觉几乎没脱过衣服,一是怕冷,二嫌费事。北京跑了不知多少次,就为观摩一场演出。回来以后关在屋里认真学习阅读,一个字一个字地爬格子,一遍又一遍地反复修改,一个话题一个话题艰难地写作。那时还没有电脑,二十多万字的书稿写在五百字的大稿纸上,抄写修改了三遍,常常是干到天亮。书稿终于强迫自己如期完成。一年多的心血,收获的不仅仅是一部书稿,而且在写作的同时,逼着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丰富了许多知识,对话剧艺术有了进一步系统的了解。
说到第一本书的缘起,至今难忘。以我当时的年龄、水平、资历无论如何也不会斗胆冒出写书的奢望。当时,北京的一家出版社来津约稿,沾了一位前辈的光,约我们合写一本话剧方面的普及性论著,我的任务是独立完成二十多万字的初稿。
说句心里话,这本书当时只是选题而已,自己能否驾驶这种体裁,能否胜任写作任务,心中实在没底。还是心里的那个信念支撑着我,边学边练,急用先学,只要付出辛苦就有所得。有时候强迫自己涉足不太熟悉的领域,从头做起,不失为一种自我提高的选择。
写作就是学习,只要你付出辛苦就有所得。人非圣贤,生有涯而知无涯,每个人的知识面都有一定限度,相对博学多才者毕竟是极少数。以我的水平,即使对所从事的行业,了解的知识也相当有限,畏难不做只能是一事无成,强迫自己做一些能做和可做的事,对自己是一种磨炼,也是一种提高。力不从心却迎难而上,能接触很多知识,丰富自己的学识。人没有目标做不成事,没有压力更做不成事,写文章如此,做其他事亦同此理。
望着眼前成摞的稿纸,想着它们最终能变成铅字,能印成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图书,自己心潮澎湃,兴奋异常,激动了好长一段时间。谁知书写成了,审稿通过了,结果却因订数不理想而最终搁浅。付出的心血得不到承认是件挺痛苦的事,好在这种痛苦在我早已习以为常了。后来虽有出版界的朋友帮忙,免费提供书号,自费印刷,这在许多人看来已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是我不想这么做,辛辛苦苦写完的东西,稿费一分没挣,还要自己花钱出版,我对不起自己,于是作罢。
第一次写书被撞了个头破血流,总算把我撞醒了。终于明白了写东西不仅要考虑写什么,怎样写,而且更要考虑市场,考虑读者买不买账。也难怪,以自己低下的水平,无闻无名,这辈子怕难以写出什么有价值的著作,所以也从不敢指望出版社会为我赔钱出书。直到十年以后,这本书经过反复修改才得以面世。
当时,自己钟情爱慕日思夜想的“处女作”几乎成了胎死柜中的废纸,这不能不说是遗憾的,而更遗憾的便是你并不情愿并不满意的丑媳妇见了公婆,我的另一本书因为选题还有点市场,被出版社看中,很快签了合同,列入了出版计划。在朋友的反复催促鼓励下,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将其写完,其粗陋浅拙,可想而知。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它已经出来了,而且封面上署的就是你的贱名。
用不着羞羞答答,说心里话,当时自己还是暗中高兴了一阵。我至今记得二十几年前那个深冬的夜晚,我站在单位大楼门前的台阶上,像盼着与心仪已久的恋人约会一般等着印刷厂来送样书,心里不禁掠过一丝梦想成真的兴奋,毕竟三十岁不到就出了第一本书,还得到了一笔不算少的稿费,这是每一个读书人久藏心底的愿望,尽管现在看起来它只不过是一本十几万字很浅很薄的普及类小册子,可它毕竟是我的第一本书——所谓的“处女作”,仅这一点就应该值得珍重。如今,薄薄厚厚的书也出了十几本,可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当年的“处女作”。
张映勤 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编审。出版有《故人故居故事》《流年碎影》《鲁迅新观察》《浮生似水》《口红与猫》等十余种。编辑出版各类文学图书百部以上。发表有小说、散文、随笔等作品600余万字。部分作品被转载或获奖。
□叶耳
行人从不探问现实
生活的伏笔无人可及
她们将吐出多少心思
树上的麻雀一言难尽
你的
请原谅。你的名字
在这之前
云朵和楼顶
无数次震荡你的心
灯已沉沉睡去
关于你以及你的经历
越来越小
在命运面前
白是一个未知的谜
人间和上帝
农人的手稿
赤裸的胃越来越小
飞机飞过我的头顶
刀子和几只昆虫
石头树木归于石头树木
风尘之上吹熄孤独
谈何容易?请离我远点
叶耳 青年作家,中国作协会员,现居深圳。


□曾维浩
岩头江村上椅子岭的道路变得不通畅的时候,到城市的路变得越来越方便。屋前是002乡道,有客车穿过,招手即停,像城市公共汽车一样方便。隆回县城的客车,则从龙江下游通到邻村娄山下,全程30里。六哥买了辆“大路易”的摩托车,周日开着送六嫂和两个孙子去隆回县城上学,半小时车程。他经常帮人主持祭祀仪式,有摩托车方便到黄桥铺采买祭祀用品。那个给父亲入土司仪的年轻师公,开着一台枣红色的广州传祺SUV到处做法事,据说他拥有大专文凭。隆回县城有只需三个多小时就直达广州的高铁。沪昆高速的隆回出口,离岩头江仅20里。
农业税曾经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税,俗称“公粮”。全国的平均农业税税率过去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这个税率真不算低。纳税人获得过什么样的服务呢?乡下人不会追问。回老家给父亲“总七”的时候,在火塘边,八十多岁的小舅舅一边添柴禾,一边兴奋地对我说:“历朝历代,哪有不交税的?俗话说皇粮国税。可现在真的取消了。这个沿用几千年的税收取消了!种田不但不缴钱,还补贴钱。政策真是好得很。你说国家怎么一下就发达成这样了?”在城市,面向企业经营者,减税或免除某些税收,不会给人这么强烈的心灵激荡。一直耕作并靠土地收成养家糊口的农民对此感恩戴德!但是,在年轻人看来,减免不减免,已经无所谓了。小舅舅的孙子不再种田,学汽车维修,在长沙的4S店摆弄汽车,每月有过万的收入。
2018年10月,84岁高龄的曾祥正从上海打来电话。我是晚辈,平时都是我主动给他老人家打电话问安。这一回,他主动给我打来电话。他说回了湖南老家一趟,心情很是沉重:很好的低保政策可能会让农民变懒。他的忧虑在岩头江得不到回应,在上海更无处诉说,只好跟我聊聊。
曾祥正已经在上海工作生活了六十年,是桥梁高级工程师,上海市高级专家委员会成员,对上海充满感情,在电话里总是邀我带老婆孩子到上海去走走。他住在浦东塘桥路,离东方明珠不远。我也邀他们来珠海看看。他参与设计的横琴大桥所通达的横琴,已不是一个荒岛,是国家级的自贸片区,高楼林立。他答应来,尤其想来看看港珠澳大桥——这是中国桥梁建设者的荣耀。我们不自觉地会讨论故乡岩头江。我已经在珠海生活三十多年。我们讨论岩头江,实际上是一个上海人与一个珠海人在讨论湘西。一个东海之滨的桥梁工程师与一位南海之滨的文字工作者在讨论湘西的留守农民。我们为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牵肠挂肚。我知道珠海请过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师,参照过许多城市的规划。我说:“整个中国乡村都需要规划。珠海已经有规划师下乡了。”岩头江实际上没有规划,都建房“占地盘”。曾祥正建议村里人把房子前面的路修好,方便走动。乡亲们说:“这个啊,政府拿钱来!”他感到非常吃惊。此前的岩头江人不是这样的,人们自力更生,任劳任怨。
四哥花了三年时间建房,一年多时间装修,四层,每层四房一厅。他还深思熟虑地在正房外留了一处柴灶房,正房内只烧煤气。我走进去,光洁的瓷地板,淡金色顶饰,富丽堂皇。难怪他怕柴火烟尘进房。四哥介绍,那些实木床3000元一张。我说:“你山上有树,自己砍树做会不会合算些?”四哥说:“自己砍树做,时间久,还没这个合算。再说了,人家机器刨磨。现在家里木匠手工哪里做得到?”四哥其实并不住岩头江,一直住武冈市城区,陪孙子读书。儿子在深圳,接单做眼镜架。四哥感叹:“我们这地方就是太偏了。要是在别的地方就好了。比如城郊有这样一个房子,想租房的人很多。”这才是建了房子的岩头江人的真实想法!若有游客,这栋房做民宿,一年收入不菲。
我探亲后返回广东,堂弟曾维圳送他刚满18岁的儿子搭便车去东莞打工。在路边,他用不无苦涩的幽默表情告诉我:“我现在一家五口人,四个吃‘国家粮’。不打工怎么办?”我仔细问才知道,农村生产责任制后,所分土地很难改动。他在结婚前分得一个人的土地,妻子和三个孩子都没有再分配土地。这是中国乡村所面对的现实。只有“世界工厂”给了岩头江人底气——只要远方的工厂没有倒闭,年轻人就不在乎有没有土地。
一场声势浩大、持久广泛的改革开放是如此地与岩头江人紧密相连息息相关,这是我和我的父老乡亲过去从未料到的。在岩头江, 60岁以上的农民每月获得103元养老金,钱很少——乡村砌砖匠的日薪已到200元,但它却是开创性的,改变长期的自耕农生活结局。年过七旬未成家的堂哥患有风湿病,干不了活,住进镇养老院。我去这个养老院探视,四个人一间房子,有电视。堂哥说,吃饭在食堂,养老院有点地,还种菜、喂猪,伙食还行,每月有点零钱。岩头江人不一定靠土地养老,也不一定靠儿女提供老年人的经济保障了。
我没有曾祥正那么悲观,一切可能会变得更好,撂荒或可以涵养土地。穿村而过的乡道上,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在夜晚它的照明十分有限。岩头江人好像也不太需要夜生活,其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实际意义。
人们筹措资金修一条路通向椅子岭。为什么要修这样一条路?是为了上山砍柴,还是种红薯?不得而知。2018年10月,我回到岩头江参加三伯母的葬礼。村民小组的负责人找到我,小声说修这条路大家得凑点份子钱,每人150元,看看我算多少人。他们反复说:“路修好,你清明节回来扫墓,车就可以开到屋后来。给你父母竖墓碑时,运石碑也能直通到屋后。你出点钱一点也不亏的。”我不在乎是否受益,但我很愿意出点钱。我把份子钱交给他时,他再次诚恳地对我说:“你不会吃亏的。”
农村在凋敝,所有的城市都在快速扩张。珠江三角洲已成世界级的大湾区城市群。长沙城区已达800万人口。无论是建设者还是管理者,一直都面对新来的乡下人。岩头江人正向这些城区进发。
千百万个岩头江顶在这儿,他的儿孙们都指望着让自己受益的改革开放深化,指着在长株潭务工,在粤港澳大湾区务工,在长江三角洲务工,所得收入用于养家糊口。解决温饱后,他们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珠江三角洲的百行百业,都与岩头江人紧密相连。
曾维浩 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弑父》、中短篇小说集《凉快》、非虚构作品《一个公民的成长笔记》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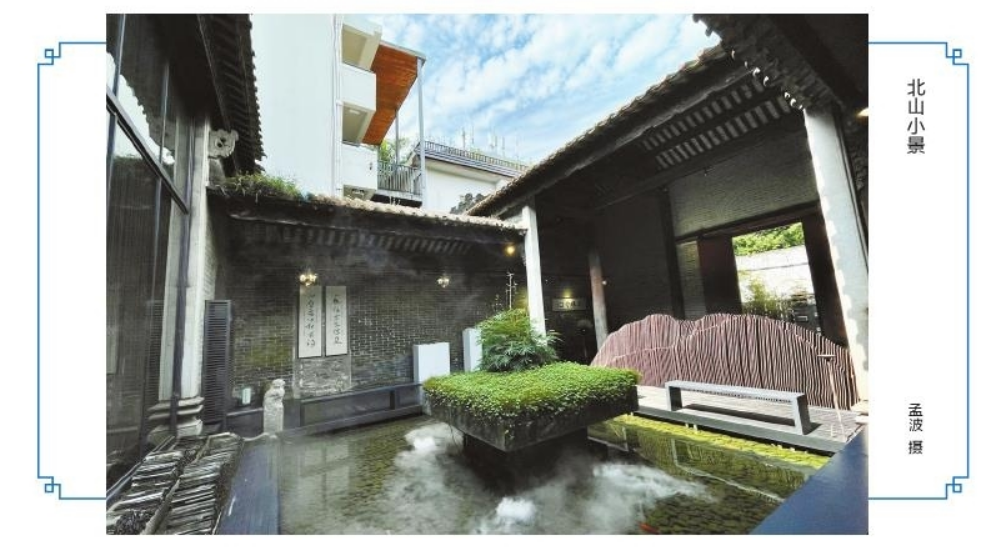
——读路文彬《当教育遇上电影》
□方守金
随笔集《当教育遇上电影》初版两年旋即再版,一本书大受欢迎,不止是国人对教育和电影两大话题格外关注所致,还在于这本书文辞中闪烁出来的火花,令人敞亮和温暖。
揽阅此书,我首先感受到了行文之美,字词句段里,充盈着高贵而独到的情操和意味。观察的细深、情致的高远,以及一语道破事物本质的睿智,更令我着迷。倘把此书的文字绵延比作清澈的河流,那河面上蓝天白云的倒影或粼粼波光,皆诗情和哲理也。顺手拈几个例句吧:其一,“瓦尔瓦拉的教育理想不求回报,因为这教育实践本身就在时刻点点滴滴地回报着。”我从这句朴素的话语里,读出了几乎所有人皆可适用的普遍意义。真想把这句话送给对子女抱怨不休的老年朋友:甭再说什么孝顺不孝顺回报不回报了好不?我们养育的孩子,不是从襁褓里睁开眼对你咧嘴一笑起,就开始点点滴滴给你回报了吗?其二,“调皮是孩子的天性,同他们的调皮为敌,其实就是同孩子为敌。”此为至理名言,可惜许多师者和父母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往往以正确和爱为名,伤害孩子的同时也伤害着自己。第三,“满眼泪花的基汀老师足可以告慰自己了,他点燃了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同时也温暖了他。”后面这两个短语,是不是比传诵千年的“教学相长”更富有人情味?还有,“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快乐是这一年龄阶段所有少年活动的灵魂”,“成功是存在,它永远不能被占有”,等等,皆为珠玑,俯拾即是。
当然,最能拨动我心弦的,还是路文彬在述评16部教育主题电影时,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情怀和教育理念。这些电影中,大学题材的仅《心灵捕手》和《三个白痴》两部,其余14部的故事内容都是中小学教育。而在这14部电影里,竟有《乡村女教师》《鲁冰花》《凤凰琴》《放牛班的春天》和《地球上的星星》5部的故事,发生在偏远封闭、贫穷落后的乡村,占到同类电影的三分之一以上。深入读下去,我还发现,除《乡村女教师》的女主角瓦尔瓦拉是个令人敬重的正面形象外,其余的老师大都是不合时宜的另类,且结局悲催:能用爱来发现并培养天才的郭云天、基汀、麦修遭到了开除,牺牲了梦想用一生的努力改变了学生改变了学校甚至还改变了社区的霍兰德被“下课”,美国的凯瑟琳和中国的张英子无奈而怅惘地别离……放眼这些电影中的学生,也少有省油的灯。不是先天有疾者如海伦、威尔、布莱德,就是劣迹斑斑的捣蛋虫、缺德鬼,或智商似乎不高成绩也不好的不受待见者。然而,就是这些师生,演绎了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脱胎换骨地变了,进而出现了天才,出现了品德高尚的人、意志坚定的人、能力超凡的人。作者令人信服地分析到,这一切才是真正的教育!我从中读到的关键词有:爱与自由、希望、快乐、个性、耐心和反抗等等。
反观当下我国基础教育的现实,不能不说契合上述关键词的少之又少。能上热搜的,至今还是我戏谑了几十年的“三点式”:重点难点知识点,以及考试、打卡、学霸、刷题、听话、秩序、提分……围绕这些热词,多少中小学师生和家长,团团转晕乎乎难知轻松快乐为何物!作为一个站了四十年讲台的退休教师,我非常怜惜现在的孩子,亦不愿指责当下的同行,更同情如今的家长。故我强烈建议老师、家长和教育官员们,读一读《当教育遇上电影》这本书,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顺应孩子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减缓他们稚嫩肩膀上的重压,进而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此外,路文彬这部随笔,还强力佐证了我的一个观点,即人在什么时候什么状况下才能称之为成功?又由谁来评价和验证你的成功?高官名利,富贵权威,孔老夫子早就说了,皆浮云尔。我倒认为,唯一能够确证你成功的,只有你兢兢业业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为之付诸的工作对象。庄稼证明农民的成功,牛羊证明牧人的成功,公民证明官员的成功,病人证明医生的成功;当然了,就教师而言,学生,唯有学生,才能证明你的成功。
方守金 文学评论家,曾发表多篇文学评论,现居珠海。
我的第一本书
□张映勤
出了校门进校门,书读了二十年,时间不算很长,也不算太短,读书的好处自不必说了,先贤圣哲的训示在耳边萦绕不绝;坏处是在不知不觉中磨灭掉了你的锐气、朝气和自信。
毕业后别无所长,就一直和文字打交道,“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接触多了便也蠢蠢欲动,产生投笔一试的欲望。
说句心里话,当年,以我之平庸才疏之辈,本不该心存著书出书的奢望。读过几本书,“文章千古事”这句古训是早就记下了,始终把写文章看作是天底下最神圣的事,虽然常年与笔墨(后来是电脑)打交道,可是轻易不敢轻举妄动,贸然下笔,一怕污了读者法眼,二怕坏了文章名声。
缺乏自信,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是我辈庸碌无为者的通病,之所以当年敢硬着头皮写一些东西,其实心里始终装着一个信念:写书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强迫自己多读书,多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系统地了解一门学问,也学会怎样去思考。
记得三十多年前在大学读书时,看过朱光潜先生的一本小册子,也许叫《与青年朋友谈美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谈到他二十多岁在法国留学写作《西方美学史》时,有一段话我牢记在心,大意是,他一边学习一边写作,写作强迫他更广泛更深入地阅读,系统地钻研学问。
正是受到朱先生的启发,我牢记在心,坚守这个信念,强迫自己多读多学,深入思考,间或练笔,充实自己。
记得二十几年前写第一本关于话剧方面的书时,心中异常兴奋,以我当时的年龄、水平、阅历而蒙人错爱,只有用加倍的努力来回报。自己才疏学浅、出校门不久,应约完成一部二十多万字的书稿,难度可想而知。正是心底的信念支撑着我、鼓动着我咬牙接下任务。清楚地记得那一年的夏天天气奇热,近四十度的高温我泡在图书馆里,一点一点地熟悉材料。冬天,我独居一处,夜里睡觉几乎没脱过衣服,一是怕冷,二嫌费事。北京跑了不知多少次,就为观摩一场演出。回来以后关在屋里认真学习阅读,一个字一个字地爬格子,一遍又一遍地反复修改,一个话题一个话题艰难地写作。那时还没有电脑,二十多万字的书稿写在五百字的大稿纸上,抄写修改了三遍,常常是干到天亮。书稿终于强迫自己如期完成。一年多的心血,收获的不仅仅是一部书稿,而且在写作的同时,逼着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丰富了许多知识,对话剧艺术有了进一步系统的了解。
说到第一本书的缘起,至今难忘。以我当时的年龄、水平、资历无论如何也不会斗胆冒出写书的奢望。当时,北京的一家出版社来津约稿,沾了一位前辈的光,约我们合写一本话剧方面的普及性论著,我的任务是独立完成二十多万字的初稿。
说句心里话,这本书当时只是选题而已,自己能否驾驶这种体裁,能否胜任写作任务,心中实在没底。还是心里的那个信念支撑着我,边学边练,急用先学,只要付出辛苦就有所得。有时候强迫自己涉足不太熟悉的领域,从头做起,不失为一种自我提高的选择。
写作就是学习,只要你付出辛苦就有所得。人非圣贤,生有涯而知无涯,每个人的知识面都有一定限度,相对博学多才者毕竟是极少数。以我的水平,即使对所从事的行业,了解的知识也相当有限,畏难不做只能是一事无成,强迫自己做一些能做和可做的事,对自己是一种磨炼,也是一种提高。力不从心却迎难而上,能接触很多知识,丰富自己的学识。人没有目标做不成事,没有压力更做不成事,写文章如此,做其他事亦同此理。
望着眼前成摞的稿纸,想着它们最终能变成铅字,能印成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图书,自己心潮澎湃,兴奋异常,激动了好长一段时间。谁知书写成了,审稿通过了,结果却因订数不理想而最终搁浅。付出的心血得不到承认是件挺痛苦的事,好在这种痛苦在我早已习以为常了。后来虽有出版界的朋友帮忙,免费提供书号,自费印刷,这在许多人看来已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是我不想这么做,辛辛苦苦写完的东西,稿费一分没挣,还要自己花钱出版,我对不起自己,于是作罢。
第一次写书被撞了个头破血流,总算把我撞醒了。终于明白了写东西不仅要考虑写什么,怎样写,而且更要考虑市场,考虑读者买不买账。也难怪,以自己低下的水平,无闻无名,这辈子怕难以写出什么有价值的著作,所以也从不敢指望出版社会为我赔钱出书。直到十年以后,这本书经过反复修改才得以面世。
当时,自己钟情爱慕日思夜想的“处女作”几乎成了胎死柜中的废纸,这不能不说是遗憾的,而更遗憾的便是你并不情愿并不满意的丑媳妇见了公婆,我的另一本书因为选题还有点市场,被出版社看中,很快签了合同,列入了出版计划。在朋友的反复催促鼓励下,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将其写完,其粗陋浅拙,可想而知。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它已经出来了,而且封面上署的就是你的贱名。
用不着羞羞答答,说心里话,当时自己还是暗中高兴了一阵。我至今记得二十几年前那个深冬的夜晚,我站在单位大楼门前的台阶上,像盼着与心仪已久的恋人约会一般等着印刷厂来送样书,心里不禁掠过一丝梦想成真的兴奋,毕竟三十岁不到就出了第一本书,还得到了一笔不算少的稿费,这是每一个读书人久藏心底的愿望,尽管现在看起来它只不过是一本十几万字很浅很薄的普及类小册子,可它毕竟是我的第一本书——所谓的“处女作”,仅这一点就应该值得珍重。如今,薄薄厚厚的书也出了十几本,可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当年的“处女作”。
张映勤 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编审。出版有《故人故居故事》《流年碎影》《鲁迅新观察》《浮生似水》《口红与猫》等十余种。编辑出版各类文学图书百部以上。发表有小说、散文、随笔等作品600余万字。部分作品被转载或获奖。
□叶耳
行人从不探问现实
生活的伏笔无人可及
她们将吐出多少心思
树上的麻雀一言难尽
你的
请原谅。你的名字
在这之前
云朵和楼顶
无数次震荡你的心
灯已沉沉睡去
关于你以及你的经历
越来越小
在命运面前
白是一个未知的谜
人间和上帝
农人的手稿
赤裸的胃越来越小
飞机飞过我的头顶
刀子和几只昆虫
石头树木归于石头树木
风尘之上吹熄孤独
谈何容易?请离我远点
叶耳 青年作家,中国作协会员,现居深圳。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