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梆子声声

□ 丁杰
周围五六层的宿舍楼,两侧高高的水泥墙,使得脚下狭长坚硬的水泥巷子,成了一道寸草不生的“峡谷”。炎夏,灼热的阳光把“峡谷”烤成一条火巷,过往行人,便如“过街老鼠”一般;寒冬,“峡谷”内终日阴晦,朔风裹挟着枯枝败叶长驱直入,偶有过路人,皆耸肩缩颈,跑得比老鼠还快。
这是一条孤寂的长巷,只在巷子四分之三处是四户人家的屋子,如同四枚匍匐谷底的石头,并排挤着。多年以前,我们的陋室是其中一户。
那日向晚,巷子里响起清脆悦耳的竹梆子敲击声。须臾,一个看上去七十开外的小个子黑瘦老头,着一身灰色棉衣裤,挑一副担子,不紧不慢从窗前经过。我开门询问,原来是卖蜜酒酿的。
本地风俗,凡走街串巷卖蜜酒酿,皆以敲竹梆子示意。我喜欢这别出心裁的“吆喝”,不张扬,而声动长巷。
女儿刚刚蹒跚学步,那是她第一次吃蜜酒酿。意外发现女儿与我有着同样的爱好。橘色灯光下,娘儿俩小桌椅对坐。一碗蜜酒酿,你一勺我一勺,直吃得心口如蜜糖似的,寒冬的陋室暖意融融。
自那以后,每隔一段日子,老人总要挑着担子从门前走过。“笃笃笃,笃笃笃”,声音拨开长巷的幽寂,钻进耳朵里,笑意便爬上我的面颊。
女儿听见了,会立刻安静下来,指指门外,神情惊喜地望着我,奶声奶气说:“酒酿爷爷。”于是,我拿碗出门。
老人便歇下担子,轻轻揭开捂在木桶上的棉盖头,里头有一口钢精锅。掀开锅盖,用有些年头的小铜勺搲酒酿,小秤秤得翘翘的。临了,总会多多地舀一勺蜜汁浇上。
渐渐地,我们习惯了老人的来去,如同习惯了斗转星移,风起雨落一样。
听,竹梆子声近了,一点一点的叩击连成一条虚线,仿佛一串亮晶晶的小灯泡,在孤清的长巷欢欣跳荡。
女儿忙不迭地取她的小木碗,开门,出出进进,小大人似的,越来越稳妥了。
我拿起他担子里的一只敞口玻璃瓶,帮老人续上热茶水。
“爷爷,来,喝口热茶,歇歇脚。”我招呼老人,“这条巷子没几户人家,您怎么回回绕道这里呢?”
老人抿一口茶水,拉起了家常:“我有个小孙女,也喜欢吃我做的蜜酒酿,那时候儿子在外打工,把她留在我身边,一直带到上一年级才离开。现在除了过年,一年到头难得见到她,想啊。”老人一声叹息,慈爱地望向女儿说,“头一次见到小家伙爱吃,我就想好了,以后只要往这边跑,一定到你家,权当看我那孙女的呢。”
竹梆子声远了,游丝一般,如荒原上的一痕逝水。
暮色中,老人挑着担子远去的背影,蹒跚,沧桑,如秋叶,如风烛。
这地老天荒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
忽一日,不经意间侧耳聆听,又打开门,移步望向长巷那头,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在等待那位爷爷。咦,怎么许久听不到竹梆子声?酒酿爷爷哪里去了?
这是二十年前的往事,如今已很难看到走街串巷的叫卖了。蜜酒酿一直爱吃,只是,每回看到蜜酒酿,总不免想起那清亮如银的竹梆子声,望见暮色中的酒酿担子飘飘摇摇,飘进夕阳,飘向虚空。说不出是什么原因,也许因为老人孤独的背影,也许因为陋室温馨的灯火。
□ 涂启智
河水打破冰封束缚,浩浩荡荡,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像在弹奏喜庆的迎宾曲,迎接燕子如期归来。
唧唧、喳喳、啾啾……燕子叫声或舒缓,似情侣间的温言细语,又像山泉流进干枯的河床。或急促,仿佛林中冒出的一支响箭,清亮而又激越;好似阳光穿透参天大树繁茂的枝叶,洒在星星点点的灌木丛中。无论婉约还是高亢,燕子发出的都是美声,铿锵悦耳,戛然而止,极尽低调内敛。
岁月不居,四季轮回。每一个季节都有特定的风物,成为时令的使者,彰显不同季节特征,因而成为人们记忆底版上难以抹去的物候景象。
我对燕子的好感始于少年。那时候,我家住在小山沟。房屋背靠青山,门前沟冲绵延一两公里,是呈梯级分布的稻田。稻田那一边,又是满目青山。夕阳挂在山巅大松树枝丫上,就像橘红色的大火球。每当春天到来,燕子三五成群,从房前屋后、田畈上空,轻盈而迅速地掠过,犹如飞机在万米高空巡航前进或是自由滑翔。燕子常结伴落在电线或是房顶上栖息,时而欢快地啼鸣,时而勾头梳理羽毛,还有些时候静若处子,好像农闲时节的乡邻,蹲在一起集体发呆。
燕子的窝大多筑于房檐以及室内屋顶。在我老家,乡亲们认为,燕子上门是吉祥多福的象征,所以大家都乐意燕子在自家屋顶安居乐业和生儿育女。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尽管我很喜欢燕子,看到燕子归来总感到莫名的欢欣鼓舞,但是,我对燕子飞进我们家并不抱幻想。生产队当时三四十户人家,约有三分之二住瓦房,剩下十多户为草房。我家是十多户之一。草房经常漏雨,屋檐或房顶筑巢不牢固,猜想燕子不会来。
母亲知道我的心思,笑着说:“红娃儿,燕子肯定会来我们家!”母亲定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说。
出乎意料的是,我家旁边住瓦房的邻居家,尚未有燕子进驻,却有两只燕子直奔我家在房梁筑起精致漂亮的窝,与我们朝夕相处。每当燕子盘旋着飞进屋,我就仰起头,目不转睛盯着它们,感觉它们像是我的兄弟姐妹一般。燕子也会眨着乌溜溜的眼睛与我对视,毫无生疏感。
我虽然年幼,但已有清晰的贫富意识。我对不会“嫌贫爱富”的燕子充满感激。那两只燕子在我们家繁衍生息,给我这个单亲少年带来无以估量的精神慰藉。我想,等我长大了,我们家就能摆脱贫困。
两只燕子,后来孵出四只小燕子。第二年春天,我家同时飞来六只燕子。我笃定地相信,这是那两只燕子带着四个儿女重返故里。
其实,就算燕子不来我们家垒窝居住,我也不会怪它们。我教书两年后,我家才搬离茅草屋。此去经年,我常常从梦中惊醒——我家仍然住着破草房,到处漏雨,床都无处安放。我教书第一年,班上有个女生,是跟我关系很铁同学的表妹。她父亲不幸早逝,同学要我陪他去参加葬礼。我给了十元礼金。因为这件事,那女生竟来我家拜年,算是还人情。
不知那两只燕子还有它们的儿女,如今安在,可安好?
秋声萧瑟、蝉鸣渐远之际,片片树叶把飘向何方的命运交由风来安排,燕子恋恋不舍离开北方。当草长莺飞,万物勃发时,燕子又成群结队,一路北上,抵达魂牵梦萦的家园,回到心心念念的故乡。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大自然总是和谐守衡,燕子归来给人们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智慧启迪。
不管是风和日丽,还是风吹雨打,燕子都会忠于职守,飞过岁月的河流,翻越光阴的山峰,向着亘古以来的初心,披星戴月进发,沧海桑田,矢志无悔。
当燕子归来,世间蜂飞蝶舞,姹紫嫣红,人勤春早。所有生命都意气风发,精神振奋,怀抱新的希望走向下一轮圆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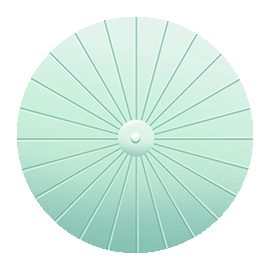
□ 朱辉
我的青少年时代,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大多梦想将来当科学家;成绩中下,颜值还行的,很多想当电影明星。我二哥属于后者。
和大多数做过白日梦的少年一样,离开学校后二哥就渐渐务实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顶父亲的职,进了一家国营大厂。原本打算在那里平平安安干到退休,不料10多年后,工厂改制了。后来,二哥先后去了多个沿海城市,靠以前在厂里学到的技术、积累的工作经验当个技术工人。一晃到了前年,数数日子,不到3年就可以退休了。二哥忽然做出一个惊人之举,他辞了职。一大把年纪了,跑去浙江横店当起了群众演员。
一晃两年过去了,二哥有了一些“作品”,大多是镜头一扫而过,脸都难以看清的角色。最出彩的一场戏不过5秒,“啊”了一声中枪倒地,总算有了一个字的台词。算算他微薄的收入,不及打工时的三分之一,这两年不知道怎么混过来的。
“我和另一位群演,合租农户的一小间房,每人每月200元。中午,附近一所寺庙有免费的斋饭,我天天去吃。晚上总有些剧组有多余的盒饭,我信息渠道多,到处去‘赶场’……算下来,一个月开支500元就够了。”二哥娓娓道来,一副颇为自豪的样子。
在许多人眼里,二哥有点“神经”,年近花甲背井离乡自讨苦吃。我却很羡慕他,多少人憋着一个年少时的梦想,终身都没有尝试过去追一追。二哥的明星梦,现在看来实现不了了。但他终于去追了一把,此生无憾矣。
二哥并不“神经”。人生是一趟旅程,渴望做什么,只要不违法,尽量去做,就心满意足了。

□ 杨桂敏
一个人能在工作之余,有自己的爱好是幸运的。弹吉他便是我的这份幸运。
最初想学吉他,是在我上大二的时候。那时觉得弹吉他的人很潇洒、文艺,我也想成为有文艺范的人。学校门口有一家琴行,路过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会多看几眼。有时我会看到琴行的老师抱着吉他在弹曲子,我的心跟着吉他的弦音一起颤动。有时看到老师在教学生弹奏,我便想象着自己抱着吉他的样子。但也只能空想一下。因为那时,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得靠自己做兼职赚,去琴行学吉他有点奢望。
大概十年前,我参加工作了。一天,我再次经过大学门口那家琴行。我忐忑地走进琴行,问老师我的年龄会不会太大?老师答道:“若是想去国际大舞台,那确是起步太晚;若是弹给自己,那你还年轻。我们这里,年过六十的也有。”我顿时打消了顾虑。
我从简单的右手拨弦开始,“5323,1323”的节奏开练。乐理知识学得尚可,犯难的是学习和弦。左手按和弦时,不是按不紧发不出声音,就是和弦转换动作太慢连贯不起来。学习之初,左手指尖全是血泡,后来指尖慢慢都是茧子。我断断续续,一直没有放弃。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我学会了第一首曲子《传奇》,再后来是许巍的《旅行》,还有就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三毛作词的《橄榄树》等。过了第一关,以后便学得越来越顺畅。有一次同学聚会,我现场弹唱了一首我们大学毕业时唱的《心愿》,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我仿佛梦到了自己大学时代潇洒地弹吉他的样子,小小自豪了一番。
自从学会了弹吉他,假期出游时,我会随身带上吉他,在景色优美的野外,爱人在画画写生,我则拿出吉他来弹唱,有时引得不少人驻足。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把孩子哄睡后,在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里,弹唱一首,心情瞬间放松下来,一天的疲惫也烟消云散了。怀着愉悦的心情入睡,梦格外香甜。
音乐是人类的第二语言。我弹吉他主要是悦己。每当我抱起吉他,心立刻就安静下来;当我轻轻拨动琴弦,便沉醉在音符里。记得曾读到作家雪小禅的一句话:“人的爱好,在生死关头总会拯救他。因为漫长的时光是无法打发的,这些爱好,可以与时间为敌。”我倒不认为生活无趣至需要打发时间,而是觉得做一件热爱的事,会给平淡的生活增添风采,使生命更加动人。

□ 晴澜
每天早上七点一刻,我骑上心爱的自行车,准时出发上班。
现在出行如不超过20公里路程,我首选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不论严寒还是酷暑。每天骑行20公里,是基本运动量。骑行越多,生活越受骑行所影响与塑造;骑行越多,我就确定自己正往真正的美好前进——拥有健美的体格、平静的心理和身心灵的完整。
太阳初升,踩上自行车踏板的那一刻,想到我们的祖先此时一定是在奔跑的路上,他们必须去寻觅、猎杀动物以便生存下来。我们其实都是动物,所以首先要成为够格的动物,需要有敏捷的动作、结实的体魄、良好的视力。那些目光如炬、奔跑如飞、战斗力爆棚的古人,最终生存下来了。
骑行时,映入眼帘的是碧蓝的大海和天空,白鹭翻飞,鲜花绽放,绿草如茵……海风拂面,融入大自然,神清气爽,心里满是快乐和满足,感到身心灵前所未有的自由。没有压力,心理平和,自由自在,所以此时大脑处在最松弛、最具创新的最佳状态。那些可爱的句子、新奇的点子、久违的往事、解决问题的办法等,好像就突然从天而降,落到脑子里了。
骑行在路上,我觉得自己像个做游戏的孩子,时而悠哉游哉驻足拍照,时而以最快速度猛冲。运动让我心跳、呼吸加速,心肺输出更多血液和氧气,我仿佛感受到奔流的血液滋养正每一个肌肉细胞,肌纤维有力地收缩和舒张。
太阳沿着大海铺就一条金光大道,把万丈光芒投射到我的身上,温暖每一寸裸露的肌肤。朋友告诉我,在我骑行的这40多分钟时间里,获得了每日需要量的大多数维生素D。它被称为“阳光激素”,人体每日需要的绝大部分维生素D来自太阳默默的馈赠。
因为骑行,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健康、活力、快乐、平和、积极。

□ 崔岸儿
蘑菇与凉亭
田野上的蘑菇
像一个个凉亭
大地上的凉亭
像一朵朵蘑菇
我实在分不清楚
哪是凉亭哪是蘑菇
妈妈说:
“青蛙跑进去躲雨的是蘑菇,
我们跑进去躲雨的是凉亭。”
蜻蜓飞啊飞
小蜻蜓,飞啊飞
飞过竹篱笆,
变成牵牛花。
小蜻蜓,飞啊飞
飞过小枝桠,
变成小飞侠。
小蜻蜓,飞啊飞
飞过一群鸭,
变成一幅画。
雨点抓痒痒
花朵痒了
雨点给她抓痒痒
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
小河痒了
雨点给她抓痒痒
叮咚叮咚
叮咚叮咚
窗户痒了
雨点给她抓痒痒
噼啪噼啪
噼啪噼啪
我的脸上痒了
啪嗒啪嗒
啪嗒啪嗒
咦?
还给我抓痒痒来了



竹梆子声声

□ 丁杰
周围五六层的宿舍楼,两侧高高的水泥墙,使得脚下狭长坚硬的水泥巷子,成了一道寸草不生的“峡谷”。炎夏,灼热的阳光把“峡谷”烤成一条火巷,过往行人,便如“过街老鼠”一般;寒冬,“峡谷”内终日阴晦,朔风裹挟着枯枝败叶长驱直入,偶有过路人,皆耸肩缩颈,跑得比老鼠还快。
这是一条孤寂的长巷,只在巷子四分之三处是四户人家的屋子,如同四枚匍匐谷底的石头,并排挤着。多年以前,我们的陋室是其中一户。
那日向晚,巷子里响起清脆悦耳的竹梆子敲击声。须臾,一个看上去七十开外的小个子黑瘦老头,着一身灰色棉衣裤,挑一副担子,不紧不慢从窗前经过。我开门询问,原来是卖蜜酒酿的。
本地风俗,凡走街串巷卖蜜酒酿,皆以敲竹梆子示意。我喜欢这别出心裁的“吆喝”,不张扬,而声动长巷。
女儿刚刚蹒跚学步,那是她第一次吃蜜酒酿。意外发现女儿与我有着同样的爱好。橘色灯光下,娘儿俩小桌椅对坐。一碗蜜酒酿,你一勺我一勺,直吃得心口如蜜糖似的,寒冬的陋室暖意融融。
自那以后,每隔一段日子,老人总要挑着担子从门前走过。“笃笃笃,笃笃笃”,声音拨开长巷的幽寂,钻进耳朵里,笑意便爬上我的面颊。
女儿听见了,会立刻安静下来,指指门外,神情惊喜地望着我,奶声奶气说:“酒酿爷爷。”于是,我拿碗出门。
老人便歇下担子,轻轻揭开捂在木桶上的棉盖头,里头有一口钢精锅。掀开锅盖,用有些年头的小铜勺搲酒酿,小秤秤得翘翘的。临了,总会多多地舀一勺蜜汁浇上。
渐渐地,我们习惯了老人的来去,如同习惯了斗转星移,风起雨落一样。
听,竹梆子声近了,一点一点的叩击连成一条虚线,仿佛一串亮晶晶的小灯泡,在孤清的长巷欢欣跳荡。
女儿忙不迭地取她的小木碗,开门,出出进进,小大人似的,越来越稳妥了。
我拿起他担子里的一只敞口玻璃瓶,帮老人续上热茶水。
“爷爷,来,喝口热茶,歇歇脚。”我招呼老人,“这条巷子没几户人家,您怎么回回绕道这里呢?”
老人抿一口茶水,拉起了家常:“我有个小孙女,也喜欢吃我做的蜜酒酿,那时候儿子在外打工,把她留在我身边,一直带到上一年级才离开。现在除了过年,一年到头难得见到她,想啊。”老人一声叹息,慈爱地望向女儿说,“头一次见到小家伙爱吃,我就想好了,以后只要往这边跑,一定到你家,权当看我那孙女的呢。”
竹梆子声远了,游丝一般,如荒原上的一痕逝水。
暮色中,老人挑着担子远去的背影,蹒跚,沧桑,如秋叶,如风烛。
这地老天荒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
忽一日,不经意间侧耳聆听,又打开门,移步望向长巷那头,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在等待那位爷爷。咦,怎么许久听不到竹梆子声?酒酿爷爷哪里去了?
这是二十年前的往事,如今已很难看到走街串巷的叫卖了。蜜酒酿一直爱吃,只是,每回看到蜜酒酿,总不免想起那清亮如银的竹梆子声,望见暮色中的酒酿担子飘飘摇摇,飘进夕阳,飘向虚空。说不出是什么原因,也许因为老人孤独的背影,也许因为陋室温馨的灯火。
□ 涂启智
河水打破冰封束缚,浩浩荡荡,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像在弹奏喜庆的迎宾曲,迎接燕子如期归来。
唧唧、喳喳、啾啾……燕子叫声或舒缓,似情侣间的温言细语,又像山泉流进干枯的河床。或急促,仿佛林中冒出的一支响箭,清亮而又激越;好似阳光穿透参天大树繁茂的枝叶,洒在星星点点的灌木丛中。无论婉约还是高亢,燕子发出的都是美声,铿锵悦耳,戛然而止,极尽低调内敛。
岁月不居,四季轮回。每一个季节都有特定的风物,成为时令的使者,彰显不同季节特征,因而成为人们记忆底版上难以抹去的物候景象。
我对燕子的好感始于少年。那时候,我家住在小山沟。房屋背靠青山,门前沟冲绵延一两公里,是呈梯级分布的稻田。稻田那一边,又是满目青山。夕阳挂在山巅大松树枝丫上,就像橘红色的大火球。每当春天到来,燕子三五成群,从房前屋后、田畈上空,轻盈而迅速地掠过,犹如飞机在万米高空巡航前进或是自由滑翔。燕子常结伴落在电线或是房顶上栖息,时而欢快地啼鸣,时而勾头梳理羽毛,还有些时候静若处子,好像农闲时节的乡邻,蹲在一起集体发呆。
燕子的窝大多筑于房檐以及室内屋顶。在我老家,乡亲们认为,燕子上门是吉祥多福的象征,所以大家都乐意燕子在自家屋顶安居乐业和生儿育女。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尽管我很喜欢燕子,看到燕子归来总感到莫名的欢欣鼓舞,但是,我对燕子飞进我们家并不抱幻想。生产队当时三四十户人家,约有三分之二住瓦房,剩下十多户为草房。我家是十多户之一。草房经常漏雨,屋檐或房顶筑巢不牢固,猜想燕子不会来。
母亲知道我的心思,笑着说:“红娃儿,燕子肯定会来我们家!”母亲定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说。
出乎意料的是,我家旁边住瓦房的邻居家,尚未有燕子进驻,却有两只燕子直奔我家在房梁筑起精致漂亮的窝,与我们朝夕相处。每当燕子盘旋着飞进屋,我就仰起头,目不转睛盯着它们,感觉它们像是我的兄弟姐妹一般。燕子也会眨着乌溜溜的眼睛与我对视,毫无生疏感。
我虽然年幼,但已有清晰的贫富意识。我对不会“嫌贫爱富”的燕子充满感激。那两只燕子在我们家繁衍生息,给我这个单亲少年带来无以估量的精神慰藉。我想,等我长大了,我们家就能摆脱贫困。
两只燕子,后来孵出四只小燕子。第二年春天,我家同时飞来六只燕子。我笃定地相信,这是那两只燕子带着四个儿女重返故里。
其实,就算燕子不来我们家垒窝居住,我也不会怪它们。我教书两年后,我家才搬离茅草屋。此去经年,我常常从梦中惊醒——我家仍然住着破草房,到处漏雨,床都无处安放。我教书第一年,班上有个女生,是跟我关系很铁同学的表妹。她父亲不幸早逝,同学要我陪他去参加葬礼。我给了十元礼金。因为这件事,那女生竟来我家拜年,算是还人情。
不知那两只燕子还有它们的儿女,如今安在,可安好?
秋声萧瑟、蝉鸣渐远之际,片片树叶把飘向何方的命运交由风来安排,燕子恋恋不舍离开北方。当草长莺飞,万物勃发时,燕子又成群结队,一路北上,抵达魂牵梦萦的家园,回到心心念念的故乡。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大自然总是和谐守衡,燕子归来给人们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智慧启迪。
不管是风和日丽,还是风吹雨打,燕子都会忠于职守,飞过岁月的河流,翻越光阴的山峰,向着亘古以来的初心,披星戴月进发,沧海桑田,矢志无悔。
当燕子归来,世间蜂飞蝶舞,姹紫嫣红,人勤春早。所有生命都意气风发,精神振奋,怀抱新的希望走向下一轮圆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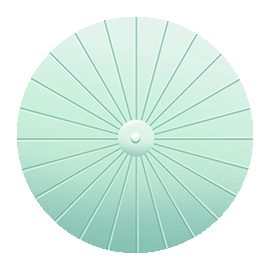
□ 朱辉
我的青少年时代,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大多梦想将来当科学家;成绩中下,颜值还行的,很多想当电影明星。我二哥属于后者。
和大多数做过白日梦的少年一样,离开学校后二哥就渐渐务实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顶父亲的职,进了一家国营大厂。原本打算在那里平平安安干到退休,不料10多年后,工厂改制了。后来,二哥先后去了多个沿海城市,靠以前在厂里学到的技术、积累的工作经验当个技术工人。一晃到了前年,数数日子,不到3年就可以退休了。二哥忽然做出一个惊人之举,他辞了职。一大把年纪了,跑去浙江横店当起了群众演员。
一晃两年过去了,二哥有了一些“作品”,大多是镜头一扫而过,脸都难以看清的角色。最出彩的一场戏不过5秒,“啊”了一声中枪倒地,总算有了一个字的台词。算算他微薄的收入,不及打工时的三分之一,这两年不知道怎么混过来的。
“我和另一位群演,合租农户的一小间房,每人每月200元。中午,附近一所寺庙有免费的斋饭,我天天去吃。晚上总有些剧组有多余的盒饭,我信息渠道多,到处去‘赶场’……算下来,一个月开支500元就够了。”二哥娓娓道来,一副颇为自豪的样子。
在许多人眼里,二哥有点“神经”,年近花甲背井离乡自讨苦吃。我却很羡慕他,多少人憋着一个年少时的梦想,终身都没有尝试过去追一追。二哥的明星梦,现在看来实现不了了。但他终于去追了一把,此生无憾矣。
二哥并不“神经”。人生是一趟旅程,渴望做什么,只要不违法,尽量去做,就心满意足了。

□ 杨桂敏
一个人能在工作之余,有自己的爱好是幸运的。弹吉他便是我的这份幸运。
最初想学吉他,是在我上大二的时候。那时觉得弹吉他的人很潇洒、文艺,我也想成为有文艺范的人。学校门口有一家琴行,路过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会多看几眼。有时我会看到琴行的老师抱着吉他在弹曲子,我的心跟着吉他的弦音一起颤动。有时看到老师在教学生弹奏,我便想象着自己抱着吉他的样子。但也只能空想一下。因为那时,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得靠自己做兼职赚,去琴行学吉他有点奢望。
大概十年前,我参加工作了。一天,我再次经过大学门口那家琴行。我忐忑地走进琴行,问老师我的年龄会不会太大?老师答道:“若是想去国际大舞台,那确是起步太晚;若是弹给自己,那你还年轻。我们这里,年过六十的也有。”我顿时打消了顾虑。
我从简单的右手拨弦开始,“5323,1323”的节奏开练。乐理知识学得尚可,犯难的是学习和弦。左手按和弦时,不是按不紧发不出声音,就是和弦转换动作太慢连贯不起来。学习之初,左手指尖全是血泡,后来指尖慢慢都是茧子。我断断续续,一直没有放弃。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我学会了第一首曲子《传奇》,再后来是许巍的《旅行》,还有就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三毛作词的《橄榄树》等。过了第一关,以后便学得越来越顺畅。有一次同学聚会,我现场弹唱了一首我们大学毕业时唱的《心愿》,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我仿佛梦到了自己大学时代潇洒地弹吉他的样子,小小自豪了一番。
自从学会了弹吉他,假期出游时,我会随身带上吉他,在景色优美的野外,爱人在画画写生,我则拿出吉他来弹唱,有时引得不少人驻足。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把孩子哄睡后,在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里,弹唱一首,心情瞬间放松下来,一天的疲惫也烟消云散了。怀着愉悦的心情入睡,梦格外香甜。
音乐是人类的第二语言。我弹吉他主要是悦己。每当我抱起吉他,心立刻就安静下来;当我轻轻拨动琴弦,便沉醉在音符里。记得曾读到作家雪小禅的一句话:“人的爱好,在生死关头总会拯救他。因为漫长的时光是无法打发的,这些爱好,可以与时间为敌。”我倒不认为生活无趣至需要打发时间,而是觉得做一件热爱的事,会给平淡的生活增添风采,使生命更加动人。

□ 晴澜
每天早上七点一刻,我骑上心爱的自行车,准时出发上班。
现在出行如不超过20公里路程,我首选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不论严寒还是酷暑。每天骑行20公里,是基本运动量。骑行越多,生活越受骑行所影响与塑造;骑行越多,我就确定自己正往真正的美好前进——拥有健美的体格、平静的心理和身心灵的完整。
太阳初升,踩上自行车踏板的那一刻,想到我们的祖先此时一定是在奔跑的路上,他们必须去寻觅、猎杀动物以便生存下来。我们其实都是动物,所以首先要成为够格的动物,需要有敏捷的动作、结实的体魄、良好的视力。那些目光如炬、奔跑如飞、战斗力爆棚的古人,最终生存下来了。
骑行时,映入眼帘的是碧蓝的大海和天空,白鹭翻飞,鲜花绽放,绿草如茵……海风拂面,融入大自然,神清气爽,心里满是快乐和满足,感到身心灵前所未有的自由。没有压力,心理平和,自由自在,所以此时大脑处在最松弛、最具创新的最佳状态。那些可爱的句子、新奇的点子、久违的往事、解决问题的办法等,好像就突然从天而降,落到脑子里了。
骑行在路上,我觉得自己像个做游戏的孩子,时而悠哉游哉驻足拍照,时而以最快速度猛冲。运动让我心跳、呼吸加速,心肺输出更多血液和氧气,我仿佛感受到奔流的血液滋养正每一个肌肉细胞,肌纤维有力地收缩和舒张。
太阳沿着大海铺就一条金光大道,把万丈光芒投射到我的身上,温暖每一寸裸露的肌肤。朋友告诉我,在我骑行的这40多分钟时间里,获得了每日需要量的大多数维生素D。它被称为“阳光激素”,人体每日需要的绝大部分维生素D来自太阳默默的馈赠。
因为骑行,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健康、活力、快乐、平和、积极。

□ 崔岸儿
蘑菇与凉亭
田野上的蘑菇
像一个个凉亭
大地上的凉亭
像一朵朵蘑菇
我实在分不清楚
哪是凉亭哪是蘑菇
妈妈说:
“青蛙跑进去躲雨的是蘑菇,
我们跑进去躲雨的是凉亭。”
蜻蜓飞啊飞
小蜻蜓,飞啊飞
飞过竹篱笆,
变成牵牛花。
小蜻蜓,飞啊飞
飞过小枝桠,
变成小飞侠。
小蜻蜓,飞啊飞
飞过一群鸭,
变成一幅画。
雨点抓痒痒
花朵痒了
雨点给她抓痒痒
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
小河痒了
雨点给她抓痒痒
叮咚叮咚
叮咚叮咚
窗户痒了
雨点给她抓痒痒
噼啪噼啪
噼啪噼啪
我的脸上痒了
啪嗒啪嗒
啪嗒啪嗒
咦?
还给我抓痒痒来了

-我已经到底线啦-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