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平
吃是一种执念。尤其是我生活在川渝两个热衷于吃的城市俗人,吃不仅是天大的事,而且可以把吃过的好吃的,数落成名词反复咀嚼,悉数收藏到我的记忆里。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八月南海之行,风过广州、东莞、珠海,所际遇的人和看过的风景,沿海的时尚与现代,惊艳的港珠澳大桥和横琴口岸,从我离开的那天开始,就不明不白地模糊了。而珠海的吃,尽管与川渝的生猛麻辣大相径庭,却能闭目念想,时不时还满口生津,真是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想想我的老乡苏东坡也算是超级吃货,一生颠沛流离,却一路吃得满地生烟,吃得肆无忌惮,吃出很多心得留于后世,倍感欣慰。
去珠海吃的重点是海鲜,各种各样眼花缭乱的海鲜。这对于我来讲,简直就是窃喜。往常在自己的城市餐聚,偶尔会有三五个耳熟能详从海上过来的活物,更多的都是从冰柜里捞出来的,即使进了明确招牌的海鲜馆落座,海上那些名门闺秀怎么也是稀罕物,怎么也不轻易召之即来。而在珠海吃的海鲜,多得让你叫不出名字,有的还从未见过,这就显得特别豪横、奢侈了。
海鲜在古代人那里叫“海错”,几千年前的古人把海洋中能吃的活物统称“海错”。我还查了一下资料,这里的“错”,并不是错误的“错”,而是指错综复杂的意思。之所以称之为“海错”,是由于古代人对海洋生物了解较少,无法一一为其命名,面对品种繁多的海洋生物,就以“错”来表达其纷繁。清朝著名画家聂璜绘制的《海错图》,就是根据自己所见所闻,描绘了各种海洋生物形象。一本画册让海底生物的习性、姿态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至于吃,靠海吃海的沿海先人们,虽然吃不出什么花样,但海鲜已是一种“地位极高”的食物,《汉书·王莽传》中记载:“王莽事将败,悉不下饭,唯饮酒,啖鲍鱼肝”。曹植提到其父曹操生前喜食“啖鲍鱼肝”,就明白鲍鱼那时已是王公贵族的喜爱。考古学家在历史文化遗址中发现大量贝壳的化石,如海螺贝、牡蛎壳等,这些发现也应证了海鲜已经是我们祖先的食材。《周礼·天官》详细记录早在周朝时期,中国沿海居民就有吃生鱼的习俗。
大排档在珠海的威风绝不输给高楼大厦。那天走完香山湖栈道,一个退休多年还没到退休年龄的兄弟太明白我的心思,绕开富丽堂皇的门脸,寻了一家排档“香山小厨”直奔而去。装修一般,环境一般,门前大大小小水盆里的海鲜倒是琳琅满目,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了九宫图,朋友圈顿时大惊小叫,当然也是像我一样常年见不到海的朋友的惊叫。珠海的“肥原”们一点也不意外,估计是见多了我这等内陆崽。落座,不一会功夫店家七碗八碟已经堆满桌子,浅尝辄止。我在恭候一道非吃不可的大菜,就是牡蛎。早些年我来过珠海,横琴岛还是原生态,有一条土路可以把车开到离城市霓虹很远的“海里”,海边稀疏的渔船在岸边都摆有简易的桌子、几只凳子和一堆篝火,篝火上的铁架被海风吹得吱吱作响。那一次一大袋数十只牡蛎就是从小渔船上直接拎上来的,他们很娴熟,剥了壳蘸点食盐什么的,吃得津津有味。我试了一只实在太腥咽不下去。还是船家拿去铁架上烤熟了,还拿出一碟辣椒面,即刻成了天下无敌的美味,一口气吃了七八只。朋友说你这样吃晚上要流鼻血的,结果一晚相安无事,一觉睡到大天亮。横琴岛那年的旧迹荡然无存,而眼前排档的牡蛎和那年的长相一模一样。
牡蛎被称作“海中牛奶”,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蚝”,在内陆是一只一只卖,有时候卖到了天价,谁叫它稀罕呢。店家说,珠海146个岛屿中最大的横琴岛,岛的东南端是蚝的养殖集中地,各个木桩上都寄居着各种不同大小的蚝,上千亩养蚝场中的每一只蚝,立等可取。店家说,他们家的蚝都是横琴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生吃,或者蒸、烤,任何一种吃法绝对是对身体的“大补”。这在《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典籍里都有记载。香山小厨三种吃法都有,熟吃采用蒜茸粉丝清蒸烹饪,蒜茸的香驱逐了牡蛎的腥味,底下铺满的粉丝也吸收了牡蛎和蒜茸的鲜香,味道极具层次感。烧烤的简单多了,店家烤好了大盘端上,可就椒盐、辣椒面蘸食,回味无穷。我还是没有去碰生吃的,但我算是看完了全过程,小二把蚝生擘开,刮去泥沙,批破,清水洗净就能进嘴,他们说原汁原味,还有点清甜。
毋米粥早在19世纪的顺德就已经流行了。据说它的发源和重庆火锅很近似,重庆火锅最早是船夫在泊岸以后,收罗些没人买的猪牛的肠肠肚肚,那些称之为“下水”的便宜货,拿回船上用一只铁铸的鼎锅,辣椒、花椒一锅煮,这一煮就煮成了横行江湖的美食。毋米粥也是熬粥熬过了头,把一锅白米煮得稀烂,索性继续煮然后把饭渣捞起,“只取米精华”之汤,在米浆里就地取材煮些花式海鲜,就成了现在很高级的待客大牌。火锅的江湖与毋米粥的厅堂不能相提并论,但都是无意而为之成为锅煮的佳肴。在珠海的那家毋米粥店,居然想不起名字了,一上桌就是营养学,毋米粥的米都是上等米,毋米就是几个小时熬制以后看不见米了,只有稠状的粥样,以火锅的方式涮烫虾、蟹、鲍鱼各式海鲜,应有尽有,以及非常讲究的时令蔬菜,矿物质、低碳水化合物、食物纤维等等搭配,科学、健康,西南的麻辣、北方的麻酱,乃至腐乳之类都是不可以上桌的。浓稠的粥浆可以更好地锁住鲜味,再加上海鲜酱油撒一些芝麻、香菜末,鲜味十足,吃完菜肴再喝一碗粥,真是补身、补心。像我这样重口味的人,原以为整个过程是煎熬,却不知不觉中谈吐皆鸿儒,在珠海升级为“一顿饭”雅士。
珠海香洲情侣北路有家“我在海边等你”的酒楼,临海,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城市文学阳台”。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天色已晚,情侣路上似乎没撞见卿卿我我的情侣。在珠海长住且经常“夜出没”的老叶,煞有介事地说,我也没撞见过。对此只能将信将疑。尽管如此,这个酒楼把名字取这么长,这么煽情,至少是在这条路上有心在等。从酒店名字和这里的别称,应该想到这个老板有点意思。老板高志东早年闯荡海外,生意风生水起。人很低调,很儒雅,他说自己是这里的管家,主要是张罗一下来珠海的文朋诗友的活动,管点吃喝。酒楼装饰清雅,活动空间比吃饭的包间还多。进了房间,墙上有一壁照片,两壁签名,非常惹眼。照片上的人因为名气太大有不少都认识,留下签名的也是,我如果把这些名字罗列下来,还以为吃饭误入了中国当代文学馆。这个景象,想起多年前我在三联商务印书馆门厅墙壁上见过两壁照片,一壁“我们的员工”,一壁“我们的作者”,两壁照片上的人,每个都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巨椽,无需再有多余的字。这是我见过最高蹈、最辉煌的门脸。“我在海边等你”酒楼的高管家估计也去看过,那些留下笔迹的人若干年之后,再来看这个当代文学的聚散地,确是一道有滋有味的大菜。
“我在海边等你”,终于等到了极为清淡的梨虾球,雪梨,鲜虾,食材简单,操作应该也不复杂。清炒梨丁与虾球,梨的果甜,虾的鲜美,毫不相干的食材,却互不抢味,上盘之后再撒一些花椒粉末,三味三撞,既是味觉上的刺激,又是心理上的刺激,再佐以一杯白酒或者红酒,想的就多了,余味连绵。小小一碟,几双筷子过去就没了,美好总是瞬间即逝,只留下念想。后来才知道这是相当著名的“梨撞虾”,清代美食家袁牧《随园食单》早有记载,用材、步骤说得一清二楚。这个“撞”字了不得,之所以撞,就不是顺理成章的常态。撞出来的美味,有点像撞出来的文字,像撞出来的情感,不经意间而大获快感,妙不可言。
珠海在南中国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仅仅因为吃,我就愿意以身相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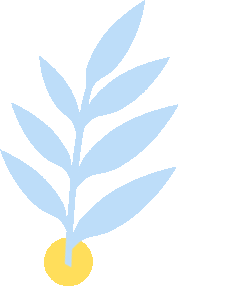
梁平 当代诗人、职业编辑。著有诗集、散文随笔、诗歌批评十余卷。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成都市文联名誉主席、《草堂》诗刊主编。现居成都。

七星瓢虫 李逊 摄
□陈再见
在拉美作家中,久负盛名的,如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略萨、博尔赫斯、阿斯图里亚斯等,他们对世界文坛的影响,简直可以用“大地震”来形容。而且,他们还都是大体量的作家,推土机的写作样式,碾压群雄。不过也有例外,如鲁尔福,相比而言,他的著作少得可怜,至今能找到的也就三部,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原野》,还有一本《金鸡》,也是一个不长的故事。
凭着这么少量的著作,鲁尔福仍是拉美作家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甚至在马尔克斯看来,发现鲁尔福,就像发现卡夫卡一样伟大,他在文章里写道:“我可以整段背诵《佩德罗·巴拉莫》……我能够背诵全文,且能倒背,不出大错。并且还能说出每个故事在我读的那本书的哪一页上,没有一个人物的任何特点我不熟悉。”由此看来,鲁尔福还是作家中的作家,他对马尔克斯的影响巨大,可以说,如果没有《佩德罗·巴拉莫》,就没有后来震惊世界文坛的《百年孤独》。
对鲁尔福,我早有耳闻——那时身边的评论家宫敏捷一见面必提老鲁。而真正的阅读,是在2013年,我一次性把鲁尔福的作品都买了回来,其实也就两本,一本《燃烧的原野》,一本《佩德罗·巴拉莫》。我先读了《燃烧的原野》,当时很吃惊,像《都是因为我们穷》和《你听见狗叫了吗》这些小说,至今印象深刻。一段时间后,我开始阅读《佩德罗·巴拉莫》,结果简直可以用“震惊”来形容,竟故意放慢阅读速度,舍不得一下子看完。那段时间刚好是我写作的瓶颈期,几乎写不出任何东西,一方面是能力有限,一方面也是对文字失去了敬畏感,似乎所有文字都失去了迷人的光环,变得平凡无奇,如街边枯黄的落叶。我知道,我亟需好的文字来激活感官,重获对文字的敬意和追求。《佩德罗·巴拉莫》就是在恰当的时间,准确无误地闯进了我的内心。
《佩德罗·巴拉莫》让人着迷的还不仅是意致疏远的文字,而且他打通了事物的边界,让现实与虚幻无缝连接起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已经够伟大,他还表达完成得那么别致而深刻。我一下子如获新生,哦,原来小说还能写这些,原来小说还能这么写……我们一直觉得不可能的事,包括题材的挖掘和处理,表达的形式和方向,隐喻的制设和运用,人家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如此纯熟地写出来了——绝望的情绪当然是有的,更多则是豁然开朗的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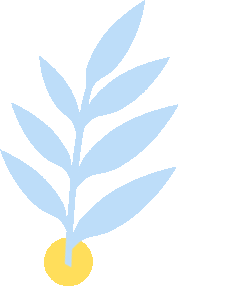
陈再见 1982年生于广东陆丰。发表作品多篇,著有长篇小说《六歌》《出花园记》《骨盐》,小说集《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等五部;曾获《小说选刊》年度新人奖、广东短篇小说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
□杨角
地平线
飞机上见过的景象
在岷江边,我又一次看见
七年前去长春,曾转机天津
飞机在滑翔中有一次
懒懒的转弯。舷窗外,天际线
和地平线叠在一起
无尽的天光来自大海方向
昨日我在菜坝镇喝酒
微醺中走向岷江边一块草坪
一梦醒来,黄昏已经落地
天空尽是云彩
那一刻,地平线比一株
狗尾草还低
天地一线
地球的表面一马平川
落日无解
在我的眼里
落日落下,不一定会再次升起
一个进入黄昏的人
已没有资格挥霍落日
落日如火笼,我在冬天爱它
到夏天照样爱它
只有在夏天仍照样热爱落日的人
才知道落日的无解
与无法求证
能看见今天落日的人
不一定能看到明日的落日
正是这种不确定性
使落日无限接近一个高龄老人
和一只刚刚熄火的瓦罐
我想抱住他
又怕他突然散架
冷月孤悬
去长江边走步回来
看见一轮冷月还悬挂在31楼上空
突然想叫它下来,想说说话
说这些年我每次见它
都要拼命地仰头
喉结和声带被紧紧绷住
想它在高处看我,也有不适
也有遮挡和障碍物
冷月孤悬,它的身边已经
没有一颗星星
而人世匆忙,只有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想这寂寥的人间
月亮和我,也有相同的孤单
旅途问答
坐绿皮火车去北京
要一天两夜
真是怪哈,窗外的景色一旦
飞起来,人就昏昏欲睡
于是找来扑克:升级、拱猪、斗地主
会玩的游戏都玩过一遍
火车才过西安。难以入眠的夜里
一个人坐在卧铺走廊的靠椅上
窗外的祖国正万家灯火
这时,我希望有人从远处轻轻走来
拍一拍我的肩
然后问我:你去哪里?
然后我答:铁轨的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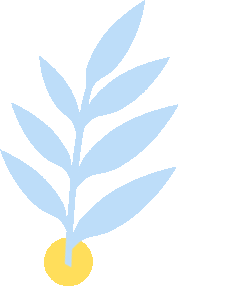
杨角 四川宜宾人。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星星》等,被收入多种选本,获过奖。出版个人诗集7部。
□张建春


□梁平
吃是一种执念。尤其是我生活在川渝两个热衷于吃的城市俗人,吃不仅是天大的事,而且可以把吃过的好吃的,数落成名词反复咀嚼,悉数收藏到我的记忆里。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八月南海之行,风过广州、东莞、珠海,所际遇的人和看过的风景,沿海的时尚与现代,惊艳的港珠澳大桥和横琴口岸,从我离开的那天开始,就不明不白地模糊了。而珠海的吃,尽管与川渝的生猛麻辣大相径庭,却能闭目念想,时不时还满口生津,真是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想想我的老乡苏东坡也算是超级吃货,一生颠沛流离,却一路吃得满地生烟,吃得肆无忌惮,吃出很多心得留于后世,倍感欣慰。
去珠海吃的重点是海鲜,各种各样眼花缭乱的海鲜。这对于我来讲,简直就是窃喜。往常在自己的城市餐聚,偶尔会有三五个耳熟能详从海上过来的活物,更多的都是从冰柜里捞出来的,即使进了明确招牌的海鲜馆落座,海上那些名门闺秀怎么也是稀罕物,怎么也不轻易召之即来。而在珠海吃的海鲜,多得让你叫不出名字,有的还从未见过,这就显得特别豪横、奢侈了。
海鲜在古代人那里叫“海错”,几千年前的古人把海洋中能吃的活物统称“海错”。我还查了一下资料,这里的“错”,并不是错误的“错”,而是指错综复杂的意思。之所以称之为“海错”,是由于古代人对海洋生物了解较少,无法一一为其命名,面对品种繁多的海洋生物,就以“错”来表达其纷繁。清朝著名画家聂璜绘制的《海错图》,就是根据自己所见所闻,描绘了各种海洋生物形象。一本画册让海底生物的习性、姿态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至于吃,靠海吃海的沿海先人们,虽然吃不出什么花样,但海鲜已是一种“地位极高”的食物,《汉书·王莽传》中记载:“王莽事将败,悉不下饭,唯饮酒,啖鲍鱼肝”。曹植提到其父曹操生前喜食“啖鲍鱼肝”,就明白鲍鱼那时已是王公贵族的喜爱。考古学家在历史文化遗址中发现大量贝壳的化石,如海螺贝、牡蛎壳等,这些发现也应证了海鲜已经是我们祖先的食材。《周礼·天官》详细记录早在周朝时期,中国沿海居民就有吃生鱼的习俗。
大排档在珠海的威风绝不输给高楼大厦。那天走完香山湖栈道,一个退休多年还没到退休年龄的兄弟太明白我的心思,绕开富丽堂皇的门脸,寻了一家排档“香山小厨”直奔而去。装修一般,环境一般,门前大大小小水盆里的海鲜倒是琳琅满目,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了九宫图,朋友圈顿时大惊小叫,当然也是像我一样常年见不到海的朋友的惊叫。珠海的“肥原”们一点也不意外,估计是见多了我这等内陆崽。落座,不一会功夫店家七碗八碟已经堆满桌子,浅尝辄止。我在恭候一道非吃不可的大菜,就是牡蛎。早些年我来过珠海,横琴岛还是原生态,有一条土路可以把车开到离城市霓虹很远的“海里”,海边稀疏的渔船在岸边都摆有简易的桌子、几只凳子和一堆篝火,篝火上的铁架被海风吹得吱吱作响。那一次一大袋数十只牡蛎就是从小渔船上直接拎上来的,他们很娴熟,剥了壳蘸点食盐什么的,吃得津津有味。我试了一只实在太腥咽不下去。还是船家拿去铁架上烤熟了,还拿出一碟辣椒面,即刻成了天下无敌的美味,一口气吃了七八只。朋友说你这样吃晚上要流鼻血的,结果一晚相安无事,一觉睡到大天亮。横琴岛那年的旧迹荡然无存,而眼前排档的牡蛎和那年的长相一模一样。
牡蛎被称作“海中牛奶”,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蚝”,在内陆是一只一只卖,有时候卖到了天价,谁叫它稀罕呢。店家说,珠海146个岛屿中最大的横琴岛,岛的东南端是蚝的养殖集中地,各个木桩上都寄居着各种不同大小的蚝,上千亩养蚝场中的每一只蚝,立等可取。店家说,他们家的蚝都是横琴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生吃,或者蒸、烤,任何一种吃法绝对是对身体的“大补”。这在《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典籍里都有记载。香山小厨三种吃法都有,熟吃采用蒜茸粉丝清蒸烹饪,蒜茸的香驱逐了牡蛎的腥味,底下铺满的粉丝也吸收了牡蛎和蒜茸的鲜香,味道极具层次感。烧烤的简单多了,店家烤好了大盘端上,可就椒盐、辣椒面蘸食,回味无穷。我还是没有去碰生吃的,但我算是看完了全过程,小二把蚝生擘开,刮去泥沙,批破,清水洗净就能进嘴,他们说原汁原味,还有点清甜。
毋米粥早在19世纪的顺德就已经流行了。据说它的发源和重庆火锅很近似,重庆火锅最早是船夫在泊岸以后,收罗些没人买的猪牛的肠肠肚肚,那些称之为“下水”的便宜货,拿回船上用一只铁铸的鼎锅,辣椒、花椒一锅煮,这一煮就煮成了横行江湖的美食。毋米粥也是熬粥熬过了头,把一锅白米煮得稀烂,索性继续煮然后把饭渣捞起,“只取米精华”之汤,在米浆里就地取材煮些花式海鲜,就成了现在很高级的待客大牌。火锅的江湖与毋米粥的厅堂不能相提并论,但都是无意而为之成为锅煮的佳肴。在珠海的那家毋米粥店,居然想不起名字了,一上桌就是营养学,毋米粥的米都是上等米,毋米就是几个小时熬制以后看不见米了,只有稠状的粥样,以火锅的方式涮烫虾、蟹、鲍鱼各式海鲜,应有尽有,以及非常讲究的时令蔬菜,矿物质、低碳水化合物、食物纤维等等搭配,科学、健康,西南的麻辣、北方的麻酱,乃至腐乳之类都是不可以上桌的。浓稠的粥浆可以更好地锁住鲜味,再加上海鲜酱油撒一些芝麻、香菜末,鲜味十足,吃完菜肴再喝一碗粥,真是补身、补心。像我这样重口味的人,原以为整个过程是煎熬,却不知不觉中谈吐皆鸿儒,在珠海升级为“一顿饭”雅士。
珠海香洲情侣北路有家“我在海边等你”的酒楼,临海,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城市文学阳台”。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天色已晚,情侣路上似乎没撞见卿卿我我的情侣。在珠海长住且经常“夜出没”的老叶,煞有介事地说,我也没撞见过。对此只能将信将疑。尽管如此,这个酒楼把名字取这么长,这么煽情,至少是在这条路上有心在等。从酒店名字和这里的别称,应该想到这个老板有点意思。老板高志东早年闯荡海外,生意风生水起。人很低调,很儒雅,他说自己是这里的管家,主要是张罗一下来珠海的文朋诗友的活动,管点吃喝。酒楼装饰清雅,活动空间比吃饭的包间还多。进了房间,墙上有一壁照片,两壁签名,非常惹眼。照片上的人因为名气太大有不少都认识,留下签名的也是,我如果把这些名字罗列下来,还以为吃饭误入了中国当代文学馆。这个景象,想起多年前我在三联商务印书馆门厅墙壁上见过两壁照片,一壁“我们的员工”,一壁“我们的作者”,两壁照片上的人,每个都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巨椽,无需再有多余的字。这是我见过最高蹈、最辉煌的门脸。“我在海边等你”酒楼的高管家估计也去看过,那些留下笔迹的人若干年之后,再来看这个当代文学的聚散地,确是一道有滋有味的大菜。
“我在海边等你”,终于等到了极为清淡的梨虾球,雪梨,鲜虾,食材简单,操作应该也不复杂。清炒梨丁与虾球,梨的果甜,虾的鲜美,毫不相干的食材,却互不抢味,上盘之后再撒一些花椒粉末,三味三撞,既是味觉上的刺激,又是心理上的刺激,再佐以一杯白酒或者红酒,想的就多了,余味连绵。小小一碟,几双筷子过去就没了,美好总是瞬间即逝,只留下念想。后来才知道这是相当著名的“梨撞虾”,清代美食家袁牧《随园食单》早有记载,用材、步骤说得一清二楚。这个“撞”字了不得,之所以撞,就不是顺理成章的常态。撞出来的美味,有点像撞出来的文字,像撞出来的情感,不经意间而大获快感,妙不可言。
珠海在南中国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仅仅因为吃,我就愿意以身相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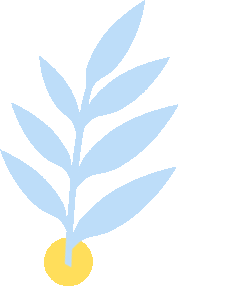
梁平 当代诗人、职业编辑。著有诗集、散文随笔、诗歌批评十余卷。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成都市文联名誉主席、《草堂》诗刊主编。现居成都。

七星瓢虫 李逊 摄
□陈再见
在拉美作家中,久负盛名的,如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略萨、博尔赫斯、阿斯图里亚斯等,他们对世界文坛的影响,简直可以用“大地震”来形容。而且,他们还都是大体量的作家,推土机的写作样式,碾压群雄。不过也有例外,如鲁尔福,相比而言,他的著作少得可怜,至今能找到的也就三部,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原野》,还有一本《金鸡》,也是一个不长的故事。
凭着这么少量的著作,鲁尔福仍是拉美作家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甚至在马尔克斯看来,发现鲁尔福,就像发现卡夫卡一样伟大,他在文章里写道:“我可以整段背诵《佩德罗·巴拉莫》……我能够背诵全文,且能倒背,不出大错。并且还能说出每个故事在我读的那本书的哪一页上,没有一个人物的任何特点我不熟悉。”由此看来,鲁尔福还是作家中的作家,他对马尔克斯的影响巨大,可以说,如果没有《佩德罗·巴拉莫》,就没有后来震惊世界文坛的《百年孤独》。
对鲁尔福,我早有耳闻——那时身边的评论家宫敏捷一见面必提老鲁。而真正的阅读,是在2013年,我一次性把鲁尔福的作品都买了回来,其实也就两本,一本《燃烧的原野》,一本《佩德罗·巴拉莫》。我先读了《燃烧的原野》,当时很吃惊,像《都是因为我们穷》和《你听见狗叫了吗》这些小说,至今印象深刻。一段时间后,我开始阅读《佩德罗·巴拉莫》,结果简直可以用“震惊”来形容,竟故意放慢阅读速度,舍不得一下子看完。那段时间刚好是我写作的瓶颈期,几乎写不出任何东西,一方面是能力有限,一方面也是对文字失去了敬畏感,似乎所有文字都失去了迷人的光环,变得平凡无奇,如街边枯黄的落叶。我知道,我亟需好的文字来激活感官,重获对文字的敬意和追求。《佩德罗·巴拉莫》就是在恰当的时间,准确无误地闯进了我的内心。
《佩德罗·巴拉莫》让人着迷的还不仅是意致疏远的文字,而且他打通了事物的边界,让现实与虚幻无缝连接起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已经够伟大,他还表达完成得那么别致而深刻。我一下子如获新生,哦,原来小说还能写这些,原来小说还能这么写……我们一直觉得不可能的事,包括题材的挖掘和处理,表达的形式和方向,隐喻的制设和运用,人家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如此纯熟地写出来了——绝望的情绪当然是有的,更多则是豁然开朗的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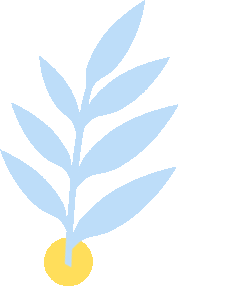
陈再见 1982年生于广东陆丰。发表作品多篇,著有长篇小说《六歌》《出花园记》《骨盐》,小说集《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等五部;曾获《小说选刊》年度新人奖、广东短篇小说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
□杨角
地平线
飞机上见过的景象
在岷江边,我又一次看见
七年前去长春,曾转机天津
飞机在滑翔中有一次
懒懒的转弯。舷窗外,天际线
和地平线叠在一起
无尽的天光来自大海方向
昨日我在菜坝镇喝酒
微醺中走向岷江边一块草坪
一梦醒来,黄昏已经落地
天空尽是云彩
那一刻,地平线比一株
狗尾草还低
天地一线
地球的表面一马平川
落日无解
在我的眼里
落日落下,不一定会再次升起
一个进入黄昏的人
已没有资格挥霍落日
落日如火笼,我在冬天爱它
到夏天照样爱它
只有在夏天仍照样热爱落日的人
才知道落日的无解
与无法求证
能看见今天落日的人
不一定能看到明日的落日
正是这种不确定性
使落日无限接近一个高龄老人
和一只刚刚熄火的瓦罐
我想抱住他
又怕他突然散架
冷月孤悬
去长江边走步回来
看见一轮冷月还悬挂在31楼上空
突然想叫它下来,想说说话
说这些年我每次见它
都要拼命地仰头
喉结和声带被紧紧绷住
想它在高处看我,也有不适
也有遮挡和障碍物
冷月孤悬,它的身边已经
没有一颗星星
而人世匆忙,只有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想这寂寥的人间
月亮和我,也有相同的孤单
旅途问答
坐绿皮火车去北京
要一天两夜
真是怪哈,窗外的景色一旦
飞起来,人就昏昏欲睡
于是找来扑克:升级、拱猪、斗地主
会玩的游戏都玩过一遍
火车才过西安。难以入眠的夜里
一个人坐在卧铺走廊的靠椅上
窗外的祖国正万家灯火
这时,我希望有人从远处轻轻走来
拍一拍我的肩
然后问我:你去哪里?
然后我答:铁轨的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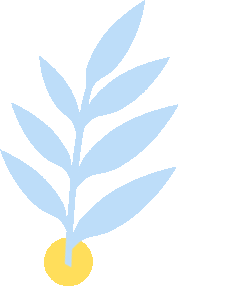
杨角 四川宜宾人。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星星》等,被收入多种选本,获过奖。出版个人诗集7部。
□张建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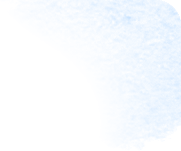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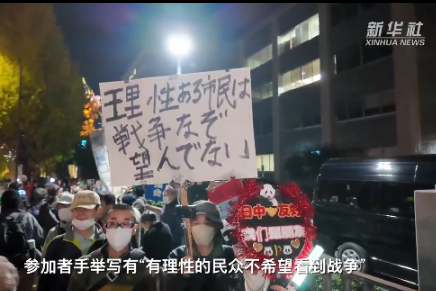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