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读梁冬霓散文集《时光倒影》
□ 李春鹏
《时光倒影》是一本呕心沥血之作。全书分为三辑:《乡情咏叹》回望故乡松口古镇,瞩目工作生活之地斗门;《路遇微风》錾刻岁月履迹,于时光流转中感念亲情并记录自己的成长;《书斋浅谈》则对耿立、陈继明等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度的个性化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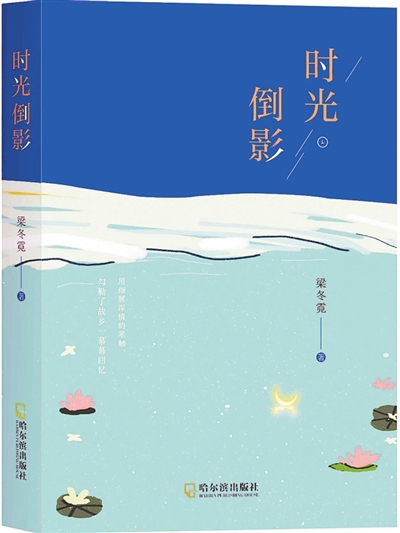
梁冬霓散文最大的特色是对故乡的深情回望。这种回望融入了眷眷深情,也夹杂着淡淡愁绪,凸显了她对故乡变迁发展的深刻思考。辛格说: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根。《时光倒影》确属一部寻根之作。梅州松口镇,是梁冬霓的故乡,是客家人下南洋的首站。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尤其是客家文化)底蕴深厚。梁冬霓深情回望故乡,用诗性的文字,叙写历史的松口和现实的松口,将岁月镌刻在古镇身上的光环与伤痕一并呈现。故乡在变迁,故乡在发展。一些在涌现,一些又在失去。故乡或远或近,远的是自己和故乡的时空间隔,是非物质文化遗存的日渐式微,近的是自己与故乡之间的精神契合与情感纽连。记忆里温暖热闹的裤裆街,似被世人遗忘。松江大酒店与火船码头,繁华之时共沐风月,寂寥之时互诉沧桑。她在沉思中慨叹,在慨叹中沉思,她沉甸甸的述说里,浸透着岁月沧桑的厚重历史感。
《时光倒影》也是一本感念亲情的书。这些表达亲情的文字质朴真切,感人至深。全身布满灰尘,心里却透亮无比的母亲,推着板车把一袋袋水泥搬运到货船上,坚信自己的勤劳一定能够让女儿飞出这片贫穷孤绝之地。《天堂的吻痕》回忆外婆,甜甜的甘蔗、微酸的马齿苋汤、闪着奶油光亮的雪糕、儿时与外婆的绕膝之欢、手摇蒲扇带来的丝丝凉风……“她抱着我,灰白的头发撂在耳根后,在我脸颊边亲了又亲。她说她亲我一下,我就会长得更快,变得更聪明,这个秘密一直珍藏在我心里,而那吻痕里的温柔与甜蜜,更让我今生难以忘怀。”如同电影慢镜头,轻柔细腻,深情温暖。
《时光倒影》记录了作家的自我成长。从求学到工作,身处不同环境,际遇各色人等,历经酸甜苦辣,她深切体味来自身边的感动,“人与人之间……重要的是心里有爱、有光。”她用诗情慧心记录和描述身边的变化,见证斗门的发展。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家的笔触一旦挣脱个人心性的园囿,情感的天地便豁然开朗起来。旧街的嬗变生辉,老薇茶铺质朴的诗意,走向世界的白蕉海鲈,时光深处的水松林,笑意盈盈的白藤湖,天然氧吧黄杨河湿地公园,水墨画一样的莲江村,历经沧桑气韵流动的排山村,宁静温婉无处不飞花的井岸……她从事园林绿化管理工作,与花草树木成了朋友,与土地结下深厚感情,琐碎的工作与平凡的劳动,在她笔下呈现出乐观平和的情绪和恬淡舒适的惬意。“一撮泥土,一滴雨露,一缕花香,都是意料之中的恩赐(《最初的庭院》)”。这些朴素的文字,是她对生活的自然诠释,更是她心境的自然流露。
厚厚的《时光倒影》,馥郁诗意氤氲其间。这种诗意,源于其深刻思想和丰富情感,还源于它凝重纯净的语言之美,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画面感。“风清水阔,白鹭群飞,草逸花闲,廊亭沐霞。”这是简洁洗练的白描。“一江清水静静东流,泊岸的野舟,是古朴岁月的见证者,把沧桑与烟波中的灵动,摆在时光的记忆中。”这是淡雅悠远的水墨。“菉猗堂像一位经历了沧桑巨变的老人,归隐于寻常巷陌、山云涧水,在阳光中瞭望人世繁华,静听松风石泉。”这是朴拙厚重的木刻。“美人蕉鹅黄、粉红、橘红的花朵,交织起一条条彩带,与霞光相映成绚丽的黄昏。”这是灿烂热烈的油画。
这种画面感甚至是质朴的,如同黑白电影。“只记得一个雨天,姐姐被蜈蚣蜇了之后,父亲坐在门口用酒精给她消毒。狭长的巷子上面,两边的灰瓦夹着青色的天空。我坐在姐姐旁边,听她的哭嚷声,然后望望门前的巷道。雨水洗过的青石板路,与姐姐的脸一样,有一种深厚的潮湿(《或远或近的故乡》)”。这种画面感的呈现,是感性的有温度的,用记忆中的童年往事写石板路,既有一份亲切的爱意,又有一种心灵深处被触及的痛感。姐姐的脸与雨水洗过的青石板路,在浓厚的潮湿里共情。
梁冬霓秉持精品意识,凝练并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背后,蕴藏着她执着的匠心。不过,我倒希望她写作时少些刻意,多些随意,只因“散文需要的就是一种散步者的心境”。

——读麦家《人间信》
□ 胡胜盼
“成功也是一种障碍,写多了容易自我重复,我不想再循着套路打转。”有了这份“执念”,或者应该说是清醒,作家麦家努力摆脱掉“中国谍战小说之父”的光环,2019年推出转型之作《人生海海》。5年后,麦家携长篇小说《人间信》再度走入读者视野。故事里没有英雄,没有传奇,有的是每一个普通人在尘世浮沉中为自己争取的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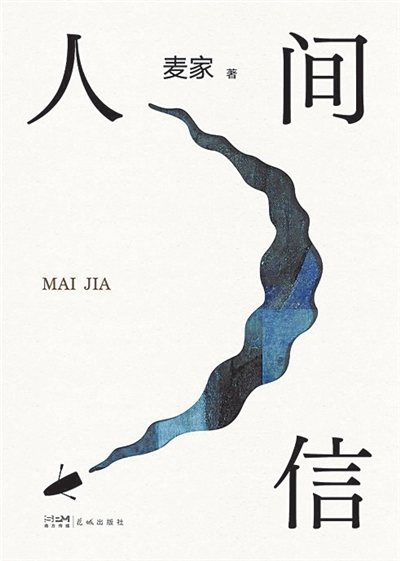
这是一本作家从心底喊出来的书。故事以“我”的经历为引,围绕富春江边双家村的一个家庭展开,讲述了四代人、半个世纪爱与恨的循环往复。小说上卷详写家族史,重点放在奶奶和父亲身上。父亲如何不堪,奶奶如何用残存的家族意志去试图挽回衰颓。意在写“命运的承受”。小说下卷的叙述者“我”走到前台,成为故事推动者。意在写“命运的奋力过招”。如此,两卷交融,点明“命运不仅是承受,还要奋力过招”。小说写出了不被承认的创伤和未被看见的痛苦,诉说着人生的种种不可言说。
麦家是一位擅长讲故事的小说家。读《人间信》,很自然会想到《人生海海》。《人生海海》中,我们能看到作家一如既往地沉迷于故事性与戏剧性,为了“说好中国故事”,甚至有意借鉴古典文学资源完成通俗形式的构造,向古典通俗叙事模式靠拢。然而,《人间信》却又有意淡化了故事性。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更像是一个深邃的哲学命题,一则深沉的寓言故事。不依赖戏剧化情节,麦家转向自己内心深处,寻找精神原乡的意志变得更为坚决,小说“写人生无可避免的命运,写给被过往和缺憾困住的人”也显得更加明确。
生活未及之处,文学终将抵达。《人间信》映射有作家童年的影子。小说的主人公是世人眼中的英雄,却是家人口中的叛徒。他鄙视父亲,揭发父亲,在他眼里,“在父亲的众多绰号中,最为贴切、跟随他一生的,叫作‘潦坯’。潦坯不是逆子,不是混蛋,只是骨头轻,守不住做人做事的底线。潦坯不作恶外人,只作践自己和亲人。”故事隐约写进了麦家的亲身经历,与父亲的交恶,被困在命运之中,和内心幽灵厮杀,童年的不幸让他用一生去治愈,这是一场寻求救赎与自我和解的旅程。
麦家的小说多对女性人物饱含热情。《人间信》亦如是。书中,奶奶、母亲和妹妹,她们本应拥有自己的精彩人生,却不幸被卷入了父亲的困境中。三代女性在男性缺位的情况下,缝补破碎的人间,小说既书写了她们被辜负、被剥夺的一面,也以真挚的笔触向她们如野草般的生命力致敬。麦家一直走不出童年的阴影,做不到对父亲一笑释然。他的八旬老母亲对他说,“你读了那么多书,跑了那么多码头,见了那么多领导,竟然还放不下对过去那些人的恨?”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母亲的睿智和豁达,使得作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也有了一份更真诚的体悟。
《人间信》虽然没有神秘莫测且跌宕起伏的故事,但是作家出色的语言能力却依然得以充分展现。他说寂寞:“寂寞是一把刀,时间是磨刀石,越磨越锋利。”他说爱:“爱一个人,可能会反目,从爱到恨,有时只隔着一句话,一个眼色,一次粗心。”他说做人:“做人要心平,心平才能平安。”他写少女的心扉:“其实什么花都比不得一个少女,少女才是世间独一无二的花,所谓花季少女,豆蔻年华,心里装着朦胧的爱情和向往——尚未开始,就以为会天长地久——像一个蓓蕾一样,随时准备轰轰烈烈去争奇斗艳。”富有理趣,读来意味深长。
和《人生海海》一样,《人间信》书名取得很有意思。这是写给人世间的一封深情家书。一封写给那些在漂泊中挣扎半生,终于能鼓起勇气面对自我的游子的信,也是一封写给那些被社会淹没、被命运辜负的女性的信,更是一封写给每一个在人间困顿浮沉的我们的信。不过,在作者麦家看来,解读“人间信”非常简单,即“信人间”。这种最简洁的解读背后,是作家对生活最长情的告白,对生命最质朴的诠释,对命运最通透的理解。
“哪怕溃败无常,也要尊敬自己。”学会释怀,学会接受,学会在逆境中挖掘内心的力量,在挣扎中重新唤起站起来的勇气。普通人的英雄主义,是坦然直视伤口。如同本书封面的镂空设计,既是心灵的创伤,也是承载着记忆的河流,象征着人生的苦与乐。这是《人间信》给予读者最诗意的柔情馈赠。
——世宾随笔集《目标在寻找它的神枪手》的思想性与文学性
□ 黄金明
当初世宾说在写一部片段体的著作时,我吃了一惊,片段体写作难度特别大。在20世纪,有很多片段体经典,譬如卡夫卡的一些随笔、佩索阿的《不安之书》、齐奥朗的《解体概要》和卡内蒂的《人的疆域》,可能还可以算上格拉克的《首字花饰》、波德里亚的《冷记忆》、罗扎诺夫的《落叶》。这些著作体量都不大,卡内蒂的厚重些,但他写了一辈子。由此,我对世宾肃然起敬,也为他捏着一把冷汗。但他每隔几天就说,又完成了几条。他在广州市天河公园散步时用手机录音,或者在工作间隙一条条地写,毫不费劲、游刃有余,到了挥洒自如、拈之即来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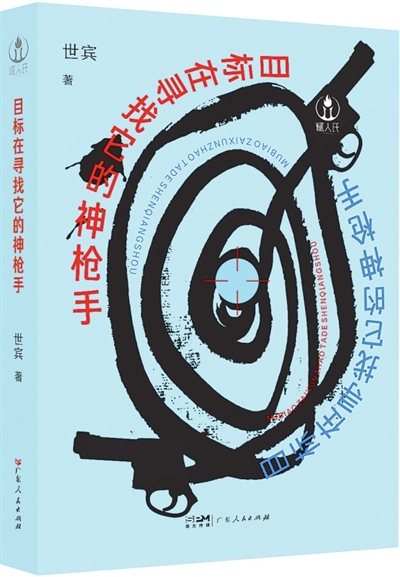
我注意到,书里面有关于“知天命”的感悟。这本书确实是他过了50岁之后写的。作为见证者,我在该书出版之前看过一些——有时他在电脑上还没有改定便邀我看。这部片段体著作的内容极其广泛,包罗万象,贯通了很多不同领域,首先是从诗学扩展到文学,然后是哲学、宗教、心理学、伦理学等。他的写作方式有其独到之处,其中的思辨、言说、驳难,有多声部多层次的书写,且完成得很漂亮。
他对“三生”(生命、生活、人生)的理解很深刻,文本里常有不同声音在对话、辩论、交锋,还有反思和倾听,我特别看重这种反思。譬如第87页最后一条,“就像你说的,我是大灰狼”,他注意到自己天使的属性(亦即神性),还注意到兽性,这个就不简单了。人凭借神性而拓展生命的可能性,并尽量克服兽性,这一条讲得很深刻。书中对两性关系、对爱情的探讨,也让人耳目一新。他对人的心理有深入研究,对现实社会也洞若观火。像第五页最后一条,谈到爱情最大的障碍是占有,他认为必须消除占有或让其消融于爱。
世宾反省的、犹疑的姿态我特别欣赏。相比一些人用无比坚定的语气诉说“真理在握”,我更信任不断证否不断求真的反复质询。世宾说,“我说话的时候语气不连贯,断断续续”,他的反省很深入,也很自觉,他像佩索阿那样,创造出一批“导师”和“同道”教育自己。有朋友说世宾是青年的好导师,我倒是觉得他是一个好学生,在他的身后有一大堆更冷静、更睿智的“世宾”在教育他、鞭策他、完善他。这让我想起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说,能说清楚的就尽量说清楚,说不清楚的就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在讲课时结结巴巴,他头脑里在刹那间有很多话语、思想、事件之类,像洪水一样要冲破他的喉咙,但他想要更精确更清晰地说出来,就需字斟句酌,语速缓慢,谨慎小心。我觉得世宾有时候也是这样,这样的文本更可靠,因为他并不自诩真理,反有自我质疑的成分。
有一条是我特别喜欢的,第91页最后一条,“两个人隔着几百公里的河山聊天,双方都是独自一人,喝茶,相互间谈论一些深奥的事物”。他说“这个意象绝对是现代的,在古代是没有的”。两个独自喝茶的人又独立又联结,有散文的笔调,有诗性的话语,还有一种镜头般的画面感,生动形象,这种表达就更有文学性了,不仅仅是言说,还有叙述、描写和抒情,有不同的声音在此交融,有一种复调性的效果。写思想随笔要有文学性,这才算是由思想入而从随笔出。

□ 龙建雄
最近看“唐宋八大家”,娓娓道来的文字极易让大脑里塞满“江湖”的刀光剑影,把我原本平静的思绪搅得乱成一团浆糊。故事情节和生平往事其实不复杂,但他们的诗词歌赋有如天上飘来一朵朵白云,太多太多的好词好句眩晕了记忆的“水平面”,不煮成“一锅粥”实在是难。平时基本上不看电视的我,看央视的视频又是另外一番情形,里面煽情的场面让人控制不住自己,极易潸然泪下。
发现一个小巧合:叫“梦得”的人值得信任,20年以上的挚友更是值得一生深交。
唐朝的柳宗元有个朋友叫梦得,他便是鼎鼎有名的刘禹锡、字梦得,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那位。刘梦得与柳宗元相识于793年同中进士的开榜日,有“城里考生”质疑刘禹锡有何本事位列榜中第五名,第四名的柳宗元勇敢站出来相救,一席话语把人家说得灰溜溜而走。柳宗元的个人魅力和政治远见很快让刘禹锡膜拜,二人结为兄弟,刘长于柳一岁为兄,柳为贤弟。805年“永贞革新”失败后,作为中坚力量的柳宗元被贬湖南永州、刘禹锡被贬湖南朗州(今常德),均任州府司马;其间,二人不间断保持书信联系,互相鼓励,分享彼此的生活和情感。
814年,柳宗元和刘禹锡奉诏回京,次年三月又分别调任远离朝廷的柳州刺史和连州刺史,两人一同从长安出发,至衡阳分路而行。面对古道风烟,前程茫茫,二人赠诗惜别,柳宗元作《重别梦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不幸的是,819年柳宗元在广西柳州任上郁郁而终,他将自己所有亲人和毕生诗文全部交托给刘禹锡,刘禹锡穷尽后半生之力完成《柳宗元集》,并把平生所学尽数传给了柳宗元之子。“二十年来万事同”“晚岁当为邻舍翁”,把这14个字在脑海里闪过一念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该是何等幸甚至哉!
北宋的苏轼有个朋友也叫梦得,大名马正卿、字梦得,他和苏轼同年同月生,生日只差八天。马梦得原来在京城太学里做官,“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因为性情太耿直不招人喜欢,学生不喜欢他,也不受上司的信任,后来干脆就不做官。马梦得跟苏轼很聊得来,一直追随,既是苏的铁杆粉丝,又是他的管家,还是他的随从。苏轼被贬黄州,老友马梦得后脚随到。万幸有这个马梦得,才会有后世响亮千古的“东坡”。苏轼在黄州把仅有的钱用完之后,眼看着就要面对无米之炊的窘境,追随他的马梦得动用各种关系去官府为苏轼批得了一块荒地,让苏开始了自给自足、自耕自乐的日子,也让苏成为了黄州一个远近闻名的“农民”,正是这接地气的身份,才成就了如今被我们宠爱千年的“苏东坡”。
苏轼在黄州写《东坡八首》,其中有一首写道:“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马梦得曾经盼着偶像飞黄腾达,梦想有朝一日分点钱给他买个山头,但苏轼一贬再贬,一直毫无大富大贵的迹象,马梦得依然义无反顾地帮衬苏轼一家渡过众多难关。苏轼笑话马梦得这个铁杆老友跟错了“老大”,说“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无论从苏轼的角度,还是从我们今人的立场来看,得此一友,夫复何求?
入心感怀,这兴许是一件好事。读到千年前柳宗元、苏轼的“老友记”,免不了也感叹自己身边有那么几位友谊了二三十年的老朋友。他们从来没有计较过我的出身,也从来没有嫌弃过我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那几个老友,一旦我有需要,他们再忙也愿意陪,再穷也愿意帮,细想之下,他们除了与我分享快乐,似乎从来没有所求之事来烦扰于我。因为感同身受,所以“梦得老友”感动了我自己这件事也就不足为奇。
打趣来说,行事干脆的朋友有很多,待友纯粹的朋友难能可贵,叫“梦得”的朋友则物以稀为贵。得之,幸之。
解读深邃的宇宙之谜
□ 刘昌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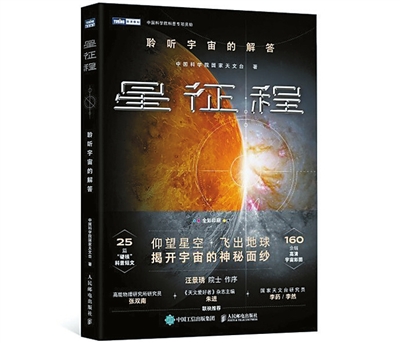
千百年来,深邃迷人的星空总是吸引着人们探求的目光,浩瀚无垠的宇宙大世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组织编写的科普读物《星征程:聆听宇宙的解答》,用25篇精彩短文介绍了宇宙的基本概貌、天文学发展历程及研究前沿动向,见证了天文学发展的里程碑,激发我们探索宇宙的好奇心与探求欲。
天文学既古老又现代,古埃及的数学家对天体位置和运动作出了解释:自17世纪伽利略把望远镜指向天空以来,探测技术和理性思维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进入21世纪后,已有十余位科学家凭借10项天文学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本书集合了我国一线的天文学家,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一个“现代”的宇宙。在书中,天文学家们带着问题意识,用专业的学识为我们解答了星系是如何形成的、宇宙的尽头是什么、人类如何探测群星、星际旅行靠什么导航、宇宙的命运将走向何方等前沿话题。我们在仰望星空的同时,也将从书本上获得天文学家最新的科学解答。



——我读梁冬霓散文集《时光倒影》
□ 李春鹏
《时光倒影》是一本呕心沥血之作。全书分为三辑:《乡情咏叹》回望故乡松口古镇,瞩目工作生活之地斗门;《路遇微风》錾刻岁月履迹,于时光流转中感念亲情并记录自己的成长;《书斋浅谈》则对耿立、陈继明等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度的个性化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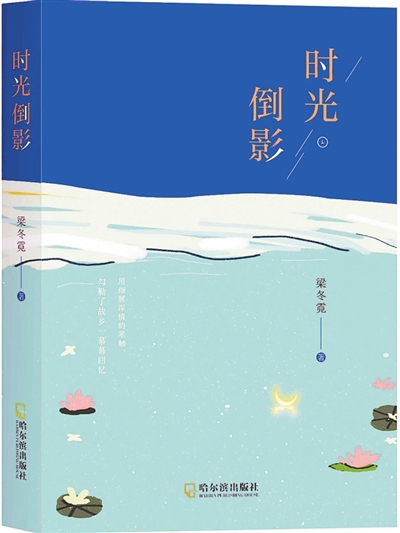
梁冬霓散文最大的特色是对故乡的深情回望。这种回望融入了眷眷深情,也夹杂着淡淡愁绪,凸显了她对故乡变迁发展的深刻思考。辛格说: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根。《时光倒影》确属一部寻根之作。梅州松口镇,是梁冬霓的故乡,是客家人下南洋的首站。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尤其是客家文化)底蕴深厚。梁冬霓深情回望故乡,用诗性的文字,叙写历史的松口和现实的松口,将岁月镌刻在古镇身上的光环与伤痕一并呈现。故乡在变迁,故乡在发展。一些在涌现,一些又在失去。故乡或远或近,远的是自己和故乡的时空间隔,是非物质文化遗存的日渐式微,近的是自己与故乡之间的精神契合与情感纽连。记忆里温暖热闹的裤裆街,似被世人遗忘。松江大酒店与火船码头,繁华之时共沐风月,寂寥之时互诉沧桑。她在沉思中慨叹,在慨叹中沉思,她沉甸甸的述说里,浸透着岁月沧桑的厚重历史感。
《时光倒影》也是一本感念亲情的书。这些表达亲情的文字质朴真切,感人至深。全身布满灰尘,心里却透亮无比的母亲,推着板车把一袋袋水泥搬运到货船上,坚信自己的勤劳一定能够让女儿飞出这片贫穷孤绝之地。《天堂的吻痕》回忆外婆,甜甜的甘蔗、微酸的马齿苋汤、闪着奶油光亮的雪糕、儿时与外婆的绕膝之欢、手摇蒲扇带来的丝丝凉风……“她抱着我,灰白的头发撂在耳根后,在我脸颊边亲了又亲。她说她亲我一下,我就会长得更快,变得更聪明,这个秘密一直珍藏在我心里,而那吻痕里的温柔与甜蜜,更让我今生难以忘怀。”如同电影慢镜头,轻柔细腻,深情温暖。
《时光倒影》记录了作家的自我成长。从求学到工作,身处不同环境,际遇各色人等,历经酸甜苦辣,她深切体味来自身边的感动,“人与人之间……重要的是心里有爱、有光。”她用诗情慧心记录和描述身边的变化,见证斗门的发展。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家的笔触一旦挣脱个人心性的园囿,情感的天地便豁然开朗起来。旧街的嬗变生辉,老薇茶铺质朴的诗意,走向世界的白蕉海鲈,时光深处的水松林,笑意盈盈的白藤湖,天然氧吧黄杨河湿地公园,水墨画一样的莲江村,历经沧桑气韵流动的排山村,宁静温婉无处不飞花的井岸……她从事园林绿化管理工作,与花草树木成了朋友,与土地结下深厚感情,琐碎的工作与平凡的劳动,在她笔下呈现出乐观平和的情绪和恬淡舒适的惬意。“一撮泥土,一滴雨露,一缕花香,都是意料之中的恩赐(《最初的庭院》)”。这些朴素的文字,是她对生活的自然诠释,更是她心境的自然流露。
厚厚的《时光倒影》,馥郁诗意氤氲其间。这种诗意,源于其深刻思想和丰富情感,还源于它凝重纯净的语言之美,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画面感。“风清水阔,白鹭群飞,草逸花闲,廊亭沐霞。”这是简洁洗练的白描。“一江清水静静东流,泊岸的野舟,是古朴岁月的见证者,把沧桑与烟波中的灵动,摆在时光的记忆中。”这是淡雅悠远的水墨。“菉猗堂像一位经历了沧桑巨变的老人,归隐于寻常巷陌、山云涧水,在阳光中瞭望人世繁华,静听松风石泉。”这是朴拙厚重的木刻。“美人蕉鹅黄、粉红、橘红的花朵,交织起一条条彩带,与霞光相映成绚丽的黄昏。”这是灿烂热烈的油画。
这种画面感甚至是质朴的,如同黑白电影。“只记得一个雨天,姐姐被蜈蚣蜇了之后,父亲坐在门口用酒精给她消毒。狭长的巷子上面,两边的灰瓦夹着青色的天空。我坐在姐姐旁边,听她的哭嚷声,然后望望门前的巷道。雨水洗过的青石板路,与姐姐的脸一样,有一种深厚的潮湿(《或远或近的故乡》)”。这种画面感的呈现,是感性的有温度的,用记忆中的童年往事写石板路,既有一份亲切的爱意,又有一种心灵深处被触及的痛感。姐姐的脸与雨水洗过的青石板路,在浓厚的潮湿里共情。
梁冬霓秉持精品意识,凝练并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背后,蕴藏着她执着的匠心。不过,我倒希望她写作时少些刻意,多些随意,只因“散文需要的就是一种散步者的心境”。

——读麦家《人间信》
□ 胡胜盼
“成功也是一种障碍,写多了容易自我重复,我不想再循着套路打转。”有了这份“执念”,或者应该说是清醒,作家麦家努力摆脱掉“中国谍战小说之父”的光环,2019年推出转型之作《人生海海》。5年后,麦家携长篇小说《人间信》再度走入读者视野。故事里没有英雄,没有传奇,有的是每一个普通人在尘世浮沉中为自己争取的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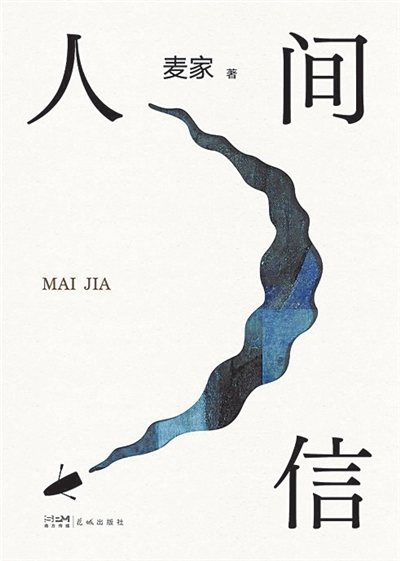
这是一本作家从心底喊出来的书。故事以“我”的经历为引,围绕富春江边双家村的一个家庭展开,讲述了四代人、半个世纪爱与恨的循环往复。小说上卷详写家族史,重点放在奶奶和父亲身上。父亲如何不堪,奶奶如何用残存的家族意志去试图挽回衰颓。意在写“命运的承受”。小说下卷的叙述者“我”走到前台,成为故事推动者。意在写“命运的奋力过招”。如此,两卷交融,点明“命运不仅是承受,还要奋力过招”。小说写出了不被承认的创伤和未被看见的痛苦,诉说着人生的种种不可言说。
麦家是一位擅长讲故事的小说家。读《人间信》,很自然会想到《人生海海》。《人生海海》中,我们能看到作家一如既往地沉迷于故事性与戏剧性,为了“说好中国故事”,甚至有意借鉴古典文学资源完成通俗形式的构造,向古典通俗叙事模式靠拢。然而,《人间信》却又有意淡化了故事性。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更像是一个深邃的哲学命题,一则深沉的寓言故事。不依赖戏剧化情节,麦家转向自己内心深处,寻找精神原乡的意志变得更为坚决,小说“写人生无可避免的命运,写给被过往和缺憾困住的人”也显得更加明确。
生活未及之处,文学终将抵达。《人间信》映射有作家童年的影子。小说的主人公是世人眼中的英雄,却是家人口中的叛徒。他鄙视父亲,揭发父亲,在他眼里,“在父亲的众多绰号中,最为贴切、跟随他一生的,叫作‘潦坯’。潦坯不是逆子,不是混蛋,只是骨头轻,守不住做人做事的底线。潦坯不作恶外人,只作践自己和亲人。”故事隐约写进了麦家的亲身经历,与父亲的交恶,被困在命运之中,和内心幽灵厮杀,童年的不幸让他用一生去治愈,这是一场寻求救赎与自我和解的旅程。
麦家的小说多对女性人物饱含热情。《人间信》亦如是。书中,奶奶、母亲和妹妹,她们本应拥有自己的精彩人生,却不幸被卷入了父亲的困境中。三代女性在男性缺位的情况下,缝补破碎的人间,小说既书写了她们被辜负、被剥夺的一面,也以真挚的笔触向她们如野草般的生命力致敬。麦家一直走不出童年的阴影,做不到对父亲一笑释然。他的八旬老母亲对他说,“你读了那么多书,跑了那么多码头,见了那么多领导,竟然还放不下对过去那些人的恨?”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母亲的睿智和豁达,使得作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也有了一份更真诚的体悟。
《人间信》虽然没有神秘莫测且跌宕起伏的故事,但是作家出色的语言能力却依然得以充分展现。他说寂寞:“寂寞是一把刀,时间是磨刀石,越磨越锋利。”他说爱:“爱一个人,可能会反目,从爱到恨,有时只隔着一句话,一个眼色,一次粗心。”他说做人:“做人要心平,心平才能平安。”他写少女的心扉:“其实什么花都比不得一个少女,少女才是世间独一无二的花,所谓花季少女,豆蔻年华,心里装着朦胧的爱情和向往——尚未开始,就以为会天长地久——像一个蓓蕾一样,随时准备轰轰烈烈去争奇斗艳。”富有理趣,读来意味深长。
和《人生海海》一样,《人间信》书名取得很有意思。这是写给人世间的一封深情家书。一封写给那些在漂泊中挣扎半生,终于能鼓起勇气面对自我的游子的信,也是一封写给那些被社会淹没、被命运辜负的女性的信,更是一封写给每一个在人间困顿浮沉的我们的信。不过,在作者麦家看来,解读“人间信”非常简单,即“信人间”。这种最简洁的解读背后,是作家对生活最长情的告白,对生命最质朴的诠释,对命运最通透的理解。
“哪怕溃败无常,也要尊敬自己。”学会释怀,学会接受,学会在逆境中挖掘内心的力量,在挣扎中重新唤起站起来的勇气。普通人的英雄主义,是坦然直视伤口。如同本书封面的镂空设计,既是心灵的创伤,也是承载着记忆的河流,象征着人生的苦与乐。这是《人间信》给予读者最诗意的柔情馈赠。
——世宾随笔集《目标在寻找它的神枪手》的思想性与文学性
□ 黄金明
当初世宾说在写一部片段体的著作时,我吃了一惊,片段体写作难度特别大。在20世纪,有很多片段体经典,譬如卡夫卡的一些随笔、佩索阿的《不安之书》、齐奥朗的《解体概要》和卡内蒂的《人的疆域》,可能还可以算上格拉克的《首字花饰》、波德里亚的《冷记忆》、罗扎诺夫的《落叶》。这些著作体量都不大,卡内蒂的厚重些,但他写了一辈子。由此,我对世宾肃然起敬,也为他捏着一把冷汗。但他每隔几天就说,又完成了几条。他在广州市天河公园散步时用手机录音,或者在工作间隙一条条地写,毫不费劲、游刃有余,到了挥洒自如、拈之即来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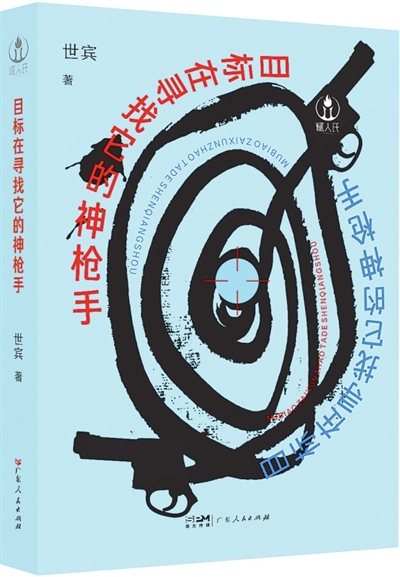
我注意到,书里面有关于“知天命”的感悟。这本书确实是他过了50岁之后写的。作为见证者,我在该书出版之前看过一些——有时他在电脑上还没有改定便邀我看。这部片段体著作的内容极其广泛,包罗万象,贯通了很多不同领域,首先是从诗学扩展到文学,然后是哲学、宗教、心理学、伦理学等。他的写作方式有其独到之处,其中的思辨、言说、驳难,有多声部多层次的书写,且完成得很漂亮。
他对“三生”(生命、生活、人生)的理解很深刻,文本里常有不同声音在对话、辩论、交锋,还有反思和倾听,我特别看重这种反思。譬如第87页最后一条,“就像你说的,我是大灰狼”,他注意到自己天使的属性(亦即神性),还注意到兽性,这个就不简单了。人凭借神性而拓展生命的可能性,并尽量克服兽性,这一条讲得很深刻。书中对两性关系、对爱情的探讨,也让人耳目一新。他对人的心理有深入研究,对现实社会也洞若观火。像第五页最后一条,谈到爱情最大的障碍是占有,他认为必须消除占有或让其消融于爱。
世宾反省的、犹疑的姿态我特别欣赏。相比一些人用无比坚定的语气诉说“真理在握”,我更信任不断证否不断求真的反复质询。世宾说,“我说话的时候语气不连贯,断断续续”,他的反省很深入,也很自觉,他像佩索阿那样,创造出一批“导师”和“同道”教育自己。有朋友说世宾是青年的好导师,我倒是觉得他是一个好学生,在他的身后有一大堆更冷静、更睿智的“世宾”在教育他、鞭策他、完善他。这让我想起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说,能说清楚的就尽量说清楚,说不清楚的就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在讲课时结结巴巴,他头脑里在刹那间有很多话语、思想、事件之类,像洪水一样要冲破他的喉咙,但他想要更精确更清晰地说出来,就需字斟句酌,语速缓慢,谨慎小心。我觉得世宾有时候也是这样,这样的文本更可靠,因为他并不自诩真理,反有自我质疑的成分。
有一条是我特别喜欢的,第91页最后一条,“两个人隔着几百公里的河山聊天,双方都是独自一人,喝茶,相互间谈论一些深奥的事物”。他说“这个意象绝对是现代的,在古代是没有的”。两个独自喝茶的人又独立又联结,有散文的笔调,有诗性的话语,还有一种镜头般的画面感,生动形象,这种表达就更有文学性了,不仅仅是言说,还有叙述、描写和抒情,有不同的声音在此交融,有一种复调性的效果。写思想随笔要有文学性,这才算是由思想入而从随笔出。

□ 龙建雄
最近看“唐宋八大家”,娓娓道来的文字极易让大脑里塞满“江湖”的刀光剑影,把我原本平静的思绪搅得乱成一团浆糊。故事情节和生平往事其实不复杂,但他们的诗词歌赋有如天上飘来一朵朵白云,太多太多的好词好句眩晕了记忆的“水平面”,不煮成“一锅粥”实在是难。平时基本上不看电视的我,看央视的视频又是另外一番情形,里面煽情的场面让人控制不住自己,极易潸然泪下。
发现一个小巧合:叫“梦得”的人值得信任,20年以上的挚友更是值得一生深交。
唐朝的柳宗元有个朋友叫梦得,他便是鼎鼎有名的刘禹锡、字梦得,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那位。刘梦得与柳宗元相识于793年同中进士的开榜日,有“城里考生”质疑刘禹锡有何本事位列榜中第五名,第四名的柳宗元勇敢站出来相救,一席话语把人家说得灰溜溜而走。柳宗元的个人魅力和政治远见很快让刘禹锡膜拜,二人结为兄弟,刘长于柳一岁为兄,柳为贤弟。805年“永贞革新”失败后,作为中坚力量的柳宗元被贬湖南永州、刘禹锡被贬湖南朗州(今常德),均任州府司马;其间,二人不间断保持书信联系,互相鼓励,分享彼此的生活和情感。
814年,柳宗元和刘禹锡奉诏回京,次年三月又分别调任远离朝廷的柳州刺史和连州刺史,两人一同从长安出发,至衡阳分路而行。面对古道风烟,前程茫茫,二人赠诗惜别,柳宗元作《重别梦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不幸的是,819年柳宗元在广西柳州任上郁郁而终,他将自己所有亲人和毕生诗文全部交托给刘禹锡,刘禹锡穷尽后半生之力完成《柳宗元集》,并把平生所学尽数传给了柳宗元之子。“二十年来万事同”“晚岁当为邻舍翁”,把这14个字在脑海里闪过一念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该是何等幸甚至哉!
北宋的苏轼有个朋友也叫梦得,大名马正卿、字梦得,他和苏轼同年同月生,生日只差八天。马梦得原来在京城太学里做官,“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因为性情太耿直不招人喜欢,学生不喜欢他,也不受上司的信任,后来干脆就不做官。马梦得跟苏轼很聊得来,一直追随,既是苏的铁杆粉丝,又是他的管家,还是他的随从。苏轼被贬黄州,老友马梦得后脚随到。万幸有这个马梦得,才会有后世响亮千古的“东坡”。苏轼在黄州把仅有的钱用完之后,眼看着就要面对无米之炊的窘境,追随他的马梦得动用各种关系去官府为苏轼批得了一块荒地,让苏开始了自给自足、自耕自乐的日子,也让苏成为了黄州一个远近闻名的“农民”,正是这接地气的身份,才成就了如今被我们宠爱千年的“苏东坡”。
苏轼在黄州写《东坡八首》,其中有一首写道:“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马梦得曾经盼着偶像飞黄腾达,梦想有朝一日分点钱给他买个山头,但苏轼一贬再贬,一直毫无大富大贵的迹象,马梦得依然义无反顾地帮衬苏轼一家渡过众多难关。苏轼笑话马梦得这个铁杆老友跟错了“老大”,说“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无论从苏轼的角度,还是从我们今人的立场来看,得此一友,夫复何求?
入心感怀,这兴许是一件好事。读到千年前柳宗元、苏轼的“老友记”,免不了也感叹自己身边有那么几位友谊了二三十年的老朋友。他们从来没有计较过我的出身,也从来没有嫌弃过我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那几个老友,一旦我有需要,他们再忙也愿意陪,再穷也愿意帮,细想之下,他们除了与我分享快乐,似乎从来没有所求之事来烦扰于我。因为感同身受,所以“梦得老友”感动了我自己这件事也就不足为奇。
打趣来说,行事干脆的朋友有很多,待友纯粹的朋友难能可贵,叫“梦得”的朋友则物以稀为贵。得之,幸之。
解读深邃的宇宙之谜
□ 刘昌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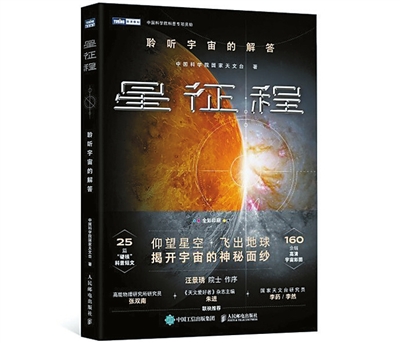
千百年来,深邃迷人的星空总是吸引着人们探求的目光,浩瀚无垠的宇宙大世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组织编写的科普读物《星征程:聆听宇宙的解答》,用25篇精彩短文介绍了宇宙的基本概貌、天文学发展历程及研究前沿动向,见证了天文学发展的里程碑,激发我们探索宇宙的好奇心与探求欲。
天文学既古老又现代,古埃及的数学家对天体位置和运动作出了解释:自17世纪伽利略把望远镜指向天空以来,探测技术和理性思维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进入21世纪后,已有十余位科学家凭借10项天文学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本书集合了我国一线的天文学家,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一个“现代”的宇宙。在书中,天文学家们带着问题意识,用专业的学识为我们解答了星系是如何形成的、宇宙的尽头是什么、人类如何探测群星、星际旅行靠什么导航、宇宙的命运将走向何方等前沿话题。我们在仰望星空的同时,也将从书本上获得天文学家最新的科学解答。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