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雅玲
2024-10-28 02:15
刘雅玲
2024-10-28 0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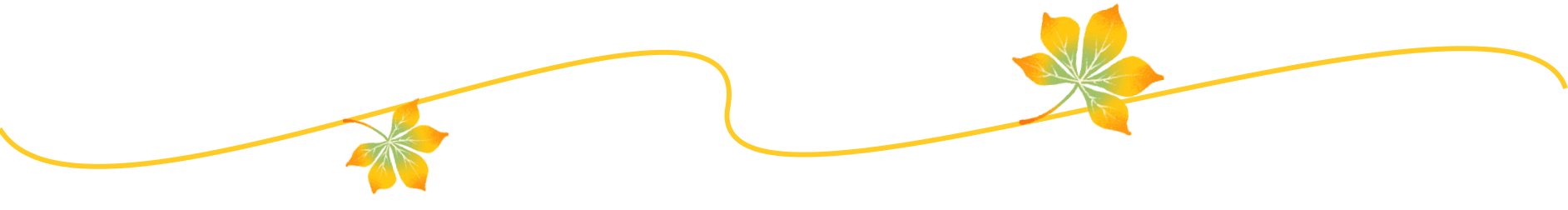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实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进程。三星堆是如何从“沉睡数千年”到“一醒惊天下”的?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中有着怎样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三星堆还有哪些未解之谜?
10月27日,珠海市工人文化宫报告厅座无虚席、掌声热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研究院学术副院长、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做客2024年第八期珠海大讲堂,以《沉睡数千年 数醒惊天下——从三星堆看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为题,深入解读三星堆文化的奥秘,带领大家追溯古蜀文明的辉煌。

三星堆如何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四川古称‘蜀’。四川盆地西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古老的蜀国,蜀国曾参加过武王伐纣之战。‘蜀’这一名称曾多次出现于殷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当中。”讲座伊始,雷雨通过“蜀”字的历史演变,引出三星堆与古蜀文明的密切关系。
他通过图文介绍了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秦篆中的蜀字(目虫)形象:一个上有大眼睛,下有蜷曲身体的类似虫子形状的象形文字。“我们在三星堆1号坑和2号坑中发现了大量单独用青铜做的眼睛,而且大量青铜人头像和人面具的眼球也和正常人不一样,做得非常突出。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的三星堆人患有甲亢,所以双眼突出,不过目前很难开展DNA和病理学的考古研究,所以关于这一解读并没有证据。”雷雨讲解道。
不过,“蜀”字上半部像只眼睛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雷雨分析,成都平原日照非常少,可能三千多年前成都平原的日照与现在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古蜀人对太阳、对眼睛、对光明有特别的感情。
关于古蜀国的历史,在中国的正史中几乎不见踪影,仅见于少量地方志,但都极其简略,且多带有神话和传说性质。根据有限的文献记载,古蜀国的五个王朝分别是: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蜀地从此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
“要正确了解古蜀国的历史,只能依赖于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讲座中,雷雨提到,近百年来,四川盆地西部发现、发掘了包括什邡桂园桥遗址、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成都商业街船棺墓地等在内的一系列距今5100-2200年的属于古蜀文明的遗址和墓葬。
众多古蜀文明遗存中,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使得扑朔迷离的早期古蜀文明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

雷雨介绍道,三星堆首次发现是在1927年,广汉农民燕道成在月亮湾燕家院子门前掏沟时发现一坑400余件精美的玉石器,部分玉器流散到古董市场,“广汉玉器”声名鹊起。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在馆长葛维汉的带领下,在燕家院子及其附近进行了三星堆历史上的首次发掘,初步命名“广汉文化”。
上世纪50-70年代,四川省多家考古机构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并对月亮湾台地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认识到三星堆遗址应为古蜀文化遗址,并可能是古蜀国一个极为重要的中心都邑性遗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三星堆遗址持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得以正式命名。
“目前我们已基本掌握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堆积和保存状况,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先秦时代的遗址,核心区域为3.6平方公里由夯土城墙合围起来的三星堆古城。”雷雨介绍。
他谈到,三星堆遗址主体文化堆积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夏、商、西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但三星堆文化的鼎盛时期距今3000年左右,上限可以到距今4800年。到目前为止,三星堆出土的遗物有陶、石、玉、铜、金、象牙、海贝、丝绸等,数量逾5万件。
1986年,砖厂工人取土施工时偶然发现了1号坑,坑内有一些青铜器,考古队马上进行抢救式的考古发掘,发现两个距今3000年左右的“祭祀坑”,出土一批前所未见、造型奇特的器物,埋藏方式十分独特,三星堆由此名扬天下。
其中,一、二号坑的器物,除部分中原地区商时期常见的玉器、青铜礼(容)器外,很多是中国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青铜群像(人像、神像、面具等)、神树、神坛、太阳形器、眼睛(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构成了三星堆文化中最为辉煌同时又是最为独特的部分。
三星堆文物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具有超高辨识度,拥有全世界青铜时代最多的青铜雕像,最多的贴金面青铜人像,最多最大的青铜面具,最多的象牙以及最高的青铜神树与单体人像等“世界之最”。
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以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人像、神像、半人半神像、祭祀用具等为造型主体,对祭司、巫师等神职人员的形象着墨颇多。雷雨认为,与中原商文化相比,三星堆文化的神巫和神权色彩更为浓郁和突出,反映出古蜀国独特的权力架构,神职人员的地位非常高。

总的来讲,三星堆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物当属陶器和石器,这些最常见的日常用品绝大多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文化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又深深地烙上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印迹,体现了古蜀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人像、神像为青铜器造型主体以及崇尚黄金的传统,不是那个时期华夏文明的核心特征,可能跟域外的某种文化因素或审美情趣有所关联,是古蜀人创新能力的体现。
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祭祀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成果。陆续发现了三、四、五、六、七、八等6个新坑,面积从3.5-19平方米不等。发掘了巨型青铜人面具、巨型青铜兽面具、青铜顶尊跪坐人像、青铜大立人、金面具、金鸟形饰,以及神似诸葛亮的青铜高髻(冠)人头像、神似奥特曼造型的青铜小立人等。这些巧夺天工的祭祀神器,在神巫文化背景的映衬下,极富艺术张力,尽显造化之妙和创造之美,在造型艺术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曾经在一次考察中提出这样的观点:“鉴于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如果没有对古蜀文明的深入研究,便不能够构成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
对此,雷雨这样分析:李学勤先生强调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众多区域性青铜文明中最为独特的一支,古蜀文明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文明丰富性、多样性的最好表达。
“三星堆虽然很独特,但仍然很中国。”雷雨认为,几个祭祀坑里面出土了较多与人们对中国文明的固有认知有很大出入的器物,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仍然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雷雨认为,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三星堆文化中以陶器和石器为代表的土著因素自始至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几大祭祀坑出土了不少常见于遗址其它区域的蜀式陶器,说明几大祭祀坑与遗址同属一体。
其次,虽然几大祭祀坑里面的不少高等级器物显示古蜀文明有可能与更遥远的地区发生了交流与往来,但目前的确还找不到这种联系的直接证据。可以这样认为,来自黄河流域的青铜铸造技术、青铜礼器制度、尚玉传统以及可能源自于其它文明的圆雕艺术和尚金习俗,在四川盆地这个独特的地理单元中产生了碰撞和交融,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区域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一套看似特立独行的东西仍然可以视为地域文化的范畴。
此外,即便那些看起来最独特怪异的青铜器,其铸造技术和合金比例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青铜器亦属同一系统,器物身上还有很多典型的中国元素和符号,如跪坐人像(祭司)手里拿的牙璋、跪坐人像(祭司)头上顶的不同形制的尊、1号大神树上自天而降的飞龙、长袍上的龙纹、神殿上的龙纹等。
“三星堆的发现与发掘,从根本上改变了世人对古蜀文明发展水平的传统认识。”雷雨认为,就文明的发达程度而言,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虽然没有达到黄河流域夏、商、周文明的高度,但在艺术的想象力和创新性、大型复杂铜器的铸造、黄金的制作与利用等方面,则远远超过了当时的黄河流域。独特瑰丽的古蜀文明昭示了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实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进程。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文理学院教授武家璧:
作为第一线的考古工作者,您怎样看待三星堆遗存和古史记载传说之间的关系?
雷雨:
中国考古和国外考古有很大的不同,有自己的独家优势。我们有庞大浩瀚的历史文献,历史时期的考古可以相互印证。但在没有正式记载的史前时期,考古人也不能把神话性质很高的传说置之不理。很多人相信,《山海经》的作者一定了解过三星堆或古蜀文明,所以有些片段描写才能如此契合。我认为,不应该把考古发现和历史传说、神话传说严重对立起来,还是要合理加以利用,当然这个度要把握,发表材料时不一定过度地解读。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武汉大学考古学博士赵春光:
三星堆出土了很多玉器,其中包括牙璋,请您介绍一下三星堆牙璋与离我们较近的珠三角和越南牙璋之间的关系,是否体现了古代人的迁徙和文化交流?
雷雨:
牙璋的确是华夏文明的核心特征,能够出土这些器物的地方一定可以建立起一个共同的文化圈,说明他们的价值观或审美是一致的。以前认为三星堆的象牙都是本地产的,后来做了溯源,发现相当一部分象牙来自云南及越南、缅甸、斯里兰卡等地。这都体现了中华文明核心元素或价值观的一种趋同,应该是文化传播或人群迁徙和贸易交流才能实现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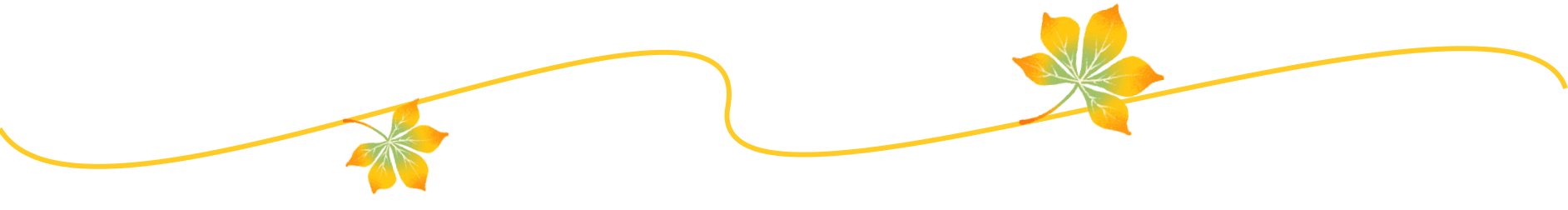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实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进程。三星堆是如何从“沉睡数千年”到“一醒惊天下”的?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中有着怎样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三星堆还有哪些未解之谜?
10月27日,珠海市工人文化宫报告厅座无虚席、掌声热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研究院学术副院长、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做客2024年第八期珠海大讲堂,以《沉睡数千年 数醒惊天下——从三星堆看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为题,深入解读三星堆文化的奥秘,带领大家追溯古蜀文明的辉煌。

三星堆如何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四川古称‘蜀’。四川盆地西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古老的蜀国,蜀国曾参加过武王伐纣之战。‘蜀’这一名称曾多次出现于殷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当中。”讲座伊始,雷雨通过“蜀”字的历史演变,引出三星堆与古蜀文明的密切关系。
他通过图文介绍了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秦篆中的蜀字(目虫)形象:一个上有大眼睛,下有蜷曲身体的类似虫子形状的象形文字。“我们在三星堆1号坑和2号坑中发现了大量单独用青铜做的眼睛,而且大量青铜人头像和人面具的眼球也和正常人不一样,做得非常突出。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的三星堆人患有甲亢,所以双眼突出,不过目前很难开展DNA和病理学的考古研究,所以关于这一解读并没有证据。”雷雨讲解道。
不过,“蜀”字上半部像只眼睛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雷雨分析,成都平原日照非常少,可能三千多年前成都平原的日照与现在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古蜀人对太阳、对眼睛、对光明有特别的感情。
关于古蜀国的历史,在中国的正史中几乎不见踪影,仅见于少量地方志,但都极其简略,且多带有神话和传说性质。根据有限的文献记载,古蜀国的五个王朝分别是: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蜀地从此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
“要正确了解古蜀国的历史,只能依赖于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讲座中,雷雨提到,近百年来,四川盆地西部发现、发掘了包括什邡桂园桥遗址、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成都商业街船棺墓地等在内的一系列距今5100-2200年的属于古蜀文明的遗址和墓葬。
众多古蜀文明遗存中,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使得扑朔迷离的早期古蜀文明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

雷雨介绍道,三星堆首次发现是在1927年,广汉农民燕道成在月亮湾燕家院子门前掏沟时发现一坑400余件精美的玉石器,部分玉器流散到古董市场,“广汉玉器”声名鹊起。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在馆长葛维汉的带领下,在燕家院子及其附近进行了三星堆历史上的首次发掘,初步命名“广汉文化”。
上世纪50-70年代,四川省多家考古机构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并对月亮湾台地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认识到三星堆遗址应为古蜀文化遗址,并可能是古蜀国一个极为重要的中心都邑性遗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三星堆遗址持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得以正式命名。
“目前我们已基本掌握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堆积和保存状况,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先秦时代的遗址,核心区域为3.6平方公里由夯土城墙合围起来的三星堆古城。”雷雨介绍。
他谈到,三星堆遗址主体文化堆积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夏、商、西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但三星堆文化的鼎盛时期距今3000年左右,上限可以到距今4800年。到目前为止,三星堆出土的遗物有陶、石、玉、铜、金、象牙、海贝、丝绸等,数量逾5万件。
1986年,砖厂工人取土施工时偶然发现了1号坑,坑内有一些青铜器,考古队马上进行抢救式的考古发掘,发现两个距今3000年左右的“祭祀坑”,出土一批前所未见、造型奇特的器物,埋藏方式十分独特,三星堆由此名扬天下。
其中,一、二号坑的器物,除部分中原地区商时期常见的玉器、青铜礼(容)器外,很多是中国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青铜群像(人像、神像、面具等)、神树、神坛、太阳形器、眼睛(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构成了三星堆文化中最为辉煌同时又是最为独特的部分。
三星堆文物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具有超高辨识度,拥有全世界青铜时代最多的青铜雕像,最多的贴金面青铜人像,最多最大的青铜面具,最多的象牙以及最高的青铜神树与单体人像等“世界之最”。
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以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人像、神像、半人半神像、祭祀用具等为造型主体,对祭司、巫师等神职人员的形象着墨颇多。雷雨认为,与中原商文化相比,三星堆文化的神巫和神权色彩更为浓郁和突出,反映出古蜀国独特的权力架构,神职人员的地位非常高。

总的来讲,三星堆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物当属陶器和石器,这些最常见的日常用品绝大多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文化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又深深地烙上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印迹,体现了古蜀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人像、神像为青铜器造型主体以及崇尚黄金的传统,不是那个时期华夏文明的核心特征,可能跟域外的某种文化因素或审美情趣有所关联,是古蜀人创新能力的体现。
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祭祀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成果。陆续发现了三、四、五、六、七、八等6个新坑,面积从3.5-19平方米不等。发掘了巨型青铜人面具、巨型青铜兽面具、青铜顶尊跪坐人像、青铜大立人、金面具、金鸟形饰,以及神似诸葛亮的青铜高髻(冠)人头像、神似奥特曼造型的青铜小立人等。这些巧夺天工的祭祀神器,在神巫文化背景的映衬下,极富艺术张力,尽显造化之妙和创造之美,在造型艺术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曾经在一次考察中提出这样的观点:“鉴于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如果没有对古蜀文明的深入研究,便不能够构成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
对此,雷雨这样分析:李学勤先生强调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众多区域性青铜文明中最为独特的一支,古蜀文明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文明丰富性、多样性的最好表达。
“三星堆虽然很独特,但仍然很中国。”雷雨认为,几个祭祀坑里面出土了较多与人们对中国文明的固有认知有很大出入的器物,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仍然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雷雨认为,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三星堆文化中以陶器和石器为代表的土著因素自始至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几大祭祀坑出土了不少常见于遗址其它区域的蜀式陶器,说明几大祭祀坑与遗址同属一体。
其次,虽然几大祭祀坑里面的不少高等级器物显示古蜀文明有可能与更遥远的地区发生了交流与往来,但目前的确还找不到这种联系的直接证据。可以这样认为,来自黄河流域的青铜铸造技术、青铜礼器制度、尚玉传统以及可能源自于其它文明的圆雕艺术和尚金习俗,在四川盆地这个独特的地理单元中产生了碰撞和交融,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区域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一套看似特立独行的东西仍然可以视为地域文化的范畴。
此外,即便那些看起来最独特怪异的青铜器,其铸造技术和合金比例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青铜器亦属同一系统,器物身上还有很多典型的中国元素和符号,如跪坐人像(祭司)手里拿的牙璋、跪坐人像(祭司)头上顶的不同形制的尊、1号大神树上自天而降的飞龙、长袍上的龙纹、神殿上的龙纹等。
“三星堆的发现与发掘,从根本上改变了世人对古蜀文明发展水平的传统认识。”雷雨认为,就文明的发达程度而言,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虽然没有达到黄河流域夏、商、周文明的高度,但在艺术的想象力和创新性、大型复杂铜器的铸造、黄金的制作与利用等方面,则远远超过了当时的黄河流域。独特瑰丽的古蜀文明昭示了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实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进程。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文理学院教授武家璧:
作为第一线的考古工作者,您怎样看待三星堆遗存和古史记载传说之间的关系?
雷雨:
中国考古和国外考古有很大的不同,有自己的独家优势。我们有庞大浩瀚的历史文献,历史时期的考古可以相互印证。但在没有正式记载的史前时期,考古人也不能把神话性质很高的传说置之不理。很多人相信,《山海经》的作者一定了解过三星堆或古蜀文明,所以有些片段描写才能如此契合。我认为,不应该把考古发现和历史传说、神话传说严重对立起来,还是要合理加以利用,当然这个度要把握,发表材料时不一定过度地解读。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武汉大学考古学博士赵春光:
三星堆出土了很多玉器,其中包括牙璋,请您介绍一下三星堆牙璋与离我们较近的珠三角和越南牙璋之间的关系,是否体现了古代人的迁徙和文化交流?
雷雨:
牙璋的确是华夏文明的核心特征,能够出土这些器物的地方一定可以建立起一个共同的文化圈,说明他们的价值观或审美是一致的。以前认为三星堆的象牙都是本地产的,后来做了溯源,发现相当一部分象牙来自云南及越南、缅甸、斯里兰卡等地。这都体现了中华文明核心元素或价值观的一种趋同,应该是文化传播或人群迁徙和贸易交流才能实现的现象。


-我已经到底线啦-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