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白看松(上)
□ 陈先发
越野吉普的引擎轰地一声低低吼起,我们开始攀向长白山主峰。一幅天然的山水图轴,在窗玻璃中渐次展开了:白得耀眼的,是不规则披覆山体、填满千沟万壑的冰雪;灰白平匀的,是午后昏沉欲雪的低空。浅黑中掺进了褐赤、灰青的,是成片绵延又难以辨清树种的林木;深黑犹如泼墨的,是裸露的山体或是避风处的大片砂岩……南方来的两个朋友显然兴奋了点,眼贴在窗玻璃上,时不时发出几声叹息。
而我此行,心里埋伏着另外一个执念:看松。
正是隆冬时节。远景中,墨迹般嵌入山色的各种林木。我想,主体一定是松树。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迟凋,乃至不凋,理所当然地契合了人对生命力生生不息的渴望。以松柏为喻,孔子又发了一系列的感慨:“君子之道,如松之荣。君子之德,如松之茂”“松柏之茂,其贞也特”等,直让人觉得松的本体已被掏空了,只剩下一个长髯端肃的老者,枯坐在那里喃喃自语。诗人就轻松了许多,他们写松,写的多是些直觉与姿态。以前读杜荀鹤《题唐兴寺小松》,由松树“虽小天然别,难与众木同”入手,结尾来了句狠话,“如今未看,须是霜雪中”。把没入冰雪境界的松之美,一笔全给废掉了。李商隐写松,“无雪试幽姿”,憾则憾矣,一个幽字,毕竟存了份神秘的愉快。仿佛松与雪之间,真的潜藏着一种诗的密码。进山时,我在脑中照着王维枯雪寒林的笔意,草草勾勒了一幅老松倚雪的画样:蜷曲虬枝黝黑苍郁,新雪霎亮地凝结在松肤之上……及至眼前,长白山松,却全然不是这般模样。
其实,我知道我所期待的,也根本不必是这般模样。
小时候逃学,晴好暖和的春秋天,常常溜到学校后山腰的一块空地上睡大觉。这是一块被巨松守护的荫庇之地。这棵巨松,蜷起一抱多粗又布满瘤结的身子,斜伸着,探向岩下深深的溪谷。除了夏季涨洪水时,这条溪谷平时是干涸的。松冠最是好看,发怒时一样张得很开,松针又密,下小雨时,松下地面也是干干的。傍晚时看,松冠像一张拍向谷中的巨手,山下一两里外,也看得清清楚楚。这块空地,准确地说,是巨型山岩的一面,微微有点坡度,雨水将上面的积土腐叶,冲刷得干干净净。紧靠着岩壁的空地上,有几截一尺多高的残墙和几堆废砖瓦。后来我听说,这是一座小土地庙的遗址。松树,本应是有两棵吧,在废庙址右侧,还有一截粗而黑的树墩。从根部看,这两棵巨松是从石缝中长出来的,除了点烂叶子沤成的腐殖土外,再无别的养料,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月,才生成如此的庞然大物。无数个暖洋洋的下午,我躺在厚厚软软的松针上,用黄帆布书包作枕头,心中一无所挂地沉沉睡去。树下,安静得仿佛松针往下掉时,刺破空气之声也清晰可闻。好长一个懒觉啊!有时一激灵,被凉风吹醒,睁眼一看,哦,快到傍晚了。松下渐渐起了些潮气。过不多久,放学钟声就要从前山校区那边,悠扬传来。夏天放假时,我闯了祸,一般也要藏到这棵松树下来,躲避父母的棍棒教育。那几年,攀向山腰这块空地的,有好长一截荆棘小径,只有小孩子抱着脑袋,才能从缝隙中钻过来,大人们几乎发现不了。
当年家中有个远房亲戚,在邻村做木匠,他是一个你得提着三斤鲜猪肉上门,才请得动的上好木匠。小时去他家玩儿,总觉得膝盖中酸酸的,迈不开步子,说不出的一种紧张感。别人家的门前,种些花花草草,栀子茉莉的。他家门前偌大空场子,锤得平平整整,却栽着六七棵松树。这些松树虬劲多枝,松冠繁茂如盖。从远处看,松树伴着三间茅草屋子,真有点野寺的味道。这个亲戚是鳏夫,四十几岁时,得了肺结核病,也不去医院治疗,不知从哪里弄来个偏方子,照着煎中药。几棵松间,常年就飘荡着怪怪的中草药气味。折腾了几年,也不见好,最后索性就失踪了。1983年夏季洪水,老屋子的三面墙都垮掉了,几件本来好模好样的旧家具,砸了个稀巴烂。村里人就说,这松,栽得不好。家乡一带,素有“前不栽松、桑,后不种梨、柳”的说法,大家也都讲究这老规矩。十里八乡的,唯独这个至今杳无踪迹的亲戚,曾破了这个例,孤例。
说来也怪,这几棵松树,清清爽爽映在我脑神经中。这么多年,像新栽的一样。
我想起一个词来:松冢。
去年秋末,我去过一次那个老屋址。松树没了,废墟也没了。不知是谁建了一排彩钢瓦的板房商铺,卖农药化肥。我坐在门前,发了会儿呆。心里有些失落。那几棵消失的老松,原来只是几朵徒具松树面貌的过眼烟云。
没料到,在我心里挂得黄泛的两幅老松图,来长白山的第一晚,就被颠覆了。那天好一路颠簸,傍晚才到山脚下。刚住下,还没来得及烧水煮茶,就被几个急性子的朋友拽到了宾馆门口,要在松林中合影。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美人松”!抓紧按下快门吧,趁着这几抹夕照犹存!我们紧裹着从前台租来的笨重军大衣,顶着割脸的北风,站在相机前哆嗦着。合影罢了,我猛跺了一通脚,把身子弄得热乎了点,才去松林里逛了一大圈。
这松,哪里有什么虬干曲枝?我在南方见惯了游龙探海、绝壁倒挂这一类奇状异形,这松却一律地身形颀长,通直挺拔,一股子少女向上跳脱的苗条劲儿。哪里有什么松皮苍劲如铁?我喜欢的松,多是体肤如斧劈火燎过,沉郁蓊苍,有苏轼所言“不到千般恨不消”的沧桑之味。这松的皮色,却分明是灰白、棕黄中透着股子脂粉气。此刻,夕光从林梢透入,树身犹镀微金,在林间白雪的映衬下,倍显恬静婀娜,一如刚刚出浴的佳人。杨万里曾讲松树“一生清苦不敷腴”,这松,冠盖饱满略呈锥形,美如盘发,典雅端方,哪里有一丁点身出寒门的清苦味儿?
陈先发 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文联主席,安徽省作协主席。1967年10月生于安徽桐城,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主要著作有诗集《写碑之心》《九章》《陈先发诗选》,随笔集《黑池坝笔记》(系列)、长篇小说《拉魂腔》等二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十月文学奖等国内外数十种文学奖项。

小说与人性休戚相关
□ 泊 心
潘军是一个传奇。
作为著名作家,他是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独白与手势》《风》《死刑报告》堪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为剧作家,他的话剧《合同婚姻》《霸王歌行》分别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演,并在世界上十几个国家巡演,获得“世界戏剧节”优秀剧目奖;作为画家,他出版了三卷本大型画册《泊心堂墨意》,并在多地举办了个人画展;作为影视导演,他自编自导的电视剧《五号特工组》《虎口拔牙》《分界线》风靡全国;现在,潘军又推出了独特的小说文本“春秋战国秦汉三部曲”——《春秋乱》。
2000年,潘军在《花城》上发表了中篇小说《重瞳——霸王自叙》,立即被海内外多家报刊转载,并位列“中国当代小说排行榜榜首”。潘军是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有批评家说,正是因为一部《重瞳》的问世,才使得中国“先锋小说”有了一个漂亮的结尾。也有人认为,《重瞳》既是“先锋小说”的落幕之作,同时又是“新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时隔24年的今天,新年伊始,两家著名的文学期刊《作家》与《天涯》,都在第一期以重要位置推出了他的两部中篇小说——《刺秦考》和《与程婴书》,从当年的“楚汉争锋”说到“赵氏孤儿”和“荆轲刺秦”,构成了“春秋战国秦汉三部曲”。最近,作者又以“作家手记”的方式将其连为一体,取名《春秋乱》,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据悉,安徽作家协会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将在合肥联合举行这部作品的首发式和研讨会。
潘军认为,某种意义上,读者可以认为这是一部由三部中篇构成的一部长篇,这样的小说文本或许有点新意,虽然表现手法和叙事风格有所不同,但都是重新解构,都是在《史记》《左传》《资治通鉴》这样的历史典籍中,寻找出一个重新解读的可能性,都是一次颠覆性的写作,从而使这三个历史时期发生的家喻户晓的故事获得了新意。
但凡家喻户晓的故事皆是耳熟能详,颠覆肯定是不容易的。潘军说,如果没有新的认知,不作出新的独立的判断,就没有意思了。我一直强调的是,认知高于表现。这种意识贯穿了我的全部创作生活,无论是写作还是绘画。比如《赵氏孤儿》,如果依旧去写程婴拿自己的亲生骨肉去换取所谓忠良之后,这种价值取向显然值得商榷。荆轲刺秦也是如此,司马迁构想的“图穷匕见”的情形不可能发生,荆轲连一根针也无法带进秦王宫的,怎么刺秦?像这样的支点如果都站不住脚,重新解读就是一句空话。作为一名出色的剑客,荆轲只要接近并瞬间控制了秦王,目的即已达成。杀一个人与证明能杀一个人,对于剑客,境界高下立判。荆轲不可能成为燕太子丹把玩的又一枚棋子,他要完成的只是自己的“一意”——证明自己,圆了英雄梦。显然他没有从肉体上消灭秦王,他不屑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精神上彻底挫败了嬴政。
《重瞳——霸王自叙》《与程婴书》和《刺秦考》分别用了“我”“你”“他”三个讲述视角,很像一个刻意为之的游戏。对此,潘军解释说:他写小说,会自觉地先去考虑“怎么写”?不同的题材,应该有不同的写法,得先找到一个最合适也最舒服的叙事方式。他认为小说就是通过文字造型的艺术,某种意义上,现代小说就是对形式的发现和确立。《重瞳——霸王自叙》采用了第一人称,开篇就是“我叫项羽”,这是项羽亡灵的视角,能从两千年前看到眼下。潘军说,我还是信奉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强调的还是一种个人对历史的认知。所谓捕风捉影,即是在扑朔迷离的历史缝隙中去寻求另一种解读的可能,或者依靠想象来重构这个支离破碎的故事。至于真实,那只能存在于我的内心,《春秋乱》是一部充满悲悯情怀的小说文本。潘军说,悲悯应该成为一个作家最炽热充沛的情怀,我希望我的小说与人性的复杂多样休戚相关,折射出人道主义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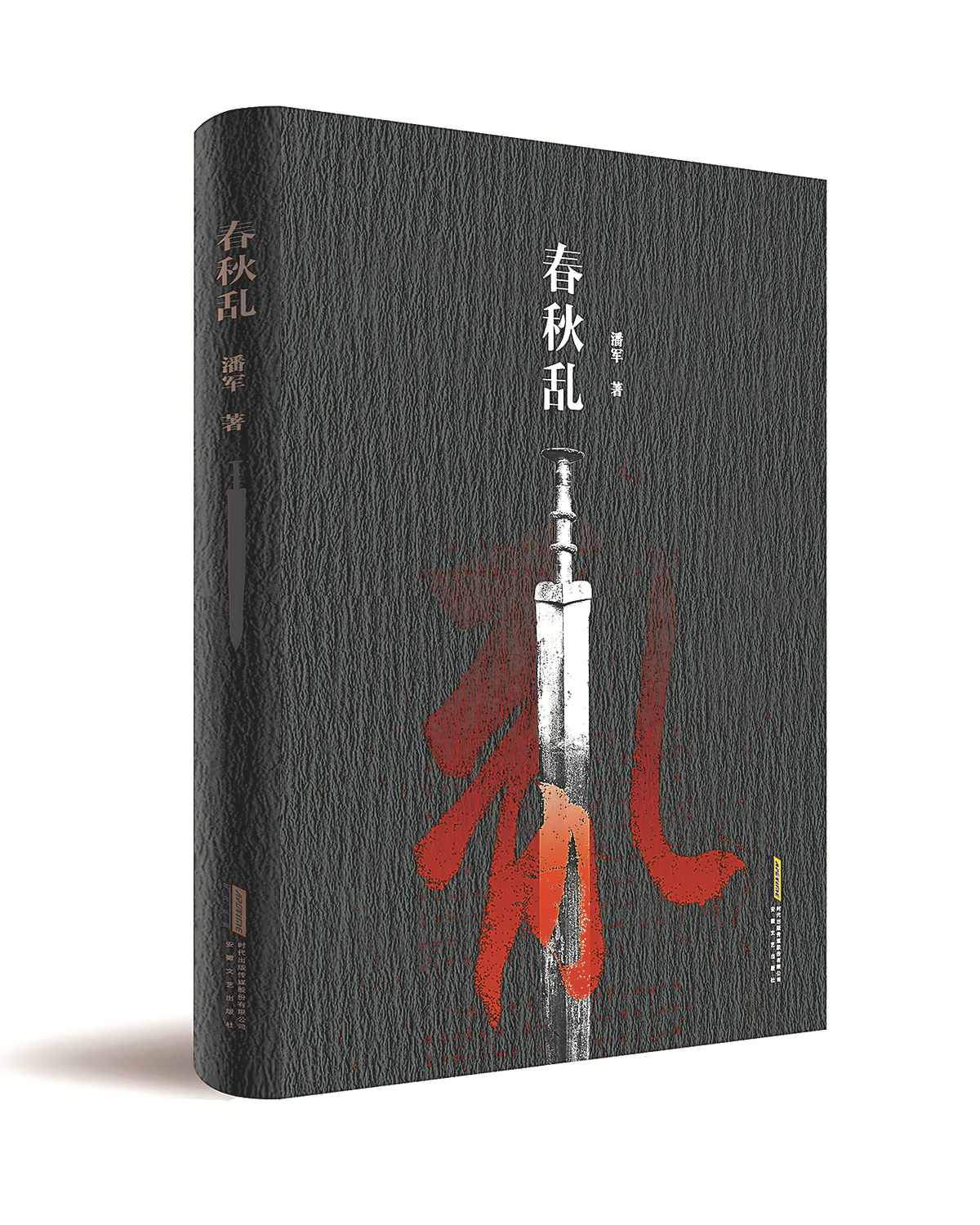
行走的风景(组诗)
□ 刘福申
在刘河湾坐看风生水起
长长的春风刮过
牡丹花开
千年花朵
在水的光影中盛开
有水的地方
一定会有风的长歌
有风的地方
一定会有水的浩气
要不风水这个词
怎么会亲密无间地
在刘河湾这片醒着的土地上
千变万幻
风声水声
现代化的交响
乡愁被一朝又一朝的音符打上烙印
光阴被一朝又一朝的音符洗亮
在这里落脚的天鹅
是有眼光的
以贴近土地的方式
爱着这里
风 刘河湾的语言
水 刘河湾的翅膀
一只比雪还白的鸽子
一把比山还重的铡刀
一包比云彩还轻的茱萸叶儿
一杯比玉露还浓的菊花酒
千年不老的富贵牡丹
铺成一条彩色的路
天高地远
在物竞天择的土地追逐
追逐得风生水起
霜降
天气,一定是被掌控的
就像我们生活中的电灯开关一样
望着一地的白
我笨拙地想
是不是缺钙的人间
更需要补充一下盐
上架的黄烟
叶片上的纹路
一点点加深着颜色
此刻,而我的纠结不在于此
对于霜降的降字,这个
转动季节的动词
在秋风中演奏着命运的交响
在枯荣的交替中
死亡与新生一样伟大
大雪
夜色里的明亮
只因一场大雪
无法停止的咳嗽
覆盖地上万物
红泥小火炉的火焰
伸着任性的舌头
温暖地调侃着
蝴蝶一路风情的姿式
时光沉默的智者
在薄情的世界里变着魔术
把浮躁的河流
切换成一块石头
那些口出真理的哲学家
盲人一样想着女人的姿色
白 无疑成为
掩埋黑的真相的罪人
听雪
月满西楼梅花怒放
我用心把漫天繁星点亮
简单浪漫而又不失风雅
这是我最喜欢的重复
雪地上的花影
是开放的孤独
喧嚣后的寂静
是厌倦了尘世间的纷扰
此刻
我站在临渊之畔
如同
在冬泳中起舞
用热情驱散寒冷
用寒冷拥抱思想
卑微却不轻贱
叹息却不失自信
听雪
这无声的对话
谁能够理解这其中禅机
又有谁能听懂这雪夜隔世的绝唱
刘福申 中国作协会员。曾在《诗刊》《中国作家》《星星》《草堂》《诗选刊》《诗歌月刊》等报刊发表诗歌。曾获屈原杯诗歌奖、曹植杯诗歌奖、林徽因杯诗歌奖等。
唐诗之路(组诗)
□ 唐德亮
走在唐诗之路上
走在陕西的大路 便走在
一条逶迤璀璨的唐诗之路
诗之故乡
在长安,辋川,蓝田,临潼,渭水……
我邂逅
众多的灿烂诗星
他们照亮唐朝 照亮千年时空
那些诗歌的太阳,月亮,巨星
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孟浩然,王勃,李贺……
诗仙,诗圣,诗豪,诗佛,诗鬼……
汇成一条光芒夺目的星河
朗照天地 人间 心灵
我,成了一个追星者
追李白,邈视权贵,醉卧长安
拔剑四顾 斗酒三百
再沾一点仙气 独步天地
追杜甫,在杜公祠
我见到忧国忧民的诗圣 忧愤的目光
穿透千年时光隧道
向他讨教:如何才能让我的诗
增加一点深度、高度与厚度
追白居易,让他赐我一把
诗歌“以情动人”的钥匙
追王维,在终南山沾一点禅味
让我的诗多几丝山水的灵气
追高适,长安三万里
金戈铁马,建不朽功勋
追李商隐,期待一段
朦胧而令人回味的感情……
也曾比较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
李白的床前明月,张九龄的海上明月
哪个更圆,哪个更柔,哪个更亮
哪个更有人情、人性
哪个更有诗的悠长韵味
哪个更能醉人将人带入诗的梦乡
我纵横神州,追尽大唐诗人,探寻他们
何以金句琳琅,诗传千古 香飘万里
走在陕西唐诗之路
心在大唐徜徉
沐浴唐诗之光
诗风扑面而来
万树诗叶 万花诗香
万山诗峰 万水诗声
万云诗涌 万诗撼心……
满眼的诗情,遍地的画意
诗火如炽 诗心如海 诗潮澎湃
在诗中,我活出了最美的人生
华清宫
寒夜笼罩的骊山脚下
一声枪响,惊醒沉寂千年的华清宫
五间厅里,一个外战外行的大人物
仓皇翻身 越墙逃窜
兵谏亭前的山洞与树木
见证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十二日
张杨二将军 将天捅破了一个大窟窿
历史 在这一夜开始
悄然转身 华清宫
再度走进中国的历史
时间一瓣一瓣地凋谢
今日,华清宫道路两旁的石榴
红得那么艳丽耀眼
不知向湛蓝的天空
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大唐芙蓉园
奇石险峻 飞瀑流泉
展不尽大唐诗人的才情
碧湖秋水 飞瀑流泉
流的是大唐风韵
无论爱国忧民的壮怀激烈
或者感喟人生的温婉柔情
都有缕缕诗魂的灵气升腾
壮观的诗墙上
每一个诗人的名字
都蕴含珠玑
每一行诗句
都灼灼闪光
巨大的诗人塑像不过几丈
但在后世诗人与百姓心中
却高过雁塔、秦岭、华山……
唐德亮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诗刊》《光明日报》等200多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3000多篇,出版诗集8部。有近百篇作品被《新华文摘》《中国文学年鉴》《青年文摘》《诗选刊》《散文选刊》等选刊转载。

长白看松(上)
□ 陈先发
越野吉普的引擎轰地一声低低吼起,我们开始攀向长白山主峰。一幅天然的山水图轴,在窗玻璃中渐次展开了:白得耀眼的,是不规则披覆山体、填满千沟万壑的冰雪;灰白平匀的,是午后昏沉欲雪的低空。浅黑中掺进了褐赤、灰青的,是成片绵延又难以辨清树种的林木;深黑犹如泼墨的,是裸露的山体或是避风处的大片砂岩……南方来的两个朋友显然兴奋了点,眼贴在窗玻璃上,时不时发出几声叹息。
而我此行,心里埋伏着另外一个执念:看松。
正是隆冬时节。远景中,墨迹般嵌入山色的各种林木。我想,主体一定是松树。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迟凋,乃至不凋,理所当然地契合了人对生命力生生不息的渴望。以松柏为喻,孔子又发了一系列的感慨:“君子之道,如松之荣。君子之德,如松之茂”“松柏之茂,其贞也特”等,直让人觉得松的本体已被掏空了,只剩下一个长髯端肃的老者,枯坐在那里喃喃自语。诗人就轻松了许多,他们写松,写的多是些直觉与姿态。以前读杜荀鹤《题唐兴寺小松》,由松树“虽小天然别,难与众木同”入手,结尾来了句狠话,“如今未看,须是霜雪中”。把没入冰雪境界的松之美,一笔全给废掉了。李商隐写松,“无雪试幽姿”,憾则憾矣,一个幽字,毕竟存了份神秘的愉快。仿佛松与雪之间,真的潜藏着一种诗的密码。进山时,我在脑中照着王维枯雪寒林的笔意,草草勾勒了一幅老松倚雪的画样:蜷曲虬枝黝黑苍郁,新雪霎亮地凝结在松肤之上……及至眼前,长白山松,却全然不是这般模样。
其实,我知道我所期待的,也根本不必是这般模样。
小时候逃学,晴好暖和的春秋天,常常溜到学校后山腰的一块空地上睡大觉。这是一块被巨松守护的荫庇之地。这棵巨松,蜷起一抱多粗又布满瘤结的身子,斜伸着,探向岩下深深的溪谷。除了夏季涨洪水时,这条溪谷平时是干涸的。松冠最是好看,发怒时一样张得很开,松针又密,下小雨时,松下地面也是干干的。傍晚时看,松冠像一张拍向谷中的巨手,山下一两里外,也看得清清楚楚。这块空地,准确地说,是巨型山岩的一面,微微有点坡度,雨水将上面的积土腐叶,冲刷得干干净净。紧靠着岩壁的空地上,有几截一尺多高的残墙和几堆废砖瓦。后来我听说,这是一座小土地庙的遗址。松树,本应是有两棵吧,在废庙址右侧,还有一截粗而黑的树墩。从根部看,这两棵巨松是从石缝中长出来的,除了点烂叶子沤成的腐殖土外,再无别的养料,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月,才生成如此的庞然大物。无数个暖洋洋的下午,我躺在厚厚软软的松针上,用黄帆布书包作枕头,心中一无所挂地沉沉睡去。树下,安静得仿佛松针往下掉时,刺破空气之声也清晰可闻。好长一个懒觉啊!有时一激灵,被凉风吹醒,睁眼一看,哦,快到傍晚了。松下渐渐起了些潮气。过不多久,放学钟声就要从前山校区那边,悠扬传来。夏天放假时,我闯了祸,一般也要藏到这棵松树下来,躲避父母的棍棒教育。那几年,攀向山腰这块空地的,有好长一截荆棘小径,只有小孩子抱着脑袋,才能从缝隙中钻过来,大人们几乎发现不了。
当年家中有个远房亲戚,在邻村做木匠,他是一个你得提着三斤鲜猪肉上门,才请得动的上好木匠。小时去他家玩儿,总觉得膝盖中酸酸的,迈不开步子,说不出的一种紧张感。别人家的门前,种些花花草草,栀子茉莉的。他家门前偌大空场子,锤得平平整整,却栽着六七棵松树。这些松树虬劲多枝,松冠繁茂如盖。从远处看,松树伴着三间茅草屋子,真有点野寺的味道。这个亲戚是鳏夫,四十几岁时,得了肺结核病,也不去医院治疗,不知从哪里弄来个偏方子,照着煎中药。几棵松间,常年就飘荡着怪怪的中草药气味。折腾了几年,也不见好,最后索性就失踪了。1983年夏季洪水,老屋子的三面墙都垮掉了,几件本来好模好样的旧家具,砸了个稀巴烂。村里人就说,这松,栽得不好。家乡一带,素有“前不栽松、桑,后不种梨、柳”的说法,大家也都讲究这老规矩。十里八乡的,唯独这个至今杳无踪迹的亲戚,曾破了这个例,孤例。
说来也怪,这几棵松树,清清爽爽映在我脑神经中。这么多年,像新栽的一样。
我想起一个词来:松冢。
去年秋末,我去过一次那个老屋址。松树没了,废墟也没了。不知是谁建了一排彩钢瓦的板房商铺,卖农药化肥。我坐在门前,发了会儿呆。心里有些失落。那几棵消失的老松,原来只是几朵徒具松树面貌的过眼烟云。
没料到,在我心里挂得黄泛的两幅老松图,来长白山的第一晚,就被颠覆了。那天好一路颠簸,傍晚才到山脚下。刚住下,还没来得及烧水煮茶,就被几个急性子的朋友拽到了宾馆门口,要在松林中合影。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美人松”!抓紧按下快门吧,趁着这几抹夕照犹存!我们紧裹着从前台租来的笨重军大衣,顶着割脸的北风,站在相机前哆嗦着。合影罢了,我猛跺了一通脚,把身子弄得热乎了点,才去松林里逛了一大圈。
这松,哪里有什么虬干曲枝?我在南方见惯了游龙探海、绝壁倒挂这一类奇状异形,这松却一律地身形颀长,通直挺拔,一股子少女向上跳脱的苗条劲儿。哪里有什么松皮苍劲如铁?我喜欢的松,多是体肤如斧劈火燎过,沉郁蓊苍,有苏轼所言“不到千般恨不消”的沧桑之味。这松的皮色,却分明是灰白、棕黄中透着股子脂粉气。此刻,夕光从林梢透入,树身犹镀微金,在林间白雪的映衬下,倍显恬静婀娜,一如刚刚出浴的佳人。杨万里曾讲松树“一生清苦不敷腴”,这松,冠盖饱满略呈锥形,美如盘发,典雅端方,哪里有一丁点身出寒门的清苦味儿?
陈先发 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文联主席,安徽省作协主席。1967年10月生于安徽桐城,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主要著作有诗集《写碑之心》《九章》《陈先发诗选》,随笔集《黑池坝笔记》(系列)、长篇小说《拉魂腔》等二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十月文学奖等国内外数十种文学奖项。

小说与人性休戚相关
□ 泊 心
潘军是一个传奇。
作为著名作家,他是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独白与手势》《风》《死刑报告》堪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为剧作家,他的话剧《合同婚姻》《霸王歌行》分别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演,并在世界上十几个国家巡演,获得“世界戏剧节”优秀剧目奖;作为画家,他出版了三卷本大型画册《泊心堂墨意》,并在多地举办了个人画展;作为影视导演,他自编自导的电视剧《五号特工组》《虎口拔牙》《分界线》风靡全国;现在,潘军又推出了独特的小说文本“春秋战国秦汉三部曲”——《春秋乱》。
2000年,潘军在《花城》上发表了中篇小说《重瞳——霸王自叙》,立即被海内外多家报刊转载,并位列“中国当代小说排行榜榜首”。潘军是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有批评家说,正是因为一部《重瞳》的问世,才使得中国“先锋小说”有了一个漂亮的结尾。也有人认为,《重瞳》既是“先锋小说”的落幕之作,同时又是“新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时隔24年的今天,新年伊始,两家著名的文学期刊《作家》与《天涯》,都在第一期以重要位置推出了他的两部中篇小说——《刺秦考》和《与程婴书》,从当年的“楚汉争锋”说到“赵氏孤儿”和“荆轲刺秦”,构成了“春秋战国秦汉三部曲”。最近,作者又以“作家手记”的方式将其连为一体,取名《春秋乱》,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据悉,安徽作家协会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将在合肥联合举行这部作品的首发式和研讨会。
潘军认为,某种意义上,读者可以认为这是一部由三部中篇构成的一部长篇,这样的小说文本或许有点新意,虽然表现手法和叙事风格有所不同,但都是重新解构,都是在《史记》《左传》《资治通鉴》这样的历史典籍中,寻找出一个重新解读的可能性,都是一次颠覆性的写作,从而使这三个历史时期发生的家喻户晓的故事获得了新意。
但凡家喻户晓的故事皆是耳熟能详,颠覆肯定是不容易的。潘军说,如果没有新的认知,不作出新的独立的判断,就没有意思了。我一直强调的是,认知高于表现。这种意识贯穿了我的全部创作生活,无论是写作还是绘画。比如《赵氏孤儿》,如果依旧去写程婴拿自己的亲生骨肉去换取所谓忠良之后,这种价值取向显然值得商榷。荆轲刺秦也是如此,司马迁构想的“图穷匕见”的情形不可能发生,荆轲连一根针也无法带进秦王宫的,怎么刺秦?像这样的支点如果都站不住脚,重新解读就是一句空话。作为一名出色的剑客,荆轲只要接近并瞬间控制了秦王,目的即已达成。杀一个人与证明能杀一个人,对于剑客,境界高下立判。荆轲不可能成为燕太子丹把玩的又一枚棋子,他要完成的只是自己的“一意”——证明自己,圆了英雄梦。显然他没有从肉体上消灭秦王,他不屑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精神上彻底挫败了嬴政。
《重瞳——霸王自叙》《与程婴书》和《刺秦考》分别用了“我”“你”“他”三个讲述视角,很像一个刻意为之的游戏。对此,潘军解释说:他写小说,会自觉地先去考虑“怎么写”?不同的题材,应该有不同的写法,得先找到一个最合适也最舒服的叙事方式。他认为小说就是通过文字造型的艺术,某种意义上,现代小说就是对形式的发现和确立。《重瞳——霸王自叙》采用了第一人称,开篇就是“我叫项羽”,这是项羽亡灵的视角,能从两千年前看到眼下。潘军说,我还是信奉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强调的还是一种个人对历史的认知。所谓捕风捉影,即是在扑朔迷离的历史缝隙中去寻求另一种解读的可能,或者依靠想象来重构这个支离破碎的故事。至于真实,那只能存在于我的内心,《春秋乱》是一部充满悲悯情怀的小说文本。潘军说,悲悯应该成为一个作家最炽热充沛的情怀,我希望我的小说与人性的复杂多样休戚相关,折射出人道主义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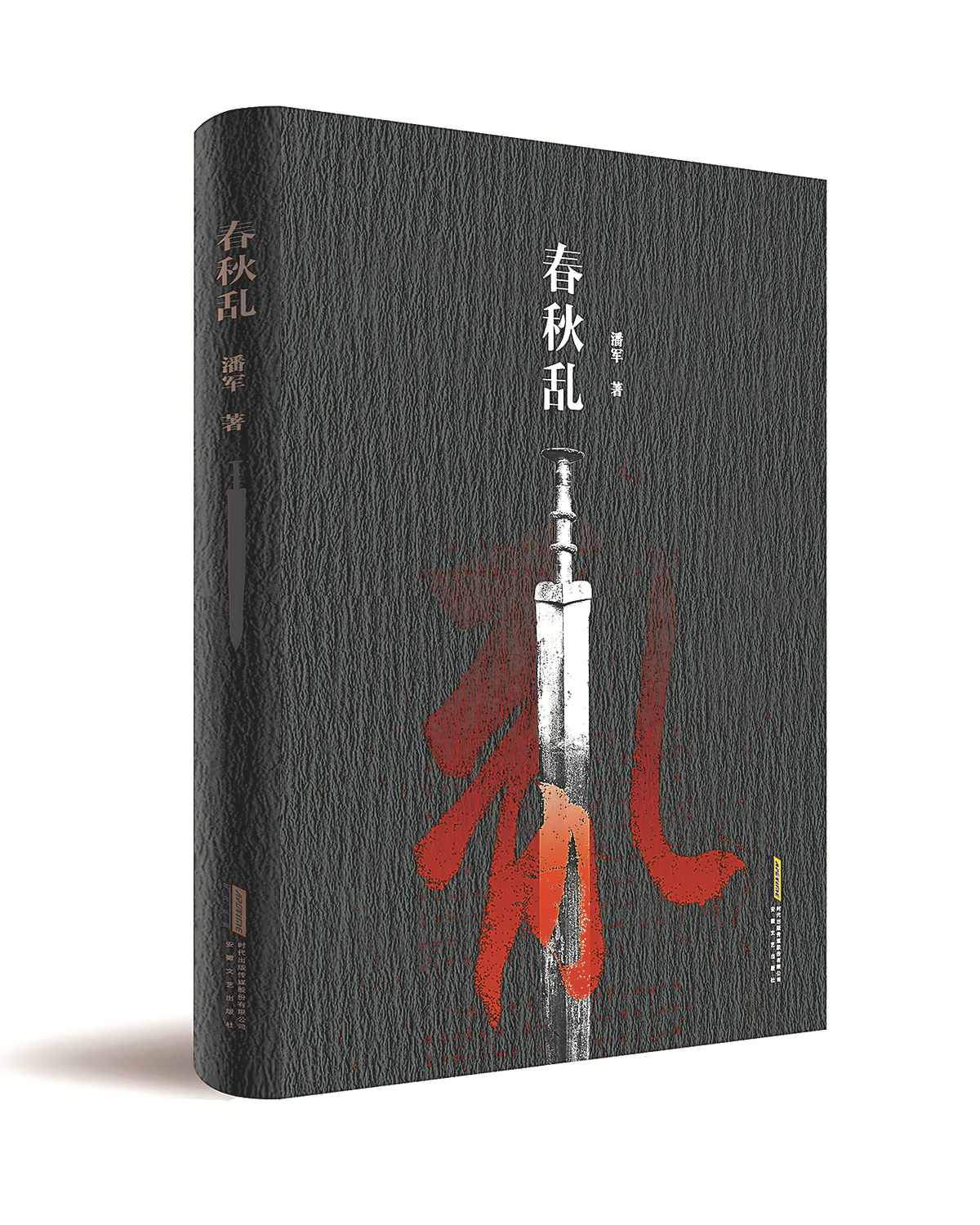
行走的风景(组诗)
□ 刘福申
在刘河湾坐看风生水起
长长的春风刮过
牡丹花开
千年花朵
在水的光影中盛开
有水的地方
一定会有风的长歌
有风的地方
一定会有水的浩气
要不风水这个词
怎么会亲密无间地
在刘河湾这片醒着的土地上
千变万幻
风声水声
现代化的交响
乡愁被一朝又一朝的音符打上烙印
光阴被一朝又一朝的音符洗亮
在这里落脚的天鹅
是有眼光的
以贴近土地的方式
爱着这里
风 刘河湾的语言
水 刘河湾的翅膀
一只比雪还白的鸽子
一把比山还重的铡刀
一包比云彩还轻的茱萸叶儿
一杯比玉露还浓的菊花酒
千年不老的富贵牡丹
铺成一条彩色的路
天高地远
在物竞天择的土地追逐
追逐得风生水起
霜降
天气,一定是被掌控的
就像我们生活中的电灯开关一样
望着一地的白
我笨拙地想
是不是缺钙的人间
更需要补充一下盐
上架的黄烟
叶片上的纹路
一点点加深着颜色
此刻,而我的纠结不在于此
对于霜降的降字,这个
转动季节的动词
在秋风中演奏着命运的交响
在枯荣的交替中
死亡与新生一样伟大
大雪
夜色里的明亮
只因一场大雪
无法停止的咳嗽
覆盖地上万物
红泥小火炉的火焰
伸着任性的舌头
温暖地调侃着
蝴蝶一路风情的姿式
时光沉默的智者
在薄情的世界里变着魔术
把浮躁的河流
切换成一块石头
那些口出真理的哲学家
盲人一样想着女人的姿色
白 无疑成为
掩埋黑的真相的罪人
听雪
月满西楼梅花怒放
我用心把漫天繁星点亮
简单浪漫而又不失风雅
这是我最喜欢的重复
雪地上的花影
是开放的孤独
喧嚣后的寂静
是厌倦了尘世间的纷扰
此刻
我站在临渊之畔
如同
在冬泳中起舞
用热情驱散寒冷
用寒冷拥抱思想
卑微却不轻贱
叹息却不失自信
听雪
这无声的对话
谁能够理解这其中禅机
又有谁能听懂这雪夜隔世的绝唱
刘福申 中国作协会员。曾在《诗刊》《中国作家》《星星》《草堂》《诗选刊》《诗歌月刊》等报刊发表诗歌。曾获屈原杯诗歌奖、曹植杯诗歌奖、林徽因杯诗歌奖等。
唐诗之路(组诗)
□ 唐德亮
走在唐诗之路上
走在陕西的大路 便走在
一条逶迤璀璨的唐诗之路
诗之故乡
在长安,辋川,蓝田,临潼,渭水……
我邂逅
众多的灿烂诗星
他们照亮唐朝 照亮千年时空
那些诗歌的太阳,月亮,巨星
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孟浩然,王勃,李贺……
诗仙,诗圣,诗豪,诗佛,诗鬼……
汇成一条光芒夺目的星河
朗照天地 人间 心灵
我,成了一个追星者
追李白,邈视权贵,醉卧长安
拔剑四顾 斗酒三百
再沾一点仙气 独步天地
追杜甫,在杜公祠
我见到忧国忧民的诗圣 忧愤的目光
穿透千年时光隧道
向他讨教:如何才能让我的诗
增加一点深度、高度与厚度
追白居易,让他赐我一把
诗歌“以情动人”的钥匙
追王维,在终南山沾一点禅味
让我的诗多几丝山水的灵气
追高适,长安三万里
金戈铁马,建不朽功勋
追李商隐,期待一段
朦胧而令人回味的感情……
也曾比较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
李白的床前明月,张九龄的海上明月
哪个更圆,哪个更柔,哪个更亮
哪个更有人情、人性
哪个更有诗的悠长韵味
哪个更能醉人将人带入诗的梦乡
我纵横神州,追尽大唐诗人,探寻他们
何以金句琳琅,诗传千古 香飘万里
走在陕西唐诗之路
心在大唐徜徉
沐浴唐诗之光
诗风扑面而来
万树诗叶 万花诗香
万山诗峰 万水诗声
万云诗涌 万诗撼心……
满眼的诗情,遍地的画意
诗火如炽 诗心如海 诗潮澎湃
在诗中,我活出了最美的人生
华清宫
寒夜笼罩的骊山脚下
一声枪响,惊醒沉寂千年的华清宫
五间厅里,一个外战外行的大人物
仓皇翻身 越墙逃窜
兵谏亭前的山洞与树木
见证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十二日
张杨二将军 将天捅破了一个大窟窿
历史 在这一夜开始
悄然转身 华清宫
再度走进中国的历史
时间一瓣一瓣地凋谢
今日,华清宫道路两旁的石榴
红得那么艳丽耀眼
不知向湛蓝的天空
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大唐芙蓉园
奇石险峻 飞瀑流泉
展不尽大唐诗人的才情
碧湖秋水 飞瀑流泉
流的是大唐风韵
无论爱国忧民的壮怀激烈
或者感喟人生的温婉柔情
都有缕缕诗魂的灵气升腾
壮观的诗墙上
每一个诗人的名字
都蕴含珠玑
每一行诗句
都灼灼闪光
巨大的诗人塑像不过几丈
但在后世诗人与百姓心中
却高过雁塔、秦岭、华山……
唐德亮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诗刊》《光明日报》等200多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3000多篇,出版诗集8部。有近百篇作品被《新华文摘》《中国文学年鉴》《青年文摘》《诗选刊》《散文选刊》等选刊转载。

-我已经到底线啦-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