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栈的大姐敲门,问我几点吃晚饭,我说七点吧。大姐问:太迟了吧,不饿?不饿,中午吃得太饱了。
出房间,走到院子中,天色已暗,高耸的墙壁撑起宽大的屋顶,像是撑起一把巨伞,屋子里的椅子、桌子面目模糊,惟有天井下方亮着一片光,如一块白手帕铺在地上。
我们是下午四点抵达这个名叫龙潭寨的古村落的。入冬了,大山深处进入最寒冷的季节,朋友刘承亮惦记山里的孩子,要给他们捐点款,我也跟了去,给每个孩子带去一本书,又跟他们说些鼓励的话。五十年前,在老家下放的一位上海知青对着我作业本上的钢笔字说了几句赞扬的话,他没想到他这个外人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会让我这个乡下孩子激动好些日子,至今还没忘记当初的那份窃喜,总想着要给乡下娃做点事。这些年,老刘一直做点生意,风里来雨里去,却始终没忘记帮助别人。他的达观,让我感动,也让我自己庆幸,身边还有这样自带光亮的人,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做完活动,村里的干部请我们吃饭,菜是他们从自家菜园摘来的,那些莴笋、白菜、萝卜因为经历了几场霜,格外甜,我一口气吃了两碗米饭,又喝了满满一碗锅巴汤,丢下碗,身上的寒气也被消掉,热气正从肺腑外溢,周身舒服极了。
阳光无遮无拦,雨水一样汪洋恣肆,洒在无垠的田野和远处的山林中。往回去的路上,车子拐上另一条路,一棵柿子树上立在院墙边,枯瘦的枝干上挂着密密麻麻的果子,一粒粒晶莹剔透,晃晃悠悠,让人疑心风要是再大一点,会不会把它们吹破。惊叹一番之后,蓦然瞥见一溜子古旧的房舍鱼脊一样浮在远处的山谷,旁人道:那是“龙潭寨”。
两排连绵的大山相对而立,留下一条细长的缝隙,一座座房子落在两边。下车近观,一条峡谷从远处飘然而下。峡谷中,巨石密布,如野兽,如小舟,如美人侧卧,如壮汉静坐……一条溪水左冲右突,蜿蜒而来,虽不复有汹涌之势,但依然淙淙有声,闪闪发亮。
沿峡谷移步向前,一座座房舍飞檐翘角,黑黑的瓦片琴弦一般排列,屋檐下、窗台上的砖雕、木雕虽已被风雨侵蚀,但面目依然可辨。再看屋后的连绵高山,耸立于蓝天白云之下,简直就是大地给村庄定制的一面面天然屏风。
一座苍老的拱桥赫然在目,远远望去,仿佛一只深绿色的灌木和杂树围成的花环悬在空中,近前,方知是一块块方形石头垒砌而成的桥,曰“五福桥”,村中一胡姓人家所建,意在祝福自己的五个儿子,也是祝福天下苍生。到底是善良人家。善良人家才可能是富贵人家。
炊烟从房顶上飘起,一老妇人在溪水中洗菜,影子在水中晃动,碎碎的阳光在水中荡漾、跳跃。亭子边,几位老人在闲聊,旁边是四五只巨大的竹扁,晾晒着山里特产的豆丝。有黄梅音袅袅而来,是严凤英的《小辞店》,那位六旬左右的男人身着藏青色中山装,把一摞摞长秆芥菜放在青石板垒成的墙垛上,清亮的水从碧绿的菜叶间往地上滴。
忽然就有了冲动。我跟同行的人说,不走了,要在这个大山深处的古村落住一个晚上。遇到一个气息相投的人要珍惜,遇到一个喜欢的地方也要珍惜。
夜色越来越浓。坐在门口的麻石条上,有微薄的凉意,但并不冷。没有人影。溪水在铃铃地响。对面人家的灯光映在溪水里,摇摇晃晃。我像一块石头坐着。有多久没这样安静地坐进夜色?对面的大山在看我,而我看不到它们,只能看到自己的脚尖。
大姐立在门口喊我吃饭。菜已摆在桌子上,一个萝卜烧肉,一个清炒黄芽白,一个辣椒炒毛鱼,是我自己看着厨房的食材点的。大姐又送来她自己腌制的藟头。我让大姐拿来一瓶酒,给自己倒了一杯。大姐说:你慢慢吃,吃完了把碗筷丢在这里,我明天早上再来收。
大姐睡觉去了,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萝卜和肉在炉子上突突响,似小河淌水,飘浮的热气在桌子上方弥漫、盘旋。萝卜和黄芽白真是甜,藟头真是晶莹透亮,毛鱼真是香,我慢慢吃,慢慢喝,喝一口,吃一条毛鱼,再放下筷子,任香味在口腔里萦绕、回复,再把炉子的火拨小一点,让沸腾的声音小一点。
这样独自喝酒,于我来说真是少有,而在偶遇的深山里这么独自喝酒,六十年的人生中还是第一回。
又突发奇想,把茶杯洗干净,往里面倒一些酒,左手握着酒杯,右手握着茶杯,先用酒杯敬茶杯,就当对面正坐着另一个我,这么一想,觉得趣味多了不少。喝一口杯里的酒,吃一口萝卜,再喝一口茶杯里的酒,吃一粒藟头。茶杯和酒杯郑重相碰,发出清脆的声音。无意中侧头,墙上的影子也正双手举着杯子呢!那个影子是我吗?是的,好像又不是。就这样慢慢地喝,慢慢地敬,一瓶酒喝了大半,桌子上的菜也吃了大半。起身,有些摇晃,仿佛我是我自己,又不是我自己。
回到房间,躺到床上,身子正在飘起来。窗外夜色深重,没有一点声响。我似乎躺在黑黑的云层上。
今夜,我只管沉睡如石,融入无边夜色,与大山共眠。

客栈的大姐敲门,问我几点吃晚饭,我说七点吧。大姐问:太迟了吧,不饿?不饿,中午吃得太饱了。
出房间,走到院子中,天色已暗,高耸的墙壁撑起宽大的屋顶,像是撑起一把巨伞,屋子里的椅子、桌子面目模糊,惟有天井下方亮着一片光,如一块白手帕铺在地上。
我们是下午四点抵达这个名叫龙潭寨的古村落的。入冬了,大山深处进入最寒冷的季节,朋友刘承亮惦记山里的孩子,要给他们捐点款,我也跟了去,给每个孩子带去一本书,又跟他们说些鼓励的话。五十年前,在老家下放的一位上海知青对着我作业本上的钢笔字说了几句赞扬的话,他没想到他这个外人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会让我这个乡下孩子激动好些日子,至今还没忘记当初的那份窃喜,总想着要给乡下娃做点事。这些年,老刘一直做点生意,风里来雨里去,却始终没忘记帮助别人。他的达观,让我感动,也让我自己庆幸,身边还有这样自带光亮的人,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做完活动,村里的干部请我们吃饭,菜是他们从自家菜园摘来的,那些莴笋、白菜、萝卜因为经历了几场霜,格外甜,我一口气吃了两碗米饭,又喝了满满一碗锅巴汤,丢下碗,身上的寒气也被消掉,热气正从肺腑外溢,周身舒服极了。
阳光无遮无拦,雨水一样汪洋恣肆,洒在无垠的田野和远处的山林中。往回去的路上,车子拐上另一条路,一棵柿子树上立在院墙边,枯瘦的枝干上挂着密密麻麻的果子,一粒粒晶莹剔透,晃晃悠悠,让人疑心风要是再大一点,会不会把它们吹破。惊叹一番之后,蓦然瞥见一溜子古旧的房舍鱼脊一样浮在远处的山谷,旁人道:那是“龙潭寨”。
两排连绵的大山相对而立,留下一条细长的缝隙,一座座房子落在两边。下车近观,一条峡谷从远处飘然而下。峡谷中,巨石密布,如野兽,如小舟,如美人侧卧,如壮汉静坐……一条溪水左冲右突,蜿蜒而来,虽不复有汹涌之势,但依然淙淙有声,闪闪发亮。
沿峡谷移步向前,一座座房舍飞檐翘角,黑黑的瓦片琴弦一般排列,屋檐下、窗台上的砖雕、木雕虽已被风雨侵蚀,但面目依然可辨。再看屋后的连绵高山,耸立于蓝天白云之下,简直就是大地给村庄定制的一面面天然屏风。
一座苍老的拱桥赫然在目,远远望去,仿佛一只深绿色的灌木和杂树围成的花环悬在空中,近前,方知是一块块方形石头垒砌而成的桥,曰“五福桥”,村中一胡姓人家所建,意在祝福自己的五个儿子,也是祝福天下苍生。到底是善良人家。善良人家才可能是富贵人家。
炊烟从房顶上飘起,一老妇人在溪水中洗菜,影子在水中晃动,碎碎的阳光在水中荡漾、跳跃。亭子边,几位老人在闲聊,旁边是四五只巨大的竹扁,晾晒着山里特产的豆丝。有黄梅音袅袅而来,是严凤英的《小辞店》,那位六旬左右的男人身着藏青色中山装,把一摞摞长秆芥菜放在青石板垒成的墙垛上,清亮的水从碧绿的菜叶间往地上滴。
忽然就有了冲动。我跟同行的人说,不走了,要在这个大山深处的古村落住一个晚上。遇到一个气息相投的人要珍惜,遇到一个喜欢的地方也要珍惜。
夜色越来越浓。坐在门口的麻石条上,有微薄的凉意,但并不冷。没有人影。溪水在铃铃地响。对面人家的灯光映在溪水里,摇摇晃晃。我像一块石头坐着。有多久没这样安静地坐进夜色?对面的大山在看我,而我看不到它们,只能看到自己的脚尖。
大姐立在门口喊我吃饭。菜已摆在桌子上,一个萝卜烧肉,一个清炒黄芽白,一个辣椒炒毛鱼,是我自己看着厨房的食材点的。大姐又送来她自己腌制的藟头。我让大姐拿来一瓶酒,给自己倒了一杯。大姐说:你慢慢吃,吃完了把碗筷丢在这里,我明天早上再来收。
大姐睡觉去了,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萝卜和肉在炉子上突突响,似小河淌水,飘浮的热气在桌子上方弥漫、盘旋。萝卜和黄芽白真是甜,藟头真是晶莹透亮,毛鱼真是香,我慢慢吃,慢慢喝,喝一口,吃一条毛鱼,再放下筷子,任香味在口腔里萦绕、回复,再把炉子的火拨小一点,让沸腾的声音小一点。
这样独自喝酒,于我来说真是少有,而在偶遇的深山里这么独自喝酒,六十年的人生中还是第一回。
又突发奇想,把茶杯洗干净,往里面倒一些酒,左手握着酒杯,右手握着茶杯,先用酒杯敬茶杯,就当对面正坐着另一个我,这么一想,觉得趣味多了不少。喝一口杯里的酒,吃一口萝卜,再喝一口茶杯里的酒,吃一粒藟头。茶杯和酒杯郑重相碰,发出清脆的声音。无意中侧头,墙上的影子也正双手举着杯子呢!那个影子是我吗?是的,好像又不是。就这样慢慢地喝,慢慢地敬,一瓶酒喝了大半,桌子上的菜也吃了大半。起身,有些摇晃,仿佛我是我自己,又不是我自己。
回到房间,躺到床上,身子正在飘起来。窗外夜色深重,没有一点声响。我似乎躺在黑黑的云层上。
今夜,我只管沉睡如石,融入无边夜色,与大山共眠。


-我已经到底线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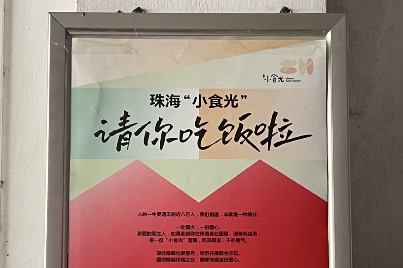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