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慧谋
李好的《海在低处》摄影艺术作品展近日在珠海古元美术馆开展,并引起轰动,这是我意料中的事情。策展人通过光影和场景氛围,把李好的这组《海在低处》衬托得淋漓尽致,别具匠心的创意,大大提升了这组摄影作品的艺术效果。策展者是珠海古元美术馆策展部主任庄丽,整个展场的氛围质朴大气,与《海在低处》这组以黑白为主调的摄影艺术作品浑然一体。可见,策展者读懂了李好,读懂了一位摄影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我与李好同在一个纬度的海岸线上出生成长,从小闻着海腥味、听着浪涛声长大,见证了渔人与海的共存,见证了这些年人类与大海的博弈,甚至见证了时间的足迹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流逝,像地里的庄稼一样被海浪收割,又随着潮汐澎湃而生。当若干年前作为摄影爱好者的李好,八进青藏高原完成《朝拜者》系列作品后,在蓦然回首中,他看见了南方那片熟悉的大海,如同一次巅峰高潮过后,他的内心归复平静,回归到海的低处。
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首关于海的诗,其中有句:“……云啊,高高在上,白白的浮云。海在低处,潮汐在低处,渔网挂在低处……”我与李好的年龄有一定差距,当我伏在“海的低处”写诗时,他还在求学之路。当他从高原回望“海的低处”时,我已经完成了与海有关的诗集《渔火把夜色吹白》。
我与李好有个共同点,就是喜欢吃海鲜。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大海的基因,因此在某些方面,形成了海的个性。比如说李好,他是个非常爱冲动的人,喜欢面对挑战,喜欢在浪尖上舞蹈,充满冒险精神。又比如我,喜欢夜色,喜欢海上渔火,面对多变的世界,总是像渔火一样怀抱光芒,冷静得近于无情。我与李好,传承了海的两面性,因为,我们都是大海的儿子。
李好的整个创作过程,我是旁观者,更是知音。摄影和文学是对孪生兄弟,两者之间有距离,但更多的是共通共融,共鸣共感。摄影是以镜头以影像记录生活,文学是以笔以文字书写灵感,但归根到底,摄影和文学展示的都是人性内心世界。从李好的摄影作品里,我常常读到画面文字,甚至读出心跳、读出怜悯、读出沧桑。但我深信,李好读我的文字时,也会读出同样的感觉。
尽管我对李好的摄影作品非常熟悉,但那天在古元美术馆观看《海在低处》时,不仅仅是震撼,更有一种久违的“陌生感”。面对这些黑白照片,我仿佛回到远古的洪荒时代,回到夜与昼的初始期。黑白如此鲜明,几乎把当下眼花缭乱的颜色抽光,只有黑与白,才是永恒的。
是的,李好一直在追求永恒,孤身一人在广袤旷野上行走,在无人随行的漫长海岸线行走。他用他的镜头在建立“一个人的海岸线”,不与他人争道,他走他的独木桥,坚持走下去,哪怕他是这条道上唯一的孤行者。
作品成功与否并非是一个摄影家的唯一标准,没有哪门艺术是可以统一天下人心的,更何况是把自己定格在镜头有限空间的摄影艺术家。李好虽然摘取了国内摄影界最高的“金像奖”,但对于他,仅仅是评委们对他的作品认可和肯定,或者说,这是他摄影生涯的一个新高度新起点。但是,作为旁观者,作为李好认可的亲如兄弟般的老哥,我更看重李好在做什么?做了些什么?
在展馆里陪着我观展的还有《广州文艺》主编、作家张鸿,除了主编、作家身份,张鸿同样是一位资深的摄影家。我与张鸿探讨一个问题,李好这个主题的摄影作品在隐喻着什么?作品背后的那个李好他内心在思考着什么?这才是我和张鸿看展时探讨的话题。
我无法说出李好的这批作品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因为我根本就不懂得摄影艺术的标准和深度,我只知道一幅作品给了我启发和有话可说的感觉,在乎它给我灵魂的震撼和内心的感动,这就足够了。理论是理论家们的话语权,是他们的发现和对摄影标准重构的一个世界,有方向性的指引和境界上的升华。而我,是一个不懂门道只看品质的外行人。我在观看李好的摄影作品时,似乎有一双深邃得难以莫测的“眼睛”在看着我。
我特别在乎看影展时油然而生的这种感觉,或者是作品自身的隐喻,给我带来的这份“陌生感”。
在场的作品都是经过李好精心挑选的,可以说,这是李好从他的几十万张底片里选出几十幅构成《海在低处》主题的摄影作品展,每一张都有着难以拔掉的理由和空间,它们构成的整体,虽然不能绝对代表“海在低处”主题的全部创作,但它们可以撑起这个主题的高度或者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部分。
展出的每幅作品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并且引起强烈共鸣。也许我太熟悉李好的作品了,异常平静地观看,异常平静地品味,异常平静地思考。作品中的场景都是我司空见惯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那么似曾相识,甚至可以叫出他们的辈分和名字。因为看到他们,就想起我的渔民父亲和他的渔民兄弟。这就是大海的基因始终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看见大海在一天天地老去,看到如此庞大无比而又富饶的大海在步步临近贫困线,我在想,物产再丰富的大海也会被无度的掠夺者掏空。当大海仅剩下海水时,人类的生存也难以为继,这绝对不是骇人听闻的预言。
或许,这就是《海在低处》的隐喻和内涵,但愿我的判断和理解是错误的。


□ 谌山石
树一旦被种下
它的一生大概就被注定
也许早早衰老凋零
也许长期绿盖成荫
它没有任何选择权
只能尽自己的可能
与雨雪水火努力抗争
采天地之灵气续命
它成为周遭的风景
也成为变迁的眼睛
那些匆匆来去的身影
那些存在消失的近邻
树总是沉默不语
因为抱怨不如行动
它把根深扎于土地里
它让枝叶与风声和鸣
树处世的态度
触动了我们的神经
都是造物主的棋子
何不善待所有的曾经

□ 潘 泮
老家有个“荔园”,半亩田的大小,原先园子里长的是一些马尾松和野生苦楝树,母亲每天必去园子拾掇,她管着一家的温饱,柴火也很要紧,所以园子被收拾得非常整洁,几乎见不到落叶。现在想来,家有这么个“燃料库”,解了些后顾之忧。
眨眼之间,儿女们个个与老家渐行渐远。母亲一个人依然住在老家,但做饭她已学会用燃气,少了打柴取草的辛劳。自从母亲用上清洁能源,园子里的野草杂树又荒长了起来。母亲曾自问:哪会儿园子里才挂着果呢?
母亲六十岁那年,想改变杂草丛生的园子,但已显得乏力。她只好回到屋前屋后的空地种上三棵果树,到了果熟季节,小院子满眼的火红和金黄,弥漫着果香,这时,母亲就盼着儿女们回来,品尝她的劳动果实。
有一年中秋回家,我觉得家门口的龙眼树遮天蔽日,有时白天也难见天日,母亲长期住在那里,光线实在阴暗,母亲勉强同意我砍去两棵。次年,我们再次回来看望她老人家,这回母亲并不注意儿子长胖了还是瘦了,而是微笑着站在树旁三米远处,看挂满树梢头的荔枝,心里头不知有多甜,老脸也开心得灿烂,继而她又若有所思:“那两棵树还留下来的话,不出一个月,你们还能回来尝龙眼呢。”看来当时母亲的话口是心非啊,望着母亲十分惋惜的样子,我说龙眼大批量上市后,价钱便宜哩,一百块钱的水果全家人能吃个饱!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自言自语:不同样的,不同样的……
老家房子重建时,母亲叮嘱不要损伤那棵荔枝树。我说一定会把荔枝树挪到园子里去保护好,老人家知道是挪树,顿时就紧张起来:“使不得,‘人挪活,树挪死’啊!”我好说歹说,母亲的认知就是伤筋动骨“就怕万一”。我故意气一下母亲,挪开树就建房子,让荔枝树留在原地就不建房子了,二选一吧!话音才落,母亲就服软了。
母亲亲手种下的三棵果树,砍的砍挪的挪,不是搬了头就是搬了家,也难怪母亲心痛。从此以后,母亲每天出去散步,必绕园子经过,驻足园子边看一会儿,荔枝树能不能再长新芽,观察一下能不能再开花结果。当然我也怕母亲的多虑言中,有意在家住了好一段时间,就为给荔枝树输输营养液。一系列的操作后,母亲依然放心不下,每天必在我耳边重复那句:“树缺水了不,缺肥了不?”
荔枝树搬到园子里,母亲走这条坑洼路已成常态,村民行走这路尚觉不便,何况是耄耋老人呢?每当想到母亲要出行散步,我又多了一个担心。后来,硬底化这段路的想法我坚定且果断。平整通行的那一刻,身心一下子无比轻松。原来做好事不仅方便了别人更有益自己。
第一个走过这条路的村民,就谬赞了一番这是“好心路”。打那之后村里小公园种花植树,我都乐此不疲。过了几天,女儿回来见我又黑又瘦还幽默了一番:“干了这一点点的事情,黑成这个样子,哪里还是我爸呀!”“你不觉得爸更像一块铁一块钢吗?”此时,不会说好听话的母亲也破天荒头一次表扬她的儿子:“每天不停不歇的,好在荔枝树没有旱死。”听着这话,好像母亲爱她的荔枝树多一点点。
因为母亲如此爱荔枝,我也把园子里的树全部更换,种上了果树。这天,母亲一直站在那里微笑地看着。
村中路路硬底,连接东西贯通南北,小公园就要竣工了,大姐和小妹相约回来看望老母亲,大姐看着这些变化,话里藏话,都是为那棵老荔枝树吧,然后笑了一笑。
又快到一年荔红时,待到荔枝成熟,母亲准要一个个电话报信的。其实不打电话,我们也会每时每刻惦记着园子里的荔枝树,更惦记着年迈的妈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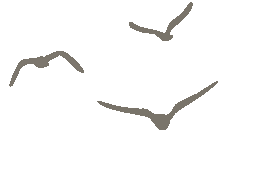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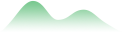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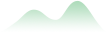
春日访莲洲
□谢成成
炊烟袅袅逸清啼,十里莲洲唱小溪。
巷陌和风攀喜事,家家门上对联齐。
诗意三冲
□黄俊霞
清溪十里绕村庄,两岸洋房映水光。
鱼跃方塘波荡漾,禾翻金浪陌芬芳。
谁家笑语满庭院,入户新联扮靓妆。
最是秋风吹韵起,诗花相伴稻花香。
三冲印象
□宋君
三冲胜境韵悠长,水绕村田稻菽香。
旧巷幽怀联意雅,新楼喜映日华光。
醒狮舞动传风习,画壁呈祥蕴瑞章。
民俗千年情未改,田园画卷韵悠扬。
歌三冲村
□王继荣
翠岭连绵绕白云,重峦叠嶂入天宸。
山清水秀风光好,鸟语花香景色新。
皆悦目,美怡神。自然环境胜仙尘。
此情此景心陶醉,愿做山间一隐人。
过珠海
□叶明增
将军山外锦帆多,九曲蛟龙静卧波。
日月横空争绚烂,烟霞带雨弄婆娑。
千重海岳连三地,百载风云一夕过。
烽火当年堪问取,长天浩渺与谁歌。
思金台寺有感
□涂啸楠
青岭衔云古韵存,金台寺外百花繁。
欲离尘世寻何处,河畔林中隐佛门。
赞三冲村
□张健
曾记三冲初到,满眼风光奇妙。
田野绿波盈,更有古风文藻。
真好,真好,心底醉情难了。
题白藤湖度假区
□张鹏
一处好风光,悠悠放眼量。
峰遥开宿雾,波渺涌朝阳。
闲览鳄鱼闹,欣看蝴蝶狂。
纷纷来去客,远近美名扬!
咏三冲村
□索文梅
斗门胜地誉三冲,古韵今风意未终。
翠影千重山染黛,清波万叠水涵穹。
田园旖旎诗中绘,民俗淳和梦里融。
守正创新承伟绩,桃源胜境焕新容。
斗门春好
□龚远峰
宽敞街衢耳目新,门前百姓叙扶贫。
南窗涵碧尘埃少,北雁横空本性纯。
稚子追看鱼吻月,老妻偏赏鸟迎宾。
现代田园生紫气,扶摇直上满城春。
锅盖栋
□贾成平
珠海排名第二高,夫妻石上白云飘。八方驴友乐逍遥。
青鸟福音传碧海,画眉欢唱隐烟峤。竹林深掩小灵猫。
三冲村即事
□龙斯福
锦绣三冲满院花,金黄稻穗沐朝霞。
村前街巷门牌号,田里渔塘罗氏虾。
闪闪红联留两壁,悠悠雅韵进千家。
民间咸水歌声起,婚娶弘扬传统嘉。
题三冲村孝亲敬老
□刘广大
敬老尊贤意味长,孝亲礼义韵含香。
春晖暖处温情在,德润家门福寿康。
斗门风情
□王洪仁
斗门山水媚,古邑韵绵悠。
民俗千秋颂,莲洲诗意流。
楹联特色村
□李学任
联村携手此深情,雨霁云开碧水呈。
文韵加持增秀色,千重稻菽惠风生。
斗门区三冲村
□张世强
粤海之滨,斗门区内,三冲韵长。
望青山环绕,层林叠翠;炊烟袅袅,碧水汤汤。
荔果盈枝,稻香十里,田舍风光入画廊。
晴阳下,赏村庐错落,诗意徜徉。
淳风厚俗传扬,聚邻里、和谐岁月香。
忆古贤轶事,声声在耳;今朝盛景,历历盈眶。
乐业安居,勤劳致富,共绘乡村锦绣章。
期明日,更繁荣兴旺,再谱辉煌。

□ 何百源
猴子小黑从小个子瘦小,加上受到父母宠溺,成天窝在家里不爱走动,饮食都靠父母供养,因此身体总是很弱,个头比同龄猴子小得多。父母怀疑他有病,猴爸就带他去找猴大夫。
猴大夫对小黑进行了全面体检,又问了相关情况,之后对猴爸说:孩子身体没病,主要是运动量太小,因此发育不良。
为引导小黑多活动,猴爸伤透了脑筋。
一天,猴爸对小黑说,爸妈年纪大了,按照自然规律,照看不了你多少年了。爸妈走了以后,你这样子会饿死的。
懒惰成性的小黑听了,就开始忧虑起来。
一天,猴爸像忽然想起什么,对小黑说,很久以前,我曾经在大森林里见到过一种会结面包的树,不过具体地点想不起了。如果你能找到这种树,以后的日子就不用愁了。
于是小黑就开始了早出晚归地寻找面包树。尽管很辛苦,但为了生存,辛苦也得熬下去。
猴妈就问猴爸,你可是真的见过这样的树?
猴爸附在猴妈耳朵旁悄声说:这是我编造的一种树,目的是让孩子改变不好动的习性,让他身体强壮起来。
小黑漫山遍野地寻找,一次次都失败了。但他坚信父亲的话,立定志向:只要努力,总会找到的。
终于,他真的找到一种树身又粗又大的树,树上吊着许多大面包一样的果实,采下来一尝,果然又香又甜。他高兴坏了,赶忙跑回家告诉爸妈。
这个消息轰动了猴族村民,大家蜂拥着跟着去看,果然是这样。大伙一合计,不如就称这种树为猴面包树吧!
遇见碉楼
□ 张 凯
一张碉楼的图片
望一眼
柔软了心
怎就一个怅然若失
泪流满面
辗转反侧好多个夜晚
它在哪呢
切切在心
必须去看看
是上一世颠沛流离
魂未归乡吗
还是奈何桥前
刻入骨,铭入心
这一世跋山涉水
来到咫尺
却游历半生
也得遇见
从未相逢
却一见如故
怎就是那样的熟悉
一座碉楼
若不是前世的闺房
那堂上的照片
怎就是你的模样
是你吗
这一别
再无挂念


□ 张慧谋
李好的《海在低处》摄影艺术作品展近日在珠海古元美术馆开展,并引起轰动,这是我意料中的事情。策展人通过光影和场景氛围,把李好的这组《海在低处》衬托得淋漓尽致,别具匠心的创意,大大提升了这组摄影作品的艺术效果。策展者是珠海古元美术馆策展部主任庄丽,整个展场的氛围质朴大气,与《海在低处》这组以黑白为主调的摄影艺术作品浑然一体。可见,策展者读懂了李好,读懂了一位摄影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我与李好同在一个纬度的海岸线上出生成长,从小闻着海腥味、听着浪涛声长大,见证了渔人与海的共存,见证了这些年人类与大海的博弈,甚至见证了时间的足迹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流逝,像地里的庄稼一样被海浪收割,又随着潮汐澎湃而生。当若干年前作为摄影爱好者的李好,八进青藏高原完成《朝拜者》系列作品后,在蓦然回首中,他看见了南方那片熟悉的大海,如同一次巅峰高潮过后,他的内心归复平静,回归到海的低处。
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首关于海的诗,其中有句:“……云啊,高高在上,白白的浮云。海在低处,潮汐在低处,渔网挂在低处……”我与李好的年龄有一定差距,当我伏在“海的低处”写诗时,他还在求学之路。当他从高原回望“海的低处”时,我已经完成了与海有关的诗集《渔火把夜色吹白》。
我与李好有个共同点,就是喜欢吃海鲜。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大海的基因,因此在某些方面,形成了海的个性。比如说李好,他是个非常爱冲动的人,喜欢面对挑战,喜欢在浪尖上舞蹈,充满冒险精神。又比如我,喜欢夜色,喜欢海上渔火,面对多变的世界,总是像渔火一样怀抱光芒,冷静得近于无情。我与李好,传承了海的两面性,因为,我们都是大海的儿子。
李好的整个创作过程,我是旁观者,更是知音。摄影和文学是对孪生兄弟,两者之间有距离,但更多的是共通共融,共鸣共感。摄影是以镜头以影像记录生活,文学是以笔以文字书写灵感,但归根到底,摄影和文学展示的都是人性内心世界。从李好的摄影作品里,我常常读到画面文字,甚至读出心跳、读出怜悯、读出沧桑。但我深信,李好读我的文字时,也会读出同样的感觉。
尽管我对李好的摄影作品非常熟悉,但那天在古元美术馆观看《海在低处》时,不仅仅是震撼,更有一种久违的“陌生感”。面对这些黑白照片,我仿佛回到远古的洪荒时代,回到夜与昼的初始期。黑白如此鲜明,几乎把当下眼花缭乱的颜色抽光,只有黑与白,才是永恒的。
是的,李好一直在追求永恒,孤身一人在广袤旷野上行走,在无人随行的漫长海岸线行走。他用他的镜头在建立“一个人的海岸线”,不与他人争道,他走他的独木桥,坚持走下去,哪怕他是这条道上唯一的孤行者。
作品成功与否并非是一个摄影家的唯一标准,没有哪门艺术是可以统一天下人心的,更何况是把自己定格在镜头有限空间的摄影艺术家。李好虽然摘取了国内摄影界最高的“金像奖”,但对于他,仅仅是评委们对他的作品认可和肯定,或者说,这是他摄影生涯的一个新高度新起点。但是,作为旁观者,作为李好认可的亲如兄弟般的老哥,我更看重李好在做什么?做了些什么?
在展馆里陪着我观展的还有《广州文艺》主编、作家张鸿,除了主编、作家身份,张鸿同样是一位资深的摄影家。我与张鸿探讨一个问题,李好这个主题的摄影作品在隐喻着什么?作品背后的那个李好他内心在思考着什么?这才是我和张鸿看展时探讨的话题。
我无法说出李好的这批作品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因为我根本就不懂得摄影艺术的标准和深度,我只知道一幅作品给了我启发和有话可说的感觉,在乎它给我灵魂的震撼和内心的感动,这就足够了。理论是理论家们的话语权,是他们的发现和对摄影标准重构的一个世界,有方向性的指引和境界上的升华。而我,是一个不懂门道只看品质的外行人。我在观看李好的摄影作品时,似乎有一双深邃得难以莫测的“眼睛”在看着我。
我特别在乎看影展时油然而生的这种感觉,或者是作品自身的隐喻,给我带来的这份“陌生感”。
在场的作品都是经过李好精心挑选的,可以说,这是李好从他的几十万张底片里选出几十幅构成《海在低处》主题的摄影作品展,每一张都有着难以拔掉的理由和空间,它们构成的整体,虽然不能绝对代表“海在低处”主题的全部创作,但它们可以撑起这个主题的高度或者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部分。
展出的每幅作品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并且引起强烈共鸣。也许我太熟悉李好的作品了,异常平静地观看,异常平静地品味,异常平静地思考。作品中的场景都是我司空见惯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那么似曾相识,甚至可以叫出他们的辈分和名字。因为看到他们,就想起我的渔民父亲和他的渔民兄弟。这就是大海的基因始终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看见大海在一天天地老去,看到如此庞大无比而又富饶的大海在步步临近贫困线,我在想,物产再丰富的大海也会被无度的掠夺者掏空。当大海仅剩下海水时,人类的生存也难以为继,这绝对不是骇人听闻的预言。
或许,这就是《海在低处》的隐喻和内涵,但愿我的判断和理解是错误的。


□ 谌山石
树一旦被种下
它的一生大概就被注定
也许早早衰老凋零
也许长期绿盖成荫
它没有任何选择权
只能尽自己的可能
与雨雪水火努力抗争
采天地之灵气续命
它成为周遭的风景
也成为变迁的眼睛
那些匆匆来去的身影
那些存在消失的近邻
树总是沉默不语
因为抱怨不如行动
它把根深扎于土地里
它让枝叶与风声和鸣
树处世的态度
触动了我们的神经
都是造物主的棋子
何不善待所有的曾经

□ 潘 泮
老家有个“荔园”,半亩田的大小,原先园子里长的是一些马尾松和野生苦楝树,母亲每天必去园子拾掇,她管着一家的温饱,柴火也很要紧,所以园子被收拾得非常整洁,几乎见不到落叶。现在想来,家有这么个“燃料库”,解了些后顾之忧。
眨眼之间,儿女们个个与老家渐行渐远。母亲一个人依然住在老家,但做饭她已学会用燃气,少了打柴取草的辛劳。自从母亲用上清洁能源,园子里的野草杂树又荒长了起来。母亲曾自问:哪会儿园子里才挂着果呢?
母亲六十岁那年,想改变杂草丛生的园子,但已显得乏力。她只好回到屋前屋后的空地种上三棵果树,到了果熟季节,小院子满眼的火红和金黄,弥漫着果香,这时,母亲就盼着儿女们回来,品尝她的劳动果实。
有一年中秋回家,我觉得家门口的龙眼树遮天蔽日,有时白天也难见天日,母亲长期住在那里,光线实在阴暗,母亲勉强同意我砍去两棵。次年,我们再次回来看望她老人家,这回母亲并不注意儿子长胖了还是瘦了,而是微笑着站在树旁三米远处,看挂满树梢头的荔枝,心里头不知有多甜,老脸也开心得灿烂,继而她又若有所思:“那两棵树还留下来的话,不出一个月,你们还能回来尝龙眼呢。”看来当时母亲的话口是心非啊,望着母亲十分惋惜的样子,我说龙眼大批量上市后,价钱便宜哩,一百块钱的水果全家人能吃个饱!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自言自语:不同样的,不同样的……
老家房子重建时,母亲叮嘱不要损伤那棵荔枝树。我说一定会把荔枝树挪到园子里去保护好,老人家知道是挪树,顿时就紧张起来:“使不得,‘人挪活,树挪死’啊!”我好说歹说,母亲的认知就是伤筋动骨“就怕万一”。我故意气一下母亲,挪开树就建房子,让荔枝树留在原地就不建房子了,二选一吧!话音才落,母亲就服软了。
母亲亲手种下的三棵果树,砍的砍挪的挪,不是搬了头就是搬了家,也难怪母亲心痛。从此以后,母亲每天出去散步,必绕园子经过,驻足园子边看一会儿,荔枝树能不能再长新芽,观察一下能不能再开花结果。当然我也怕母亲的多虑言中,有意在家住了好一段时间,就为给荔枝树输输营养液。一系列的操作后,母亲依然放心不下,每天必在我耳边重复那句:“树缺水了不,缺肥了不?”
荔枝树搬到园子里,母亲走这条坑洼路已成常态,村民行走这路尚觉不便,何况是耄耋老人呢?每当想到母亲要出行散步,我又多了一个担心。后来,硬底化这段路的想法我坚定且果断。平整通行的那一刻,身心一下子无比轻松。原来做好事不仅方便了别人更有益自己。
第一个走过这条路的村民,就谬赞了一番这是“好心路”。打那之后村里小公园种花植树,我都乐此不疲。过了几天,女儿回来见我又黑又瘦还幽默了一番:“干了这一点点的事情,黑成这个样子,哪里还是我爸呀!”“你不觉得爸更像一块铁一块钢吗?”此时,不会说好听话的母亲也破天荒头一次表扬她的儿子:“每天不停不歇的,好在荔枝树没有旱死。”听着这话,好像母亲爱她的荔枝树多一点点。
因为母亲如此爱荔枝,我也把园子里的树全部更换,种上了果树。这天,母亲一直站在那里微笑地看着。
村中路路硬底,连接东西贯通南北,小公园就要竣工了,大姐和小妹相约回来看望老母亲,大姐看着这些变化,话里藏话,都是为那棵老荔枝树吧,然后笑了一笑。
又快到一年荔红时,待到荔枝成熟,母亲准要一个个电话报信的。其实不打电话,我们也会每时每刻惦记着园子里的荔枝树,更惦记着年迈的妈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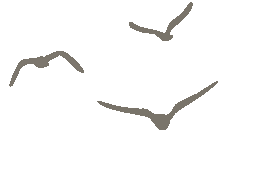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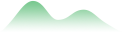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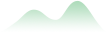
春日访莲洲
□谢成成
炊烟袅袅逸清啼,十里莲洲唱小溪。
巷陌和风攀喜事,家家门上对联齐。
诗意三冲
□黄俊霞
清溪十里绕村庄,两岸洋房映水光。
鱼跃方塘波荡漾,禾翻金浪陌芬芳。
谁家笑语满庭院,入户新联扮靓妆。
最是秋风吹韵起,诗花相伴稻花香。
三冲印象
□宋君
三冲胜境韵悠长,水绕村田稻菽香。
旧巷幽怀联意雅,新楼喜映日华光。
醒狮舞动传风习,画壁呈祥蕴瑞章。
民俗千年情未改,田园画卷韵悠扬。
歌三冲村
□王继荣
翠岭连绵绕白云,重峦叠嶂入天宸。
山清水秀风光好,鸟语花香景色新。
皆悦目,美怡神。自然环境胜仙尘。
此情此景心陶醉,愿做山间一隐人。
过珠海
□叶明增
将军山外锦帆多,九曲蛟龙静卧波。
日月横空争绚烂,烟霞带雨弄婆娑。
千重海岳连三地,百载风云一夕过。
烽火当年堪问取,长天浩渺与谁歌。
思金台寺有感
□涂啸楠
青岭衔云古韵存,金台寺外百花繁。
欲离尘世寻何处,河畔林中隐佛门。
赞三冲村
□张健
曾记三冲初到,满眼风光奇妙。
田野绿波盈,更有古风文藻。
真好,真好,心底醉情难了。
题白藤湖度假区
□张鹏
一处好风光,悠悠放眼量。
峰遥开宿雾,波渺涌朝阳。
闲览鳄鱼闹,欣看蝴蝶狂。
纷纷来去客,远近美名扬!
咏三冲村
□索文梅
斗门胜地誉三冲,古韵今风意未终。
翠影千重山染黛,清波万叠水涵穹。
田园旖旎诗中绘,民俗淳和梦里融。
守正创新承伟绩,桃源胜境焕新容。
斗门春好
□龚远峰
宽敞街衢耳目新,门前百姓叙扶贫。
南窗涵碧尘埃少,北雁横空本性纯。
稚子追看鱼吻月,老妻偏赏鸟迎宾。
现代田园生紫气,扶摇直上满城春。
锅盖栋
□贾成平
珠海排名第二高,夫妻石上白云飘。八方驴友乐逍遥。
青鸟福音传碧海,画眉欢唱隐烟峤。竹林深掩小灵猫。
三冲村即事
□龙斯福
锦绣三冲满院花,金黄稻穗沐朝霞。
村前街巷门牌号,田里渔塘罗氏虾。
闪闪红联留两壁,悠悠雅韵进千家。
民间咸水歌声起,婚娶弘扬传统嘉。
题三冲村孝亲敬老
□刘广大
敬老尊贤意味长,孝亲礼义韵含香。
春晖暖处温情在,德润家门福寿康。
斗门风情
□王洪仁
斗门山水媚,古邑韵绵悠。
民俗千秋颂,莲洲诗意流。
楹联特色村
□李学任
联村携手此深情,雨霁云开碧水呈。
文韵加持增秀色,千重稻菽惠风生。
斗门区三冲村
□张世强
粤海之滨,斗门区内,三冲韵长。
望青山环绕,层林叠翠;炊烟袅袅,碧水汤汤。
荔果盈枝,稻香十里,田舍风光入画廊。
晴阳下,赏村庐错落,诗意徜徉。
淳风厚俗传扬,聚邻里、和谐岁月香。
忆古贤轶事,声声在耳;今朝盛景,历历盈眶。
乐业安居,勤劳致富,共绘乡村锦绣章。
期明日,更繁荣兴旺,再谱辉煌。

□ 何百源
猴子小黑从小个子瘦小,加上受到父母宠溺,成天窝在家里不爱走动,饮食都靠父母供养,因此身体总是很弱,个头比同龄猴子小得多。父母怀疑他有病,猴爸就带他去找猴大夫。
猴大夫对小黑进行了全面体检,又问了相关情况,之后对猴爸说:孩子身体没病,主要是运动量太小,因此发育不良。
为引导小黑多活动,猴爸伤透了脑筋。
一天,猴爸对小黑说,爸妈年纪大了,按照自然规律,照看不了你多少年了。爸妈走了以后,你这样子会饿死的。
懒惰成性的小黑听了,就开始忧虑起来。
一天,猴爸像忽然想起什么,对小黑说,很久以前,我曾经在大森林里见到过一种会结面包的树,不过具体地点想不起了。如果你能找到这种树,以后的日子就不用愁了。
于是小黑就开始了早出晚归地寻找面包树。尽管很辛苦,但为了生存,辛苦也得熬下去。
猴妈就问猴爸,你可是真的见过这样的树?
猴爸附在猴妈耳朵旁悄声说:这是我编造的一种树,目的是让孩子改变不好动的习性,让他身体强壮起来。
小黑漫山遍野地寻找,一次次都失败了。但他坚信父亲的话,立定志向:只要努力,总会找到的。
终于,他真的找到一种树身又粗又大的树,树上吊着许多大面包一样的果实,采下来一尝,果然又香又甜。他高兴坏了,赶忙跑回家告诉爸妈。
这个消息轰动了猴族村民,大家蜂拥着跟着去看,果然是这样。大伙一合计,不如就称这种树为猴面包树吧!
遇见碉楼
□ 张 凯
一张碉楼的图片
望一眼
柔软了心
怎就一个怅然若失
泪流满面
辗转反侧好多个夜晚
它在哪呢
切切在心
必须去看看
是上一世颠沛流离
魂未归乡吗
还是奈何桥前
刻入骨,铭入心
这一世跋山涉水
来到咫尺
却游历半生
也得遇见
从未相逢
却一见如故
怎就是那样的熟悉
一座碉楼
若不是前世的闺房
那堂上的照片
怎就是你的模样
是你吗
这一别
再无挂念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