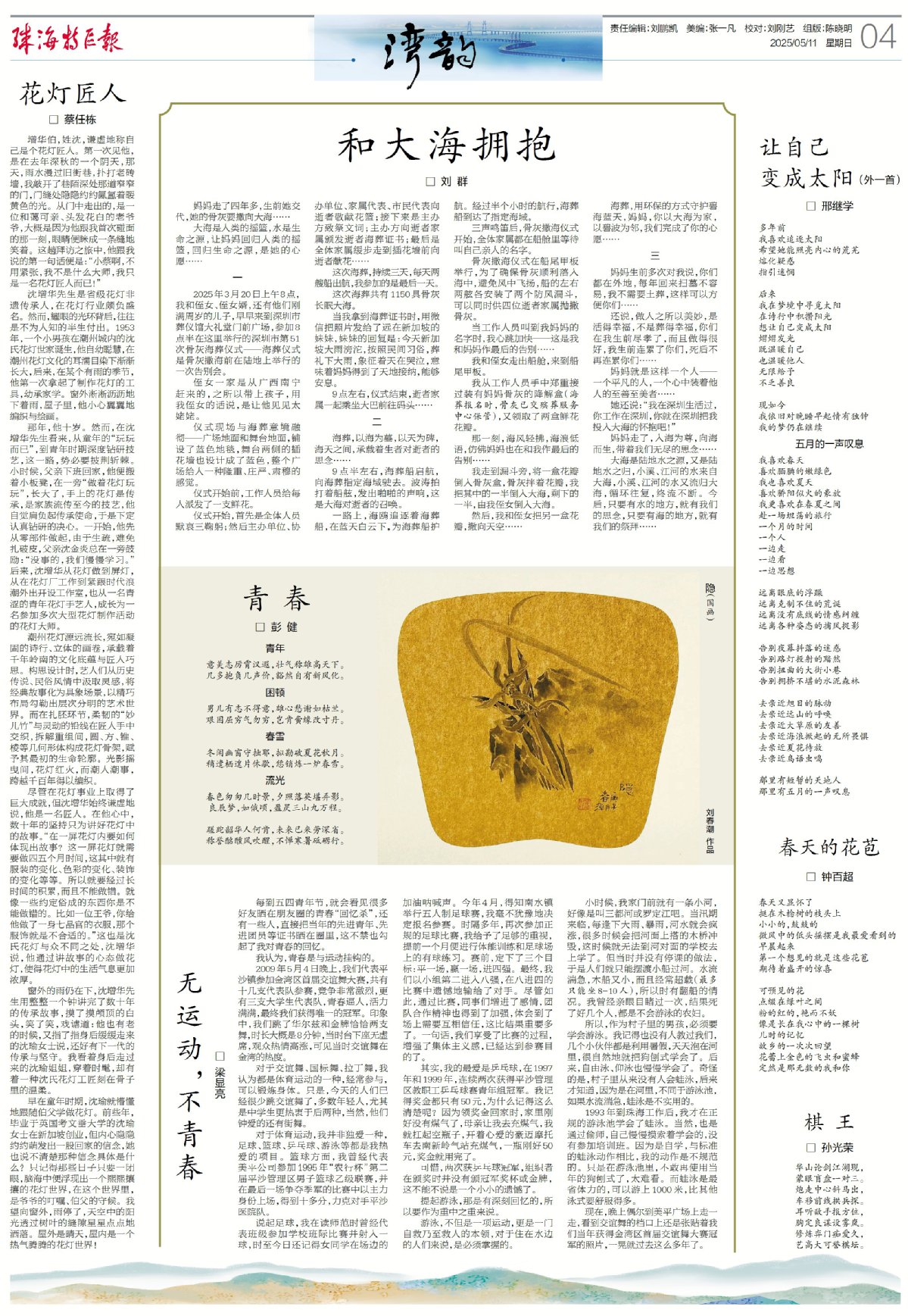
和大海拥抱
□ 刘 群
妈妈走了四年多,生前她交代,她的骨灰要撒向大海……
大海是人类的摇篮,水是生命之源,让妈妈回归人类的摇篮,回归生命之源,是她的心愿……
一
2025年3月20日上午8点,我和侄女、侄女婿,还有他们刚满周岁的儿子,早早来到深圳市葬仪馆大礼堂门前广场,参加8点半在这里举行的深圳市第51次骨灰海葬仪式——海葬仪式是骨灰撒海前在陆地上举行的一次告别会。
侄女一家是从广西南宁赶来的,之所以带上孩子,用我侄女的话说,是让他见见太姥姥。
仪式现场与海葬意境融彻——广场地面和舞台地面,铺设了蓝色地毯,舞台两侧的插花墙也设计成了蓝色,整个广场给人一种隆重、庄严、肃穆的感觉。
仪式开始前,工作人员给每人派发了一支鲜花。
仪式开始,首先是全体人员默哀三鞠躬;然后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家属代表、市民代表向逝者敬献花篮;接下来是主办方致祭文词;主办方向逝者家属颁发逝者海葬证书;最后是全体家属缓步走到插花墙前向逝者献花……
这次海葬,持续三天,每天两艘船出航,我参加的是最后一天。
这次海葬共有1150具骨灰长眠大海。
当我拿到海葬证书时,用微信把照片发给了远在新加坡的妹妹,妹妹的回复是:今天新加坡大雨滂沱,按照民间习俗,葬礼下大雨,象征着天在哭泣,意味着妈妈得到了天地接纳,能够安息。
9点左右,仪式结束,逝者家属一起乘坐大巴前往码头……
二
海葬,以海为墓,以天为碑,海天之间,承载着生者对逝者的思念……
9点半左右,海葬船启航,向海葬指定海域驶去。波涛拍打着船舷,发出啪啪的声响,这是大海对逝者的召唤。
一路上,海鸥追逐着海葬船,在蓝天白云下,为海葬船护航。经过半个小时的航行,海葬船到达了指定海域。
三声鸣笛后,骨灰撒海仪式开始,全体家属都在船舱里等待叫自己亲人的名字。
骨灰撒海仪式在船尾甲板举行,为了确保骨灰顺利落入海中,避免风中飞扬,船的左右两舷各安装了两个防风漏斗,可以同时供四位逝者家属抛撒骨灰。
当工作人员叫到我妈妈的名字时,我心跳加快——这是我和妈妈作最后的告别……
我和侄女走出船舱,来到船尾甲板。
我从工作人员手中郑重接过装有妈妈骨灰的降解盒(海葬报名时,骨灰已交殡葬服务中心保管),又领取了两盒鲜花花瓣。
那一刻,海风轻拂,海浪低语,仿佛妈妈也在和我作最后的告别……
我走到漏斗旁,将一盒花瓣倒入骨灰盒,骨灰拌着花瓣,我把其中的一半倒入大海,剩下的一半,由我侄女倒入大海。
然后,我和侄女把另一盒花瓣,撒向天空……
海葬,用环保的方式守护碧海蓝天,妈妈,你以大海为家,以碧波为邻,我们完成了你的心愿……
三
妈妈生前多次对我说,你们都在外地,每年回来扫墓不容易,我不需要土葬,这样可以方便你们……
还说,做人之所以美妙,是活得幸福,不是葬得幸福,你们在我生前尽孝了,而且做得很好,我生前连累了你们,死后不再连累你们……
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心中装着他人的至善至美者……
她还说:“我在深圳生活过,你工作在深圳,你就在深圳把我投入大海的怀抱吧!”
妈妈走了,入海为尊,向海而生,带着我们无尽的思念……
大海是陆地水之源,又是陆地水之归,小溪、江河的水来自大海,小溪、江河的水又流归大海,循环往复,终流不断。今后,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我们的思念,只要有海的地方,就有我们的祭拜……

花灯匠人
□ 蔡任栋
增华伯,姓沈,谦虚地称自己是个花灯匠人。第一次见他,是在去年深秋的一个阴天,那天,雨水漫过旧街巷,扑打老砖墙,我敲开了巷陌深处那道窄窄的门,门缝处隐隐约约氤氲着暖黄色的光。从门中走出的,是一位和蔼可亲、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大概是因为他跟我首次碰面的那一刻,眼睛便眯成一条缝地笑着。这趟拜访之旅中,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小蔡啊,不用紧张,我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一名花灯匠人而已!”
沈增华先生是省级花灯非遗传承人,在花灯行业颇负盛名。然而,耀眼的光环背后,往往是不为人知的半生付出。1953年,一个小男孩在潮州城内的沈氏花灯世家诞生,他自幼聪慧,在潮州花灯文化的耳濡目染下渐渐长大,后来,在某个有雨的季节,他第一次拿起了制作花灯的工具,幼承家学。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屋子里,他小心翼翼地编织与绘画。
那年,他十岁。然而,在沈增华先生看来,从童年的“玩玩而已”,到青年时期深度钻研技艺,这一路,势必要披荆斩棘。小时候,父亲下班回家,他便搬着小板凳,在一旁“做着花灯玩玩”,长大了,手上的花灯是传承,是家族流传至今的技艺,他自觉肩负起传承使命,于是下定认真钻研的决心。一开始,他先从零部件做起,由于生疏,难免扎破皮,父亲沈金炎总在一旁鼓励:“没事的,我们慢慢学习。”后来,沈增华从花灯做到屏灯,从在花灯厂工作到紧跟时代浪潮外出开设工作室,也从一名青涩的青年花灯手艺人,成长为一名参加多次大型花灯制作活动的花灯大师。
潮州花灯源远流长,宛如凝固的诗行、立体的画卷,承载着千年岭南的文化底蕴与匠人巧思。构思设计时,艺人们从历史传说、民俗风情中汲取灵感,将经典故事化为具象场景,以精巧布局勾勒出层次分明的艺术世界。而在扎胚环节,柔韧的“妙儿竹”与灵动的铅线在匠人手中交织,拆解重组间,圆、方、锥、棱等几何形体构成花灯骨架,赋予其最初的生命轮廓。光影摇曳间,花灯红火,而潮人潮事,跨越千百年得以编织。
尽管在花灯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沈增华始终谦虚地说,他是一名匠人。在他心中,数十年的坚持只为讲好花灯中的故事。“在一屏花灯内要如何体现出故事?这一屏花灯就需要做四五个月时间,这其中就有服装的变化、色彩的变化、装饰的变化等等。所以就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而且不能做错。就像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你是不能做错的。比如一位王爷,你给他做了一身七品官的衣服,那个服饰就是不合适的。”这也是沈氏花灯与众不同之处,沈增华说,他通过讲故事的心态做花灯,使得花灯中的生活气息更加浓厚。
窗外的雨仍在下,沈增华先生用整整一个钟讲完了数十年的传承故事,摸了摸颅顶的白头,笑了笑,戏谑道:他也有老的时候,又指了指身后缓缓走来的沈瑜女士说,还好有下一代的传承与坚守。我看着身后走过来的沈瑜姐姐,穿着时髦,却有着一种沈氏花灯工匠刻在骨子里的温柔。
早在童年时期,沈瑜就懵懂地跟随伯父学做花灯。前些年,毕业于英国考文垂大学的沈瑜女士在新加坡创业,但内心隐隐约约萌发出一股回家的信念,她也说不清楚那种信念具体是什么?只记得那些日子只要一闭眼,脑海中便浮现出一个熙熙攘攘的花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是爷爷的叮嘱、伯父的守候。我望向窗外,雨停了,天空中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星星点点地洒落。屋外是晴天,屋内是一个热气腾腾的花灯世界!

青 春
□ 彭 健
青年
意美志厉霄汉遐,壮气称雄高天下。
几多抱负几声价,豁然自有新风化。
困顿
男儿有志不得意,雄心愁谢如枯兰。
艰困屈穷气勿穷,岂肯夤缘改寸丹。
春雪
冬闲幽窗守拙耶,拟勘破夏花秋月。
稍遣栖遑片休歇,恁销炼一炉春雪。
流光
春色匆匆几时景,夕照落英堪弄影。
良辰梦,如俄顷,盈昃三山九万程。
蹉跎韶华人何肯,未来已来劳深省。
称誉酩醺风吹醒,不惮寒暑砥砺行。



无运动,不青春
□ 梁显亮
每到五四青年节,就会看见很多好友晒在朋友圈的青春“回忆杀”,还有一些人,直接把当年的先进青年、先进团员等证书晒在圈里,这不禁也勾起了我对青春的回忆。
我认为,青春是与运动挂钩的。
2009年5月4日晚上,我们代表平沙镇参加金湾区首届交谊舞大赛,共有十几支代表队参赛,竞争非常激烈,更有三支大学生代表队,青春逼人,活力满满,最终我们获得唯一的冠军。印象中,我们跳了华尔兹和金牌恰恰两支舞,时长大概是8分钟,当时台下座无虚席,观众热情高涨,可见当时交谊舞在金湾的热度。
对于交谊舞、国标舞、拉丁舞,我认为都是体育运动的一种,经常参与,可以锻炼身体。只是,今天的人们已经很少跳交谊舞了,多数年轻人,尤其是中学生更热衷于后两种,当然,他们钟爱的还有街舞。
对于体育运动,我并非独爱一种,足球、篮球、乒乓球、游泳等都是我热爱的项目。篮球方面,我曾经代表美平公司参加1995年“农行杯”第二届平沙管理区男子篮球乙级联赛,并在最后一场争夺季军的比赛中以主力身份上场,得到十多分,力克对手平沙医院队。
说起足球,我在读师范时曾经代表班级参加学校班际比赛并射入一球,时至今日还记得女同学在场边的加油呐喊声。今年4月,得知南水镇举行五人制足球赛,我毫不犹豫地决定报名参赛。时隔多年,再次参加正规的足球比赛,我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提前一个月便进行体能训练和足球场上的有球练习。赛前,定下了三个目标:平一场,赢一场,进四强。最终,我们以小组第二进入八强,在八进四的比赛中遗憾地输给了对手。尽管如此,通过比赛,同事们增进了感情,团队合作精神也得到了加强,体会到了场上需要互相信任,这比结果重要多了。一句话,我们享受了比赛的过程,增强了集体主义感,已经达到参赛目的了。
其实,我的最爱是乒乓球,在1997年和1999年,连续两次获得平沙管理区教职工乒乓球赛青年组冠军。我记得奖金都只有50元,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领奖金回家时,家里刚好没有煤气了,母亲让我去充煤气,我就扛起空瓶子,开着心爱的豪迈摩托车去南新岭气站充煤气,一瓶刚好50元,奖金就用完了。
可惜,两次获乒乓球冠军,组织者在颁奖时并没有颁冠军奖杯或金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了。
提起游泳,那是有深刻回忆的,所以要作为重中之重来说。
游泳,不但是一项运动,更是一门自救乃至救人的本领,对于住在水边的人们来说,是必须掌握的。
小时候,我家门前就有一条小河,好像是叫三都河或罗定江吧。当汛期来临,每逢下大雨、暴雨,河水就会疯涨,很多时候会把河面上搭的木桥冲毁,这时候就无法到河对面的学校去上学了。但当时并没有停课的做法,于是人们就只能摆渡小船过河。水流湍急,木船又小,而且经常超载(最多只能坐8-10人),所以时有翻船的情况。我曾经亲眼目睹过一次,结果死了好几个人,都是不会游泳的农妇。
所以,作为村子里的男孩,必须要学会游泳。我记得也没有人教过我们,几个小伙伴都是利用暑假,天天泡在河里,很自然地就把狗刨式学会了。后来,自由泳、仰泳也慢慢学会了。奇怪的是,村子里从来没有人会蛙泳,后来才知道,因为是在河里,不同于游泳池,如果水流湍急,蛙泳是不实用的。
1993年到珠海工作后,我才在正规的游泳池学会了蛙泳。当然,也是通过偷师,自己慢慢摸索着学会的,没有参加培训班。因为是自学,与标准的蛙泳动作相比,我的动作是不规范的。只是在游泳池里,不敢再使用当年的狗刨式了,太难看。而蛙泳是最省体力的,可以游上1000米,比其他泳式要舒服得多。
现在,晚上偶尔到美平广场上走一走,看到交谊舞的档口上还是张贴着我们当年获得金湾区首届交谊舞大赛冠军的照片,一晃就过去这么多年了。

让自己变成太阳(外一首)
□ 邢继学
多年前
我喜欢追逐太阳
希望她能照亮内心的荒芜
熔化疑惑
指引迷惘
后来
我在梦境中寻觅太阳
在诗行中积攒阳光
想让自己变成太阳
熠熠发光
既温暖自己
也温暖他人
无限给予
不乏善良
现如今
我依旧对晚睡早起情有独钟
我的梦仍在继续
五月的一声叹息
我喜欢春天
喜欢腼腆的嫩绿色
我也喜欢夏天
喜欢骄阳似火的豪放
我更喜欢在春夏之间
赴一场坦荡的旅行
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人
一边走
一边看
一边思想
远离眼底的浮躁
远离克制不住的荒诞
远离没有底线的情感纠缠
远离各种姿态的捕风捉影
告别夜幕抖落的迷惑
告别路灯投射的黯然
告别扭曲的大街小巷
告别拥挤不堪的水泥森林
去亲近旭日的脉动
去亲近远山的呼唤
去亲近大草原的友善
去亲近海浪掀起的无所畏惧
去亲近夏花待放
去亲近鸟语虫鸣
那里有短暂的天地人
那里有五月的一声叹息

春天的花苞
□ 钟百超
春天又显怀了
挺在木棯树的枝头上
小小的,鼓鼓的
微风中的低头摇摆是我最爱看到的
早晨起来
第一个想见的就是这些花苞
期待着盛开的惊喜
可预见的花
点缀在绿叶之间
粉的红的,艳而不妖
像是长在我心中的一棵树
儿时的记忆
故乡的一次次回望
花蕾上金色的飞虫和蜜蜂
定然是那无数的我和你

棋 王
□ 孙光荣
华山论剑江湖现,
蒙眼盲盘一对三。
炮走中心斜马岀,
车移前线拱兵探。
耳听敌手报方位,
胸定良谋设雾岚。
修炼弈门痴爱久,
艺高大可誉棋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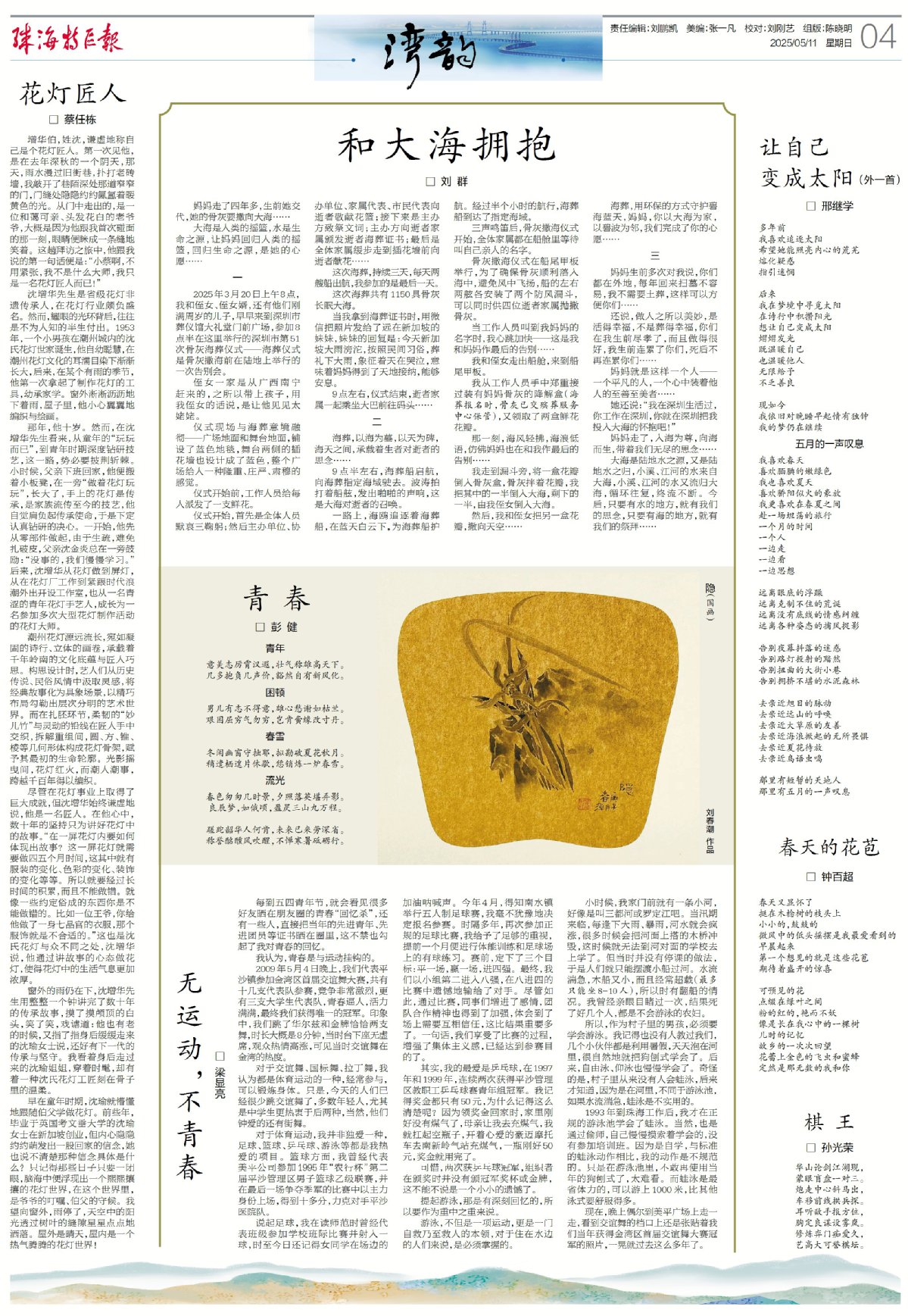
和大海拥抱
□ 刘 群
妈妈走了四年多,生前她交代,她的骨灰要撒向大海……
大海是人类的摇篮,水是生命之源,让妈妈回归人类的摇篮,回归生命之源,是她的心愿……
一
2025年3月20日上午8点,我和侄女、侄女婿,还有他们刚满周岁的儿子,早早来到深圳市葬仪馆大礼堂门前广场,参加8点半在这里举行的深圳市第51次骨灰海葬仪式——海葬仪式是骨灰撒海前在陆地上举行的一次告别会。
侄女一家是从广西南宁赶来的,之所以带上孩子,用我侄女的话说,是让他见见太姥姥。
仪式现场与海葬意境融彻——广场地面和舞台地面,铺设了蓝色地毯,舞台两侧的插花墙也设计成了蓝色,整个广场给人一种隆重、庄严、肃穆的感觉。
仪式开始前,工作人员给每人派发了一支鲜花。
仪式开始,首先是全体人员默哀三鞠躬;然后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家属代表、市民代表向逝者敬献花篮;接下来是主办方致祭文词;主办方向逝者家属颁发逝者海葬证书;最后是全体家属缓步走到插花墙前向逝者献花……
这次海葬,持续三天,每天两艘船出航,我参加的是最后一天。
这次海葬共有1150具骨灰长眠大海。
当我拿到海葬证书时,用微信把照片发给了远在新加坡的妹妹,妹妹的回复是:今天新加坡大雨滂沱,按照民间习俗,葬礼下大雨,象征着天在哭泣,意味着妈妈得到了天地接纳,能够安息。
9点左右,仪式结束,逝者家属一起乘坐大巴前往码头……
二
海葬,以海为墓,以天为碑,海天之间,承载着生者对逝者的思念……
9点半左右,海葬船启航,向海葬指定海域驶去。波涛拍打着船舷,发出啪啪的声响,这是大海对逝者的召唤。
一路上,海鸥追逐着海葬船,在蓝天白云下,为海葬船护航。经过半个小时的航行,海葬船到达了指定海域。
三声鸣笛后,骨灰撒海仪式开始,全体家属都在船舱里等待叫自己亲人的名字。
骨灰撒海仪式在船尾甲板举行,为了确保骨灰顺利落入海中,避免风中飞扬,船的左右两舷各安装了两个防风漏斗,可以同时供四位逝者家属抛撒骨灰。
当工作人员叫到我妈妈的名字时,我心跳加快——这是我和妈妈作最后的告别……
我和侄女走出船舱,来到船尾甲板。
我从工作人员手中郑重接过装有妈妈骨灰的降解盒(海葬报名时,骨灰已交殡葬服务中心保管),又领取了两盒鲜花花瓣。
那一刻,海风轻拂,海浪低语,仿佛妈妈也在和我作最后的告别……
我走到漏斗旁,将一盒花瓣倒入骨灰盒,骨灰拌着花瓣,我把其中的一半倒入大海,剩下的一半,由我侄女倒入大海。
然后,我和侄女把另一盒花瓣,撒向天空……
海葬,用环保的方式守护碧海蓝天,妈妈,你以大海为家,以碧波为邻,我们完成了你的心愿……
三
妈妈生前多次对我说,你们都在外地,每年回来扫墓不容易,我不需要土葬,这样可以方便你们……
还说,做人之所以美妙,是活得幸福,不是葬得幸福,你们在我生前尽孝了,而且做得很好,我生前连累了你们,死后不再连累你们……
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心中装着他人的至善至美者……
她还说:“我在深圳生活过,你工作在深圳,你就在深圳把我投入大海的怀抱吧!”
妈妈走了,入海为尊,向海而生,带着我们无尽的思念……
大海是陆地水之源,又是陆地水之归,小溪、江河的水来自大海,小溪、江河的水又流归大海,循环往复,终流不断。今后,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我们的思念,只要有海的地方,就有我们的祭拜……

花灯匠人
□ 蔡任栋
增华伯,姓沈,谦虚地称自己是个花灯匠人。第一次见他,是在去年深秋的一个阴天,那天,雨水漫过旧街巷,扑打老砖墙,我敲开了巷陌深处那道窄窄的门,门缝处隐隐约约氤氲着暖黄色的光。从门中走出的,是一位和蔼可亲、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大概是因为他跟我首次碰面的那一刻,眼睛便眯成一条缝地笑着。这趟拜访之旅中,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小蔡啊,不用紧张,我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一名花灯匠人而已!”
沈增华先生是省级花灯非遗传承人,在花灯行业颇负盛名。然而,耀眼的光环背后,往往是不为人知的半生付出。1953年,一个小男孩在潮州城内的沈氏花灯世家诞生,他自幼聪慧,在潮州花灯文化的耳濡目染下渐渐长大,后来,在某个有雨的季节,他第一次拿起了制作花灯的工具,幼承家学。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屋子里,他小心翼翼地编织与绘画。
那年,他十岁。然而,在沈增华先生看来,从童年的“玩玩而已”,到青年时期深度钻研技艺,这一路,势必要披荆斩棘。小时候,父亲下班回家,他便搬着小板凳,在一旁“做着花灯玩玩”,长大了,手上的花灯是传承,是家族流传至今的技艺,他自觉肩负起传承使命,于是下定认真钻研的决心。一开始,他先从零部件做起,由于生疏,难免扎破皮,父亲沈金炎总在一旁鼓励:“没事的,我们慢慢学习。”后来,沈增华从花灯做到屏灯,从在花灯厂工作到紧跟时代浪潮外出开设工作室,也从一名青涩的青年花灯手艺人,成长为一名参加多次大型花灯制作活动的花灯大师。
潮州花灯源远流长,宛如凝固的诗行、立体的画卷,承载着千年岭南的文化底蕴与匠人巧思。构思设计时,艺人们从历史传说、民俗风情中汲取灵感,将经典故事化为具象场景,以精巧布局勾勒出层次分明的艺术世界。而在扎胚环节,柔韧的“妙儿竹”与灵动的铅线在匠人手中交织,拆解重组间,圆、方、锥、棱等几何形体构成花灯骨架,赋予其最初的生命轮廓。光影摇曳间,花灯红火,而潮人潮事,跨越千百年得以编织。
尽管在花灯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沈增华始终谦虚地说,他是一名匠人。在他心中,数十年的坚持只为讲好花灯中的故事。“在一屏花灯内要如何体现出故事?这一屏花灯就需要做四五个月时间,这其中就有服装的变化、色彩的变化、装饰的变化等等。所以就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而且不能做错。就像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你是不能做错的。比如一位王爷,你给他做了一身七品官的衣服,那个服饰就是不合适的。”这也是沈氏花灯与众不同之处,沈增华说,他通过讲故事的心态做花灯,使得花灯中的生活气息更加浓厚。
窗外的雨仍在下,沈增华先生用整整一个钟讲完了数十年的传承故事,摸了摸颅顶的白头,笑了笑,戏谑道:他也有老的时候,又指了指身后缓缓走来的沈瑜女士说,还好有下一代的传承与坚守。我看着身后走过来的沈瑜姐姐,穿着时髦,却有着一种沈氏花灯工匠刻在骨子里的温柔。
早在童年时期,沈瑜就懵懂地跟随伯父学做花灯。前些年,毕业于英国考文垂大学的沈瑜女士在新加坡创业,但内心隐隐约约萌发出一股回家的信念,她也说不清楚那种信念具体是什么?只记得那些日子只要一闭眼,脑海中便浮现出一个熙熙攘攘的花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是爷爷的叮嘱、伯父的守候。我望向窗外,雨停了,天空中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星星点点地洒落。屋外是晴天,屋内是一个热气腾腾的花灯世界!

青 春
□ 彭 健
青年
意美志厉霄汉遐,壮气称雄高天下。
几多抱负几声价,豁然自有新风化。
困顿
男儿有志不得意,雄心愁谢如枯兰。
艰困屈穷气勿穷,岂肯夤缘改寸丹。
春雪
冬闲幽窗守拙耶,拟勘破夏花秋月。
稍遣栖遑片休歇,恁销炼一炉春雪。
流光
春色匆匆几时景,夕照落英堪弄影。
良辰梦,如俄顷,盈昃三山九万程。
蹉跎韶华人何肯,未来已来劳深省。
称誉酩醺风吹醒,不惮寒暑砥砺行。



无运动,不青春
□ 梁显亮
每到五四青年节,就会看见很多好友晒在朋友圈的青春“回忆杀”,还有一些人,直接把当年的先进青年、先进团员等证书晒在圈里,这不禁也勾起了我对青春的回忆。
我认为,青春是与运动挂钩的。
2009年5月4日晚上,我们代表平沙镇参加金湾区首届交谊舞大赛,共有十几支代表队参赛,竞争非常激烈,更有三支大学生代表队,青春逼人,活力满满,最终我们获得唯一的冠军。印象中,我们跳了华尔兹和金牌恰恰两支舞,时长大概是8分钟,当时台下座无虚席,观众热情高涨,可见当时交谊舞在金湾的热度。
对于交谊舞、国标舞、拉丁舞,我认为都是体育运动的一种,经常参与,可以锻炼身体。只是,今天的人们已经很少跳交谊舞了,多数年轻人,尤其是中学生更热衷于后两种,当然,他们钟爱的还有街舞。
对于体育运动,我并非独爱一种,足球、篮球、乒乓球、游泳等都是我热爱的项目。篮球方面,我曾经代表美平公司参加1995年“农行杯”第二届平沙管理区男子篮球乙级联赛,并在最后一场争夺季军的比赛中以主力身份上场,得到十多分,力克对手平沙医院队。
说起足球,我在读师范时曾经代表班级参加学校班际比赛并射入一球,时至今日还记得女同学在场边的加油呐喊声。今年4月,得知南水镇举行五人制足球赛,我毫不犹豫地决定报名参赛。时隔多年,再次参加正规的足球比赛,我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提前一个月便进行体能训练和足球场上的有球练习。赛前,定下了三个目标:平一场,赢一场,进四强。最终,我们以小组第二进入八强,在八进四的比赛中遗憾地输给了对手。尽管如此,通过比赛,同事们增进了感情,团队合作精神也得到了加强,体会到了场上需要互相信任,这比结果重要多了。一句话,我们享受了比赛的过程,增强了集体主义感,已经达到参赛目的了。
其实,我的最爱是乒乓球,在1997年和1999年,连续两次获得平沙管理区教职工乒乓球赛青年组冠军。我记得奖金都只有50元,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领奖金回家时,家里刚好没有煤气了,母亲让我去充煤气,我就扛起空瓶子,开着心爱的豪迈摩托车去南新岭气站充煤气,一瓶刚好50元,奖金就用完了。
可惜,两次获乒乓球冠军,组织者在颁奖时并没有颁冠军奖杯或金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了。
提起游泳,那是有深刻回忆的,所以要作为重中之重来说。
游泳,不但是一项运动,更是一门自救乃至救人的本领,对于住在水边的人们来说,是必须掌握的。
小时候,我家门前就有一条小河,好像是叫三都河或罗定江吧。当汛期来临,每逢下大雨、暴雨,河水就会疯涨,很多时候会把河面上搭的木桥冲毁,这时候就无法到河对面的学校去上学了。但当时并没有停课的做法,于是人们就只能摆渡小船过河。水流湍急,木船又小,而且经常超载(最多只能坐8-10人),所以时有翻船的情况。我曾经亲眼目睹过一次,结果死了好几个人,都是不会游泳的农妇。
所以,作为村子里的男孩,必须要学会游泳。我记得也没有人教过我们,几个小伙伴都是利用暑假,天天泡在河里,很自然地就把狗刨式学会了。后来,自由泳、仰泳也慢慢学会了。奇怪的是,村子里从来没有人会蛙泳,后来才知道,因为是在河里,不同于游泳池,如果水流湍急,蛙泳是不实用的。
1993年到珠海工作后,我才在正规的游泳池学会了蛙泳。当然,也是通过偷师,自己慢慢摸索着学会的,没有参加培训班。因为是自学,与标准的蛙泳动作相比,我的动作是不规范的。只是在游泳池里,不敢再使用当年的狗刨式了,太难看。而蛙泳是最省体力的,可以游上1000米,比其他泳式要舒服得多。
现在,晚上偶尔到美平广场上走一走,看到交谊舞的档口上还是张贴着我们当年获得金湾区首届交谊舞大赛冠军的照片,一晃就过去这么多年了。

让自己变成太阳(外一首)
□ 邢继学
多年前
我喜欢追逐太阳
希望她能照亮内心的荒芜
熔化疑惑
指引迷惘
后来
我在梦境中寻觅太阳
在诗行中积攒阳光
想让自己变成太阳
熠熠发光
既温暖自己
也温暖他人
无限给予
不乏善良
现如今
我依旧对晚睡早起情有独钟
我的梦仍在继续
五月的一声叹息
我喜欢春天
喜欢腼腆的嫩绿色
我也喜欢夏天
喜欢骄阳似火的豪放
我更喜欢在春夏之间
赴一场坦荡的旅行
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人
一边走
一边看
一边思想
远离眼底的浮躁
远离克制不住的荒诞
远离没有底线的情感纠缠
远离各种姿态的捕风捉影
告别夜幕抖落的迷惑
告别路灯投射的黯然
告别扭曲的大街小巷
告别拥挤不堪的水泥森林
去亲近旭日的脉动
去亲近远山的呼唤
去亲近大草原的友善
去亲近海浪掀起的无所畏惧
去亲近夏花待放
去亲近鸟语虫鸣
那里有短暂的天地人
那里有五月的一声叹息

春天的花苞
□ 钟百超
春天又显怀了
挺在木棯树的枝头上
小小的,鼓鼓的
微风中的低头摇摆是我最爱看到的
早晨起来
第一个想见的就是这些花苞
期待着盛开的惊喜
可预见的花
点缀在绿叶之间
粉的红的,艳而不妖
像是长在我心中的一棵树
儿时的记忆
故乡的一次次回望
花蕾上金色的飞虫和蜜蜂
定然是那无数的我和你

棋 王
□ 孙光荣
华山论剑江湖现,
蒙眼盲盘一对三。
炮走中心斜马岀,
车移前线拱兵探。
耳听敌手报方位,
胸定良谋设雾岚。
修炼弈门痴爱久,
艺高大可誉棋坛。

-我已经到底线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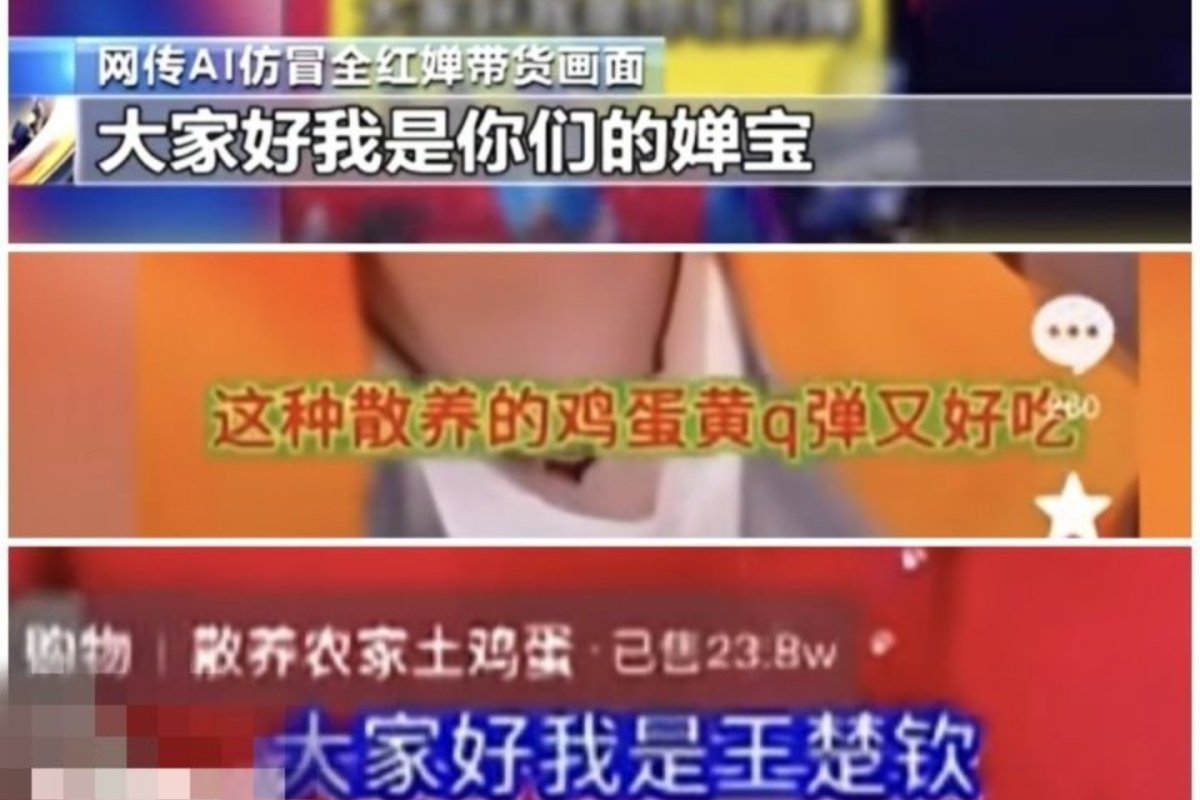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