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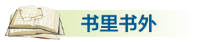
落单者的似锦繁花
——读强雯中短篇小说集《石燕》
□凸凹
“闲言少叙,却说宝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落单,也不和人玩耍,每到晚间,便索然睡了。”《红楼梦》第十三回里写到的落单者,较之强雯中短篇小说集《石燕》(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写的,其人数及落单原因,都要单一得多,单纯得多。集子由《石燕》《百万风景》两个中篇和《功德碗》等五个短篇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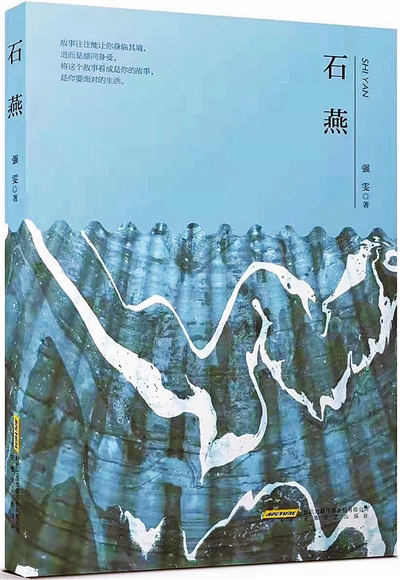
七件作品,七类人物,七种故事,同居一书,却各各不同,独守一格,自成气象。这是一本什么书、什么类型、什么题材?书前书后,里里外外,编者没有提示词,作者没有后记语,按说,如此纷繁文况,要让自带主张、多有定见的读者,从中提拎出大家伙儿共认的一宗主旨,一个公切点出来,是有难度的。进一步说,如果连作者、编者自个儿都无法办到,那就纯粹是对好事者开的一个玩笑,设下的永远走不出的迷宫。但细读全书,稍作梳理、归纳,还是会发现七件作品的一些共性的。
小说的时空坐标,定制在民国至当下的重庆地区。具体而言,时间主要为抗战时期、新旧社会改朝换代节点以及城乡嬗变的城市化过程中,地理坐标基本为长江流域的城镇。小说的故事生发、铺衍与集束,皆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七情六欲,生老病死,尤其人与人(男女、同事、同学、邻里、上下级尤其家人间)的关系与纠结——那些灵肉相处中的小欢乐、小平和与小尴尬。作者特别擅长刻画人物内心,织锦刺绣一般,将奔走在视线之外的至爱、忌恨、狂欢、战争、幺蛾子、小九九,编排成锦绣文章,悬挂炫目展厅。她也不乏高强的语言教养和文学感应异质稟赋,尤其对感觉的具象化,对外物的虚拟化,可谓自由进出,呼风唤雨,信手拈来。正是在这种将空/无坐成实/有,将实/有坐成空/无的魔术与手段,让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灿烂,一种欲说还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文辞魅力与思想魅力。
读强雯的小说,你会发现她对文物、寺庙、花草、绘画、衣饰,以及重庆大街闾巷各色人等,都很熟络和热络,状写起来得心应手,栩栩如生,让人身临其境,读文即睹物。去年盛夏,在川渝环境主题采风活动上,我认识了她,但对她的过往经历不甚了解,但我相信她对这些物事的认知,与它们的共情,应该是跟她的个人经历以及经历赋予的个体经验和个人爱好有关。书房中的知识好办,闭门谢客,凿壁偷光,头悬梁锥刺骨,埋首苦研即可,大地上的经历就不好办了。成功学读得再透,名人传读得再多,有用吗?等你读毕又想起去学事主的经历时,才发现年龄、时代背景、地缘、家室、人际、身体、性别、性格,等等方面,这不适合那不合适,出入太大,完全无法依葫芦画瓢,一蹴而就。小说不是知识的教科书,但它是为知识提供人味、细节、时空和故事的神。小说是知识、经历与文学天赋的媾合,三位一体,不可或缺。没有经历或经历不够的小说家,飞得再高再远,也是飘的,因为没有自己的发生地与母根。
我相信,以上是读者和业界人士的共识。我更相信,这本书还有一条脉向,是对落单者群像的小说集合。换言之,落单者,是七件小说共通的纠缠对象、追述主体。
七件作品中的男主或女主,自有其具体的落单理由。《石燕》中的文物修复师华绵,是因为对战时歌乐山保育院的沉溺,对文物遭遇的疼痛;《百万风景》中的艾云丽一家,是对家乡小镇的被出走与不舍乡愁,对贫民窟老巷旁一夜间传奇般冒出的“百万小区”的不解、惊惶与羡慕忌妒恨;在《功德碗》中,是因为武陵山农妇、史家大院暂住客白桂,对封建婚姻的致命反抗,并借她的眼睛,让我们感知到的史家老太太对动乱时局的恐惧,以及两人面对未来所做的不同的噩梦;而《清洁》中的慈云寺拓片抄写者、青年小海,则是因为对老家应县文物木塔和母爱的惦记,对尘世物欲和肉欲的厌恶与压抑;《水彩课》中女儿“我”眼中的长得好看又颇具画才的“父亲”,是因为个人命运在家国命运中发生了断崖式陡转,理想幻灭,难以为继。《单行道》中的职高美术教师陶玉丹,是因为性格乖僻,对家庭、社会的逆反,而一直走在自己人生的单行道上;《旗袍》中的时年46岁、单位中层贵妇高西娟,是因为对青春与美的果敢返身,对人老珠黄的不服与绝地狙击。
说来是七种不同的落单理由,归根结底,大而化之,其实也就一种理由,那就是不服从时间的安排。
这些落单者,他们坚持本我,不愿把自己的身体、脸面与命数,交到社会变迁、时代风云和包括家人在内的他者手上,而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当作内心的灯塔与信仰。他们总在进攻,总在撤退,但这种进攻和撤退,却与时代的算式不是错位就是脱节,甚至刚刚反向。而究其里因,造成这种很难周全与调和的深层矛盾,正是城乡冲突、新旧冲突、性格冲突、文化冲突的滥觞与博弈。他们中,华绵是孤儿,艾云丽是无所依傍、一切靠自己的渝漂女子,白桂是常遭家暴的农村少妇,小海是家庭“弃子”,《水彩课》中的“我”是出自单亲家庭的女子,陶玉丹是不受父母待见的女子,高西娟是青春被耽搁的中年妇。难道说,他们的际遇与遭遇,制造了他们的性格,而性格造就了落单的宿命?这个,我是不知的。
强雯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叙述速度与尺度的节制——及时刹车,不把自己的观点摆进去,点破说透,一览无余,而是把余韵留给读者去品咂,将未完成式态交与读者再创作。因为这一小说识见,她的小说,我们能睹见的,只是水面的平静和自然流动,水下的汹涌却成了文字飞溅的感知与遥想。而出现在《清洁》《水彩课》中的非虚构式的散文化策略,无疑是这一识见对日见汹涌的小说化现实的书面教训与反拨。毋庸讳言,《旗袍》主人公的偏执美与极致美,《单行道》洇染的淡淡忧伤的气场,很对我的小说旨趣。
合上《石燕》,我发现自己更清晰地看见了作者笔下那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落单者。他们以艰难而卑微的式样,活出了自己的骄傲与尊严,活出了自己的繁花似锦,也活出了自己的思考及对活法的纠偏与调校。他们以与时代走散和疏离的方式,与世界走到一起,达成逻辑学上的和解与平衡。是的,美好的世界由两部分人构成,走得快的,和走得慢的。快与大众是繁花,慢与少数也是。一路上,不管是一直走在路上,还是走成淘汰,撞上南墙,都是一种存在。而存在即合理,而合理即虚构艺术的不二生成法典。
当然,《石燕》本身就是一树繁花——长在悬崖上,可以凌空飞翔,发出石头古老啸叫的小说艺术的繁花。

抒情背后的隐性美
——步缘《咖啡染红天空》赏析
□吴荣强
作家尹宏灯曾说:“在这个浮躁的年代,一个人在漂泊打拼中仍坚持文学创作已实属不易,而坚持本真写作,更是一种品德的修炼。”何为本真写作,其实就是在生活中寻找一些朴素无华且容易被遗忘的素材,以诗歌的方式记录或守望,把原本的生活高度还原出来。
当然,真正的朴素不是远离生活,而是能在细碎的生活里找到光芒。生活素材就像一块块等待匠人雕琢的玉石。一旦被诗人以其独特的诗歌文本、饱满的情感表达和娴熟的文字技巧“开凿”出来,作品往往是最迷人、最打动人心的。诗人步缘的《牵手》,“我们手牵着手/如同山连着山/……你紧紧地将我绑住/不放,真是一根温柔的藤/我就以一棵树的姿态/迎接风和雨的来临”。
步缘在珠海生活二十来年,地域空间的转换,使人新奇欢愉,而回归到安放身心的旧处,又使人笃定踏实。可见,在步缘的诗中,总会看到他在家乡和居住地的不同文化与审美的碰撞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诗意栖居。文学评论家蒋述卓教授曾对步缘的诗有过评价:“步缘的诗洋溢着人生的坚韧和意志。诗人善于观察生活,对人类社会保持敏锐的观察和判断,于是在诗歌创作中能够熟练地提炼出诗性的素材。其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诗意叙述,都能体现出诗性的感悟。其创作手法独特,诗行中彰显出诗歌创作的价值追求与美学探索。”且看步缘的《我没有改变土地》:“我们的幸福,也依附在这片土地/我相信,一切希望寄托于土地/我们用母语去改变房屋、道路、庄稼和绿化/但没有改变土地/我知道,生活中最沉重的/算是那朴素的土粒”。相较于《我没有改变土地》,我们更为熟知的是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可以说,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没有改变土地》一诗以现代人的生活视角,冷峻沉稳的抒情方式来记录和追述生活。
步缘的《再生》一诗,正是诗人聿君所希望看到的“灵魂”诗歌:能启迪智慧,引发思考,并能带给人心灵震撼。他的《另一个人》亦是如此:“我又看到另一个人/还有另一个人,我累了/看不透他们的表情/如同我多年观察大海,仍然不知/大海何时涨潮和退潮”。此外,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低生活》一诗。诗歌这样写道:“我长年在低处,听到昆虫的歌声/也购买如生活般甘甜的水果和蔬菜/我尽量压抑自己那飘浮的欲望/让衣物晾在生活最低处”。这就印证了诗人尹宏灯的一句话:“可以看到,步缘在始终坚持‘真’和‘善’的背后,其诗歌总有一种隐性的‘美’在释放。这种美,有时是疼痛的,有时是温暖的,这就是诗歌所迸发的力量和意义。”
步缘的诗,抒情的背后释放隐性美。好的诗歌,应具有真善美的影子。诗人王建民认为,“一首好诗必须有血有肉,语言真诚朴素,情感饱满,能引领人向上、向善、向美。”诚然,诗歌的表达方式虽多样,但并不复杂。不管是直抒胸臆,还是借景抒情,亦或托物言志和即事感怀,行文中的立意、意境和情感,这三样东西是不能少的,否则就不叫诗了。
步缘的诗,以抒情为主,写实为辅。他的诗,有活出来的深刻,也有难以言说但已被他充分表达出来的复杂。这“复杂”,倒不是说一定要上升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样的高度,而是诗人创作二十多年以来,至少解决(或弄清)“何为写诗和为谁写诗”这些问题。诗人创作以抒情见长,在字里行间,诠释了人类社会的隐性美。可以看到过往著名诗人对步缘诗歌的点评。诗人郑小琼坦言:“步缘的诗歌关注社会生活具体的事物,记录城市化进程中,忧郁、坚忍、宽慈和悲悯的客观表达,其对人生、人性的观照,令诗歌的意境更具张力”。
诗人在表述审美时,同样在抒情中悄悄进行。诗人王明博曾说:“抒情是所有诗人创作时的共同特征,而诗歌如何抒情则形成了诗人风格的差异。”是的,步缘的诗歌创作已经形成了其特色。不信,你看,“那个亮着灯光的房间/坐着我和你/就像两本诗集/心里漂溢着诗的歌单芬芳”(《走进你》);“印数只有两册/同一版本的心路历程/除了一本/藏在我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另外一本送给你/你是我这本集子/惟一的读者……(《印数:2册》);“你来或不来,我们都会永远见面/在风景的某个角落,某个偏僻的地方/享受茶或酒,带着爱或恨的季节/一场不会赢或输的战斗/超越世俗的界限”(《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见你》)。读这样的诗,即使历经挫折,品诗时的心情会是愉悦的。正如生活在诗意的天空下,你和我,都是被早晨的暖阳轻吻过的。
读诗如见人,诗人阅历及性情必定丰富,这也印证了“文学来自生活”这句经典语。读步缘的诗集《咖啡染红天空》,可清晰地看到诗集中的诗,是从生活最低处蹦出来的,也是从血液最深处挤出来的!那凝炼的语言,令人时而沉思,时而内心荡漾,时而悲喜交加,可谓是进行心灵的洗礼。
如今,步缘的诗越写越清晰、明朗,越写越精粹、结实,如同一粒饱满的麦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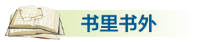
落单者的似锦繁花
——读强雯中短篇小说集《石燕》
□凸凹
“闲言少叙,却说宝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落单,也不和人玩耍,每到晚间,便索然睡了。”《红楼梦》第十三回里写到的落单者,较之强雯中短篇小说集《石燕》(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写的,其人数及落单原因,都要单一得多,单纯得多。集子由《石燕》《百万风景》两个中篇和《功德碗》等五个短篇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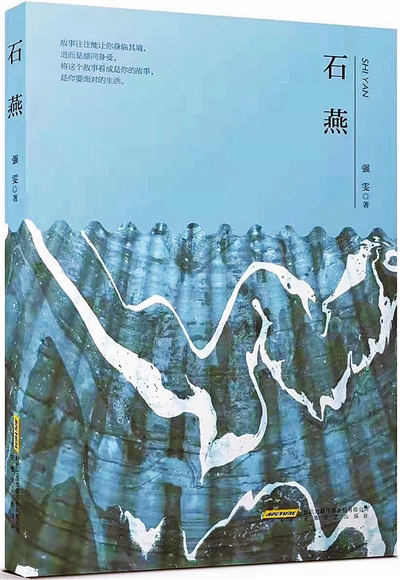
七件作品,七类人物,七种故事,同居一书,却各各不同,独守一格,自成气象。这是一本什么书、什么类型、什么题材?书前书后,里里外外,编者没有提示词,作者没有后记语,按说,如此纷繁文况,要让自带主张、多有定见的读者,从中提拎出大家伙儿共认的一宗主旨,一个公切点出来,是有难度的。进一步说,如果连作者、编者自个儿都无法办到,那就纯粹是对好事者开的一个玩笑,设下的永远走不出的迷宫。但细读全书,稍作梳理、归纳,还是会发现七件作品的一些共性的。
小说的时空坐标,定制在民国至当下的重庆地区。具体而言,时间主要为抗战时期、新旧社会改朝换代节点以及城乡嬗变的城市化过程中,地理坐标基本为长江流域的城镇。小说的故事生发、铺衍与集束,皆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七情六欲,生老病死,尤其人与人(男女、同事、同学、邻里、上下级尤其家人间)的关系与纠结——那些灵肉相处中的小欢乐、小平和与小尴尬。作者特别擅长刻画人物内心,织锦刺绣一般,将奔走在视线之外的至爱、忌恨、狂欢、战争、幺蛾子、小九九,编排成锦绣文章,悬挂炫目展厅。她也不乏高强的语言教养和文学感应异质稟赋,尤其对感觉的具象化,对外物的虚拟化,可谓自由进出,呼风唤雨,信手拈来。正是在这种将空/无坐成实/有,将实/有坐成空/无的魔术与手段,让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灿烂,一种欲说还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文辞魅力与思想魅力。
读强雯的小说,你会发现她对文物、寺庙、花草、绘画、衣饰,以及重庆大街闾巷各色人等,都很熟络和热络,状写起来得心应手,栩栩如生,让人身临其境,读文即睹物。去年盛夏,在川渝环境主题采风活动上,我认识了她,但对她的过往经历不甚了解,但我相信她对这些物事的认知,与它们的共情,应该是跟她的个人经历以及经历赋予的个体经验和个人爱好有关。书房中的知识好办,闭门谢客,凿壁偷光,头悬梁锥刺骨,埋首苦研即可,大地上的经历就不好办了。成功学读得再透,名人传读得再多,有用吗?等你读毕又想起去学事主的经历时,才发现年龄、时代背景、地缘、家室、人际、身体、性别、性格,等等方面,这不适合那不合适,出入太大,完全无法依葫芦画瓢,一蹴而就。小说不是知识的教科书,但它是为知识提供人味、细节、时空和故事的神。小说是知识、经历与文学天赋的媾合,三位一体,不可或缺。没有经历或经历不够的小说家,飞得再高再远,也是飘的,因为没有自己的发生地与母根。
我相信,以上是读者和业界人士的共识。我更相信,这本书还有一条脉向,是对落单者群像的小说集合。换言之,落单者,是七件小说共通的纠缠对象、追述主体。
七件作品中的男主或女主,自有其具体的落单理由。《石燕》中的文物修复师华绵,是因为对战时歌乐山保育院的沉溺,对文物遭遇的疼痛;《百万风景》中的艾云丽一家,是对家乡小镇的被出走与不舍乡愁,对贫民窟老巷旁一夜间传奇般冒出的“百万小区”的不解、惊惶与羡慕忌妒恨;在《功德碗》中,是因为武陵山农妇、史家大院暂住客白桂,对封建婚姻的致命反抗,并借她的眼睛,让我们感知到的史家老太太对动乱时局的恐惧,以及两人面对未来所做的不同的噩梦;而《清洁》中的慈云寺拓片抄写者、青年小海,则是因为对老家应县文物木塔和母爱的惦记,对尘世物欲和肉欲的厌恶与压抑;《水彩课》中女儿“我”眼中的长得好看又颇具画才的“父亲”,是因为个人命运在家国命运中发生了断崖式陡转,理想幻灭,难以为继。《单行道》中的职高美术教师陶玉丹,是因为性格乖僻,对家庭、社会的逆反,而一直走在自己人生的单行道上;《旗袍》中的时年46岁、单位中层贵妇高西娟,是因为对青春与美的果敢返身,对人老珠黄的不服与绝地狙击。
说来是七种不同的落单理由,归根结底,大而化之,其实也就一种理由,那就是不服从时间的安排。
这些落单者,他们坚持本我,不愿把自己的身体、脸面与命数,交到社会变迁、时代风云和包括家人在内的他者手上,而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当作内心的灯塔与信仰。他们总在进攻,总在撤退,但这种进攻和撤退,却与时代的算式不是错位就是脱节,甚至刚刚反向。而究其里因,造成这种很难周全与调和的深层矛盾,正是城乡冲突、新旧冲突、性格冲突、文化冲突的滥觞与博弈。他们中,华绵是孤儿,艾云丽是无所依傍、一切靠自己的渝漂女子,白桂是常遭家暴的农村少妇,小海是家庭“弃子”,《水彩课》中的“我”是出自单亲家庭的女子,陶玉丹是不受父母待见的女子,高西娟是青春被耽搁的中年妇。难道说,他们的际遇与遭遇,制造了他们的性格,而性格造就了落单的宿命?这个,我是不知的。
强雯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叙述速度与尺度的节制——及时刹车,不把自己的观点摆进去,点破说透,一览无余,而是把余韵留给读者去品咂,将未完成式态交与读者再创作。因为这一小说识见,她的小说,我们能睹见的,只是水面的平静和自然流动,水下的汹涌却成了文字飞溅的感知与遥想。而出现在《清洁》《水彩课》中的非虚构式的散文化策略,无疑是这一识见对日见汹涌的小说化现实的书面教训与反拨。毋庸讳言,《旗袍》主人公的偏执美与极致美,《单行道》洇染的淡淡忧伤的气场,很对我的小说旨趣。
合上《石燕》,我发现自己更清晰地看见了作者笔下那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落单者。他们以艰难而卑微的式样,活出了自己的骄傲与尊严,活出了自己的繁花似锦,也活出了自己的思考及对活法的纠偏与调校。他们以与时代走散和疏离的方式,与世界走到一起,达成逻辑学上的和解与平衡。是的,美好的世界由两部分人构成,走得快的,和走得慢的。快与大众是繁花,慢与少数也是。一路上,不管是一直走在路上,还是走成淘汰,撞上南墙,都是一种存在。而存在即合理,而合理即虚构艺术的不二生成法典。
当然,《石燕》本身就是一树繁花——长在悬崖上,可以凌空飞翔,发出石头古老啸叫的小说艺术的繁花。

抒情背后的隐性美
——步缘《咖啡染红天空》赏析
□吴荣强
作家尹宏灯曾说:“在这个浮躁的年代,一个人在漂泊打拼中仍坚持文学创作已实属不易,而坚持本真写作,更是一种品德的修炼。”何为本真写作,其实就是在生活中寻找一些朴素无华且容易被遗忘的素材,以诗歌的方式记录或守望,把原本的生活高度还原出来。
当然,真正的朴素不是远离生活,而是能在细碎的生活里找到光芒。生活素材就像一块块等待匠人雕琢的玉石。一旦被诗人以其独特的诗歌文本、饱满的情感表达和娴熟的文字技巧“开凿”出来,作品往往是最迷人、最打动人心的。诗人步缘的《牵手》,“我们手牵着手/如同山连着山/……你紧紧地将我绑住/不放,真是一根温柔的藤/我就以一棵树的姿态/迎接风和雨的来临”。
步缘在珠海生活二十来年,地域空间的转换,使人新奇欢愉,而回归到安放身心的旧处,又使人笃定踏实。可见,在步缘的诗中,总会看到他在家乡和居住地的不同文化与审美的碰撞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诗意栖居。文学评论家蒋述卓教授曾对步缘的诗有过评价:“步缘的诗洋溢着人生的坚韧和意志。诗人善于观察生活,对人类社会保持敏锐的观察和判断,于是在诗歌创作中能够熟练地提炼出诗性的素材。其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诗意叙述,都能体现出诗性的感悟。其创作手法独特,诗行中彰显出诗歌创作的价值追求与美学探索。”且看步缘的《我没有改变土地》:“我们的幸福,也依附在这片土地/我相信,一切希望寄托于土地/我们用母语去改变房屋、道路、庄稼和绿化/但没有改变土地/我知道,生活中最沉重的/算是那朴素的土粒”。相较于《我没有改变土地》,我们更为熟知的是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可以说,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没有改变土地》一诗以现代人的生活视角,冷峻沉稳的抒情方式来记录和追述生活。
步缘的《再生》一诗,正是诗人聿君所希望看到的“灵魂”诗歌:能启迪智慧,引发思考,并能带给人心灵震撼。他的《另一个人》亦是如此:“我又看到另一个人/还有另一个人,我累了/看不透他们的表情/如同我多年观察大海,仍然不知/大海何时涨潮和退潮”。此外,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低生活》一诗。诗歌这样写道:“我长年在低处,听到昆虫的歌声/也购买如生活般甘甜的水果和蔬菜/我尽量压抑自己那飘浮的欲望/让衣物晾在生活最低处”。这就印证了诗人尹宏灯的一句话:“可以看到,步缘在始终坚持‘真’和‘善’的背后,其诗歌总有一种隐性的‘美’在释放。这种美,有时是疼痛的,有时是温暖的,这就是诗歌所迸发的力量和意义。”
步缘的诗,抒情的背后释放隐性美。好的诗歌,应具有真善美的影子。诗人王建民认为,“一首好诗必须有血有肉,语言真诚朴素,情感饱满,能引领人向上、向善、向美。”诚然,诗歌的表达方式虽多样,但并不复杂。不管是直抒胸臆,还是借景抒情,亦或托物言志和即事感怀,行文中的立意、意境和情感,这三样东西是不能少的,否则就不叫诗了。
步缘的诗,以抒情为主,写实为辅。他的诗,有活出来的深刻,也有难以言说但已被他充分表达出来的复杂。这“复杂”,倒不是说一定要上升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样的高度,而是诗人创作二十多年以来,至少解决(或弄清)“何为写诗和为谁写诗”这些问题。诗人创作以抒情见长,在字里行间,诠释了人类社会的隐性美。可以看到过往著名诗人对步缘诗歌的点评。诗人郑小琼坦言:“步缘的诗歌关注社会生活具体的事物,记录城市化进程中,忧郁、坚忍、宽慈和悲悯的客观表达,其对人生、人性的观照,令诗歌的意境更具张力”。
诗人在表述审美时,同样在抒情中悄悄进行。诗人王明博曾说:“抒情是所有诗人创作时的共同特征,而诗歌如何抒情则形成了诗人风格的差异。”是的,步缘的诗歌创作已经形成了其特色。不信,你看,“那个亮着灯光的房间/坐着我和你/就像两本诗集/心里漂溢着诗的歌单芬芳”(《走进你》);“印数只有两册/同一版本的心路历程/除了一本/藏在我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另外一本送给你/你是我这本集子/惟一的读者……(《印数:2册》);“你来或不来,我们都会永远见面/在风景的某个角落,某个偏僻的地方/享受茶或酒,带着爱或恨的季节/一场不会赢或输的战斗/超越世俗的界限”(《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见你》)。读这样的诗,即使历经挫折,品诗时的心情会是愉悦的。正如生活在诗意的天空下,你和我,都是被早晨的暖阳轻吻过的。
读诗如见人,诗人阅历及性情必定丰富,这也印证了“文学来自生活”这句经典语。读步缘的诗集《咖啡染红天空》,可清晰地看到诗集中的诗,是从生活最低处蹦出来的,也是从血液最深处挤出来的!那凝炼的语言,令人时而沉思,时而内心荡漾,时而悲喜交加,可谓是进行心灵的洗礼。
如今,步缘的诗越写越清晰、明朗,越写越精粹、结实,如同一粒饱满的麦子。

-我已经到底线啦-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