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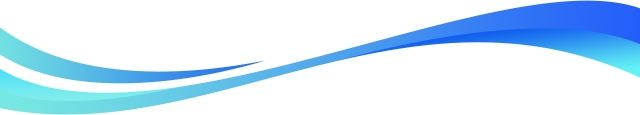
叙 事
□ 任芙康
“叙事”,原本平和的两个字,抑或安静的一个词,可它们于我,带着一份良善与庄重,天奇地怪地入心入肺,已满三十一年。
暮色将黑未黑,恰是午后四时许,我搭乘去新加坡的航班,飞离哥本哈根。九十分钟过去,降落苏黎世。此地为经停,下客、上客的扰攘,全然莫得,唯见谦谦有礼。
座位紧倚左首舷窗,望出去,停机坪灯火稀疏,似无传说中的奢华,亦非想象中的精致。苏黎世被冬夜的雨,淋出了俗李凡桃。此刻,像有劲风刮起,雨丝纷乱飘洒,隐约有人在冷雨中忙碌。一切悄无声响,令人泛起莫名苍凉,甚而不合时宜地想到“凄风苦雨”。
飞机重新起飞,尽头新加坡,中途再无停顿,会有十三个小时航程。除我之外,整机乘客,统统欧人面孔。他们不肯慢待闲暇,挈妇将雏,远走高飞,往往只为换得十天半月的暖和。
因口舌拙笨,我于所有外语均属外行。曾经接触俄文(初中学过三年),后来奉还老师。但我愚而自励,不怯异邦远行。即如此刻,面对临时旅伴的所有致意,纵然不甚了了,但仍是明白,萍水相逢,便有这般斯文,是一种涵养,更是一种秉性,心下生出可靠的安然。新航空乘女孩儿,尤有无华的婀娜,察觉我英语生分,便将配赠的吃食饮品,用悦耳汉语讲解给我,让人领受真心的体贴。虽说,夜半独行不怕鬼,我其实亦需他人帮忙。就此趟远行而言,抵达狮城,略作勾留,还会继续游走,天晓得会碰到什么难处?
舱里暗下来,众人已摆出睡姿。我轻轻推起舷窗挡板,没有皓月,没有繁星,眼前黑得无穷无尽。回想醒事以后,从未滋生过体面的“志向”,也就不曾遭逢人生挫折的失意,或是享受红尘顺遂的得志。只要有点余钱,应付起码的吃喝,便不太理会吉凶,任天涯茫茫,抬脚可走。语言不通,属交际白痴,本会心虚,但早早脱褪自惭形秽的家伙,就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无知,多半连着无忌,即或万米高空,依旧拒绝妄自菲薄,很快沉沉入睡。
一夜无话。
当瞌睡将尽,尚在醒盹,忽听前边有人欢叫开来。睁眼看去,一束光芒,已闯进舱内。人们纷纷起身,启开两侧窗档。瞬间,迥异于欧罗巴的艳阳,让人们从里到外,透透亮亮。我贴窗顾盼,先有些眩目,天海一色的蔚蓝,涌动出无垠壮阔。哎呀呀,这不就是鼎鼎大名的“南洋”吗?
忽地,旷远的左前方,阳气蒸腾处,大洋托起一片不甚真切的陆地。只是眨眼功夫,陆地幻化为阔大的坟山,布满竖立的墓碑。再眨眨眼,所有墓碑已变成壮观的大厦,甚至能分辨出粒粒移动的车影。恨不得闻鸡起舞,新加坡到了。
陡然,眼前一切消失,重现蓝天白云。感觉飞机开始爬升,右拐,再右拐,持续右拐,显然在兜一个大大的圆。莫非这城矜持,不肯轻易见人;或是这城讲究,来客得先行叩拜。
很快,仍是左前方位置,重现“墓园”,重现高楼,重现街市。景象新鲜,见所未见,绝非等闲城郭。但跟魔术一样,有形的一切,再次倏忽无影无踪,唯有碧空如洗。
飞机第三度兜回来,悄无声息地贴近城市。座椅明显有些前倾,机身在下降。高低错落的大厦,从眼前疾疾退去,心中留下的,只有都市如画,富庶入骨。似乎飞机再未犹豫,抱着坚定的锐气,义无反顾。随之,柔和触地。稍事滑行,稳稳终止。整套动作,一气浑成,毫不逊色一场飞行表演。刹那间,满舱沸腾,人们在狭窄的空间击掌、拥抱,仿佛此番同机,区别以往,彼此牵手,缔结了生死之交。
其实,所有这些情绪翻转,我都懵懵懂懂,不明就里。但愉悦总是合拍的,长途飞行圆满收尾,毕竟值得庆幸。
人们夏装着身,鱼贯而出。舱口一侧,站着仪表堂堂的中年机长。他脸带微笑,接受几乎每位乘客的握手道别。当我挨近他,直接汉语相问:“刚才,飞机有什么事吗?”对方甚为吃惊,亦用汉语反问:“有广播呀,你一点不知道吗?”“我不懂英语。”机长一下变得低声:“哦,对不起。起落架出了麻烦,后来没事了。”
顿时大梦方觉,自己刚刚跨过差点“一了百了”的门坎。我的生父,抗战中入编远征军。由缅甸开拔去印度,飞机起飞便坠落,满机官兵,死伤各半。生父醒来,巧属“伤”中一员。而今我步前尘,预示本乃沧海一粟,破茧成蝶,竟已是见过“场面”的人了。我最清楚自己,在这烟火人间,分量几近于无,倘若某日忽然飘零,除却亲朋感伤,企望刊登一则免费讣告,都恐怕力不从心。故而,当时我虽觉侥幸,并无惊悸,放下提袋,趋前抱住机长。我必得相拥一回,表达敬重,甚或敬畏。我怀抱的英雄,是带给我们否极泰来的恩人。
一步步走下舷梯,暑热中终是悟出,飞机兜出的那三个大弯,就是延缓时光的良方,只为消耗燃油、腾空场地、调集救护。当摆渡车启动,验证了我的猜想。
西侧椰树林边,一道道路口,完结使命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车、警用车……闪耀着如释重负的光亮,次第驶离。如同高明的导演,构思出一幕峰回路转的大片,我们的座驾,才敢于开启希望的着陆。
浩大的停机坪,空空如也。空旷、简洁里,仅有行进的两辆摆渡车,叫人回味业已消散的凶险。车子向航站楼驶去,椰林茂密,阳光灿烂,草木不惊,祥云瑞气,所有的危殆,未留下一丝踪迹。粗粗一想,乘客的无恙,雄鹰的无损,当然不是造化,不是福分,不是天意。我崇奉唯物论,起落架最终服从人的意志,只是凑巧。但从那以后,我明白一个常识,只要飞上天去,没有三长两短,最终正常落地,便堪称头号“幸遇”。也便是从彼时开始,我对航行,反倒愈觉寻常,三二十年间,总在飞来飞去,升空、降落,视若家常便饭。
我们这群人,一场未遂空难的幸运者,已成特殊乘客,一路由专人交替引领。下车进得二号航站楼,自助人行道将我们送进“迷你”火车,凉爽、洁净,使得安抚与压惊,臻于至妥至诚。一号航站楼的入境查验,谦和,简便。移步自动扶梯,缓缓下行中,迎面墙上,一幅红底白字撞眼:“如果你是华人,请用华语叙事。”这让我大为惊异:怎会有如此提醒?
从那天开始,我钟爱于“叙事”二字。每每读到听到,总会享受几分温文尔雅。叙事不是抒情,所以朴素。如今有人爱在“叙事”前头冠以“宏大”,无非沽名钓誉,亦是对叙事的扭曲。当自己将叙事移用于伏案,又仿佛被灌输一种态度,便不论笔下事物多么刺激,总能常言俗语,心平气和。不光斟酌用字遣词,甚至从标点符号做起,让述说进入从容。比如,惊叹号,通常只有呼喊口号,才会与叹号挂钩;而上乘行文,则应避免口号。于是,在文字表达中,往往有意为之,情绪交由安稳驾驭,成功远离惊叹。
任芙康 编审,曾任《文学自由谈》《艺术家》主编,天津市写作学会会长,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获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优秀编审工作奖”。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第七届、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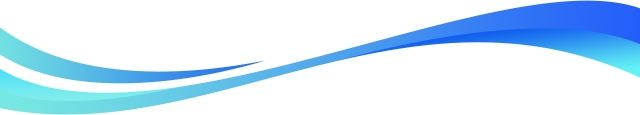
赛里木湖蓝时光
□ 张步根
清晨,从浸透了薰衣草香味的甜梦中醒来,沐浴着察罕乌苏河畔的灿烂霞光,我们脚步匆匆,从清水河镇出发,一路向北去寻找赛里木湖的蓝色时光。
清水河镇是清代伊犁九城之一的瞻德城所在地,古丝绸之路的北道要塞,也是著名的薰衣草之乡。沿着312国道奔驰,道路两边都是硕果累累的果树林,林子外边则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薰衣草庄园。紫色的薰衣草花朵,漫无边际地盛开着,把天地装饰成了美丽的蓝色宫殿,直到车子驶入果子沟,那亮晶晶的蓝色依然在天边闪耀。果子沟狭长险峻,因为盛产野果而得名。沟的左边峭壁耸立,右边却流水潺潺,坡缓上草绿山青。远处的群山之巅覆盖着皑皑白雪,雪线之下云杉葱茏苍翠。沟凹里薄雾弥漫,一朵朵白云如同圣洁的哈达,与绿树青山一起辉映在阳光里。山坡上的野花繁星一般盛开,银白、乌黑、深棕、金黄色的牛羊群,像一抹抹彩云漫过草地。野苹果、野葡萄、野山杏和野核桃树,蓬勃旺盛地簇拥在河岸边。毡房白莲花似的倒影,把河水映衬得如此沉静迷人。
抵达赛里木湖畔已是中午时分。这座藏在天山深处的一汪湖水,波动于两千米海拔之上,恍如天降圣湖。难怪蒙古语称它“赛里木淖尔”,确实是“山脊梁上的湖泊”。再看看它另外一个名字“净海”,眼前不俗的模样,真的不负“西来之异境,世外之灵壤”的美誉。
无边的蓝色湖面上,波光粼粼,帆影点点。一群群鸥鹭和野鸭子,或在低空盘旋,或在水中游曳,阵阵清脆的鸣叫声,在空旷的湖面上跳宕回旋,如同一声声激越的行板。阳光透过云层映照下来,远处的群山,一会儿金黄,一会儿深青,一会儿黝黑,一会儿湛蓝。山与树与云与水,在交错的光影里,或而重叠成淋漓的水墨,或而分明如海市蜃楼,或而又纤毫不见,唯有海天一色。湖畔行走,微澜的湖面上,飘过来阵阵雪山的寒凉,丝丝缕缕的雾岚,一遍遍打湿行人的思绪,氤氲起迷离的梦幻,弥漫在心的深处。湖水一波接一波地拍打湖岸,细碎的浪花面前是斑斓如玉的细小石头,踩踏上去发出窸窣的声响,犹如踏着浪花在行走。这些质地奇异的石头,常常逗引我俯下身去细细辨赏。湖水经年累月的抚搓,让这些圆方长短厚薄不一的石头,显现出莹白、浅绿、赭红、黛青、黝黑、金黄五彩的颜色,无一例外都叫人咂舌喜爱。更有那些难得一见的小石片,布满了难以寻解的图案线条,好像在传递着远古时代的神秘讯息。默默地凝视湖面,清澈的湖水会把你的目光传达到数米的湖底,水底下的卵石们,如玉、如龟、如叶、如花,如同一个玲珑世界映入眼帘,让人即刻心生去湖中探宝的欲望。远处忽然传来湖水的响声,抬眼一看竟然是几条游鱼在嬉戏。印象中赛里木湖是不产鱼虾的,哪来的鱼呢?一番询问得知,这是水产研究单位从遥远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引进的品种,据说是珍贵的高山冷水鱼种高白鲑和凹目白鲑,经过长达十年的适应性繁育,才在赛里木湖安家落户,从此大湖里有了鱼水之乐,沉寂的湖水迎来了生机和活力,终于还原了湖应有的与生俱来的习性。
禁不住掬起一捧湖水,凑近鼻子闻了闻,一股淡咸的味儿迎面扑来,品尝一口微微有些涩味,原来它并不是一个淡水湖。放眼看去,很难想象它的面积竟有450多平方千米之巨,岸线就有100多千米,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走遍湖岸,也找不到一条流向湖中的河水。这座最深达180多米、容量200多亿立方米的大湖,湖水竟然是湖边的雪山雪水融化后,经湖底渗透而来。赛里木湖特殊的高山地势,收纳了大西洋暖湿气流的雨水,和雪水一同造就了这汪洋万顷的苍茫奇观。这在人们眼中的“大西洋的最后一滴泪水”,从远古到今天,滴落了多少红尘往事,闪亮了多少苍茫烟云!
转过一个弯道,前面是连绵的低矮山丘。近乎裸露的山体上,几丛灌木点缀出的图案,像儿童手中的简笔画,让人抚颐生趣。山脚下的大片草地,草叶已经泛出一片金黄色。及膝的棒头青,一串串果实成熟丰美,随风摇曳生姿。遍地都是枝叶繁茂绒毡似的小草,一圈圈针尖样的蘑菇,从草丛中探出脑袋,和繁密细碎的黄色野花,热情地聚会着。山脚下紫色的鼠尾草、蓝色的亚麻花灿然盛开,鼠尾草鱼鳞似的花朵宝塔般一朵缀起一朵,与迎风摇曳的单瓣亚麻花相映成趣。原野中的紫色、蓝色、绿色、金黄色,与蔚蓝的湖水、皑皑的雪山,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图画,镶嵌在天地之间。
湖风渐渐强劲起来,阳光下的赛里木湖,湖水像一匹蓝色的锦缎绵柔丝滑。有了阳光、雪山、森林、草地的加持,这满眼的蓝色如同梦幻一般由近而远铺展开来,渐次显现出浅蓝、深蓝、墨兰、黛蓝、孔雀蓝、宝石蓝。这么丰富繁复的蓝色,犹如上帝的调色板,把赛里木湖描画得绚烂无比,让每一个身临其境的寻访者,不得不沉默、沉思、沉淀、沉静、沉迷,生命中的烦闷愁苦、悲欣得失,都将波消浪去,消融在这无边的蓝海里,人生犹如抛下重负,轻松重启。
远方出现了几只天鹅的身影,这些平常难得一见的精灵,那浮荡在湖水中的圣洁模样,像一枚勋章,一声召唤,一丝柔情,一份感念,带着上苍的祝愿,给远道而来的膜拜者捎来透彻心灵的温润和久远的慰藉。
赛里木湖,我心中的湖!
张步根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发表文学作品多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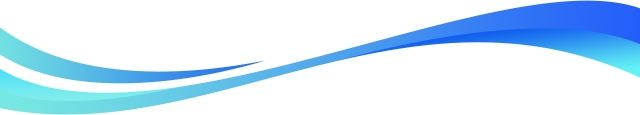
静卧海滩(组诗)
□ 罗春柏
屏蔽浮尘
红泥小炉
煮半日清闲
一壶紫砂温情
屏蔽窗外的浮尘
收起心绪的飘帘
时光流水缓慢
陆羽的汤色
亮了满席素颜
春云夏雨
秋月和冬雪
青花小盏一仰
平生的苦涩回甘
轻烟绕着房梁
不听晨钟和暮鼓
卸载的马欢奔绿野上
八 哥
一双翅膀习惯
为主人鼓掌
忘记了飞翔
习惯说恭维话
油滑的歌喉
不再为阳光歌唱
安居笼子的世界
不经风雨
无需彩云作伴
宠爱集于一身
不用为吃喝发愁
模仿成了自身的功能
你看见麻雀
飞落窗台上
望望里望望外
没有往日的欢跳
没有召唤伙伴
只是倏地飞走了
你却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
黄 鹂
娇小玲珑
跳跃在绿荫花丛
迷人的倩影
增添时光的艳容
悦耳的清音
婉转悠扬
缭绕在丽日晴空
漂洗沾尘的时风
啊……是谁派来喜神
把欢乐播入
每个黎明和黄昏
静卧海滩
满身斑驳
静卧在海滩
笛声已经沉没
只有桅杆
翘望着远方
不会忘记
昨日和大海相依
穿行波峰里
向着旭日斜阳
追赶星月和鲸鲨
今天的海
依旧在奔腾
浪没有年龄
片片新帆飘过
却没有半袭旧影
一位渔夫过来
反复端详
久久没有离去
任风抚摸
身上残存的浪迹
罗春柏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第三届理事。诗歌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十月》《星星》《花城》《诗潮》等刊物。有作品入选“中国年度诗歌精选”等多种选本。曾获《诗刊》社主办全球华文“澳门”同题诗大赛奖、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著有《一棵树站着》《枝头的绿羽》《记忆的绳子》《暮色虚张》等诗集。
秋天的第一场雨(组诗)
□ 潘飞玉
印象中的秋正在倾斜
那些草已漫不经心
树叶还在写着它的前半生
蝉鸣从雨中找出了焦虑
黄昏时分,平原会再一次廓清自己
骨子里的我是长有根的,像芦苇
钉在慢慢苍白的影子上
仰望得太久,头颅越来越沉
心里就会有一蓬野火
秋天的第一场雨
舟自横,散去的繁华里
握住击打的第一丝凉
世俗里滚过,终是那么淡漠
什么也没有说
深夜的灯火黯淡了一下
马上就会有接连不断的树叶坠下悬崖
一朵朵飞翔的蒲公英再也找不回平原
高蹈的每一只鹤都是思想家
过往
用了太多的激情
把一座山变成了我的过往
流年里也多了一棵树几缕流云
山下的人间在一只鹰眼里
看到了废墟
夜路的灯火摇曳几个花妖
一首诗就是一条大河的源头,正如
我遇见了可以静下心来思考的生活
一直流淌着远去
忽而沉静,忽而泛起几朵浪花
枫叶
尘世,谁还能像枫
逆着风行走。洞悉一个个日子和人心
也许是岁月里的寂寞太久
天地一次击掌
风雨隔着那么多的故人那么多的灯盏
眼神洗亮黄昏
每一片叶子都有倾国倾城的时候
不在春天,过往加持了生命
一尊火焰悟空熊熊燃烧
你我,正在分开河流
栾树
先是深绿的叶子上开出了黄色的云
后来云里握出了红色的瓦楞拳
如果不在一棵不起眼的树上重叠看到
如果不在羊群走远的秋天惊讶看到
我都以为日子要平凡到底
阳光兀自微温的下午
鸟在白云里撞来撞去
我站在窗前
钟情一棵树和我的一生
比别人慢,也更错落有致一点
银杏
一本书里夹着一个傍晚的夕阳
女孩的感伤,是一个贵族
有着矜持和从容的泪,掐丝的手帕
风开始多起来,忘了前尘后世
一直在原地打转
忘了无数个夜里,我只有一个杯子
装着啤酒,就装不下古老的神话
潘飞玉 1972年生,陕西华州人。现执教于咸阳职业技术学院。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出版诗集《蒹葭的河流》《平原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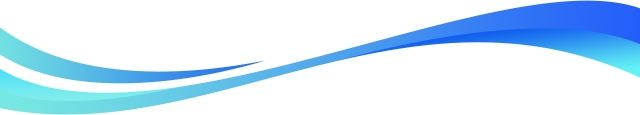
叙 事
□ 任芙康
“叙事”,原本平和的两个字,抑或安静的一个词,可它们于我,带着一份良善与庄重,天奇地怪地入心入肺,已满三十一年。
暮色将黑未黑,恰是午后四时许,我搭乘去新加坡的航班,飞离哥本哈根。九十分钟过去,降落苏黎世。此地为经停,下客、上客的扰攘,全然莫得,唯见谦谦有礼。
座位紧倚左首舷窗,望出去,停机坪灯火稀疏,似无传说中的奢华,亦非想象中的精致。苏黎世被冬夜的雨,淋出了俗李凡桃。此刻,像有劲风刮起,雨丝纷乱飘洒,隐约有人在冷雨中忙碌。一切悄无声响,令人泛起莫名苍凉,甚而不合时宜地想到“凄风苦雨”。
飞机重新起飞,尽头新加坡,中途再无停顿,会有十三个小时航程。除我之外,整机乘客,统统欧人面孔。他们不肯慢待闲暇,挈妇将雏,远走高飞,往往只为换得十天半月的暖和。
因口舌拙笨,我于所有外语均属外行。曾经接触俄文(初中学过三年),后来奉还老师。但我愚而自励,不怯异邦远行。即如此刻,面对临时旅伴的所有致意,纵然不甚了了,但仍是明白,萍水相逢,便有这般斯文,是一种涵养,更是一种秉性,心下生出可靠的安然。新航空乘女孩儿,尤有无华的婀娜,察觉我英语生分,便将配赠的吃食饮品,用悦耳汉语讲解给我,让人领受真心的体贴。虽说,夜半独行不怕鬼,我其实亦需他人帮忙。就此趟远行而言,抵达狮城,略作勾留,还会继续游走,天晓得会碰到什么难处?
舱里暗下来,众人已摆出睡姿。我轻轻推起舷窗挡板,没有皓月,没有繁星,眼前黑得无穷无尽。回想醒事以后,从未滋生过体面的“志向”,也就不曾遭逢人生挫折的失意,或是享受红尘顺遂的得志。只要有点余钱,应付起码的吃喝,便不太理会吉凶,任天涯茫茫,抬脚可走。语言不通,属交际白痴,本会心虚,但早早脱褪自惭形秽的家伙,就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无知,多半连着无忌,即或万米高空,依旧拒绝妄自菲薄,很快沉沉入睡。
一夜无话。
当瞌睡将尽,尚在醒盹,忽听前边有人欢叫开来。睁眼看去,一束光芒,已闯进舱内。人们纷纷起身,启开两侧窗档。瞬间,迥异于欧罗巴的艳阳,让人们从里到外,透透亮亮。我贴窗顾盼,先有些眩目,天海一色的蔚蓝,涌动出无垠壮阔。哎呀呀,这不就是鼎鼎大名的“南洋”吗?
忽地,旷远的左前方,阳气蒸腾处,大洋托起一片不甚真切的陆地。只是眨眼功夫,陆地幻化为阔大的坟山,布满竖立的墓碑。再眨眨眼,所有墓碑已变成壮观的大厦,甚至能分辨出粒粒移动的车影。恨不得闻鸡起舞,新加坡到了。
陡然,眼前一切消失,重现蓝天白云。感觉飞机开始爬升,右拐,再右拐,持续右拐,显然在兜一个大大的圆。莫非这城矜持,不肯轻易见人;或是这城讲究,来客得先行叩拜。
很快,仍是左前方位置,重现“墓园”,重现高楼,重现街市。景象新鲜,见所未见,绝非等闲城郭。但跟魔术一样,有形的一切,再次倏忽无影无踪,唯有碧空如洗。
飞机第三度兜回来,悄无声息地贴近城市。座椅明显有些前倾,机身在下降。高低错落的大厦,从眼前疾疾退去,心中留下的,只有都市如画,富庶入骨。似乎飞机再未犹豫,抱着坚定的锐气,义无反顾。随之,柔和触地。稍事滑行,稳稳终止。整套动作,一气浑成,毫不逊色一场飞行表演。刹那间,满舱沸腾,人们在狭窄的空间击掌、拥抱,仿佛此番同机,区别以往,彼此牵手,缔结了生死之交。
其实,所有这些情绪翻转,我都懵懵懂懂,不明就里。但愉悦总是合拍的,长途飞行圆满收尾,毕竟值得庆幸。
人们夏装着身,鱼贯而出。舱口一侧,站着仪表堂堂的中年机长。他脸带微笑,接受几乎每位乘客的握手道别。当我挨近他,直接汉语相问:“刚才,飞机有什么事吗?”对方甚为吃惊,亦用汉语反问:“有广播呀,你一点不知道吗?”“我不懂英语。”机长一下变得低声:“哦,对不起。起落架出了麻烦,后来没事了。”
顿时大梦方觉,自己刚刚跨过差点“一了百了”的门坎。我的生父,抗战中入编远征军。由缅甸开拔去印度,飞机起飞便坠落,满机官兵,死伤各半。生父醒来,巧属“伤”中一员。而今我步前尘,预示本乃沧海一粟,破茧成蝶,竟已是见过“场面”的人了。我最清楚自己,在这烟火人间,分量几近于无,倘若某日忽然飘零,除却亲朋感伤,企望刊登一则免费讣告,都恐怕力不从心。故而,当时我虽觉侥幸,并无惊悸,放下提袋,趋前抱住机长。我必得相拥一回,表达敬重,甚或敬畏。我怀抱的英雄,是带给我们否极泰来的恩人。
一步步走下舷梯,暑热中终是悟出,飞机兜出的那三个大弯,就是延缓时光的良方,只为消耗燃油、腾空场地、调集救护。当摆渡车启动,验证了我的猜想。
西侧椰树林边,一道道路口,完结使命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车、警用车……闪耀着如释重负的光亮,次第驶离。如同高明的导演,构思出一幕峰回路转的大片,我们的座驾,才敢于开启希望的着陆。
浩大的停机坪,空空如也。空旷、简洁里,仅有行进的两辆摆渡车,叫人回味业已消散的凶险。车子向航站楼驶去,椰林茂密,阳光灿烂,草木不惊,祥云瑞气,所有的危殆,未留下一丝踪迹。粗粗一想,乘客的无恙,雄鹰的无损,当然不是造化,不是福分,不是天意。我崇奉唯物论,起落架最终服从人的意志,只是凑巧。但从那以后,我明白一个常识,只要飞上天去,没有三长两短,最终正常落地,便堪称头号“幸遇”。也便是从彼时开始,我对航行,反倒愈觉寻常,三二十年间,总在飞来飞去,升空、降落,视若家常便饭。
我们这群人,一场未遂空难的幸运者,已成特殊乘客,一路由专人交替引领。下车进得二号航站楼,自助人行道将我们送进“迷你”火车,凉爽、洁净,使得安抚与压惊,臻于至妥至诚。一号航站楼的入境查验,谦和,简便。移步自动扶梯,缓缓下行中,迎面墙上,一幅红底白字撞眼:“如果你是华人,请用华语叙事。”这让我大为惊异:怎会有如此提醒?
从那天开始,我钟爱于“叙事”二字。每每读到听到,总会享受几分温文尔雅。叙事不是抒情,所以朴素。如今有人爱在“叙事”前头冠以“宏大”,无非沽名钓誉,亦是对叙事的扭曲。当自己将叙事移用于伏案,又仿佛被灌输一种态度,便不论笔下事物多么刺激,总能常言俗语,心平气和。不光斟酌用字遣词,甚至从标点符号做起,让述说进入从容。比如,惊叹号,通常只有呼喊口号,才会与叹号挂钩;而上乘行文,则应避免口号。于是,在文字表达中,往往有意为之,情绪交由安稳驾驭,成功远离惊叹。
任芙康 编审,曾任《文学自由谈》《艺术家》主编,天津市写作学会会长,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获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优秀编审工作奖”。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第七届、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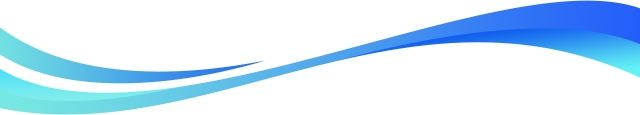
赛里木湖蓝时光
□ 张步根
清晨,从浸透了薰衣草香味的甜梦中醒来,沐浴着察罕乌苏河畔的灿烂霞光,我们脚步匆匆,从清水河镇出发,一路向北去寻找赛里木湖的蓝色时光。
清水河镇是清代伊犁九城之一的瞻德城所在地,古丝绸之路的北道要塞,也是著名的薰衣草之乡。沿着312国道奔驰,道路两边都是硕果累累的果树林,林子外边则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薰衣草庄园。紫色的薰衣草花朵,漫无边际地盛开着,把天地装饰成了美丽的蓝色宫殿,直到车子驶入果子沟,那亮晶晶的蓝色依然在天边闪耀。果子沟狭长险峻,因为盛产野果而得名。沟的左边峭壁耸立,右边却流水潺潺,坡缓上草绿山青。远处的群山之巅覆盖着皑皑白雪,雪线之下云杉葱茏苍翠。沟凹里薄雾弥漫,一朵朵白云如同圣洁的哈达,与绿树青山一起辉映在阳光里。山坡上的野花繁星一般盛开,银白、乌黑、深棕、金黄色的牛羊群,像一抹抹彩云漫过草地。野苹果、野葡萄、野山杏和野核桃树,蓬勃旺盛地簇拥在河岸边。毡房白莲花似的倒影,把河水映衬得如此沉静迷人。
抵达赛里木湖畔已是中午时分。这座藏在天山深处的一汪湖水,波动于两千米海拔之上,恍如天降圣湖。难怪蒙古语称它“赛里木淖尔”,确实是“山脊梁上的湖泊”。再看看它另外一个名字“净海”,眼前不俗的模样,真的不负“西来之异境,世外之灵壤”的美誉。
无边的蓝色湖面上,波光粼粼,帆影点点。一群群鸥鹭和野鸭子,或在低空盘旋,或在水中游曳,阵阵清脆的鸣叫声,在空旷的湖面上跳宕回旋,如同一声声激越的行板。阳光透过云层映照下来,远处的群山,一会儿金黄,一会儿深青,一会儿黝黑,一会儿湛蓝。山与树与云与水,在交错的光影里,或而重叠成淋漓的水墨,或而分明如海市蜃楼,或而又纤毫不见,唯有海天一色。湖畔行走,微澜的湖面上,飘过来阵阵雪山的寒凉,丝丝缕缕的雾岚,一遍遍打湿行人的思绪,氤氲起迷离的梦幻,弥漫在心的深处。湖水一波接一波地拍打湖岸,细碎的浪花面前是斑斓如玉的细小石头,踩踏上去发出窸窣的声响,犹如踏着浪花在行走。这些质地奇异的石头,常常逗引我俯下身去细细辨赏。湖水经年累月的抚搓,让这些圆方长短厚薄不一的石头,显现出莹白、浅绿、赭红、黛青、黝黑、金黄五彩的颜色,无一例外都叫人咂舌喜爱。更有那些难得一见的小石片,布满了难以寻解的图案线条,好像在传递着远古时代的神秘讯息。默默地凝视湖面,清澈的湖水会把你的目光传达到数米的湖底,水底下的卵石们,如玉、如龟、如叶、如花,如同一个玲珑世界映入眼帘,让人即刻心生去湖中探宝的欲望。远处忽然传来湖水的响声,抬眼一看竟然是几条游鱼在嬉戏。印象中赛里木湖是不产鱼虾的,哪来的鱼呢?一番询问得知,这是水产研究单位从遥远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引进的品种,据说是珍贵的高山冷水鱼种高白鲑和凹目白鲑,经过长达十年的适应性繁育,才在赛里木湖安家落户,从此大湖里有了鱼水之乐,沉寂的湖水迎来了生机和活力,终于还原了湖应有的与生俱来的习性。
禁不住掬起一捧湖水,凑近鼻子闻了闻,一股淡咸的味儿迎面扑来,品尝一口微微有些涩味,原来它并不是一个淡水湖。放眼看去,很难想象它的面积竟有450多平方千米之巨,岸线就有100多千米,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走遍湖岸,也找不到一条流向湖中的河水。这座最深达180多米、容量200多亿立方米的大湖,湖水竟然是湖边的雪山雪水融化后,经湖底渗透而来。赛里木湖特殊的高山地势,收纳了大西洋暖湿气流的雨水,和雪水一同造就了这汪洋万顷的苍茫奇观。这在人们眼中的“大西洋的最后一滴泪水”,从远古到今天,滴落了多少红尘往事,闪亮了多少苍茫烟云!
转过一个弯道,前面是连绵的低矮山丘。近乎裸露的山体上,几丛灌木点缀出的图案,像儿童手中的简笔画,让人抚颐生趣。山脚下的大片草地,草叶已经泛出一片金黄色。及膝的棒头青,一串串果实成熟丰美,随风摇曳生姿。遍地都是枝叶繁茂绒毡似的小草,一圈圈针尖样的蘑菇,从草丛中探出脑袋,和繁密细碎的黄色野花,热情地聚会着。山脚下紫色的鼠尾草、蓝色的亚麻花灿然盛开,鼠尾草鱼鳞似的花朵宝塔般一朵缀起一朵,与迎风摇曳的单瓣亚麻花相映成趣。原野中的紫色、蓝色、绿色、金黄色,与蔚蓝的湖水、皑皑的雪山,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图画,镶嵌在天地之间。
湖风渐渐强劲起来,阳光下的赛里木湖,湖水像一匹蓝色的锦缎绵柔丝滑。有了阳光、雪山、森林、草地的加持,这满眼的蓝色如同梦幻一般由近而远铺展开来,渐次显现出浅蓝、深蓝、墨兰、黛蓝、孔雀蓝、宝石蓝。这么丰富繁复的蓝色,犹如上帝的调色板,把赛里木湖描画得绚烂无比,让每一个身临其境的寻访者,不得不沉默、沉思、沉淀、沉静、沉迷,生命中的烦闷愁苦、悲欣得失,都将波消浪去,消融在这无边的蓝海里,人生犹如抛下重负,轻松重启。
远方出现了几只天鹅的身影,这些平常难得一见的精灵,那浮荡在湖水中的圣洁模样,像一枚勋章,一声召唤,一丝柔情,一份感念,带着上苍的祝愿,给远道而来的膜拜者捎来透彻心灵的温润和久远的慰藉。
赛里木湖,我心中的湖!
张步根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发表文学作品多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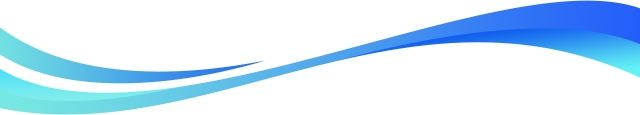
静卧海滩(组诗)
□ 罗春柏
屏蔽浮尘
红泥小炉
煮半日清闲
一壶紫砂温情
屏蔽窗外的浮尘
收起心绪的飘帘
时光流水缓慢
陆羽的汤色
亮了满席素颜
春云夏雨
秋月和冬雪
青花小盏一仰
平生的苦涩回甘
轻烟绕着房梁
不听晨钟和暮鼓
卸载的马欢奔绿野上
八 哥
一双翅膀习惯
为主人鼓掌
忘记了飞翔
习惯说恭维话
油滑的歌喉
不再为阳光歌唱
安居笼子的世界
不经风雨
无需彩云作伴
宠爱集于一身
不用为吃喝发愁
模仿成了自身的功能
你看见麻雀
飞落窗台上
望望里望望外
没有往日的欢跳
没有召唤伙伴
只是倏地飞走了
你却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
黄 鹂
娇小玲珑
跳跃在绿荫花丛
迷人的倩影
增添时光的艳容
悦耳的清音
婉转悠扬
缭绕在丽日晴空
漂洗沾尘的时风
啊……是谁派来喜神
把欢乐播入
每个黎明和黄昏
静卧海滩
满身斑驳
静卧在海滩
笛声已经沉没
只有桅杆
翘望着远方
不会忘记
昨日和大海相依
穿行波峰里
向着旭日斜阳
追赶星月和鲸鲨
今天的海
依旧在奔腾
浪没有年龄
片片新帆飘过
却没有半袭旧影
一位渔夫过来
反复端详
久久没有离去
任风抚摸
身上残存的浪迹
罗春柏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第三届理事。诗歌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十月》《星星》《花城》《诗潮》等刊物。有作品入选“中国年度诗歌精选”等多种选本。曾获《诗刊》社主办全球华文“澳门”同题诗大赛奖、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著有《一棵树站着》《枝头的绿羽》《记忆的绳子》《暮色虚张》等诗集。
秋天的第一场雨(组诗)
□ 潘飞玉
印象中的秋正在倾斜
那些草已漫不经心
树叶还在写着它的前半生
蝉鸣从雨中找出了焦虑
黄昏时分,平原会再一次廓清自己
骨子里的我是长有根的,像芦苇
钉在慢慢苍白的影子上
仰望得太久,头颅越来越沉
心里就会有一蓬野火
秋天的第一场雨
舟自横,散去的繁华里
握住击打的第一丝凉
世俗里滚过,终是那么淡漠
什么也没有说
深夜的灯火黯淡了一下
马上就会有接连不断的树叶坠下悬崖
一朵朵飞翔的蒲公英再也找不回平原
高蹈的每一只鹤都是思想家
过往
用了太多的激情
把一座山变成了我的过往
流年里也多了一棵树几缕流云
山下的人间在一只鹰眼里
看到了废墟
夜路的灯火摇曳几个花妖
一首诗就是一条大河的源头,正如
我遇见了可以静下心来思考的生活
一直流淌着远去
忽而沉静,忽而泛起几朵浪花
枫叶
尘世,谁还能像枫
逆着风行走。洞悉一个个日子和人心
也许是岁月里的寂寞太久
天地一次击掌
风雨隔着那么多的故人那么多的灯盏
眼神洗亮黄昏
每一片叶子都有倾国倾城的时候
不在春天,过往加持了生命
一尊火焰悟空熊熊燃烧
你我,正在分开河流
栾树
先是深绿的叶子上开出了黄色的云
后来云里握出了红色的瓦楞拳
如果不在一棵不起眼的树上重叠看到
如果不在羊群走远的秋天惊讶看到
我都以为日子要平凡到底
阳光兀自微温的下午
鸟在白云里撞来撞去
我站在窗前
钟情一棵树和我的一生
比别人慢,也更错落有致一点
银杏
一本书里夹着一个傍晚的夕阳
女孩的感伤,是一个贵族
有着矜持和从容的泪,掐丝的手帕
风开始多起来,忘了前尘后世
一直在原地打转
忘了无数个夜里,我只有一个杯子
装着啤酒,就装不下古老的神话
潘飞玉 1972年生,陕西华州人。现执教于咸阳职业技术学院。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出版诗集《蒹葭的河流》《平原书》等。

-我已经到底线啦-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