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亚伟 郑金城 刘 刚 刘文俊 杨靖
2024-12-15 00:40
马亚伟 郑金城 刘 刚 刘文俊 杨靖
2024-12-15 0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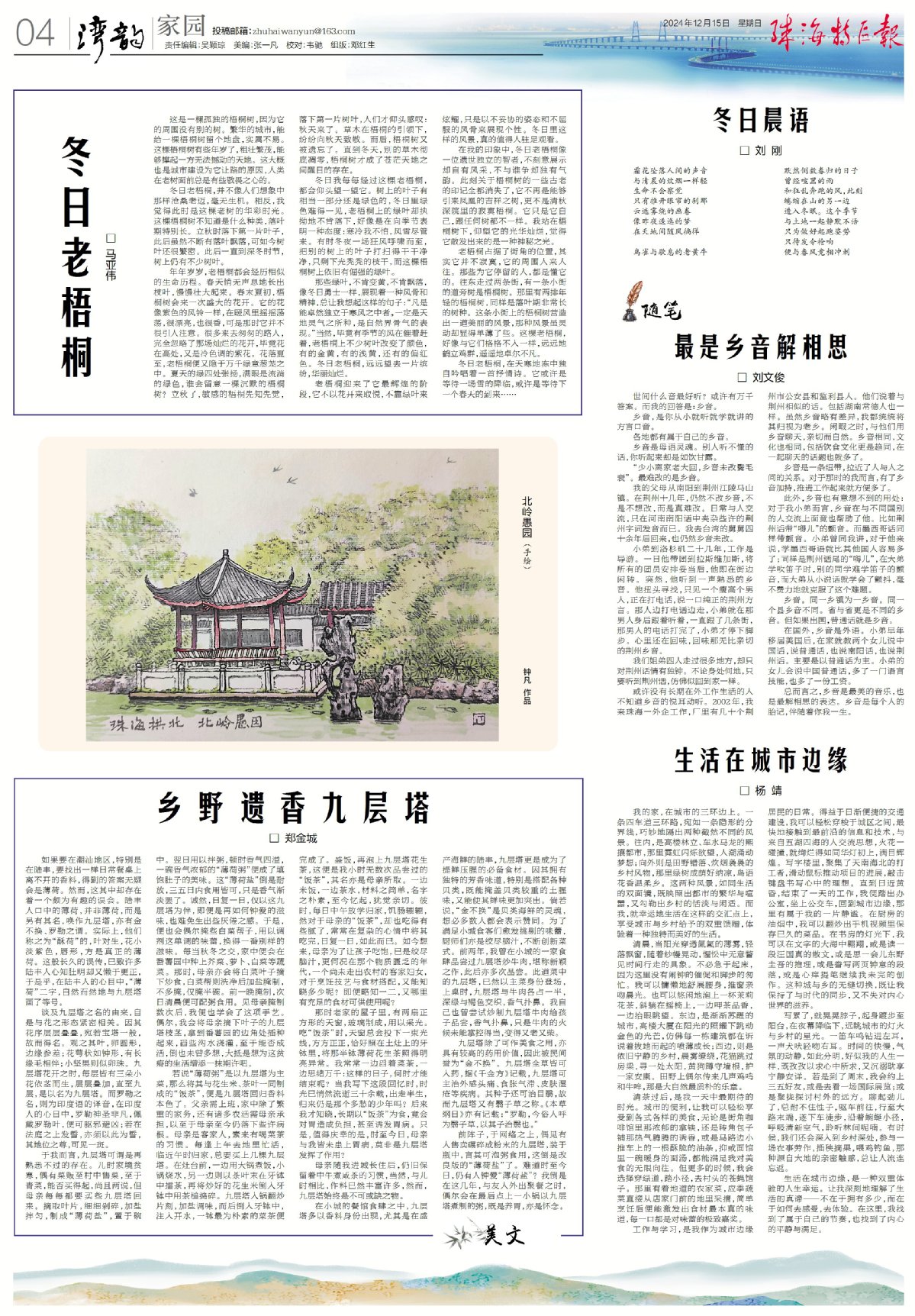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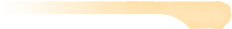

□马亚伟
这是一棵孤独的梧桐树,因为它的周围没有别的树。繁华的城市,能给一棵梧桐树留个地盘,实属不易。这棵梧桐树有些年岁了,粗壮繁茂,能够撑起一方无法撼动的天地。这大概也是城市建设为它让路的原因,人类在老树面前总是有些敬畏之心的。
冬日老梧桐,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沧桑老迈,毫无生机。相反,我觉得此时是这棵老树的华彩时光。这棵梧桐树不知道是什么种类,落叶期特别长。立秋时落下第一片叶子,此后虽然不断有落叶飘落,可如今树叶还很繁密。此后一直到深冬时节,树上仍有不少树叶。
年年岁岁,老梧桐都会经历相似的生命历程。春天悄无声息地长出枝叶,慢慢壮大起来。春末夏初,梧桐树会来一次盛大的花开。它的花像紫色的风铃一样,在暖风里摇摇荡荡,很漂亮,也很香,可是那时它并不很引人注意。很多来去匆匆的路人,完全忽略了那场灿烂的花开,毕竟花在高处,又是冷色调的紫花。花落夏至,老梧桐便又隐于万千绿意葱茏之中。夏天的绿四处张扬,满眼是流淌的绿色,谁会留意一棵沉默的梧桐树?立秋了,敏感的梧桐先知先觉,落下第一片树叶,人们才仰头感叹:秋天来了。草木在梧桐的引领下,纷纷向秋天致敬。而后,梧桐树又被遗忘了。直到冬天,别的草木彻底凋零,梧桐树才成了苍茫天地之间醒目的存在。
冬日我每每经过这棵老梧桐,都会仰头望一望它。树上的叶子有相当一部分还是绿色的,冬日里绿色难得一见,老梧桐上的绿叶却执拗地不肯落下,好像是在向季节表明一种态度:寒冷我不怕,风雪尽管来。有时冬夜一场狂风呼啸而至,把别的树上的叶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而这棵梧桐树上依旧有倔强的绿叶。
那些绿叶,不肯变黄,不肯飘落,像冬日勇士一样,展现着一种风骨和精神,总让我想起这样的句子:“凡是能卓然独立于寒风之中者,一定是天地灵气之所种,是自然界骨气的表现。”当然,毕竟有季节的风在催着赶着,老梧桐上不少树叶改变了颜色,有的金黄,有的浅黄,还有的偏红色。冬日老梧桐,远远望去一片缤纷,华丽灿烂。
老梧桐迎来了它最辉煌的阶段,它不以花开来取悦,不靠绿叶来炫耀,只是以不妥协的姿态和不屈服的风骨来展现个性。冬日里这样的风景,真的值得人驻足观看。
在我的印象中,冬日老梧桐像一位遗世独立的智者,不刻意展示却自有风采,不与谁争却独有气韵。此刻关于梧桐树的一些古老的印记全都消失了,它不再是能够引来凤凰的吉祥之树,更不是清秋深院里的寂寞梧桐。它只是它自己,跟任何树都不一样。我站在梧桐树下,仰望它的光华灿烂,觉得它散发出来的是一种神秘之光。
老梧桐占据了街角的位置,其实它并不寂寞,它的周围人来人往。那些为它停留的人,都是懂它的。往东走过两条街,有一条小街的道旁树是梧桐树。那里有两排年轻的梧桐树,同样是落叶期非常长的树种。这条小街上的梧桐树营造出一道美丽的风景,那种风景虽灵动却显得单薄了些。这棵老梧桐,好像与它们格格不入一样,远远地鹤立鸡群,遥遥地卓尔不凡。
冬日老梧桐,在天寒地冻中独自吟唱着一首抒情诗。它或许是等待一场雪的降临,或许是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郑金城
如果要在潮汕地区,特别是在陆丰,要找出一样日常餐桌上离不开的香料,得到的答案无疑会是薄荷。然而,这其中却存在着一个颇为有趣的误会。陆丰人口中的薄荷,并非薄荷,而是另有其名,唤作九层塔,亦有金不换、罗勒之谓。实际上,他们称之为“酥荷”的,叶对生,花小淡紫色,唇形,方是真正的薄荷。这般长久的误传,已致许多陆丰人心知肚明却又懒于更正,于是乎,在陆丰人的心目中,“薄荷”二字,自然而然地与九层塔画了等号。
谈及九层塔之名的由来,自是与花之形态紧密相关。因其花序层层叠叠,宛若宝塔一般,故而得名。观之其叶,卵圆形,边缘参差;花萼状如钟形,有长缘毛相伴;小坚果则似卵珠。九层塔花开之时,每层皆有三朵小花依茎而生,层层叠加,直至九层,是以名为九层塔。而罗勒之名,则为印度语的译音,在印度人的心目中,罗勒神圣非凡,佩戴罗勒叶,便可驱邪避凶;若在法庭之上发誓,亦须以此为誓,其地位之尊,可见一斑。
于我而言,九层塔可谓是再熟悉不过的存在。儿时家境贫寒,偶有菜贩至村中售菜,至于青菜,能否买得起,尚且两说,但母亲每每都要买些九层塔回来。摘取叶片,细细剁碎,加盐拌匀,制成“薄荷盐”,置于碗中。翌日用以拌粥,顿时香气四溢,一碗香气浓郁的“薄荷粥”便成了填饱肚子的美味。这“薄荷盐”倒是耐放,三五日内食用皆可,只是香气渐淡罢了。诚然,日复一日,仅以这九层塔为伴,即便是再如何钟爱的滋味,也难免生出些厌倦之感。于是,便也会偶尔腌些白菜帮子,用以调剂这单调的味蕾,换得一番别样的滋味。每当秋冬之交,家中便会在番薯园中种上芥菜、萝卜、白菜等蔬菜。那时,母亲亦会将白菜叶子摘下炒食,白菜帮则洗净后加盐腌制,不多腌,仅腌半碗。前一晚腌制,次日清晨便可配粥食用。见母亲腌制数次后,我便也学会了这项手艺。偶尔,我会将母亲摘下叶子的九层塔枝茎,拿到番薯园的边角处插种起来,舀些沟水浇灌,至于能否成活,倒也未曾多想,大抵是想为这贫瘠的生活增添一抹期许吧。
若说“薄荷粥”是以九层塔为主菜,那么将其与花生米、茶叶一同制成的“饭茶”,便是九层塔回归香料本色了。父亲需上班,家中除了繁重的家务,还有诸多农活需母亲承担,以至于母亲至今仍落下些许病根。母亲是客家人,素来有喝菜茶的习惯。每逢上午去地里忙活,临近午时归家,总要买上几棵九层塔。在灶台前,一边用大锅煮饭,小锅烧水,另一边则以茶叶末在牙钵中擂茶,再将炒好的花生米倒入牙钵中用茶槌捣碎。九层塔入锅翻炒片刻,加盐调味,而后倒入牙钵中,注入开水,一钵最为朴素的菜茶便完成了。盛饭,再泡上九层塔花生茶,这便是我小时无数次品尝过的“饭茶”,其名亦是母亲所取。一边米饭,一边茶水,材料之简单,名字之朴素,至今忆起,犹觉亲切。彼时,每日中午放学归家,饥肠辘辘,然对于母亲的“饭茶”,却也吃得有些腻了,常常在复杂的心情中将其吃完,日复一日,如此而已。如今想来,母亲为了让孩子吃饱,已是绞尽脑汁,更何况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个尚未走出农村的客家妇女,对于烹饪技艺与食材搭配,又能知晓多少呢?即便略知一二,又哪里有充足的食材可供使用呢?
那时老家的屋子里,有两扇正方形的天窗,玻璃制成,用以采光。吃“饭茶”时,天窗总会投下一束光线,方方正正,恰好照在土灶上的牙钵里,将那半钵薄荷花生茶照得明亮异常。我常常一边舀着菜茶,一边思绪万千:这样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呢?当我写下这段回忆时,时光已悄然流逝三十余载,出走半生,归来仍是那个多愁的少年吗?后来我才知晓,长期以“饭茶”为食,竟会对胃造成负担,甚至诱发胃病。只是,值得庆幸的是,时至今日,母亲与我皆未患上胃病,莫非是九层塔发挥了作用?
母亲随我进城长住后,仍旧保留着中午煮咸茶的习惯,当然,与儿时相比,作料已然丰富许多,然而,九层塔始终是不可或缺之物。
在小城的餐馆食肆之中,九层塔多以香料身份出现,尤其是在盛产海鲜的陆丰,九层塔更是成为了提鲜压腥的必备食材。因其拥有独特的芳香味道,特别是搭配各种贝类,既能掩盖贝类较重的土腥味,又能使其鲜味更加突出。倘若说,“金不换”是贝类海鲜的灵魂,想必多数人都会表示赞同。为了满足小城食客们愈发挑剔的味蕾,厨师们亦是绞尽脑汁,不断创新菜式。前两年,我曾在小城的一家食肆品尝过九层塔炒牛肉,堪称新颖之作,此后亦多次品尝。此道菜中的九层塔,已然以主菜身份登场,上桌时,九层塔与牛肉各占一半,深绿与褐色交织,香气扑鼻。我自己也曾尝试炒制九层塔牛肉给孩子品尝,香气扑鼻,只是牛肉的火候未能掌控得当,变得又老又柴。
九层塔除了可作美食之用,亦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因此被民间誉为“金不换”。九层塔全草皆可入药,据《千金方》记载,九层塔可主治外感头痛、食胀气滞、皮肤湿疮等疾病。其种子还可治目翳,故而九层塔又有翳子草之称。《本草纲目》亦有记载:“罗勒,今俗人呼为翳子草,以其子治翳也。”
前阵子,于网络之上,偶见有人售卖碾碎成粉末的九层塔,装于瓶中,言其可泡粥食用,这倒是改良版的“薄荷盐”了。难道时至今日,仍有人钟爱“薄荷盐”?我倒是在这几年,与友人外出聚餐之时,偶尔会在最后点上一小锅以九层塔煮制的粥,既是养胃,亦是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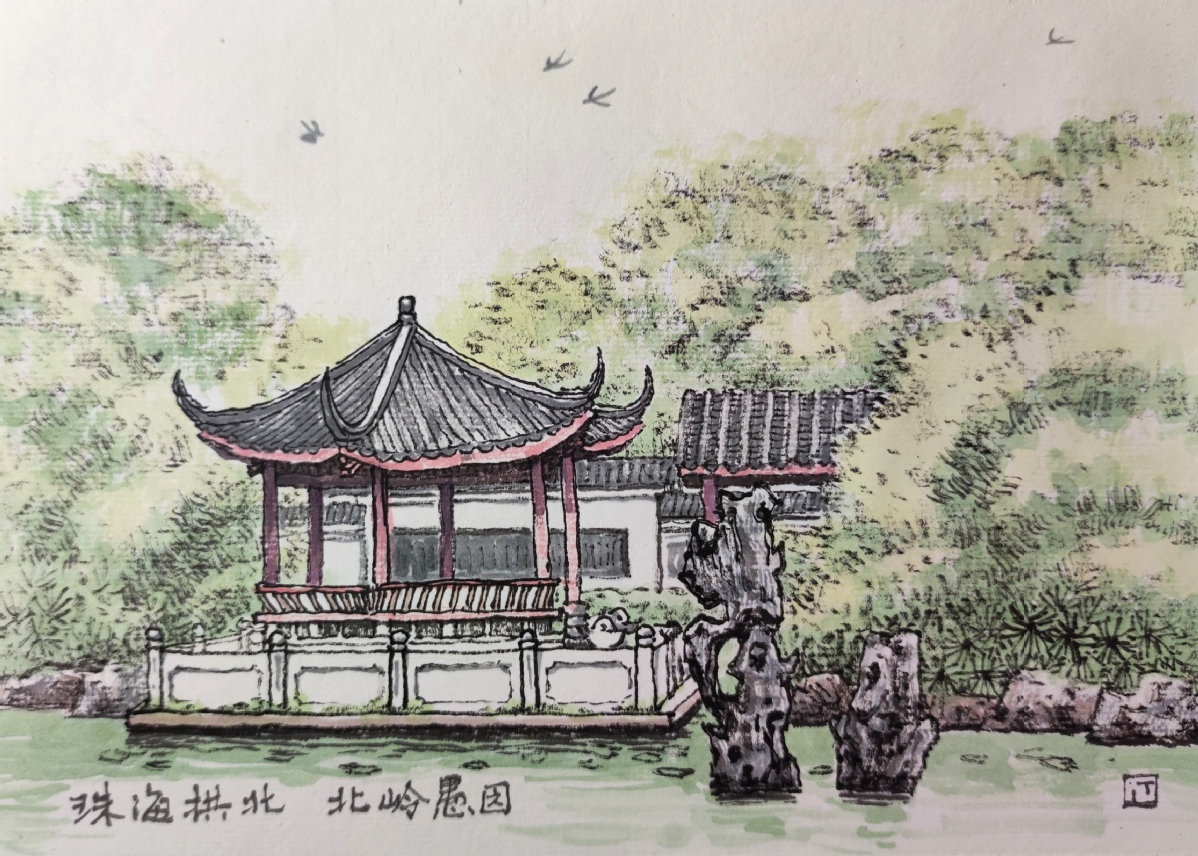


□刘刚
霜花坠落人间的声音
与清晨的炊烟一样轻
生命不会察觉
只有推开眼帘的刹那
云遮雾绕的画卷
像昨夜逶迤的梦
在天地间随风徜徉
鸟雀与歇息的老黄牛
默然倒数春归的日子
曾经喧嚣的雨
和狂乱奔跑的风,此刻
蜷缩在山的另一边
进入冬眠。这个季节
与土地一起静默不语
只为做好起跑姿势
只待发令枪响
便与春风竞相冲刺

□刘文俊
世间什么音最好听?或许有万千答案。而我的回答是:乡音。
乡音,是你从小就听就学就讲的方言口音。
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的乡音。
乡音是母语灵魂。别人听不懂的话,你听起来却是如饮甘露。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最难改的是乡音。
我的父母从南阳到荆州江陵马山镇。在荆州十几年,仍然不改乡音,不是不想改,而是真难改。日常与人交流,只在河南南阳话中夹杂些许的荆州字词发音而已。我去台湾的舅舅四十余年后回来,也仍然乡音未改。
小弟到洛杉矶二十几年,工作是导游。一日他带团到拉斯维加斯,将所有的团员安排妥当后,他即在街边闲转。突然,他听到一声熟悉的乡音。他扭头寻找,只见一个瘦高个男人,正在打电话,说一口纯正的荆州方言。那人边打电话边走,小弟就在那男人身后跟着听着,一直跟了几条街,那男人的电话打完了,小弟才停下脚步。心里还在回味,回味那无比亲切的荆州乡音。
我们姐弟四人走过很多地方,却只对荆州话情有独钟。不论身处何地,只要听到荆州话,仿佛似回到家一样。
或许没有长期在外工作生活的人不知道乡音的悦耳动听。2002年,我来珠海一外企工作,厂里有几十个荆州市公安县和监利县人。他们说着与荆州相似的话。包括湖南常德人也一样。虽然乡音略有差异,我都统统将其归视为老乡。闲暇之时,与他们用乡音聊天,亲切而自然。乡音相同,文化也相同,包括饮食文化更是趋同,在一起聊天的话题也就多了。
乡音是一条纽带,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那时的我而言,有了乡音加持,推进工作起来就方便多了。
此外,乡音也有意想不到的用处:对于我小弟而言,乡音在与不同国别的人交流上面竟也帮助了他。比如荆州话带“嘚儿”的颤音。而墨西哥话同样带颤音。小弟曾同我讲,对于他来说,学墨西哥语就比其他国人容易多了;同样是荆州话尾的“嘚儿”,在大弟学吹笛子时,别的同学难学笛子的颤音,而大弟从小说话就学会了颤抖,毫不费力地就克服了这个难题。
乡音。同一乡镇为一乡音。同一个县乡音不同。省与省更是不同的乡音。但如果出国,普通话就是乡音。
在国外,乡音是外语。小弟早年移居美国后,在家就教两个女儿说中国话,说普通话,也说南阳话,也说荆州话。主要是以普通话为主。小弟的女儿会说中国普通话,多了一门语言技能,也多了一份工资。
总而言之,乡音是最美的音乐,也是最解相思的表达。乡音是每个人的胎记,伴随着你我一生。

□杨靖
我的家,在城市的三环边上。一条四车道三环路,宛如一条隐形的分界线,巧妙地隔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景。往内,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熙攘都市,那里霓虹闪烁欲望,人潮涌动梦想;向外则是田野错落、炊烟袅袅的乡村风物,那里绿树成荫好纳凉,鸟语花香温柔乡。这两种风景,如同生活的双面镜,既映照出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又勾勒出乡村的恬淡与闲适。而我,就幸运地生活在这样的交汇点上,享受城市与乡村给予的双重馈赠,体验着一种独特而美好的生活。
清晨,当阳光穿透氤氲的薄雾,轻落飘窗,随着纱幔晃动,惺忪中无意瞥见时间行走的具象。不必急于起床,因为这里没有闹钟的催促和脚步的匆忙。我可以慵懒地舒展腰身,推窗亲吻晨光。也可以悠闲地泡上一杯茉莉花茶,斜躺在摇椅上,一边呷茶品香,一边抬眼眺望。东边,是渐渐苏醒的城市,高楼大厦在阳光的照耀下跳动金色的光芒,仿佛每一栋建筑都在诉说着拔地而起的喷薄成长;西边,则是依旧宁静的乡村,晨雾缭绕,花猫跳过房梁,寻一处太阳,黄狗蹲守墙根,护一家安康。田野上偶尔传来几声鸡鸣和牛哞,那是大自然最质朴的乐章。
清茶过后,是我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光。城市的便利,让我可以轻松享受到各式各样的美食,无论是街角咖啡馆里那浓郁的拿铁,还是转角包子铺那热气腾腾的诱香,或是马路边小推车上的一根酥脆的油条,抑或面馆里一碗暖身的面汤,都能满足我对美食的无限向往。但更多的时候,我会选择穿绿道,踏小径,去村头的苍蝇馆子。那里有着地道的农家菜,应季蔬菜直接从店家门前的地里采摘,简单烹饪后便能激发出食材最本真的味道,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嘉奖。
工作与学习,是我作为城市边缘居民的日常。得益于日渐便捷的交通建设,我可以轻松穿梭于城区之间,最快地接触到最前沿的信息和技术,与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交流思想,火花一碰撞,就绚烂得如同华灯初上,满目辉煌。写字楼里,聚集了天南海北的打工者,滑动鼠标推动项目的进展,敲击键盘书写心中的理想。直到日近黄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便踏出办公室,坐上公交车,回到城市边缘,那里有属于我的一片静谧。在厨房的油烟中,我可以翻炒出手机视频里保存已久的菜品。在书房的灯光下,我可以在文字的大海中翱翔,或是读一段汪国真的散文,或是思一会儿东野圭吾的推理,或是誊写两页钟意的段落,或是心痒提笔继续我未完的创作。这种城与乡的无缝切换,既让我保持了与时代的同步,又不失对内心世界的滋养。
写累了,就晃晃脖子,起身踱步至阳台,在夜幕降临下,远眺城市的灯火与乡村的星光。一笛车鸣钻进左耳,一声犬吠轻吻右耳。时间的快慢,气氛的动静,如此分明,好似我的人生一样,既孜孜以求心中所求,又沉溺耽享宁静安详。若是到了周末,我会约上三五好友,或是去看一场国际展览;或是聚拢探讨村外的远方。聊起劲儿了,总耐不住性子,驱车前往,行至大路末端,遂下车徒步,沿着蜿蜒小径,呼吸清新空气,聆听林间呢喃。有时候,我们还会深入到乡村深处,参与一场农事劳作,插秧摘果,喂鸡钓鱼,那种源自大地的亲密触感,总让人流连忘返。
生活在城市边缘,是一种双重体验的人生幸运。让我深刻地理解了生活的真谛——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如何去感受,去体验。在这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也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与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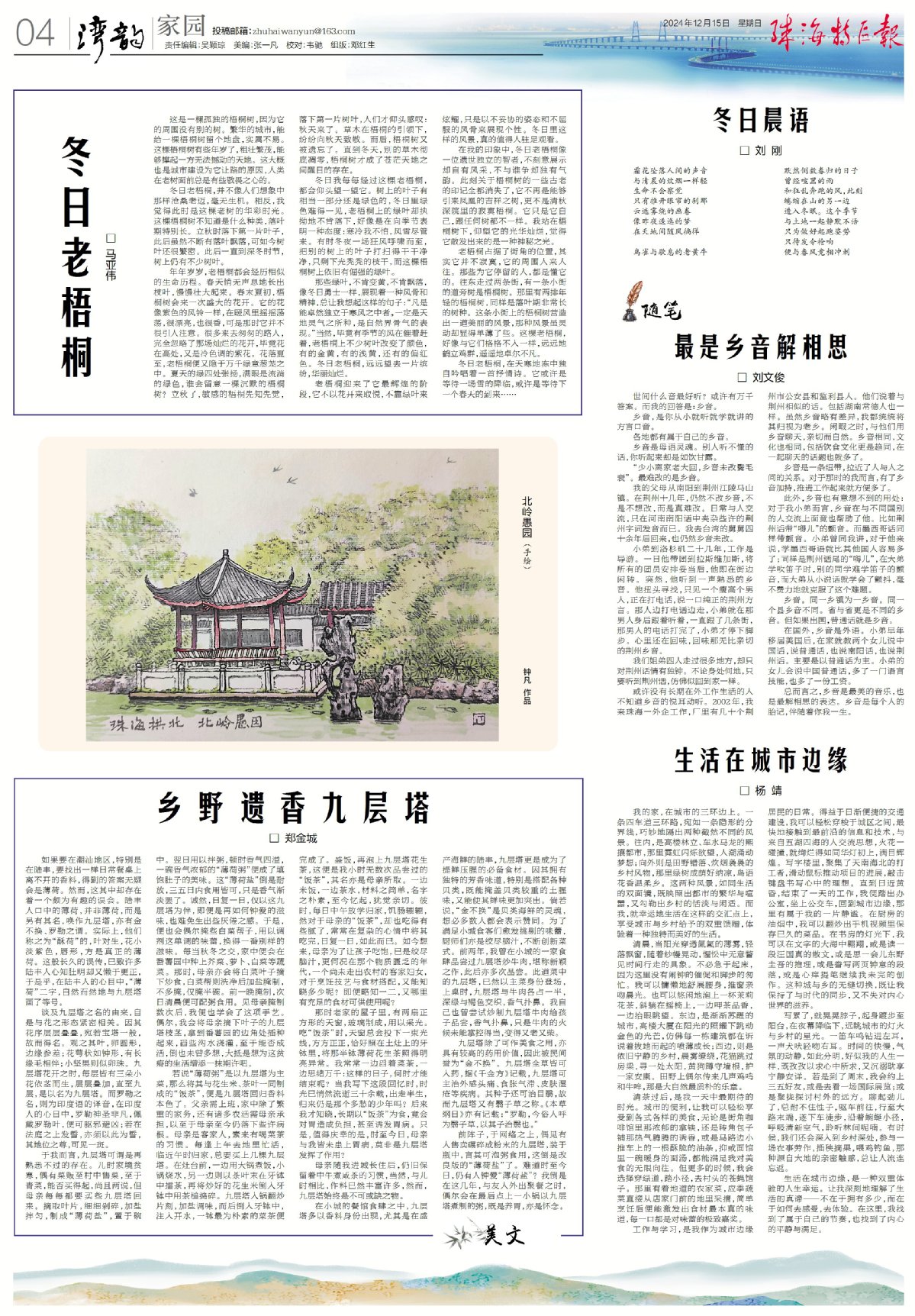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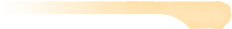

□马亚伟
这是一棵孤独的梧桐树,因为它的周围没有别的树。繁华的城市,能给一棵梧桐树留个地盘,实属不易。这棵梧桐树有些年岁了,粗壮繁茂,能够撑起一方无法撼动的天地。这大概也是城市建设为它让路的原因,人类在老树面前总是有些敬畏之心的。
冬日老梧桐,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沧桑老迈,毫无生机。相反,我觉得此时是这棵老树的华彩时光。这棵梧桐树不知道是什么种类,落叶期特别长。立秋时落下第一片叶子,此后虽然不断有落叶飘落,可如今树叶还很繁密。此后一直到深冬时节,树上仍有不少树叶。
年年岁岁,老梧桐都会经历相似的生命历程。春天悄无声息地长出枝叶,慢慢壮大起来。春末夏初,梧桐树会来一次盛大的花开。它的花像紫色的风铃一样,在暖风里摇摇荡荡,很漂亮,也很香,可是那时它并不很引人注意。很多来去匆匆的路人,完全忽略了那场灿烂的花开,毕竟花在高处,又是冷色调的紫花。花落夏至,老梧桐便又隐于万千绿意葱茏之中。夏天的绿四处张扬,满眼是流淌的绿色,谁会留意一棵沉默的梧桐树?立秋了,敏感的梧桐先知先觉,落下第一片树叶,人们才仰头感叹:秋天来了。草木在梧桐的引领下,纷纷向秋天致敬。而后,梧桐树又被遗忘了。直到冬天,别的草木彻底凋零,梧桐树才成了苍茫天地之间醒目的存在。
冬日我每每经过这棵老梧桐,都会仰头望一望它。树上的叶子有相当一部分还是绿色的,冬日里绿色难得一见,老梧桐上的绿叶却执拗地不肯落下,好像是在向季节表明一种态度:寒冷我不怕,风雪尽管来。有时冬夜一场狂风呼啸而至,把别的树上的叶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而这棵梧桐树上依旧有倔强的绿叶。
那些绿叶,不肯变黄,不肯飘落,像冬日勇士一样,展现着一种风骨和精神,总让我想起这样的句子:“凡是能卓然独立于寒风之中者,一定是天地灵气之所种,是自然界骨气的表现。”当然,毕竟有季节的风在催着赶着,老梧桐上不少树叶改变了颜色,有的金黄,有的浅黄,还有的偏红色。冬日老梧桐,远远望去一片缤纷,华丽灿烂。
老梧桐迎来了它最辉煌的阶段,它不以花开来取悦,不靠绿叶来炫耀,只是以不妥协的姿态和不屈服的风骨来展现个性。冬日里这样的风景,真的值得人驻足观看。
在我的印象中,冬日老梧桐像一位遗世独立的智者,不刻意展示却自有风采,不与谁争却独有气韵。此刻关于梧桐树的一些古老的印记全都消失了,它不再是能够引来凤凰的吉祥之树,更不是清秋深院里的寂寞梧桐。它只是它自己,跟任何树都不一样。我站在梧桐树下,仰望它的光华灿烂,觉得它散发出来的是一种神秘之光。
老梧桐占据了街角的位置,其实它并不寂寞,它的周围人来人往。那些为它停留的人,都是懂它的。往东走过两条街,有一条小街的道旁树是梧桐树。那里有两排年轻的梧桐树,同样是落叶期非常长的树种。这条小街上的梧桐树营造出一道美丽的风景,那种风景虽灵动却显得单薄了些。这棵老梧桐,好像与它们格格不入一样,远远地鹤立鸡群,遥遥地卓尔不凡。
冬日老梧桐,在天寒地冻中独自吟唱着一首抒情诗。它或许是等待一场雪的降临,或许是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郑金城
如果要在潮汕地区,特别是在陆丰,要找出一样日常餐桌上离不开的香料,得到的答案无疑会是薄荷。然而,这其中却存在着一个颇为有趣的误会。陆丰人口中的薄荷,并非薄荷,而是另有其名,唤作九层塔,亦有金不换、罗勒之谓。实际上,他们称之为“酥荷”的,叶对生,花小淡紫色,唇形,方是真正的薄荷。这般长久的误传,已致许多陆丰人心知肚明却又懒于更正,于是乎,在陆丰人的心目中,“薄荷”二字,自然而然地与九层塔画了等号。
谈及九层塔之名的由来,自是与花之形态紧密相关。因其花序层层叠叠,宛若宝塔一般,故而得名。观之其叶,卵圆形,边缘参差;花萼状如钟形,有长缘毛相伴;小坚果则似卵珠。九层塔花开之时,每层皆有三朵小花依茎而生,层层叠加,直至九层,是以名为九层塔。而罗勒之名,则为印度语的译音,在印度人的心目中,罗勒神圣非凡,佩戴罗勒叶,便可驱邪避凶;若在法庭之上发誓,亦须以此为誓,其地位之尊,可见一斑。
于我而言,九层塔可谓是再熟悉不过的存在。儿时家境贫寒,偶有菜贩至村中售菜,至于青菜,能否买得起,尚且两说,但母亲每每都要买些九层塔回来。摘取叶片,细细剁碎,加盐拌匀,制成“薄荷盐”,置于碗中。翌日用以拌粥,顿时香气四溢,一碗香气浓郁的“薄荷粥”便成了填饱肚子的美味。这“薄荷盐”倒是耐放,三五日内食用皆可,只是香气渐淡罢了。诚然,日复一日,仅以这九层塔为伴,即便是再如何钟爱的滋味,也难免生出些厌倦之感。于是,便也会偶尔腌些白菜帮子,用以调剂这单调的味蕾,换得一番别样的滋味。每当秋冬之交,家中便会在番薯园中种上芥菜、萝卜、白菜等蔬菜。那时,母亲亦会将白菜叶子摘下炒食,白菜帮则洗净后加盐腌制,不多腌,仅腌半碗。前一晚腌制,次日清晨便可配粥食用。见母亲腌制数次后,我便也学会了这项手艺。偶尔,我会将母亲摘下叶子的九层塔枝茎,拿到番薯园的边角处插种起来,舀些沟水浇灌,至于能否成活,倒也未曾多想,大抵是想为这贫瘠的生活增添一抹期许吧。
若说“薄荷粥”是以九层塔为主菜,那么将其与花生米、茶叶一同制成的“饭茶”,便是九层塔回归香料本色了。父亲需上班,家中除了繁重的家务,还有诸多农活需母亲承担,以至于母亲至今仍落下些许病根。母亲是客家人,素来有喝菜茶的习惯。每逢上午去地里忙活,临近午时归家,总要买上几棵九层塔。在灶台前,一边用大锅煮饭,小锅烧水,另一边则以茶叶末在牙钵中擂茶,再将炒好的花生米倒入牙钵中用茶槌捣碎。九层塔入锅翻炒片刻,加盐调味,而后倒入牙钵中,注入开水,一钵最为朴素的菜茶便完成了。盛饭,再泡上九层塔花生茶,这便是我小时无数次品尝过的“饭茶”,其名亦是母亲所取。一边米饭,一边茶水,材料之简单,名字之朴素,至今忆起,犹觉亲切。彼时,每日中午放学归家,饥肠辘辘,然对于母亲的“饭茶”,却也吃得有些腻了,常常在复杂的心情中将其吃完,日复一日,如此而已。如今想来,母亲为了让孩子吃饱,已是绞尽脑汁,更何况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个尚未走出农村的客家妇女,对于烹饪技艺与食材搭配,又能知晓多少呢?即便略知一二,又哪里有充足的食材可供使用呢?
那时老家的屋子里,有两扇正方形的天窗,玻璃制成,用以采光。吃“饭茶”时,天窗总会投下一束光线,方方正正,恰好照在土灶上的牙钵里,将那半钵薄荷花生茶照得明亮异常。我常常一边舀着菜茶,一边思绪万千:这样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呢?当我写下这段回忆时,时光已悄然流逝三十余载,出走半生,归来仍是那个多愁的少年吗?后来我才知晓,长期以“饭茶”为食,竟会对胃造成负担,甚至诱发胃病。只是,值得庆幸的是,时至今日,母亲与我皆未患上胃病,莫非是九层塔发挥了作用?
母亲随我进城长住后,仍旧保留着中午煮咸茶的习惯,当然,与儿时相比,作料已然丰富许多,然而,九层塔始终是不可或缺之物。
在小城的餐馆食肆之中,九层塔多以香料身份出现,尤其是在盛产海鲜的陆丰,九层塔更是成为了提鲜压腥的必备食材。因其拥有独特的芳香味道,特别是搭配各种贝类,既能掩盖贝类较重的土腥味,又能使其鲜味更加突出。倘若说,“金不换”是贝类海鲜的灵魂,想必多数人都会表示赞同。为了满足小城食客们愈发挑剔的味蕾,厨师们亦是绞尽脑汁,不断创新菜式。前两年,我曾在小城的一家食肆品尝过九层塔炒牛肉,堪称新颖之作,此后亦多次品尝。此道菜中的九层塔,已然以主菜身份登场,上桌时,九层塔与牛肉各占一半,深绿与褐色交织,香气扑鼻。我自己也曾尝试炒制九层塔牛肉给孩子品尝,香气扑鼻,只是牛肉的火候未能掌控得当,变得又老又柴。
九层塔除了可作美食之用,亦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因此被民间誉为“金不换”。九层塔全草皆可入药,据《千金方》记载,九层塔可主治外感头痛、食胀气滞、皮肤湿疮等疾病。其种子还可治目翳,故而九层塔又有翳子草之称。《本草纲目》亦有记载:“罗勒,今俗人呼为翳子草,以其子治翳也。”
前阵子,于网络之上,偶见有人售卖碾碎成粉末的九层塔,装于瓶中,言其可泡粥食用,这倒是改良版的“薄荷盐”了。难道时至今日,仍有人钟爱“薄荷盐”?我倒是在这几年,与友人外出聚餐之时,偶尔会在最后点上一小锅以九层塔煮制的粥,既是养胃,亦是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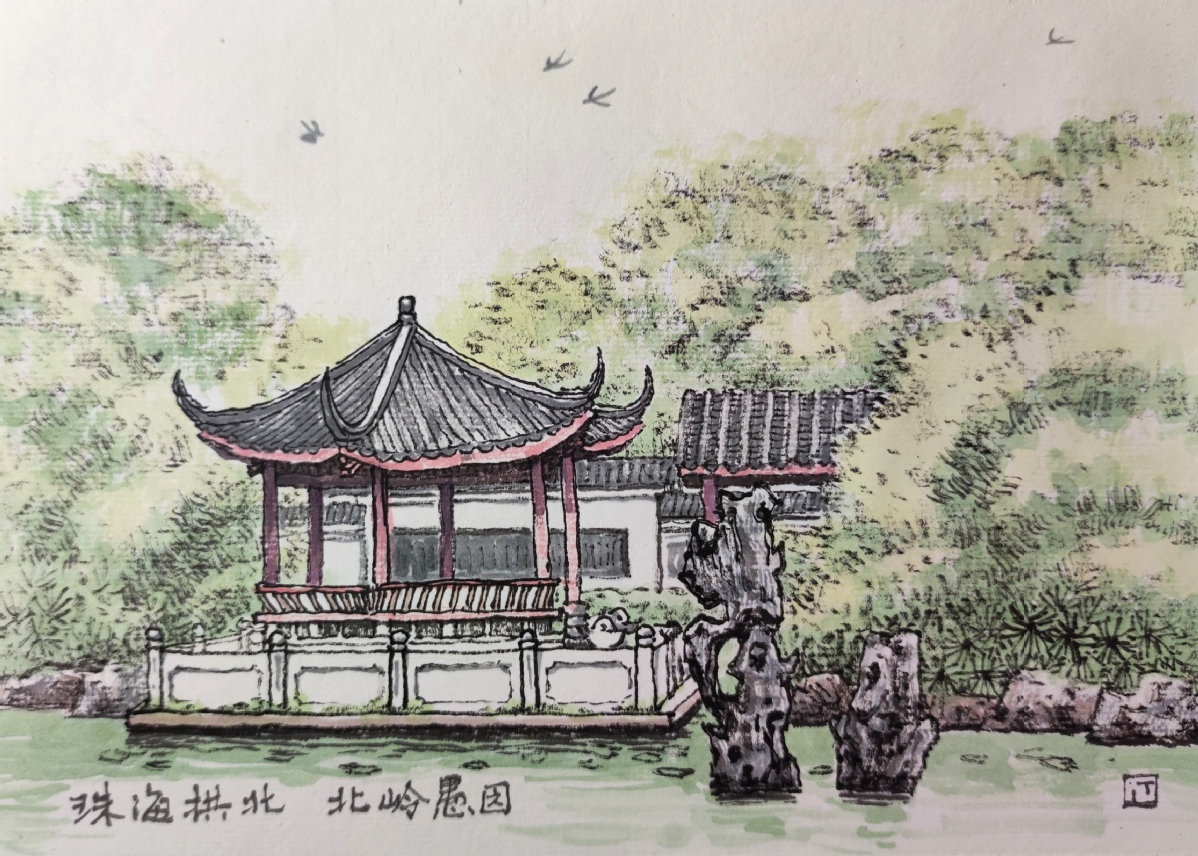


□刘刚
霜花坠落人间的声音
与清晨的炊烟一样轻
生命不会察觉
只有推开眼帘的刹那
云遮雾绕的画卷
像昨夜逶迤的梦
在天地间随风徜徉
鸟雀与歇息的老黄牛
默然倒数春归的日子
曾经喧嚣的雨
和狂乱奔跑的风,此刻
蜷缩在山的另一边
进入冬眠。这个季节
与土地一起静默不语
只为做好起跑姿势
只待发令枪响
便与春风竞相冲刺

□刘文俊
世间什么音最好听?或许有万千答案。而我的回答是:乡音。
乡音,是你从小就听就学就讲的方言口音。
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的乡音。
乡音是母语灵魂。别人听不懂的话,你听起来却是如饮甘露。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最难改的是乡音。
我的父母从南阳到荆州江陵马山镇。在荆州十几年,仍然不改乡音,不是不想改,而是真难改。日常与人交流,只在河南南阳话中夹杂些许的荆州字词发音而已。我去台湾的舅舅四十余年后回来,也仍然乡音未改。
小弟到洛杉矶二十几年,工作是导游。一日他带团到拉斯维加斯,将所有的团员安排妥当后,他即在街边闲转。突然,他听到一声熟悉的乡音。他扭头寻找,只见一个瘦高个男人,正在打电话,说一口纯正的荆州方言。那人边打电话边走,小弟就在那男人身后跟着听着,一直跟了几条街,那男人的电话打完了,小弟才停下脚步。心里还在回味,回味那无比亲切的荆州乡音。
我们姐弟四人走过很多地方,却只对荆州话情有独钟。不论身处何地,只要听到荆州话,仿佛似回到家一样。
或许没有长期在外工作生活的人不知道乡音的悦耳动听。2002年,我来珠海一外企工作,厂里有几十个荆州市公安县和监利县人。他们说着与荆州相似的话。包括湖南常德人也一样。虽然乡音略有差异,我都统统将其归视为老乡。闲暇之时,与他们用乡音聊天,亲切而自然。乡音相同,文化也相同,包括饮食文化更是趋同,在一起聊天的话题也就多了。
乡音是一条纽带,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那时的我而言,有了乡音加持,推进工作起来就方便多了。
此外,乡音也有意想不到的用处:对于我小弟而言,乡音在与不同国别的人交流上面竟也帮助了他。比如荆州话带“嘚儿”的颤音。而墨西哥话同样带颤音。小弟曾同我讲,对于他来说,学墨西哥语就比其他国人容易多了;同样是荆州话尾的“嘚儿”,在大弟学吹笛子时,别的同学难学笛子的颤音,而大弟从小说话就学会了颤抖,毫不费力地就克服了这个难题。
乡音。同一乡镇为一乡音。同一个县乡音不同。省与省更是不同的乡音。但如果出国,普通话就是乡音。
在国外,乡音是外语。小弟早年移居美国后,在家就教两个女儿说中国话,说普通话,也说南阳话,也说荆州话。主要是以普通话为主。小弟的女儿会说中国普通话,多了一门语言技能,也多了一份工资。
总而言之,乡音是最美的音乐,也是最解相思的表达。乡音是每个人的胎记,伴随着你我一生。

□杨靖
我的家,在城市的三环边上。一条四车道三环路,宛如一条隐形的分界线,巧妙地隔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景。往内,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熙攘都市,那里霓虹闪烁欲望,人潮涌动梦想;向外则是田野错落、炊烟袅袅的乡村风物,那里绿树成荫好纳凉,鸟语花香温柔乡。这两种风景,如同生活的双面镜,既映照出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又勾勒出乡村的恬淡与闲适。而我,就幸运地生活在这样的交汇点上,享受城市与乡村给予的双重馈赠,体验着一种独特而美好的生活。
清晨,当阳光穿透氤氲的薄雾,轻落飘窗,随着纱幔晃动,惺忪中无意瞥见时间行走的具象。不必急于起床,因为这里没有闹钟的催促和脚步的匆忙。我可以慵懒地舒展腰身,推窗亲吻晨光。也可以悠闲地泡上一杯茉莉花茶,斜躺在摇椅上,一边呷茶品香,一边抬眼眺望。东边,是渐渐苏醒的城市,高楼大厦在阳光的照耀下跳动金色的光芒,仿佛每一栋建筑都在诉说着拔地而起的喷薄成长;西边,则是依旧宁静的乡村,晨雾缭绕,花猫跳过房梁,寻一处太阳,黄狗蹲守墙根,护一家安康。田野上偶尔传来几声鸡鸣和牛哞,那是大自然最质朴的乐章。
清茶过后,是我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光。城市的便利,让我可以轻松享受到各式各样的美食,无论是街角咖啡馆里那浓郁的拿铁,还是转角包子铺那热气腾腾的诱香,或是马路边小推车上的一根酥脆的油条,抑或面馆里一碗暖身的面汤,都能满足我对美食的无限向往。但更多的时候,我会选择穿绿道,踏小径,去村头的苍蝇馆子。那里有着地道的农家菜,应季蔬菜直接从店家门前的地里采摘,简单烹饪后便能激发出食材最本真的味道,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嘉奖。
工作与学习,是我作为城市边缘居民的日常。得益于日渐便捷的交通建设,我可以轻松穿梭于城区之间,最快地接触到最前沿的信息和技术,与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交流思想,火花一碰撞,就绚烂得如同华灯初上,满目辉煌。写字楼里,聚集了天南海北的打工者,滑动鼠标推动项目的进展,敲击键盘书写心中的理想。直到日近黄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便踏出办公室,坐上公交车,回到城市边缘,那里有属于我的一片静谧。在厨房的油烟中,我可以翻炒出手机视频里保存已久的菜品。在书房的灯光下,我可以在文字的大海中翱翔,或是读一段汪国真的散文,或是思一会儿东野圭吾的推理,或是誊写两页钟意的段落,或是心痒提笔继续我未完的创作。这种城与乡的无缝切换,既让我保持了与时代的同步,又不失对内心世界的滋养。
写累了,就晃晃脖子,起身踱步至阳台,在夜幕降临下,远眺城市的灯火与乡村的星光。一笛车鸣钻进左耳,一声犬吠轻吻右耳。时间的快慢,气氛的动静,如此分明,好似我的人生一样,既孜孜以求心中所求,又沉溺耽享宁静安详。若是到了周末,我会约上三五好友,或是去看一场国际展览;或是聚拢探讨村外的远方。聊起劲儿了,总耐不住性子,驱车前往,行至大路末端,遂下车徒步,沿着蜿蜒小径,呼吸清新空气,聆听林间呢喃。有时候,我们还会深入到乡村深处,参与一场农事劳作,插秧摘果,喂鸡钓鱼,那种源自大地的亲密触感,总让人流连忘返。
生活在城市边缘,是一种双重体验的人生幸运。让我深刻地理解了生活的真谛——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如何去感受,去体验。在这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也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与满足。

-我已经到底线啦-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