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慧谋
2025-04-18 04:29
张慧谋
2025-04-18 04:29
李好的《海在低处》摄影艺术作品展近日在珠海古元美术馆开展,并引起轰动,这是我意料中的事情。策展人通过光影和场景氛围,把李好的这组《海在低处》衬托得淋漓尽致,别具匠心的创意,大大提升了这组摄影作品的艺术效果。策展者是珠海古元美术馆策展部主任庄丽,整个展场的氛围质朴大气,与《海在低处》这组以黑白为主调的摄影艺术作品浑然一体。可见,策展者读懂了李好,读懂了一位摄影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我与李好同在一个纬度的海岸线上出生成长,从小闻着海腥味、听着浪涛声长大,见证了渔人与海的共存,见证了这些年人类与大海的博弈,甚至见证了时间的足迹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流逝,像地里的庄稼一样被海浪收割,又随着潮汐澎湃而生。当若干年前作为摄影爱好者的李好,八进青藏高原完成《朝拜者》系列作品后,在蓦然回首中,他看见了南方那片熟悉的大海,如同一次巅峰高潮过后,他的内心归复平静,回归到海的低处。
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首关于海的诗,其中有句:“……云啊,高高在上,白白的浮云。海在低处,潮汐在低处,渔网挂在低处……”我与李好的年龄有一定差距,当我伏在“海的低处”写诗时,他还在求学之路。当他从高原回望“海的低处”时,我已经完成了与海有关的诗集《渔火把夜色吹白》。
我与李好有个共同点,就是喜欢吃海鲜。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大海的基因,因此在某些方面,形成了海的个性。比如说李好,他是个非常爱冲动的人,喜欢面对挑战,喜欢在浪尖上舞蹈,充满冒险精神。又比如我,喜欢夜色,喜欢海上渔火,面对多变的世界,总是像渔火一样怀抱光芒,冷静得近于无情。我与李好,传承了海的两面性,因为,我们都是大海的儿子。
李好的整个创作过程,我是旁观者,更是知音。摄影和文学是对孪生兄弟,两者之间有距离,但更多的是共通共融,共鸣共感。摄影是以镜头以影像记录生活,文学是以笔以文字书写灵感,但归根到底,摄影和文学展示的都是人性内心世界。从李好的摄影作品里,我常常读到画面文字,甚至读出心跳、读出怜悯、读出沧桑。但我深信,李好读我的文字时,也会读出同样的感觉。
尽管我对李好的摄影作品非常熟悉,但那天在古元美术馆观看《海在低处》时,不仅仅是震撼,更有一种久违的“陌生感”。面对这些黑白照片,我仿佛回到远古的洪荒时代,回到夜与昼的初始期。黑白如此鲜明,几乎把当下眼花缭乱的颜色抽光,只有黑与白,才是永恒的。
是的,李好一直在追求永恒,孤身一人在广袤旷野上行走,在无人随行的漫长海岸线行走。他用他的镜头在建立“一个人的海岸线”,不与他人争道,他走他的独木桥,坚持走下去,哪怕他是这条道上唯一的孤行者。
作品成功与否并非一个摄影家的唯一标准,没有哪门艺术是可以统一天下人心的,更何况是把自己定格在镜头有限空间的摄影艺术家。李好虽然摘取了国内摄影界最高的“金像奖”,但对于他,仅仅是评委们对他的作品认可和肯定,或者说,这是他摄影生涯的一个新高度新起点。但是,作为旁观者,作为李好认可的亲如兄弟般的老哥,我更看重李好在做什么?做了些什么?
在展馆里陪着我观展的还有《广州文艺》主编、作家张鸿,除了主编、作家身份,张鸿同样是一位资深的摄影家。我与张鸿探讨一个问题,李好这个主题的摄影作品在隐喻着什么?作品背后的那个李好他内心在思考着什么?这才是我和张鸿看展时探讨的话题。
我无法说出李好的这批作品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因为我根本就不懂得摄影艺术的标准和深度,我只知道一幅作品给了我启发和有话可说的感觉,在乎它给我灵魂的震撼和内心的感动,这就足够了。理论是理论家们的话语权,是他们的发现和对摄影标准重构的一个世界,有方向性的指引和境界上的升华。而我,是一个不懂门道只看品质的外行人。我在观看李好的摄影作品时,似乎有一双深邃得难以莫测的“眼睛”在看着我。
我特别在乎看影展时油然而生的这种感觉,或者是作品自身的隐喻,给我带来的这份“陌生感”。
在场的作品都是经过李好精心挑选的,可以说,这是李好从他的几十万张底片里选出几十幅构成《海在低处》主题的摄影作品展,每一张都有着难以拔掉的理由和空间,它们构成的整体,虽然不能绝对代表“海在低处”主题的全部创作,但它们可以撑起这个主题的高度或者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部分。
展出的每幅作品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并且引起强烈共鸣。也许我太熟悉李好的作品了,异常平静地观看,异常平静地品味,异常平静地思考。作品中的场景都是我司空见惯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那么似曾相识,甚至可以叫出他们的辈分和名字。因为看到他们,就想起我的渔民父亲和他的渔民兄弟。这就是大海的基因始终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看见大海在一天天地老去,看到如此庞大无比而又富饶的大海在步步临近贫困线,我在想,物产再丰富的大海也会被无度的掠夺者掏空。当大海仅剩下海水时,人类的生存也难以为继,这绝对不是骇人听闻的预言。
或许,这就是《海在低处》的隐喻和内涵,但愿我的判断和理解是错误的。

李好的《海在低处》摄影艺术作品展近日在珠海古元美术馆开展,并引起轰动,这是我意料中的事情。策展人通过光影和场景氛围,把李好的这组《海在低处》衬托得淋漓尽致,别具匠心的创意,大大提升了这组摄影作品的艺术效果。策展者是珠海古元美术馆策展部主任庄丽,整个展场的氛围质朴大气,与《海在低处》这组以黑白为主调的摄影艺术作品浑然一体。可见,策展者读懂了李好,读懂了一位摄影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我与李好同在一个纬度的海岸线上出生成长,从小闻着海腥味、听着浪涛声长大,见证了渔人与海的共存,见证了这些年人类与大海的博弈,甚至见证了时间的足迹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流逝,像地里的庄稼一样被海浪收割,又随着潮汐澎湃而生。当若干年前作为摄影爱好者的李好,八进青藏高原完成《朝拜者》系列作品后,在蓦然回首中,他看见了南方那片熟悉的大海,如同一次巅峰高潮过后,他的内心归复平静,回归到海的低处。
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首关于海的诗,其中有句:“……云啊,高高在上,白白的浮云。海在低处,潮汐在低处,渔网挂在低处……”我与李好的年龄有一定差距,当我伏在“海的低处”写诗时,他还在求学之路。当他从高原回望“海的低处”时,我已经完成了与海有关的诗集《渔火把夜色吹白》。
我与李好有个共同点,就是喜欢吃海鲜。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大海的基因,因此在某些方面,形成了海的个性。比如说李好,他是个非常爱冲动的人,喜欢面对挑战,喜欢在浪尖上舞蹈,充满冒险精神。又比如我,喜欢夜色,喜欢海上渔火,面对多变的世界,总是像渔火一样怀抱光芒,冷静得近于无情。我与李好,传承了海的两面性,因为,我们都是大海的儿子。
李好的整个创作过程,我是旁观者,更是知音。摄影和文学是对孪生兄弟,两者之间有距离,但更多的是共通共融,共鸣共感。摄影是以镜头以影像记录生活,文学是以笔以文字书写灵感,但归根到底,摄影和文学展示的都是人性内心世界。从李好的摄影作品里,我常常读到画面文字,甚至读出心跳、读出怜悯、读出沧桑。但我深信,李好读我的文字时,也会读出同样的感觉。
尽管我对李好的摄影作品非常熟悉,但那天在古元美术馆观看《海在低处》时,不仅仅是震撼,更有一种久违的“陌生感”。面对这些黑白照片,我仿佛回到远古的洪荒时代,回到夜与昼的初始期。黑白如此鲜明,几乎把当下眼花缭乱的颜色抽光,只有黑与白,才是永恒的。
是的,李好一直在追求永恒,孤身一人在广袤旷野上行走,在无人随行的漫长海岸线行走。他用他的镜头在建立“一个人的海岸线”,不与他人争道,他走他的独木桥,坚持走下去,哪怕他是这条道上唯一的孤行者。
作品成功与否并非一个摄影家的唯一标准,没有哪门艺术是可以统一天下人心的,更何况是把自己定格在镜头有限空间的摄影艺术家。李好虽然摘取了国内摄影界最高的“金像奖”,但对于他,仅仅是评委们对他的作品认可和肯定,或者说,这是他摄影生涯的一个新高度新起点。但是,作为旁观者,作为李好认可的亲如兄弟般的老哥,我更看重李好在做什么?做了些什么?
在展馆里陪着我观展的还有《广州文艺》主编、作家张鸿,除了主编、作家身份,张鸿同样是一位资深的摄影家。我与张鸿探讨一个问题,李好这个主题的摄影作品在隐喻着什么?作品背后的那个李好他内心在思考着什么?这才是我和张鸿看展时探讨的话题。
我无法说出李好的这批作品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因为我根本就不懂得摄影艺术的标准和深度,我只知道一幅作品给了我启发和有话可说的感觉,在乎它给我灵魂的震撼和内心的感动,这就足够了。理论是理论家们的话语权,是他们的发现和对摄影标准重构的一个世界,有方向性的指引和境界上的升华。而我,是一个不懂门道只看品质的外行人。我在观看李好的摄影作品时,似乎有一双深邃得难以莫测的“眼睛”在看着我。
我特别在乎看影展时油然而生的这种感觉,或者是作品自身的隐喻,给我带来的这份“陌生感”。
在场的作品都是经过李好精心挑选的,可以说,这是李好从他的几十万张底片里选出几十幅构成《海在低处》主题的摄影作品展,每一张都有着难以拔掉的理由和空间,它们构成的整体,虽然不能绝对代表“海在低处”主题的全部创作,但它们可以撑起这个主题的高度或者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部分。
展出的每幅作品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并且引起强烈共鸣。也许我太熟悉李好的作品了,异常平静地观看,异常平静地品味,异常平静地思考。作品中的场景都是我司空见惯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那么似曾相识,甚至可以叫出他们的辈分和名字。因为看到他们,就想起我的渔民父亲和他的渔民兄弟。这就是大海的基因始终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看见大海在一天天地老去,看到如此庞大无比而又富饶的大海在步步临近贫困线,我在想,物产再丰富的大海也会被无度的掠夺者掏空。当大海仅剩下海水时,人类的生存也难以为继,这绝对不是骇人听闻的预言。
或许,这就是《海在低处》的隐喻和内涵,但愿我的判断和理解是错误的。


-我已经到底线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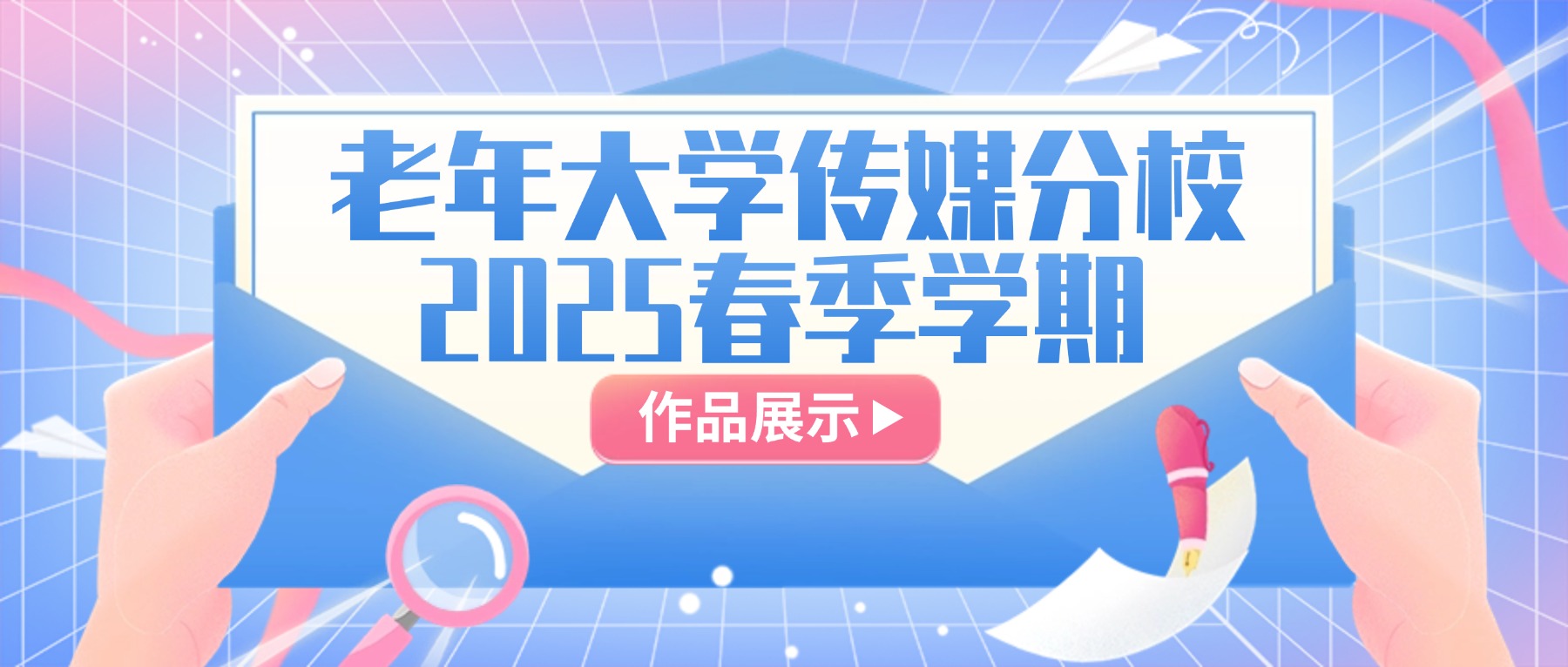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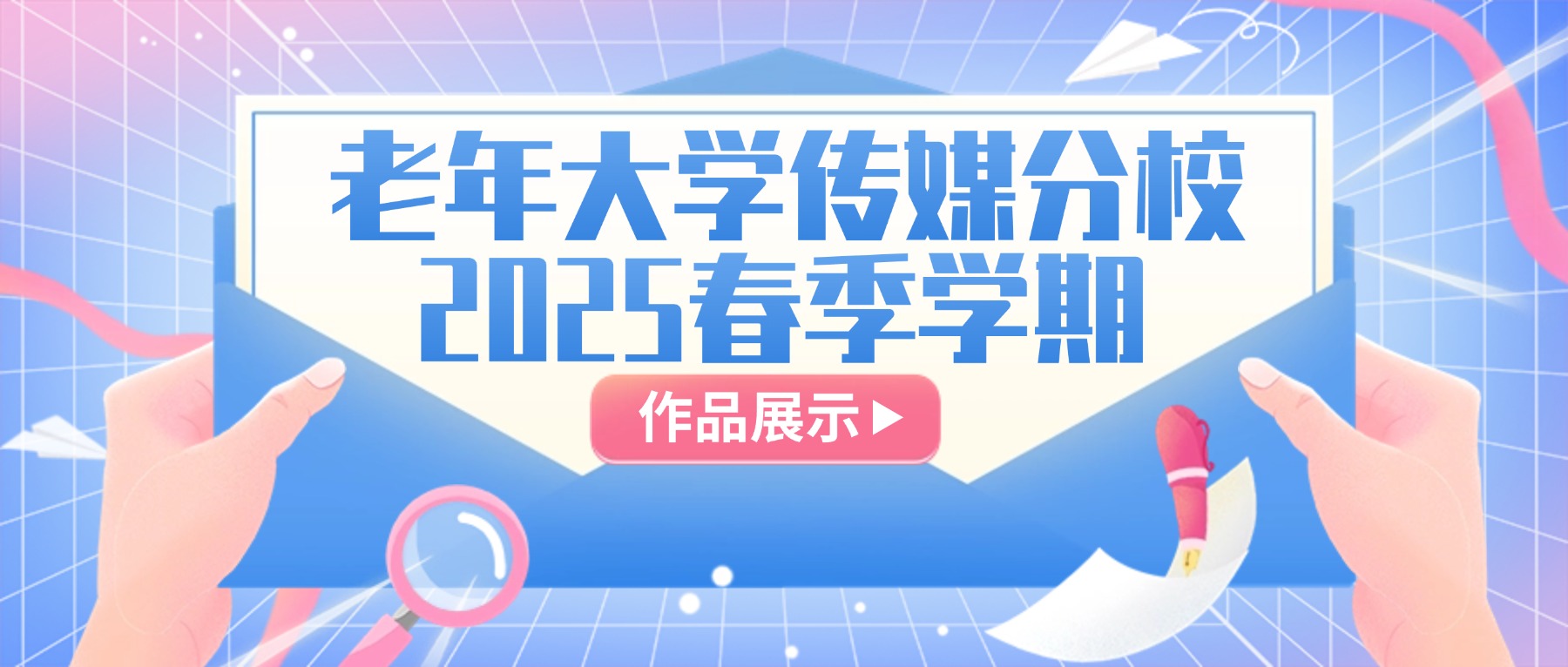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