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云帅
2025-07-14 02:12
陆云帅
2025-07-14 02:12
春山空濛,雨丝斜织成帘。
13岁的父亲,遭遇了失怙之痛,还是个半大孩子的他,早早地和多病的祖母一起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岁月赐缘,1961年的冬至,下半夜,下着毛毛细雨,寒气料峭,我与父亲的生命轨迹正式交汇。
我长到3岁时,祖母去世,接着母亲生我二弟,隔两年又生三弟,再后来是和我们同锅吃饭的婶娘生下三个堂弟妹。我婶娘一边手断残三根手指,算半个劳力。叔父在公路道班工作,微薄工资只够塞牙缝。家中只有我父亲和母亲参加劳动,工分少,口粮少,年年还“超支”,欠集体的债。伯父去世后,丢下双目失明的伯母,伯母无儿无女,我家义无反顾地挑起赡养她的责任。一个大家庭,家徒四壁,艰难异常,但父亲穷不失志,坚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信条,天大的困难,他都不放弃送子上学读书的决心。
伐薪烧炭,是走在悬崖边的高危职业,去路易,回路难,是山里人不得已而为之的活路。苦和累,没话说,难的是那时封山了,村周边的山不能砍柴。能砍柴的,自然是偏远陡峭的悬崖陡坡,还有生产队管不到的山岭。离我家六七里地远,有个叫“丹暖”的弄场,四面环山,东西两峰兀自拔高,像一对隔空对峙的犬牙,东峰一处大崖壁,阴雨天,风鸣空谷,溜滑如镜,还摔死过人。这个好吓人的“丹暖”,反倒变成了我父亲取薪烧炭的“福地”。刚开始,父亲去那里砍柴取薪,碰上街日,就挑到十多里外的地苏街去卖,后来他发现柴火重而难挑,卖价也不好,而木炭价格比柴火高四五倍,挑去街卖又方便许多,于是试着砍柴烧木炭卖,一试效果果然不错。那些年,父亲进山之前,都要预先置办上半袋玉米粉、半箩筐红薯,自己一个人用扁担挑上,一头扎进深山里半月之久,回来后,又蚂蚁搬家地赶地苏或县城的街。好在父亲挑的柴干爽易燃,烧的炭熟透不碎,在整个地苏街上早就有口皆碑了,加上好多人知道父亲挣钱是送孩子读书,常常不问价钱,二话不说就叫父亲往他们家送……记忆里,我们只有在农忙季节,或是像春节这般重大节日,才能见到父亲的身影。
我每每看着父亲进山和出山,心中酸甜苦辣咸一阵阵翻滚,无法用语言形容。父亲进山时,我倚门相送,那时还不懂得“生死两茫茫”的意思,只是觉得父亲一走,家中空得慌,想那山险陡,想那林中幽暗惊悚,一种挥之不去的担忧、愁绪终日萦绕于心,挥之不去。每当父亲从山中归来,我们先是兴奋,既而是心酸和不堪——只见从山中伐薪烧炭日久的父亲,此刻一身褴褛,十指黝黑,污发苍苍,像个叫花子,远远就闻到他身上浓浓的酸味、咸味……
我读到高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常常吃不饱饭,每天都饿得前胸贴后背。车马慢,幸福来得更慢的那两年,周末特别让我惦记,因为每到周末,父亲会在卖掉柴火或木炭后,来学校看我。父亲来时,除了带来红薯、芋头什么的,还带来卖柴炭挣来的皱巴巴的几张毛票,父亲给钱给物并简单叮嘱几句后,便斜扛扁担匆匆而去。
改革开放后,家里的日子渐渐好过起来,但他仍然留在大山里生活。他不再砍柴烧炭,而是搞起小编织,搞搞养殖什么的,挣钱供我的两个弟弟读书,直到他们毕业,有了工作。父亲说,他有编织技艺,山里乡亲们离不开他,他得把这手艺传给年轻人,让他们学了手艺,有饭吃。所以后来,村里人评价父亲有着一副热心肠:有一年冬天,村里一韦姓人家的房子倒塌了。他懂得制瓦,整整一个冬天都在帮他们制瓦,分文不取,还一顿饭都不肯吃。五保户蓝奶奶家的用水,也是父亲挑,一直挑到她去世。村里有什么纠纷,大家都爱找父亲调解,因为他总能秉公处理,让双方都心服口服。
他70岁时,老胃病发作,身体有些挺不住了,才和母亲一起搬来县城。在他住进我家的最后这13年,我常常看见他坐在阳台上,抚着他从老家带来的那根油光发亮的扁担,望着远山发呆。我知道,父亲又沉入回忆,一个人在过往的岁月里行走。
春山空濛,雨丝斜织成帘。
13岁的父亲,遭遇了失怙之痛,还是个半大孩子的他,早早地和多病的祖母一起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岁月赐缘,1961年的冬至,下半夜,下着毛毛细雨,寒气料峭,我与父亲的生命轨迹正式交汇。
我长到3岁时,祖母去世,接着母亲生我二弟,隔两年又生三弟,再后来是和我们同锅吃饭的婶娘生下三个堂弟妹。我婶娘一边手断残三根手指,算半个劳力。叔父在公路道班工作,微薄工资只够塞牙缝。家中只有我父亲和母亲参加劳动,工分少,口粮少,年年还“超支”,欠集体的债。伯父去世后,丢下双目失明的伯母,伯母无儿无女,我家义无反顾地挑起赡养她的责任。一个大家庭,家徒四壁,艰难异常,但父亲穷不失志,坚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信条,天大的困难,他都不放弃送子上学读书的决心。
伐薪烧炭,是走在悬崖边的高危职业,去路易,回路难,是山里人不得已而为之的活路。苦和累,没话说,难的是那时封山了,村周边的山不能砍柴。能砍柴的,自然是偏远陡峭的悬崖陡坡,还有生产队管不到的山岭。离我家六七里地远,有个叫“丹暖”的弄场,四面环山,东西两峰兀自拔高,像一对隔空对峙的犬牙,东峰一处大崖壁,阴雨天,风鸣空谷,溜滑如镜,还摔死过人。这个好吓人的“丹暖”,反倒变成了我父亲取薪烧炭的“福地”。刚开始,父亲去那里砍柴取薪,碰上街日,就挑到十多里外的地苏街去卖,后来他发现柴火重而难挑,卖价也不好,而木炭价格比柴火高四五倍,挑去街卖又方便许多,于是试着砍柴烧木炭卖,一试效果果然不错。那些年,父亲进山之前,都要预先置办上半袋玉米粉、半箩筐红薯,自己一个人用扁担挑上,一头扎进深山里半月之久,回来后,又蚂蚁搬家地赶地苏或县城的街。好在父亲挑的柴干爽易燃,烧的炭熟透不碎,在整个地苏街上早就有口皆碑了,加上好多人知道父亲挣钱是送孩子读书,常常不问价钱,二话不说就叫父亲往他们家送……记忆里,我们只有在农忙季节,或是像春节这般重大节日,才能见到父亲的身影。
我每每看着父亲进山和出山,心中酸甜苦辣咸一阵阵翻滚,无法用语言形容。父亲进山时,我倚门相送,那时还不懂得“生死两茫茫”的意思,只是觉得父亲一走,家中空得慌,想那山险陡,想那林中幽暗惊悚,一种挥之不去的担忧、愁绪终日萦绕于心,挥之不去。每当父亲从山中归来,我们先是兴奋,既而是心酸和不堪——只见从山中伐薪烧炭日久的父亲,此刻一身褴褛,十指黝黑,污发苍苍,像个叫花子,远远就闻到他身上浓浓的酸味、咸味……
我读到高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常常吃不饱饭,每天都饿得前胸贴后背。车马慢,幸福来得更慢的那两年,周末特别让我惦记,因为每到周末,父亲会在卖掉柴火或木炭后,来学校看我。父亲来时,除了带来红薯、芋头什么的,还带来卖柴炭挣来的皱巴巴的几张毛票,父亲给钱给物并简单叮嘱几句后,便斜扛扁担匆匆而去。
改革开放后,家里的日子渐渐好过起来,但他仍然留在大山里生活。他不再砍柴烧炭,而是搞起小编织,搞搞养殖什么的,挣钱供我的两个弟弟读书,直到他们毕业,有了工作。父亲说,他有编织技艺,山里乡亲们离不开他,他得把这手艺传给年轻人,让他们学了手艺,有饭吃。所以后来,村里人评价父亲有着一副热心肠:有一年冬天,村里一韦姓人家的房子倒塌了。他懂得制瓦,整整一个冬天都在帮他们制瓦,分文不取,还一顿饭都不肯吃。五保户蓝奶奶家的用水,也是父亲挑,一直挑到她去世。村里有什么纠纷,大家都爱找父亲调解,因为他总能秉公处理,让双方都心服口服。
他70岁时,老胃病发作,身体有些挺不住了,才和母亲一起搬来县城。在他住进我家的最后这13年,我常常看见他坐在阳台上,抚着他从老家带来的那根油光发亮的扁担,望着远山发呆。我知道,父亲又沉入回忆,一个人在过往的岁月里行走。

-我已经到底线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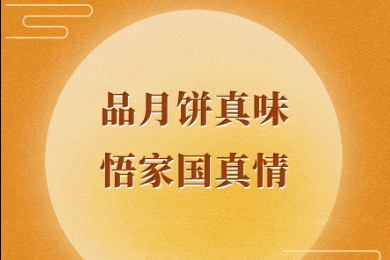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