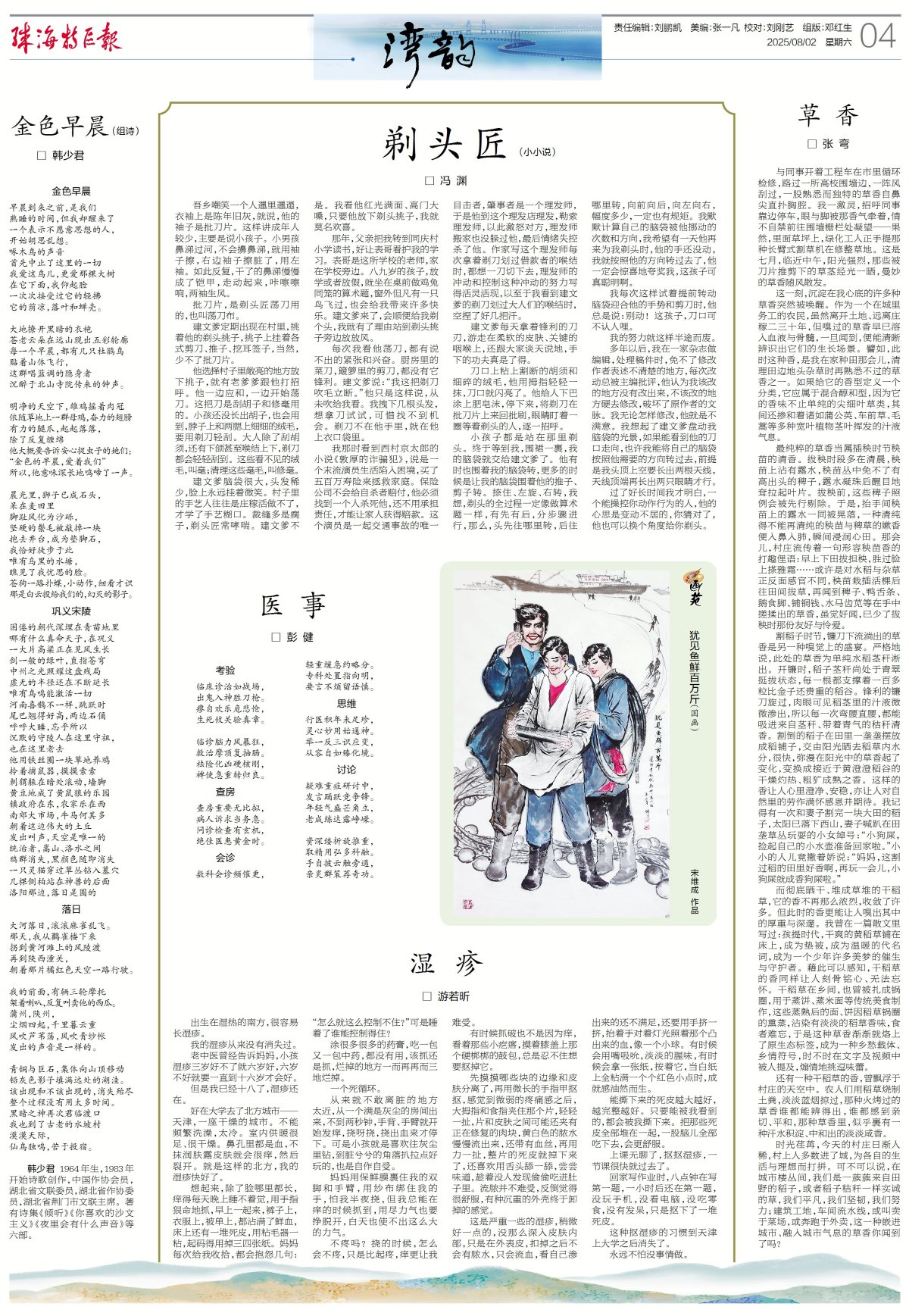


□ 冯 渊
吾乡嘲笑一个人邋里邋遢,衣袖上是陈年旧灰,就说,他的袖子是批刀片。这样讲成年人较少,主要是说小孩子。小男孩鼻涕过河,不会擤鼻涕,就用袖子擦,右边袖子擦脏了,用左袖。如此反复,干了的鼻涕慢慢成了铠甲,走动起来,咔嚓嚓响,两袖生风。
批刀片,是剃头匠荡刀用的,也叫荡刀布。
建文爹定期出现在村里,挑着他的剃头挑子,挑子上挂着各式剪刀、推子、挖耳签子,当然,少不了批刀片。
他选择村子里敞亮的地方放下挑子,就有老爹爹跟他打招呼。他一边应和,一边开始荡刀。这把刀是刮胡子和修毫用的。小孩还没长出胡子,也会用到,脖子上和两腮上细细的绒毛,要用剃刀轻刮。大人除了刮胡须,还有下颌甚至喉结上下,剃刀都会轻轻刮到。这些看不见的绒毛,叫毫;清理这些毫毛,叫修毫。
建文爹脑袋很大,头发稀少,脸上永远挂着微笑。村子里的手艺人往往是庄稼活做不了,才学了手艺糊口。裁缝多是瘸子,剃头匠常哮喘。建文爹不是。我看他红光满面、高门大嗓,只要他放下剃头挑子,我就莫名欢喜。
那年,父亲把我转到同庆村小学读书,好让表哥看护我的学习。表哥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家在学校旁边。八九岁的孩子,放学或者放假,就坐在桌前做鸡兔同笼的算术题,窗外但凡有一只鸟飞过,也会给我带来许多快乐。建文爹来了,会顺便给我剃个头,我就有了理由站到剃头挑子旁边放放风。
每次我看他荡刀,都有说不出的紧张和兴奋。厨房里的菜刀,簸箩里的剪刀,都没有它锋利。建文爹说:“我这把剃刀吹毛立断。”他只是这样说,从未吹给我看。我拽下几根头发,想拿刀试试,可惜找不到机会。剃刀不在他手里,就在他上衣口袋里。
我那时看到西村京太郎的小说《敦厚的诈骗犯》,说是一个末流演员生活陷入困境,买了五百万寿险来拯救家庭。保险公司不会给自杀者赔付,他必须找到一个人杀死他,还不用承担责任,才能让家人获得赔款。这个演员是一起交通事故的唯一目击者,肇事者是一个理发师,于是他到这个理发店理发,勒索理发师,以此激怒对方,理发师搬家也没躲过他,最后情绪失控杀了他。作家写这个理发师每次拿着剃刀划过借款者的喉结时,都想一刀切下去,理发师的冲动和控制这种冲动的努力写得活灵活现,以至于我看到建文爹的剃刀划过大人们的喉结时,空捏了好几把汗。
建文爹每天拿着锋利的刀刃,游走在柔软的皮肤、关键的咽喉上,还跟大家谈天说地,手下的功夫真是了得。
刀口上粘上割断的胡须和细碎的绒毛,他用拇指轻轻一抹,刀口就闪亮了。他给人下巴涂上肥皂沫,停下来,将剃刀在批刀片上来回批刷,眼睛盯着一圈等着剃头的人,逐一招呼。
小孩子都是站在那里剃头。终于等到我,围裙一裹,我的脑袋就交给建文爹了。他有时也围着我的脑袋转,更多的时候是让我的脑袋围着他的推子、剪子转。捺住、左旋、右转,我想,剃头的全过程一定像做算术题一样,有先有后,分步骤进行,那么,头先往哪里转,后往哪里转,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幅度多少,一定也有规矩。我默默计算自己的脑袋被他挪动的次数和方向,我希望有一天他再来为我剃头时,他的手还没动,我就按照他的方向转过去了,他一定会惊喜地夸奖我,这孩子可真聪明啊。
我每次这样试着提前转动脑袋迎合他的手势和剪刀时,他总是说:别动!这孩子,刀口可不认人哩。
我的努力就这样半途而废。
多年以后,我在一家杂志做编辑,处理稿件时,免不了修改作者表述不清楚的地方,每次改动总被主编批评,他认为我该改的地方没有改出来,不该改的地方硬去修改,破坏了原作者的文脉。我无论怎样修改,他就是不满意。我想起了建文爹盘动我脑袋的光景,如果能看到他的刀口走向,也许我能将自己的脑袋按照他需要的方向转过去,前提是我头顶上空要长出两根天线,天线顶端再长出两只眼睛才行。
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明白,一个能操控你动作行为的人,他的心思是变动不居的,你猜对了,他也可以换个角度给你剃头。
□ 彭 健
考验
临床诊治如战场,
出鬼入神胜刀枪。
瘳自欢乐危悲怆,
生死攸关验真章。
临诊脑力风暴狂,
救治摩顶复抽肠。
祛险化凶硬核刚,
裨使急重转归良。
查房
查房重要无比拟,
病人诉求当务急。
问诊检查有玄机,
绝佳医患黄金时。
会诊
数科会诊频催更,
轻重缓急约略分。
专科处置指向明,
要言不烦留语慎。
思维
行医积年未足珍,
灵心妙用始通神。
举一反三识应变,
从容自如臻化境。
讨论
疑难重症研讨中,
发言踊跃竞争锋。
年轻气盛芒角立,
老成练达露峥嵘。
资深缕析旋推重,
取精用弘多科融。
手自披云触旁通,
亲炙群策荐奇功。


□ 韩少君
金色早晨
早晨到来之前,是我们
熟睡的时间,但我却醒来了
一个表示不愿意思想的人,
开始胡思乱想。
啄木鸟的声音
首先中止了这里的一切
我爱这鸟儿,更爱那棵大树
在它下面,我仰起脸
一次次接受过它的轻拂
它的荫凉,落叶和蝉壳。
大地撩开黑暗的衣袍
苍老云朵在远山现出五彩轮廓
每一个早晨,都有几只杜鹃鸟
贴着山体飞行,
这群唱蓝调的隐身者
沉醉于北山寺院传来的钟声。
明净的天空下,雄鸡摇着肉冠
依随草地上一群母鸡,奋力的翅膀
有力的腿爪,起起落落,
除了反复缠绵
他大概要告诉安心捉虫子的她们:
“金色的早晨,爱着我们”
所以,他意味深长地鸣啼了一声。
晨光里,狮子已成石头,
呆在麦田里
脚趾风化为沙砾,
坚硬的鬃毛被敲掉一块
抱去井台,成为垫脚石,
我恰好徒步于此
唯有乌黑的水塘,
瞧见了我忧思的脸。
苍狗一路扑蝶,小动作,细看才识
那是白云投给我们的,幻灭的影子。
巩义宋陵
困倦的朝代深埋在青苗地里
哪有什么真命天子,在巩义
一大片高粱正在见风生长
剑一般的绿叶,直指苍穹
中州之光照耀这盘残局
虚无的半径还在不断延长
唯有鸟鸣能激活一切
河南喜鹊不一样,跳跃时
尾巴翘得好高,两边石俑
呼呼大睡,忘乎所以
沉默的守陵人在这里守祖,
也在这里老去
他用铁丝圈一块草地养鸡
拎着捕鼠器,摸摸索索
刺猬躲在暗处滚动,墙脚
黄豆地成了黄鼠狼的乐园
镇政府在东,农家乐在西
南郊大市场,牛马何其多
朝着这边伟大的土丘
发出叫声,天空是唯一的
统治者,嵩山、洛水之间
鸦群消失,黑颜色随即消失
一只灵猫穿过草丛钻入墓穴
几棵侧柏站在神兽的后面
洛阳那边,落日是圆的
落日
大河落日,滚滚麻雀乱飞。
那天,我从鹳雀楼下来
拐到黄河滩上的风陵渡
再到陕西潼关,
朝着那片橘红色天空一路行驶。
我的前面,有辆三轮摩托
架着喇叭,反复叫卖他的西瓜。
蒲州,陕州,
尘烟四起,千里暮云重
风吹芦苇荡,风吹青纱帐
发出的声音是一样的。
青铜与巨石,集体向山顶移动
铅灰色影子填满远处的湖洼。
该出现和不该出现的,消失殆尽
整个过程没有用太多时间。
黑暗之神再次君临渡口
我也到了古老的水坡村
漠漠天际,
仙鸟独鸣,苦于投宿。
韩少君 1964年生,1983年开始诗歌创作,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文联委员,湖北省作协委员,湖北省荆门市文联主席。著有诗集《倾听》《你喜欢的沙文主义》《夜里会有什么声音》等六部。
□ 游若昕
出生在湿热的南方,很容易长湿疹。
我的湿疹从来没有消失过。
老中医曾经告诉妈妈,小孩湿疹三岁好不了就六岁好,六岁不好就要一直到十六岁才会好。
但是我已经十八了,湿疹还在。
好在大学去了北方城市——天津,一座干燥的城市。不能频繁洗澡,太冷。室内供暖很足、很干燥。鼻孔里都是血,不抹润肤露皮肤就会很痒,然后裂开。就是这样的北方,我的湿疹快好了。
想起来,除了脸哪里都长,痒得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用手指狠命地抓,早上一起来,裤子上,衣服上,被单上,都沾满了鲜血,床上还有一堆死皮,用粘毛器一粘,起码得用掉三四张纸。妈妈每次给我收拾,都会抱怨几句:“怎么就这么控制不住?”可是睡着了谁能控制得住?
涂很多很多的药膏,吃一包又一包中药,都没有用,该抓还是抓,烂掉的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烂掉。
一个死循环。
从来就不敢离脏的地方太近,从一个满是灰尘的房间出来,不到两秒钟,手背、手臂就开始发痒,挠呀挠,挠出血来才停下。可是小孩就是喜欢往灰尘里钻,到脏兮兮的角落扒拉点好玩的,也是自作自受。
妈妈用保鲜膜裹住我的双脚和手臂,用纱布绑住我的手,怕我半夜挠,但我总能在痒的时候抓到,用尽力气也要挣脱开,白天也使不出这么大的力气。
不疼吗?挠的时候,怎么会不疼,只是比起疼,痒更让我难受。
有时候抓破也不是因为痒,看着那些小疙瘩,摸着膝盖上那个硬邦邦的鼓包,总是忍不住想要抠掉它。
先摸摸哪些块的边缘和皮肤分离了,再用微长的手指甲抠抠,感觉到微弱的疼痛感之后,大拇指和食指夹住那个片,轻轻一扯,片和皮肤之间可能还夹有正在修复的肉块,黄白色的脓水慢慢流出来,还带有血丝,再用力一扯,整片的死皮就掉下来了,还喜欢用舌头舔一舔,尝尝味道,趁着没人发现偷偷吃进肚子里。流脓并不难受,反倒觉得很舒服,有种沉重的外壳终于卸掉的感觉。
这是严重一些的湿疹,稍微好一点的,没那么深入皮肤内部,只是在外表皮,扣掉之后不会有脓水,只会流血,看自己渗出来的还不满足,还要用手挤一挤,抬着手对着灯光照着那个凸出来的血,像一个小球。有时候会用嘴吸吮,淡淡的腥味,有时候会拿一张纸,按着它,当白纸上全粘满一个个红色小点时,成就感油然而生。
能撕下来的死皮越大越好,越完整越好。只要能被我看到的,都会被我撕下来。把那些死皮全部堆在一起,一股脑儿全部吃下去,会更舒服。
上课无聊了,抠抠湿疹,一节课很快就过去了。
回家写作业时,八点钟在写第一题,一小时后还在第一题,没玩手机,没看电脑,没吃零食,没有发呆,只是抠下了一堆死皮。
这种抠湿疹的习惯到天津上大学之后消失了。
永远不怕没事情做。


□ 张 弯
与同事开着工程车在市里循环检修,路过一所高校围墙边,一阵风刮过,一股熟悉而独特的草香自鼻尖直扑胸腔。我一激灵,招呼同事靠边停车,眼与脚被那香气牵着,情不自禁前往围墙栅栏处凝望——果然,里面草坪上,绿化工人正手提那种长臂式割草机在修整草地。这是七月,临近中午,阳光强烈,那些被刀片推剪下的草茎经光一晒,曼妙的草香随风散发。
这一刻,沉淀在我心底的许多种草香突然被唤醒。作为一个在城里务工的农民,虽然离开土地、远离庄稼二三十年,但嗅过的草香早已融入血液与骨髓,一旦闻到,便能清晰辨识出它们的生长场景。譬如,此时这种香,是我在家种田那会儿,清理田边地头杂草时再熟悉不过的草香之一。如果给它的香型定义一个分类,它应属于混合醇和型,因为它的香味不止单纯的尖细叶草类,其间还掺和着诸如蒲公英、车前草、毛蒿等多种宽叶植物茎叶挥发的汁液气息。
最纯粹的草香当属插秧时节秧苗的清香。拔秧时段多在清晨,秧苗上沾有露水,秧苗丛中免不了有高出头的稗子,露水凝珠后醒目地耷拉起叶片。拔秧前,这些稗子照例会被先行剔除。于是,抬手间秧苗上的露水一同被晃落,一种清纯得不能再清纯的秧苗与稗草的嫰香便入鼻入肺,瞬间浸润心田。那会儿,村庄流传着一句形容秧苗香的打趣俚语:早上下田拔担秧,胜过脸上搽雅霜……或许是对水稻与杂草正反面感官不同,秧苗栽插活棵后往田间拔草,再闻到稗子、鸭舌条、鹅食脚、铺铜钱、水马齿苋等在手中搓揉出的草香,虽觉好闻,已少了拔秧时那份友好与怜爱。
割稻子时节,镰刀下流淌出的草香是另一种嗅觉上的盛宴。严格地说,此处的草香为单纯水稻茎秆淅出。开镰时,稻子茎秆尚处于青翠挺拔状态,每一根都支撑着一百多粒比金子还贵重的稻谷。锋利的镰刀旋过,肉眼可见稻茎里的汁液微微渗出,所以每一次弯腰直腰,都能吸进来自茎秆、带着青气的秸秆清香。割倒的稻子在田里一垄垄摆放成稻铺子,交由阳光晒去稻草内水分,很快,弥漫在阳光中的草香起了变化,变换成接近于黄澄澄稻谷的干燥灼热、粗犷成熟之香。这样的香让人心里澄净、安稳,亦让人对自然里的劳作满怀感恩并期待。我记得有一次和妻子割完一块大田的稻子,太阳已落下西山,妻子喊趴在田垄草丛玩耍的小女绰号:“小狗屎,捡起自己的小水壶准备回家啦。”小小的人儿竟撒着娇说:“妈妈,这割过稻的田里好香啊,再玩一会儿,小狗屎就成香狗屎啦。”
而彻底晒干、堆成草堆的干稻草,它的香不再那么浓烈,收敛了许多。但此时的香更能让人嗅出其中的厚重与深邃。我曾在一篇散文里写过:孩提时代,干爽的黄稻草铺在床上,成为垫被,成为温暖的代名词,成为一个少年许多美梦的催生与守护者。藉此可以感知,干稻草的香同样让人刻骨铭心、无法忘怀。干稻草在乡间,也曾被扎成锅圈,用于蒸饼、蒸米面等传统美食制作,这些蒸熟后的面、饼因稻草锅圈的熏蒸,沾染有淡淡的稻草香味,食者难忘,于是这种草香渐渐就烙上了原生态标签,成为一种乡愁载体、乡情符号,时不时在文字及视频中被人提及,煽情地挑逗味蕾。
还有一种干稻草的香,曾飘浮于村庄的天空中。农人们用稻草烧制土粪,淡淡蓝烟掠过,那种火烤过的草香谁都能辨得出,谁都感到亲切、平和,那种草香里,似乎裹有一种汗水积淀、中和出的淡淡咸香。
时光荏苒,今天的村庄日渐人稀,村上人多数进了城,为各自的生活与理想而打拼。可不可以说,在城市楼丛间,我们是一簇簇来自田野的稻子,或者稻子秸秆一样实诚的草,我们平凡,我们坚韧,我们努力;建筑工地,车间流水线,或叫卖于菜场,或奔跑于外卖,这一种嵌进城市、融入城市气息的草香你闻到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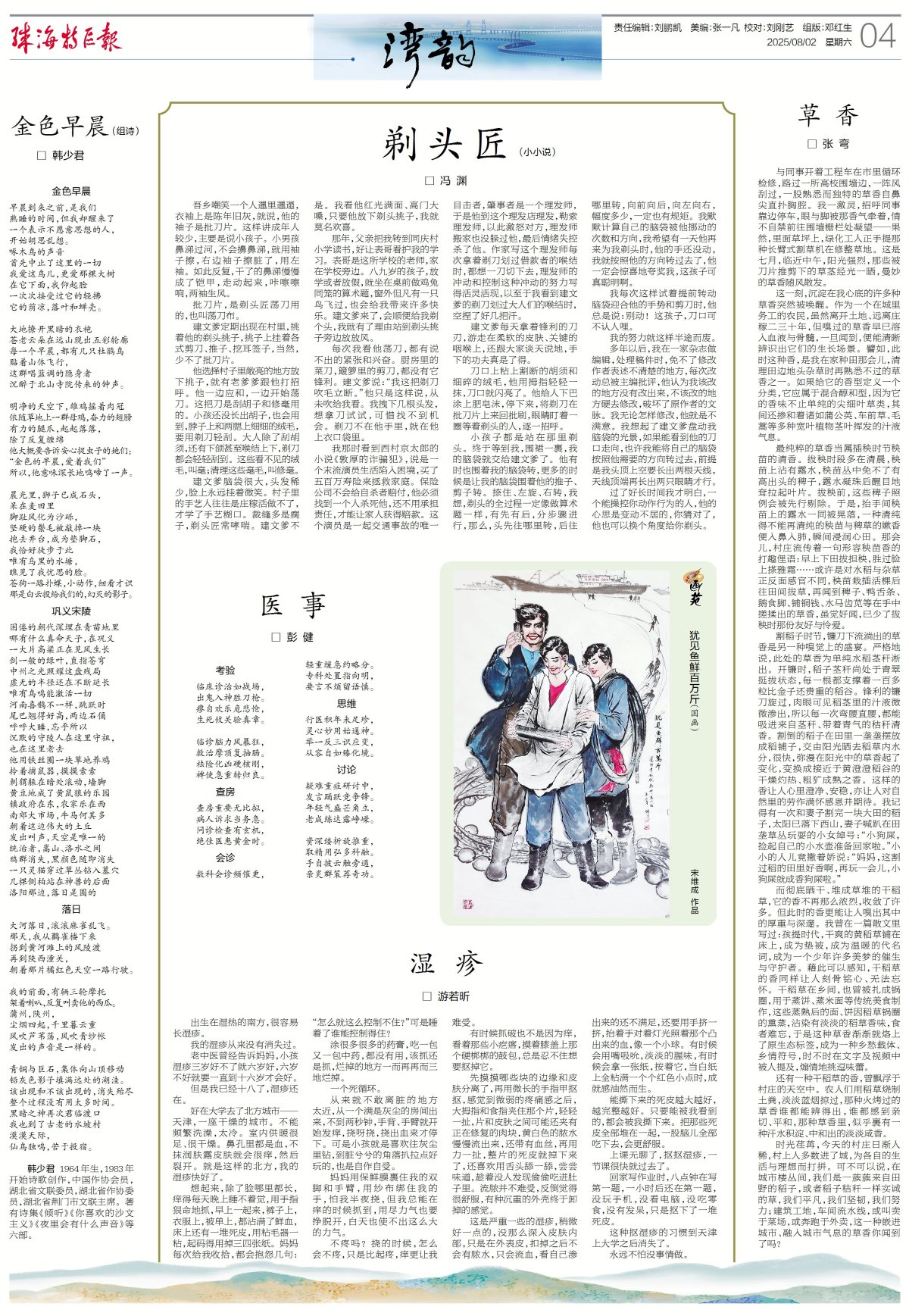


□ 冯 渊
吾乡嘲笑一个人邋里邋遢,衣袖上是陈年旧灰,就说,他的袖子是批刀片。这样讲成年人较少,主要是说小孩子。小男孩鼻涕过河,不会擤鼻涕,就用袖子擦,右边袖子擦脏了,用左袖。如此反复,干了的鼻涕慢慢成了铠甲,走动起来,咔嚓嚓响,两袖生风。
批刀片,是剃头匠荡刀用的,也叫荡刀布。
建文爹定期出现在村里,挑着他的剃头挑子,挑子上挂着各式剪刀、推子、挖耳签子,当然,少不了批刀片。
他选择村子里敞亮的地方放下挑子,就有老爹爹跟他打招呼。他一边应和,一边开始荡刀。这把刀是刮胡子和修毫用的。小孩还没长出胡子,也会用到,脖子上和两腮上细细的绒毛,要用剃刀轻刮。大人除了刮胡须,还有下颌甚至喉结上下,剃刀都会轻轻刮到。这些看不见的绒毛,叫毫;清理这些毫毛,叫修毫。
建文爹脑袋很大,头发稀少,脸上永远挂着微笑。村子里的手艺人往往是庄稼活做不了,才学了手艺糊口。裁缝多是瘸子,剃头匠常哮喘。建文爹不是。我看他红光满面、高门大嗓,只要他放下剃头挑子,我就莫名欢喜。
那年,父亲把我转到同庆村小学读书,好让表哥看护我的学习。表哥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家在学校旁边。八九岁的孩子,放学或者放假,就坐在桌前做鸡兔同笼的算术题,窗外但凡有一只鸟飞过,也会给我带来许多快乐。建文爹来了,会顺便给我剃个头,我就有了理由站到剃头挑子旁边放放风。
每次我看他荡刀,都有说不出的紧张和兴奋。厨房里的菜刀,簸箩里的剪刀,都没有它锋利。建文爹说:“我这把剃刀吹毛立断。”他只是这样说,从未吹给我看。我拽下几根头发,想拿刀试试,可惜找不到机会。剃刀不在他手里,就在他上衣口袋里。
我那时看到西村京太郎的小说《敦厚的诈骗犯》,说是一个末流演员生活陷入困境,买了五百万寿险来拯救家庭。保险公司不会给自杀者赔付,他必须找到一个人杀死他,还不用承担责任,才能让家人获得赔款。这个演员是一起交通事故的唯一目击者,肇事者是一个理发师,于是他到这个理发店理发,勒索理发师,以此激怒对方,理发师搬家也没躲过他,最后情绪失控杀了他。作家写这个理发师每次拿着剃刀划过借款者的喉结时,都想一刀切下去,理发师的冲动和控制这种冲动的努力写得活灵活现,以至于我看到建文爹的剃刀划过大人们的喉结时,空捏了好几把汗。
建文爹每天拿着锋利的刀刃,游走在柔软的皮肤、关键的咽喉上,还跟大家谈天说地,手下的功夫真是了得。
刀口上粘上割断的胡须和细碎的绒毛,他用拇指轻轻一抹,刀口就闪亮了。他给人下巴涂上肥皂沫,停下来,将剃刀在批刀片上来回批刷,眼睛盯着一圈等着剃头的人,逐一招呼。
小孩子都是站在那里剃头。终于等到我,围裙一裹,我的脑袋就交给建文爹了。他有时也围着我的脑袋转,更多的时候是让我的脑袋围着他的推子、剪子转。捺住、左旋、右转,我想,剃头的全过程一定像做算术题一样,有先有后,分步骤进行,那么,头先往哪里转,后往哪里转,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幅度多少,一定也有规矩。我默默计算自己的脑袋被他挪动的次数和方向,我希望有一天他再来为我剃头时,他的手还没动,我就按照他的方向转过去了,他一定会惊喜地夸奖我,这孩子可真聪明啊。
我每次这样试着提前转动脑袋迎合他的手势和剪刀时,他总是说:别动!这孩子,刀口可不认人哩。
我的努力就这样半途而废。
多年以后,我在一家杂志做编辑,处理稿件时,免不了修改作者表述不清楚的地方,每次改动总被主编批评,他认为我该改的地方没有改出来,不该改的地方硬去修改,破坏了原作者的文脉。我无论怎样修改,他就是不满意。我想起了建文爹盘动我脑袋的光景,如果能看到他的刀口走向,也许我能将自己的脑袋按照他需要的方向转过去,前提是我头顶上空要长出两根天线,天线顶端再长出两只眼睛才行。
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明白,一个能操控你动作行为的人,他的心思是变动不居的,你猜对了,他也可以换个角度给你剃头。
□ 彭 健
考验
临床诊治如战场,
出鬼入神胜刀枪。
瘳自欢乐危悲怆,
生死攸关验真章。
临诊脑力风暴狂,
救治摩顶复抽肠。
祛险化凶硬核刚,
裨使急重转归良。
查房
查房重要无比拟,
病人诉求当务急。
问诊检查有玄机,
绝佳医患黄金时。
会诊
数科会诊频催更,
轻重缓急约略分。
专科处置指向明,
要言不烦留语慎。
思维
行医积年未足珍,
灵心妙用始通神。
举一反三识应变,
从容自如臻化境。
讨论
疑难重症研讨中,
发言踊跃竞争锋。
年轻气盛芒角立,
老成练达露峥嵘。
资深缕析旋推重,
取精用弘多科融。
手自披云触旁通,
亲炙群策荐奇功。


□ 韩少君
金色早晨
早晨到来之前,是我们
熟睡的时间,但我却醒来了
一个表示不愿意思想的人,
开始胡思乱想。
啄木鸟的声音
首先中止了这里的一切
我爱这鸟儿,更爱那棵大树
在它下面,我仰起脸
一次次接受过它的轻拂
它的荫凉,落叶和蝉壳。
大地撩开黑暗的衣袍
苍老云朵在远山现出五彩轮廓
每一个早晨,都有几只杜鹃鸟
贴着山体飞行,
这群唱蓝调的隐身者
沉醉于北山寺院传来的钟声。
明净的天空下,雄鸡摇着肉冠
依随草地上一群母鸡,奋力的翅膀
有力的腿爪,起起落落,
除了反复缠绵
他大概要告诉安心捉虫子的她们:
“金色的早晨,爱着我们”
所以,他意味深长地鸣啼了一声。
晨光里,狮子已成石头,
呆在麦田里
脚趾风化为沙砾,
坚硬的鬃毛被敲掉一块
抱去井台,成为垫脚石,
我恰好徒步于此
唯有乌黑的水塘,
瞧见了我忧思的脸。
苍狗一路扑蝶,小动作,细看才识
那是白云投给我们的,幻灭的影子。
巩义宋陵
困倦的朝代深埋在青苗地里
哪有什么真命天子,在巩义
一大片高粱正在见风生长
剑一般的绿叶,直指苍穹
中州之光照耀这盘残局
虚无的半径还在不断延长
唯有鸟鸣能激活一切
河南喜鹊不一样,跳跃时
尾巴翘得好高,两边石俑
呼呼大睡,忘乎所以
沉默的守陵人在这里守祖,
也在这里老去
他用铁丝圈一块草地养鸡
拎着捕鼠器,摸摸索索
刺猬躲在暗处滚动,墙脚
黄豆地成了黄鼠狼的乐园
镇政府在东,农家乐在西
南郊大市场,牛马何其多
朝着这边伟大的土丘
发出叫声,天空是唯一的
统治者,嵩山、洛水之间
鸦群消失,黑颜色随即消失
一只灵猫穿过草丛钻入墓穴
几棵侧柏站在神兽的后面
洛阳那边,落日是圆的
落日
大河落日,滚滚麻雀乱飞。
那天,我从鹳雀楼下来
拐到黄河滩上的风陵渡
再到陕西潼关,
朝着那片橘红色天空一路行驶。
我的前面,有辆三轮摩托
架着喇叭,反复叫卖他的西瓜。
蒲州,陕州,
尘烟四起,千里暮云重
风吹芦苇荡,风吹青纱帐
发出的声音是一样的。
青铜与巨石,集体向山顶移动
铅灰色影子填满远处的湖洼。
该出现和不该出现的,消失殆尽
整个过程没有用太多时间。
黑暗之神再次君临渡口
我也到了古老的水坡村
漠漠天际,
仙鸟独鸣,苦于投宿。
韩少君 1964年生,1983年开始诗歌创作,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文联委员,湖北省作协委员,湖北省荆门市文联主席。著有诗集《倾听》《你喜欢的沙文主义》《夜里会有什么声音》等六部。
□ 游若昕
出生在湿热的南方,很容易长湿疹。
我的湿疹从来没有消失过。
老中医曾经告诉妈妈,小孩湿疹三岁好不了就六岁好,六岁不好就要一直到十六岁才会好。
但是我已经十八了,湿疹还在。
好在大学去了北方城市——天津,一座干燥的城市。不能频繁洗澡,太冷。室内供暖很足、很干燥。鼻孔里都是血,不抹润肤露皮肤就会很痒,然后裂开。就是这样的北方,我的湿疹快好了。
想起来,除了脸哪里都长,痒得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用手指狠命地抓,早上一起来,裤子上,衣服上,被单上,都沾满了鲜血,床上还有一堆死皮,用粘毛器一粘,起码得用掉三四张纸。妈妈每次给我收拾,都会抱怨几句:“怎么就这么控制不住?”可是睡着了谁能控制得住?
涂很多很多的药膏,吃一包又一包中药,都没有用,该抓还是抓,烂掉的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烂掉。
一个死循环。
从来就不敢离脏的地方太近,从一个满是灰尘的房间出来,不到两秒钟,手背、手臂就开始发痒,挠呀挠,挠出血来才停下。可是小孩就是喜欢往灰尘里钻,到脏兮兮的角落扒拉点好玩的,也是自作自受。
妈妈用保鲜膜裹住我的双脚和手臂,用纱布绑住我的手,怕我半夜挠,但我总能在痒的时候抓到,用尽力气也要挣脱开,白天也使不出这么大的力气。
不疼吗?挠的时候,怎么会不疼,只是比起疼,痒更让我难受。
有时候抓破也不是因为痒,看着那些小疙瘩,摸着膝盖上那个硬邦邦的鼓包,总是忍不住想要抠掉它。
先摸摸哪些块的边缘和皮肤分离了,再用微长的手指甲抠抠,感觉到微弱的疼痛感之后,大拇指和食指夹住那个片,轻轻一扯,片和皮肤之间可能还夹有正在修复的肉块,黄白色的脓水慢慢流出来,还带有血丝,再用力一扯,整片的死皮就掉下来了,还喜欢用舌头舔一舔,尝尝味道,趁着没人发现偷偷吃进肚子里。流脓并不难受,反倒觉得很舒服,有种沉重的外壳终于卸掉的感觉。
这是严重一些的湿疹,稍微好一点的,没那么深入皮肤内部,只是在外表皮,扣掉之后不会有脓水,只会流血,看自己渗出来的还不满足,还要用手挤一挤,抬着手对着灯光照着那个凸出来的血,像一个小球。有时候会用嘴吸吮,淡淡的腥味,有时候会拿一张纸,按着它,当白纸上全粘满一个个红色小点时,成就感油然而生。
能撕下来的死皮越大越好,越完整越好。只要能被我看到的,都会被我撕下来。把那些死皮全部堆在一起,一股脑儿全部吃下去,会更舒服。
上课无聊了,抠抠湿疹,一节课很快就过去了。
回家写作业时,八点钟在写第一题,一小时后还在第一题,没玩手机,没看电脑,没吃零食,没有发呆,只是抠下了一堆死皮。
这种抠湿疹的习惯到天津上大学之后消失了。
永远不怕没事情做。


□ 张 弯
与同事开着工程车在市里循环检修,路过一所高校围墙边,一阵风刮过,一股熟悉而独特的草香自鼻尖直扑胸腔。我一激灵,招呼同事靠边停车,眼与脚被那香气牵着,情不自禁前往围墙栅栏处凝望——果然,里面草坪上,绿化工人正手提那种长臂式割草机在修整草地。这是七月,临近中午,阳光强烈,那些被刀片推剪下的草茎经光一晒,曼妙的草香随风散发。
这一刻,沉淀在我心底的许多种草香突然被唤醒。作为一个在城里务工的农民,虽然离开土地、远离庄稼二三十年,但嗅过的草香早已融入血液与骨髓,一旦闻到,便能清晰辨识出它们的生长场景。譬如,此时这种香,是我在家种田那会儿,清理田边地头杂草时再熟悉不过的草香之一。如果给它的香型定义一个分类,它应属于混合醇和型,因为它的香味不止单纯的尖细叶草类,其间还掺和着诸如蒲公英、车前草、毛蒿等多种宽叶植物茎叶挥发的汁液气息。
最纯粹的草香当属插秧时节秧苗的清香。拔秧时段多在清晨,秧苗上沾有露水,秧苗丛中免不了有高出头的稗子,露水凝珠后醒目地耷拉起叶片。拔秧前,这些稗子照例会被先行剔除。于是,抬手间秧苗上的露水一同被晃落,一种清纯得不能再清纯的秧苗与稗草的嫰香便入鼻入肺,瞬间浸润心田。那会儿,村庄流传着一句形容秧苗香的打趣俚语:早上下田拔担秧,胜过脸上搽雅霜……或许是对水稻与杂草正反面感官不同,秧苗栽插活棵后往田间拔草,再闻到稗子、鸭舌条、鹅食脚、铺铜钱、水马齿苋等在手中搓揉出的草香,虽觉好闻,已少了拔秧时那份友好与怜爱。
割稻子时节,镰刀下流淌出的草香是另一种嗅觉上的盛宴。严格地说,此处的草香为单纯水稻茎秆淅出。开镰时,稻子茎秆尚处于青翠挺拔状态,每一根都支撑着一百多粒比金子还贵重的稻谷。锋利的镰刀旋过,肉眼可见稻茎里的汁液微微渗出,所以每一次弯腰直腰,都能吸进来自茎秆、带着青气的秸秆清香。割倒的稻子在田里一垄垄摆放成稻铺子,交由阳光晒去稻草内水分,很快,弥漫在阳光中的草香起了变化,变换成接近于黄澄澄稻谷的干燥灼热、粗犷成熟之香。这样的香让人心里澄净、安稳,亦让人对自然里的劳作满怀感恩并期待。我记得有一次和妻子割完一块大田的稻子,太阳已落下西山,妻子喊趴在田垄草丛玩耍的小女绰号:“小狗屎,捡起自己的小水壶准备回家啦。”小小的人儿竟撒着娇说:“妈妈,这割过稻的田里好香啊,再玩一会儿,小狗屎就成香狗屎啦。”
而彻底晒干、堆成草堆的干稻草,它的香不再那么浓烈,收敛了许多。但此时的香更能让人嗅出其中的厚重与深邃。我曾在一篇散文里写过:孩提时代,干爽的黄稻草铺在床上,成为垫被,成为温暖的代名词,成为一个少年许多美梦的催生与守护者。藉此可以感知,干稻草的香同样让人刻骨铭心、无法忘怀。干稻草在乡间,也曾被扎成锅圈,用于蒸饼、蒸米面等传统美食制作,这些蒸熟后的面、饼因稻草锅圈的熏蒸,沾染有淡淡的稻草香味,食者难忘,于是这种草香渐渐就烙上了原生态标签,成为一种乡愁载体、乡情符号,时不时在文字及视频中被人提及,煽情地挑逗味蕾。
还有一种干稻草的香,曾飘浮于村庄的天空中。农人们用稻草烧制土粪,淡淡蓝烟掠过,那种火烤过的草香谁都能辨得出,谁都感到亲切、平和,那种草香里,似乎裹有一种汗水积淀、中和出的淡淡咸香。
时光荏苒,今天的村庄日渐人稀,村上人多数进了城,为各自的生活与理想而打拼。可不可以说,在城市楼丛间,我们是一簇簇来自田野的稻子,或者稻子秸秆一样实诚的草,我们平凡,我们坚韧,我们努力;建筑工地,车间流水线,或叫卖于菜场,或奔跑于外卖,这一种嵌进城市、融入城市气息的草香你闻到了吗?

-我已经到底线啦-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