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心脏大血管上的“心尖舞者”,
在生死毫厘间守护生命律动;
从海外求学到扎根临床,
他将世界前沿技术融入手术刀尖
……
既敬畏生命的重量,
也敢闯技术的盲区,
中山五院心血管外科主任简锴陶,
带领团队筑牢生命防线,
让更多患者“把心放进肚子里”。

凌晨3时的手术室,简锴陶正全神贯注地缝合着血管——这是一台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患者的血管内膜已经撕裂,外膜开始渗血,心包腔内大量积血,需要更换人工血管,缝合稍有不慎,吻合部位就会再次破裂,“就像在废墟上重建房屋”。

从医20余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简锴陶,早已习惯在心脏与大血管的“雷区”中行走,在毫厘之间与生死过招。他是心脏大血管外科的“拆弹专家”,更是患者眼里“能把心放进肚子里”的人。

在“生死时速”中抢回生命
“每延迟一小时,死亡率增加1%。24小时内,一半患者会死亡;48小时后,75%的人将失去生命。”谈及最凶险的心血管急症——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简锴陶语气凝重。这种疾病血管内膜撕裂,血液在动脉壁内外膜间疯狂冲刷,外膜一旦破裂,患者瞬间死亡。
上周,一位常年高血压的慢性肾衰患者突发急性主动脉夹层,夹层撕裂至头部血管、肾动脉,甚至累及右侧冠状动脉。手术中,团队需同时进行主动脉瓣成形、升主动脉置换、全主动脉弓置换、支架象鼻手术、冠脉搭桥等操作,在一台手术内运用了瓣膜成形、大血管置换及冠脉搭桥技术。时间紧、任务重,多种复杂操作叠加,考验着团队的技术与耐力。从凌晨1时到上午10时,历经9小时,手术终获成功。
这样的“紧急救援”,是心血管外科的常态。


把世界前沿技术“种”进临床
2009年,简锴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先后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做访问学者。彼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心脏外科,他亲眼见证了微创瓣膜修复与替换、人工心脏植入、介入主动脉瓣置换等国内尚未开展的技术。
他注意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一年大约进行1000台手术,在数量上不及国内大型医院,却以高占比的疑难危重手术稳居全美前十;患者术后快速康复、转至合作医院继续治疗的模式,大幅提升了病房周转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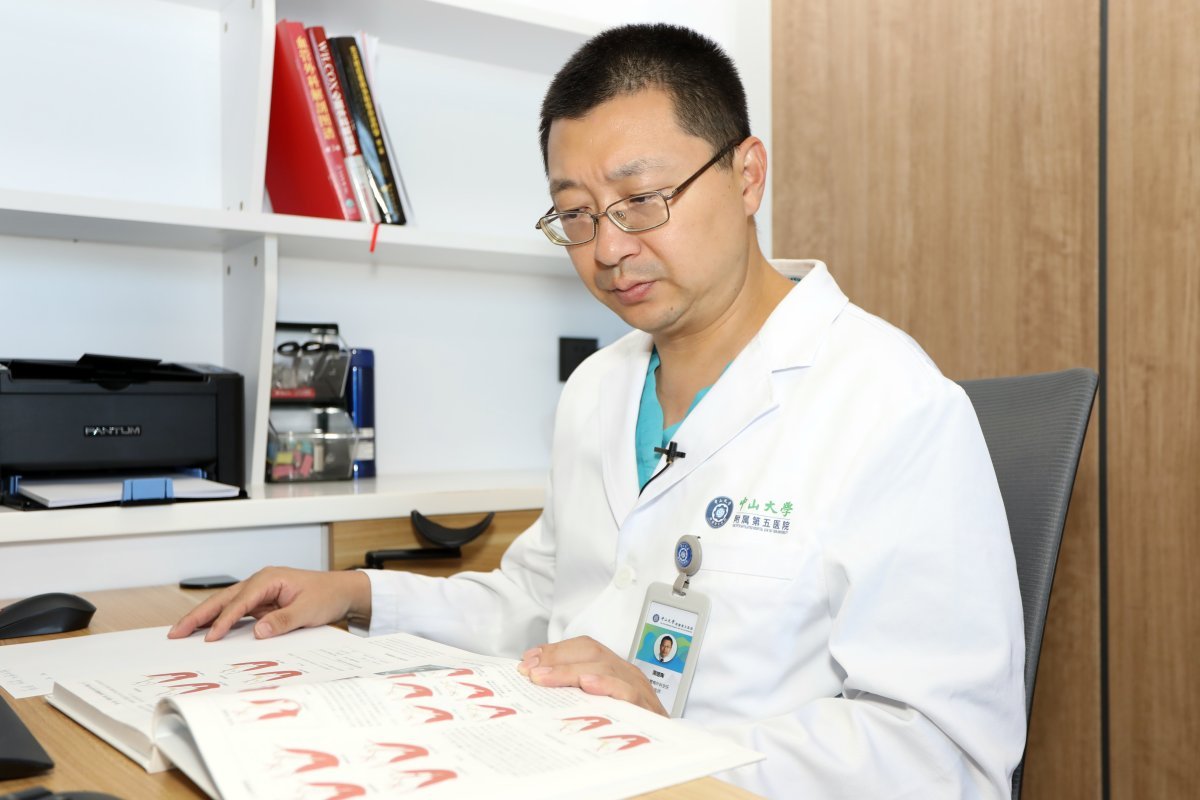
更让他触动的是“临床-科研-转化”的紧密闭环:医生既深耕手术台,也扎根实验室,介入瓣膜、人工心脏等创新成果从研发到临床应用的背后,都离不开医生的身影;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必须参与科研工作,并非局限于动物实验或细胞培养,而是将研究成果逐步转化为临床方案。
这些见闻像种子一样在简锴陶心里生根,他意识到,好的外科医生不只是开刀手术,更是解决问题的探索者。“他们一年只做一千台手术,却敢啃最硬的骨头,这颠覆了我对‘多就是好’的认知,‘质’才更重要。而这种‘头脑风暴’模式,让科研与临床像齿轮一样咬合。”
回国后,他把这份“探索欲”带进临床诊疗中。如今,他带领团队开展的心脏大血管手术,患者术后2-3天甚至更短时间就可以转出监护室,平均7-10天就能出院,快速康复理念使心脏大血管手术不再可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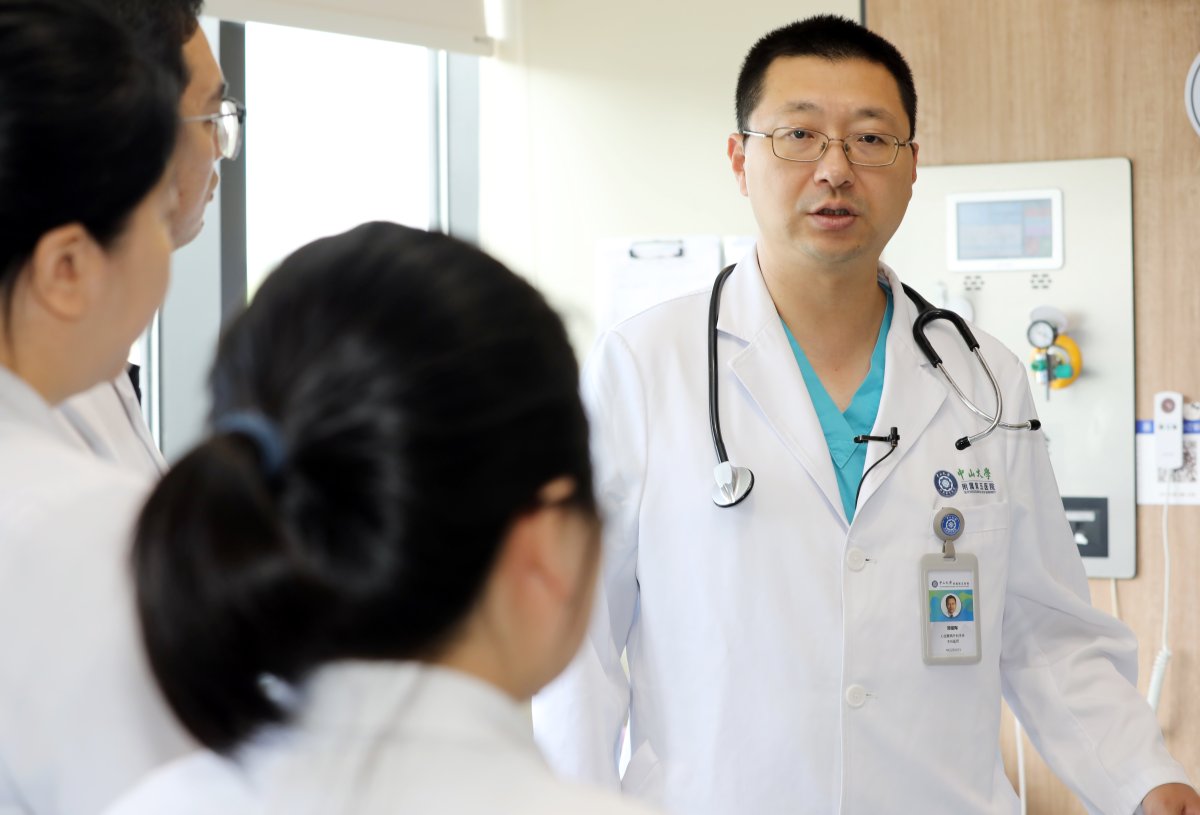

以团队之力筑牢生命防线
“心脏外科的进步,不是某个人跑得多快,而是一群人走得有多稳。”在简锴陶看来,心脏外科从不是 “一个人的战场”。
“心脏大血管疾病患者病情紧急、累及多脏器,往往是急诊手术,还可能涉及跨学科协作。” 简锴陶说,一台复杂手术的成功,背后是整个团队的托举——麻醉医生的协同、体外循环医生的生命支持、术中护理团队的配合以及术后ICU团队的细致照护,缺一不可。
而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的多学科平台,能为复杂病例提供有力支撑,例如联合创伤科进行移植物感染的皮瓣移植、与胸外科合作处理累及血管的恶性肿瘤等,让患者实现“一站式” 诊疗。

如今,临床之外,简锴陶的研究重心仍锚定在干细胞组织工程学领域,希望通过干细胞技术实现心肌组织的结构修复与功能再生,“终末期心脏病患者往往只能等心脏移植,但供体有限。通过干细胞的相关研究,希望能够探索一条新路径,让受损的心肌‘自己长好’,这是眼下最想啃下的硬骨头。”
放眼行业未来,简锴陶的目标清晰而务实:短期要推动中山五院心脏大血管疾病诊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此外,让心脏大血管手术的微创技术能够更加普及;长期则希望中山五院院内的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进而覆盖珠海全市,最终辐射粤西及港澳地区,让患者能够在区域内解决问题,免于奔波之苦。

对于年轻一代心外科医生,他认为,态度比技术先到位。住院医师阶段别嫌基础活“琐碎”,缝合、打结、看片子,这些基本功是日后“拆弹”的底气。他寄语青年医生:“希望你们接过接力棒时,既能敬畏生命的重量,也敢闯技术的盲区,让更多患者能‘把心放进肚子里’。”
他是心脏大血管上的“心尖舞者”,
在生死毫厘间守护生命律动;
从海外求学到扎根临床,
他将世界前沿技术融入手术刀尖
……
既敬畏生命的重量,
也敢闯技术的盲区,
中山五院心血管外科主任简锴陶,
带领团队筑牢生命防线,
让更多患者“把心放进肚子里”。

凌晨3时的手术室,简锴陶正全神贯注地缝合着血管——这是一台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患者的血管内膜已经撕裂,外膜开始渗血,心包腔内大量积血,需要更换人工血管,缝合稍有不慎,吻合部位就会再次破裂,“就像在废墟上重建房屋”。

从医20余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简锴陶,早已习惯在心脏与大血管的“雷区”中行走,在毫厘之间与生死过招。他是心脏大血管外科的“拆弹专家”,更是患者眼里“能把心放进肚子里”的人。

在“生死时速”中抢回生命
“每延迟一小时,死亡率增加1%。24小时内,一半患者会死亡;48小时后,75%的人将失去生命。”谈及最凶险的心血管急症——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简锴陶语气凝重。这种疾病血管内膜撕裂,血液在动脉壁内外膜间疯狂冲刷,外膜一旦破裂,患者瞬间死亡。
上周,一位常年高血压的慢性肾衰患者突发急性主动脉夹层,夹层撕裂至头部血管、肾动脉,甚至累及右侧冠状动脉。手术中,团队需同时进行主动脉瓣成形、升主动脉置换、全主动脉弓置换、支架象鼻手术、冠脉搭桥等操作,在一台手术内运用了瓣膜成形、大血管置换及冠脉搭桥技术。时间紧、任务重,多种复杂操作叠加,考验着团队的技术与耐力。从凌晨1时到上午10时,历经9小时,手术终获成功。
这样的“紧急救援”,是心血管外科的常态。


把世界前沿技术“种”进临床
2009年,简锴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先后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做访问学者。彼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心脏外科,他亲眼见证了微创瓣膜修复与替换、人工心脏植入、介入主动脉瓣置换等国内尚未开展的技术。
他注意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一年大约进行1000台手术,在数量上不及国内大型医院,却以高占比的疑难危重手术稳居全美前十;患者术后快速康复、转至合作医院继续治疗的模式,大幅提升了病房周转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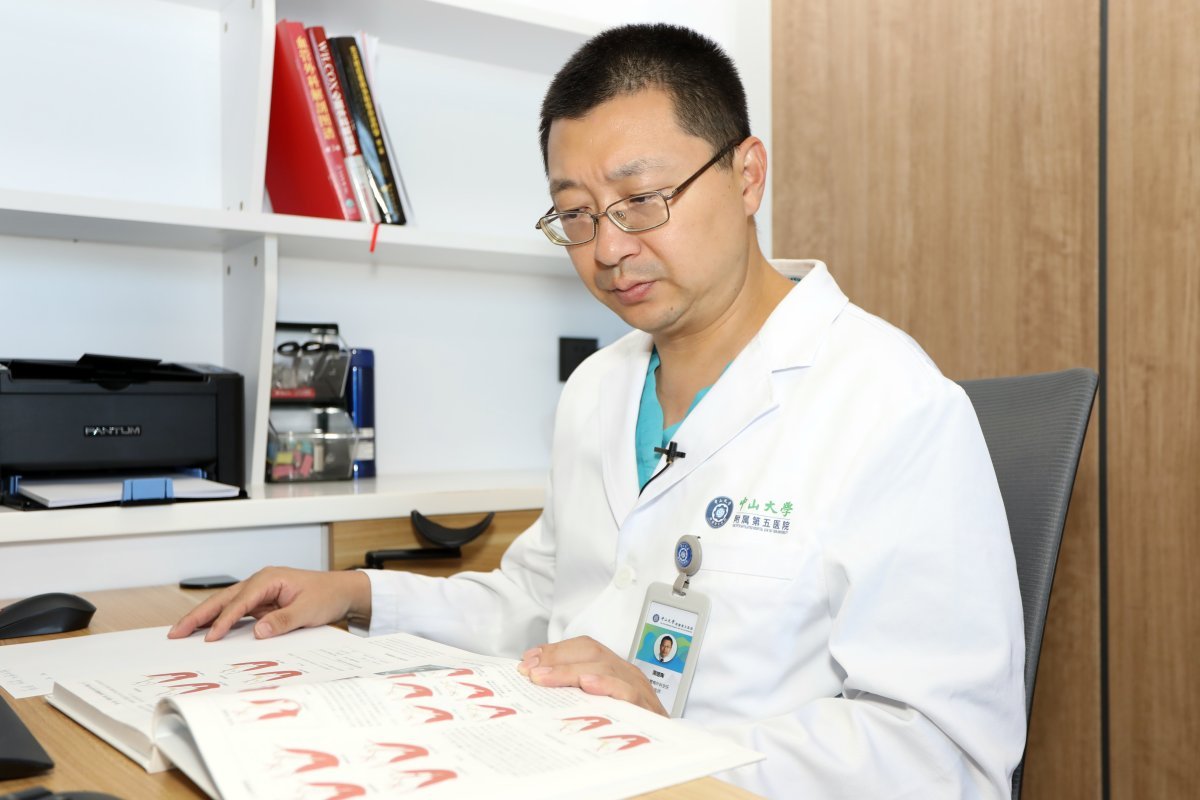
更让他触动的是“临床-科研-转化”的紧密闭环:医生既深耕手术台,也扎根实验室,介入瓣膜、人工心脏等创新成果从研发到临床应用的背后,都离不开医生的身影;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必须参与科研工作,并非局限于动物实验或细胞培养,而是将研究成果逐步转化为临床方案。
这些见闻像种子一样在简锴陶心里生根,他意识到,好的外科医生不只是开刀手术,更是解决问题的探索者。“他们一年只做一千台手术,却敢啃最硬的骨头,这颠覆了我对‘多就是好’的认知,‘质’才更重要。而这种‘头脑风暴’模式,让科研与临床像齿轮一样咬合。”
回国后,他把这份“探索欲”带进临床诊疗中。如今,他带领团队开展的心脏大血管手术,患者术后2-3天甚至更短时间就可以转出监护室,平均7-10天就能出院,快速康复理念使心脏大血管手术不再可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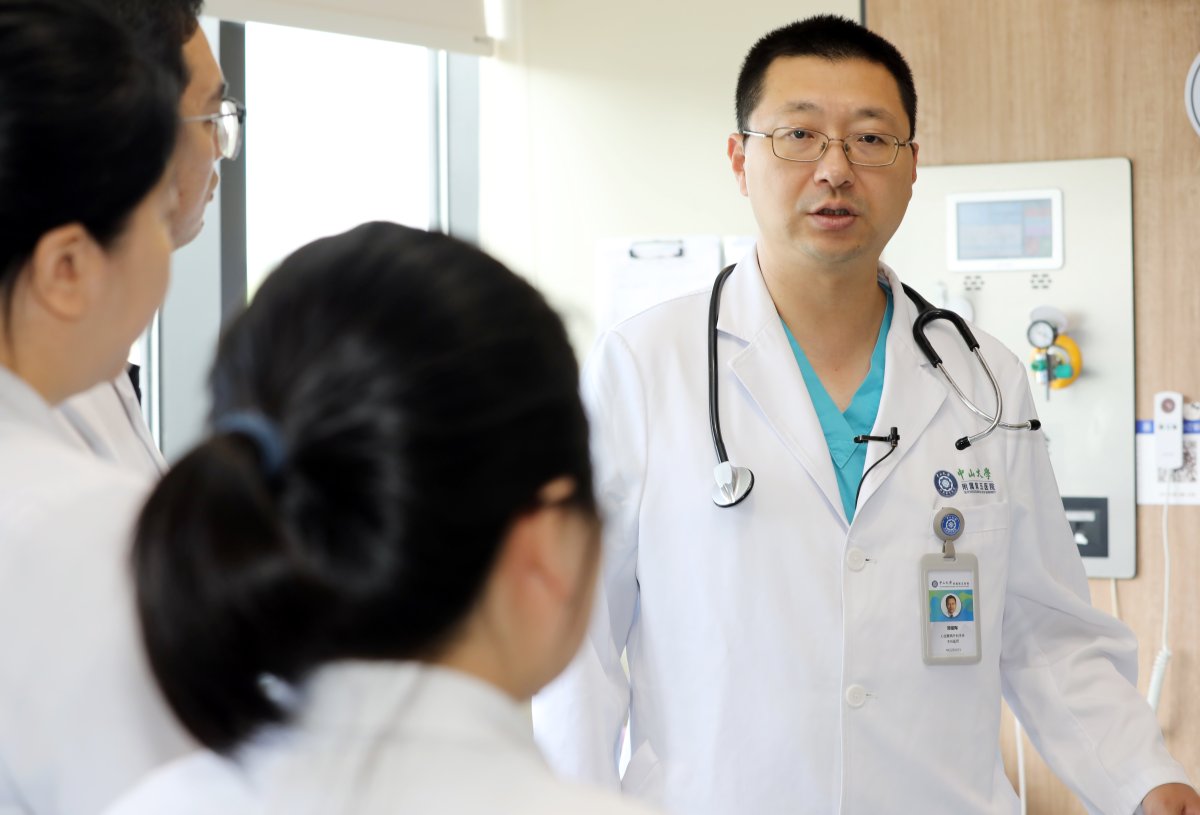

以团队之力筑牢生命防线
“心脏外科的进步,不是某个人跑得多快,而是一群人走得有多稳。”在简锴陶看来,心脏外科从不是 “一个人的战场”。
“心脏大血管疾病患者病情紧急、累及多脏器,往往是急诊手术,还可能涉及跨学科协作。” 简锴陶说,一台复杂手术的成功,背后是整个团队的托举——麻醉医生的协同、体外循环医生的生命支持、术中护理团队的配合以及术后ICU团队的细致照护,缺一不可。
而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的多学科平台,能为复杂病例提供有力支撑,例如联合创伤科进行移植物感染的皮瓣移植、与胸外科合作处理累及血管的恶性肿瘤等,让患者实现“一站式” 诊疗。

如今,临床之外,简锴陶的研究重心仍锚定在干细胞组织工程学领域,希望通过干细胞技术实现心肌组织的结构修复与功能再生,“终末期心脏病患者往往只能等心脏移植,但供体有限。通过干细胞的相关研究,希望能够探索一条新路径,让受损的心肌‘自己长好’,这是眼下最想啃下的硬骨头。”
放眼行业未来,简锴陶的目标清晰而务实:短期要推动中山五院心脏大血管疾病诊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此外,让心脏大血管手术的微创技术能够更加普及;长期则希望中山五院院内的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进而覆盖珠海全市,最终辐射粤西及港澳地区,让患者能够在区域内解决问题,免于奔波之苦。

对于年轻一代心外科医生,他认为,态度比技术先到位。住院医师阶段别嫌基础活“琐碎”,缝合、打结、看片子,这些基本功是日后“拆弹”的底气。他寄语青年医生:“希望你们接过接力棒时,既能敬畏生命的重量,也敢闯技术的盲区,让更多患者能‘把心放进肚子里’。”

-我已经到底线啦-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