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枇杷树
枇杷树
□ 蒲光树
那天回家,猛然瞥见那棵光秃秃的枇杷树,我的心为之一紧,这棵枇杷树怎么了?那疏朗的枝呢?那油亮亮的叶呢?那昂首向天的头呢?都到哪里去了?我停下匆匆的脚步,凑上前仔细打量:枇杷树的枝与头都被人砍去了,断裂处整齐光滑,可见砍刀十分锋利,挥刀人下手相当狠,仿佛有深仇大恨,砍了头斩了枝还不解恨,又在枇杷树离地一米处做了环切手术,切除了包裹的皮,切口足足三厘米宽,还在切口处扎进了一颗至少三厘米的铁钉。
我家单元门口左边有棵枇杷树。我喜欢枇杷,以及树。
不说枇杷的果有多甜,花有多美,叶有多绿,单是那名字,就让人喜欢得情不自禁。
叶似琵琶,故名枇杷。古人真有想象力,把一种水果赋予一种乐器的音乐质感。品尝枇杷,仿佛就听见了琵琶语,那缕缕思绪就飘向枇杷树的枝丫间,天籁之音悠然而起,轻叩心弦,婉转悠扬,宁静空灵,纯洁如西泠河畔的甘霖,沐浴其中,整个人便远离了世俗,洗净了凡尘杂音,无论怎么遐想连篇,都再也不想初恋了。朦胧中,头花开了,二花开了,三花也开了,一百多天,枇杷花依序开放,蜜蜂嗡嗡嗡的,枇杷蜜从蜜蜂嘴里淌出来,混在琵琶语里,仿佛“枇杷”的每一笔每一画都又甜又香。吃枇杷果,听琵琶语,好似置身西王母的蟠桃宴。这世上有多少水果与乐器扯在了一起?我孤陋寡闻,只知道有“枇杷”扯上了“琵琶”。
于是,我特别喜欢枇杷。曾经把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篡改成“日啖枇杷三百颗,不辞长做东山人”,让乡镇写成大横幅,横挂在人行道树上。所谓东山,双流的兴隆、永兴、太平、三星、大林一带丘区乡镇。这些乡镇曾经大面积种植枇杷,为助推枇杷销售,还设立了“枇杷节”。那些年,我经常跑这些乡镇,也经常下到地里,看一看枇杷长得好不好,与老百姓聊一聊枇杷种植的话题,推动散落在田间地头的期盼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惠农举措。“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枇杷黄熟时,整个东山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那滋味不亚于过年,只差杀一头肥猪。看枇杷长,品枇杷味,枇杷丰收了,我和老百姓一样的快乐。
后来,我远离了那片叫东山的农田,那一棵棵枇杷树却一直长在我的心头,让我时时念兹在兹那一树青绿。
换个地方居住,尽管容积率不小,楼房外观长相粗陋,场景亮丽指数低,也没什么舒适度,但是小区地段还算好,出门就是公园,方便散步遛弯,还有一米阳光晒着,我身不由己成了这处楼房的业主。收房时偶然发现单元门口一左一右各栽了一棵枇杷树,令我喜出望外。
枇杷树左右相对,续了我对枇杷的念想。左边数枝蜡梅陪伴,枇杷树与蜡梅日复一日深情守望;右边一树芙蓉相偎,不远处还有一棵洋槐和几丛绵竹陪衬。仅三两年时间,枇杷树就长到了三米多高,树干挺直,树型高挑,分出了四层枝丫,虽不甚茂密繁盛,却也疏朗有度,它们都长成了自己的风景。枇杷树长到应有的高度就不再往上长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开花结果,能结多少就结多少,一点也不含糊。槐花落尽,芙蓉含笑,枇杷二花刚开,蜡梅即含苞待放,绵竹则不声不响地静候枇杷三花迎春,花和花加持,香与香缠绕着,爱的长度只在四季间轮回。枇杷三花开过,几场春雨润泽,几日暖阳照耀,枇杷果一天天膨胀,由青变黄,橄榄球一样高高地挂在枝头,又像散落的星星,招摇着,众人路过都情不自禁抬头翘望,想象着枇杷的滋味。芙蓉、蜡梅、绵竹簇拥着枇杷树,还有我叫不出名的那些花花草草们都走出了自己的内心,相互加持,挨挨挤挤,争着向天空探出头去,不为浮云,只为多晒一晒红彤彤的太阳。它们在各得其所的宿命里,翻新着我家单元门前的四季韵味,美了我们的日子,也长出了我们的快乐,从枇杷树下经过,我的脚步仿佛也轻快了许多。
流年似水,日子习以为常,我总是步履匆匆走过,似乎不曾有一丝丝感激,也很少为它们特意停留一时半会儿。
自苗圃来到这个小区,栽树的人随意挖个坑,枇杷树就在我家单元门口落地生根。每天清晨,枇杷树醒来,揉揉惺忪的眼睛,打量着进进出出的人们,他们一个个穿戴得整整齐齐,包裹得严严实实,和自己一样好看,间或有人朝自己瞟一瞟,眼睛里好像也充满了善意。枇杷树感到很踏实,也很欣慰,那个栽树的人随便挖个坑,就为自己的一生选择了一处好风水。几年来,枇杷树卖力生长,一茎一脉,等身长头一般默默向上,只为快快长高,长得枝繁叶茂,让头顶上那片天空不空,让周遭的空气更加清新甜润,让粗粝的墙体幻化成一幅婉约的画,让滴翠的枝叶为人们送上满眼青绿,遮挡一星半点阳光。

□ 彭 健
学诗
行医之余妄学诗,
工夫深浅惟自知。
炼字熔句搜枯肠,
始是沉吟初成时。
疏狂
李杜诗篇曜银河,
余亦飘零自此过。
拟把疏狂付弦歌,
星月陶然从天落。
礼仪
礼仪之大故称夏,
服章之美谓之华。
明是非,正性情,
踵事增华经国家。
聆听
大音希声邈寂静,
虚空无垠惊雷闻。
侧听山水弥琮琤,
林间飞鸟啁啾鸣。
花开草长自低吟,
响浃肌髓诗乐音。
澄怀观道聆真淳,
箴言语重抵人心。

□ 龙志球
夫人在金湾开了一家棋院,我偶尔过去帮忙。碰巧隔壁正在敲敲打打搞装修,我抬头一看,四个大字——穗华书店!
这名字眼熟呀。我问老板:是不是以前前山那个穗华书城?
老板点头。我说:“以前我经常去这家书店看书呢……”
二十多年前,父母在珠海打工。读高中的我,每逢寒暑假就像候鸟一样,从湖南过来团聚。一有空,我就自己坐公交车去逛书店。
那时珠海市区的公交车,普通车收费1元,空调车要2元。为了省1块钱,我宁肯多等也要坐普通车,即便一上车就热得大汗淋漓。我对自己说:没事,到书店就好了。
从翠景工业区出发,有时坐5路车或15路车去南坑。南坑市场对面的新一佳超市人气很旺。我不逛超市,直奔二楼的凤凰书城。书城虽不算大,但一摞一摞的书足够你看了。有时坐8路车去拱北,华润万家超市地下,有一个超级大书店——文华书城。说实话,单从规模来看,凤凰书城其实还算不上“城”,叫“书店”更准确,文华书城那规模才配得上这个“城”字。在里面一排排逛,光是选择就得耗费不少时间,看这本还是读那本呢?那时囊中羞涩,买得少,一般都是就地坐下“蹭”书看。但售货员经常来回巡逻,喊你起来,让我想起挤火车时,那熟悉的“瓜子可乐矿泉水”。免费看个书,不容易!
当然,人家做生意也不容易。不过,我这个人还是讲原则的,不管去哪个店,至少买一本书。买得最多的,是年度小说选(短篇或者中篇);也买文具,比如笔记本——那时我每天写日记。前山的穗华书城,其实我去得不多,但确实在那买过好几个精美笔记本。
去得最多的,是吉大的新华书店,也就是珠海书城。这当然是珠海最大的书店了。每天,我也像个上班族,吃了早餐就去挤40路公交车,到新华书店“上班”。一般在二楼或三楼,选一本喜欢的书——文学或历史类比较多,时政或人物传记也喜欢,找个拐角僻静的地方“躲”起来,席地而坐。吹着空调,安安静静地读书,多美的时光!但新华书店的店员也非常称职,走来走去地喊“起来哈起来哈”,把一众像我一样“蹭知识”的人搞得像打游击似的。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部分的书都套了一层塑料膜,非买勿拆!这可怎么办?顾客问:你这书打不开,我都不晓得写得好不好,怎么敢买呢?书店觉得有道理,于是每种书都拆开一本——类似卖糕点的人,切些小块让你免费试吃,好吃了再买。于是那本拆开的样书,往往被我这样的人翻得“饱经沧桑”。
然而话说回来,一本书要是没人翻,它干干净净地立在书架上,又有什么意义呢?
看了一上午,肚子饿了。我也“下班”,到对面一家桂林米粉店吃碗粉。吃饱了,我是不午休的——也没条件呀。于是又回到新华书店,继续席地而坐“蹭”书看。中午店员也困,我这边反而可以专心致志了——就是空调开得有点低,经常冷得要左右手互相“摩擦生热”。夜色阑珊时,我也赶公交车“下班”,回家去了。
等参加工作,生了娃,于是又带娃一起逛书店。这些年,我们在日月贝新华书店书笙馆搞过沙龙,在优特汇西西弗书店买过珍藏版四大名著,在扬名广场文华书城买过老乡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在无界书店看过博洛尼亚插画展,在北山停云书房买过生肖陶瓷杯……
最夸张的一次,我一个人带5个小孩去香山公园对面的阅潮书店读绘本,孩子们特别喜欢躺在墙壁凹进去的圆形座位上,优哉游哉地翻书。
最难忘的一次,是在吉大新华书店一个僻静的角落,发现了一本写近现代名人逸闻趣事的《野史记》,忍不住发朋友圈:“在成千上万堆书中,淘到它全靠运气,有趣还有所思有所得,一本好书碰到了有缘人!”
当然还有幸运的事。2020年某个周末,我在北师大珠海校区加班干活,无意中听说梁鸿来无界书店,于是赶过去听她讲梁庄人的故事,买了《出梁庄记》。2021年某天,我去华发商都阅潮书店参加刘震云《一日三秋》分享会,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我拿之前买过他的几本小说一并请他签名。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还一起合了影。
最意难平的一次,是去年3月,在会同村举行《湾韵》创刊2周年纪念活动后,蒋子龙、潘军、田瑛等著名作家闲逛时,我热情地向他们推介旁边古色古香的阅潮书店,结果走到那里才发现,书店关门了。我忍不住一声长叹,一段文坛佳话就此完美错过,可惜!
二十多年来,能够静下心来读书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书店的经营自然也越发举步维艰。2019年,拱北文华书城关停,但比起消失的凤凰书城,它算幸运的,最起码它依然存在。
时代的脚步仿佛正在俯冲,它自带加速度,裹挟着我们个个行色匆匆。然而万物运转,也需动静调和。那么,不妨偶尔找个空隙,躲进某个书店:偷得浮生半日闲,遨游书海赛神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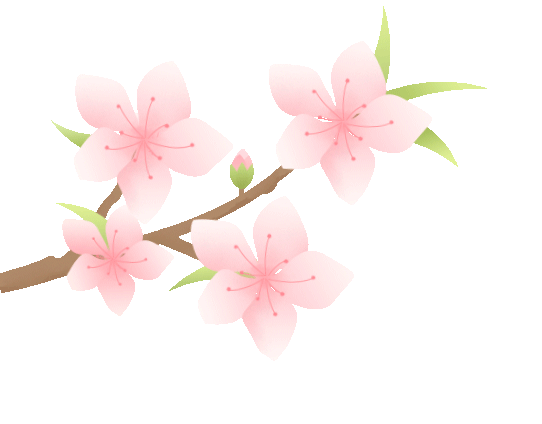
□ 赵同江
日历轻轻一翻,冬便悄然而至了。
窗外的风,果然换了一副腔调,从高楼的窗缝里挤进来,吹得小北屋的窗格子微微作响,带着些凛冽的、不容分说的冬的声音。可这寒意,偏偏是叫人清醒的;透过玻璃望去,绿意消失,它将天地间纷繁的杂色一并收拾了去,只剩下疏朗的枝干,与高而远的、铅灰色的天空。
儿时的冬,人坐在屋里,守着红泥小炉上咕嘟着的茶,那热气袅袅地升腾起来,混着茶香,便觉得那窗外的寒,倒成了这室内暖的一种陪衬了。呷一口暖茶,与三五故人,说些闲话,也无非是桑麻收成、旧年光景。这光阴,真是快得吓人,像一只飞得决绝的鸟儿,倏忽间,便只剩个小小的影儿了。
这般想着,心里便不由得盘桓起“冬”的意味来。这“冬”,又何尝只是时令上的呢?
人生的路途上,谁不曾走过自己的“冬”呢?那青涩年华里,揣着一颗滚烫的心,在陌生的城池里奔走,尝过多少冷眼,碰过多少壁。那为着一个前程,点灯熬夜的酸楚;那为一个机会,赔尽小心的卑微;那眼看努力付诸东流,心头泛起的苦涩……这一切,都像是人生里一场又一场的寒风,砭人肌骨。创业的艰辛,更是如此了。那是一条少有人走的、布满荆棘的路。资金的窘迫,如同数九的冰;市场的莫测,好似突来的雪;同行的倾轧,又像刺骨的霜。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无边的暗夜里,独自守着一点不肯熄灭的星火,那滋味,是真正的寒冬。
还有那情爱里的“冬”,怕是最叫人断肠的。也像是公式和方程,这样被人们遵循着,由起初的炽热,到后来的猜疑、怨怼,终至分离。那爱里的恨,舍中的痛,离别的哀,都积在心里,冻成一块沉甸甸的、永不融化的冰。每每想起,便是一阵彻骨的凉意,仿佛生命里最明媚的一段春光,被硬生生地夺了去,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若将眼光再放得开阔些,我们脚下这片古老的土地,又何尝不是从漫长的“冬”里跋涉出来的呢?我仿佛还能从史书的字缝里,听见那百年来的苦难与悲歌。战争的烽火,灼伤了她的肌肤;贫穷的枷锁,禁锢了她的脚步;还有那些内里的危机与外来的欺侮,像一层又一层的坚冰,将她紧紧封冻。那是一段多么漫长而酷烈的严冬啊,山河呜咽,天地同悲。
然而,你且看——
那行路的人,虽在寒风中瑟缩,却总将衣领竖得更高,脚步踩得更实;那创业的灯火,在深夜里,反而燃得更亮,更旺;那颗受过伤的心,在无尽的冬日里,默默地积蓄着、修复着,等待着下一次勇敢地跳动。而我们这多难兴邦的国家,更是在这严寒里,迸发出最惊人的热力。一代代人,怀着那伟大复兴的梦想,胼手胝足,奋力前行。这梦想,便如冬日里一轮不落的太阳,光芒虽不炽烈,却源源不断地供给着温暖与希望。于是,冻土松动了,生机萌发了,一条崭新的、洒满晨光的路,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
炉上的茶,又滚了一回。那“咕嘟咕嘟”的声音,听着就叫人心里踏实。窗外的天色,似乎也不那么阴沉了,云层后面,隐隐透出些光来。
是的,还带着数字中国的风,冬天既已堂堂正正地来了,那么,那莺飞草长、春暖花开的日子,难道还会远吗?

□ 陈毅艺
凯旋门般的树荫
每次经过老香洲的桃园路,都被路两旁粗生粗长的大叶榕树与绿意所震撼;被她双向对弯成凯旋门般的姿势与绿荫所敬仰。
每当看着那浓浓的绿,在四季的守候中依然不改容颜,哪怕台风袭来,她也坚韧地在风中沉默对抗风的肆虐。
我想起那不太遥远的1979年,想起南疆木棉花怒放的那个三月底,踏着硝烟凯旋的子弟兵,走在欢呼鲜花凯旋门那一望无际的沾满征尘的绿军装中!
那长成凯旋门般的树荫,是大自然馈赠的杰作。那沉默的绿荫,每天为夏日献出她清凉的爱。她得到行人的声声赞美,也获取走过此路游人一瞥羡慕的眼光。
冬天将至,她绿荫依旧,她一年四季都在绿色中成长。她在岁月的暗夜里酝酿绿意,在黎明之后她释放爱的绿荫。
她是城市里一抹永恒的颜色,每次经过这条路,都仿如走进一幅画、一首散文诗……
鸡山半湾沙滩
有空,你真应往那个地方走走看看。半山半海半村庄的鸡山村,其外滩是珠海情侣路北段最美最大的一个半湾。若说情侣路是城市的裙裾,那这半湾就是镶嵌在裙边最闪亮的那块珠片。
潮涨潮退,褪不去的是海湾四季迷人的美景。风来风去,吹不走的是美人踩在沙滩上的风情。云聚云散,看湾区五大机场客机云上的翱翔。
多羡慕那些栖居半湾海边的人啊,白天能眺望鸥飞鹭翔,静夜可一揽万千星辉,头枕海水轻漫上岸来,倾听潮声飒飒,在梦中与浅海那点点隐约渔火相拥入眠……
鸡山半湾沙滩,也是有待你寄给远方一封情书上的那枚邮票。
十字门两岸
不见当年的硝烟与拼杀!
不闻当年的战鼓与呐喊!
伫立十字门岸边,水道海面不再现南宋覆灭的最后惨烈一战。那千艘沿海一路苦难鏖战的船舶,在交战中早已樯橹灰飞烟灭……如今的海上古战场,四岸崛起座座宏伟的建筑,宛如当年威风凛凛,迎面而来的艘艘战船。
我静静凝望沉思,我凭吊737年前由此至崖山的南宋与元军终极一战!在此历经四场血火大海战,一代宋朝宁死明志不降,用尸山筑我大宋民族之威武,用血海抒写我堂堂大朝之浩气!
我凭栏眺望,水道潮涌崖门缓缓而去,平静的海水呢喃诉说昔日宋元大战的风云,那沉没海底的战船没有静卧岁月的海床,更迭的历史风暴,一次次把它从大海深处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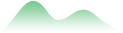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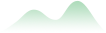
□ 赵艳芬
北方的凤凰,携着一缕清凉,
掠过南海的碧波,
抵达这方港湾——
绿草如茵,山水相伴。
四季如春,海色云天。
那是一只怎样的凤凰?
羽翅驮着星月的光,尾翎轻过云端。
惊鸿一瞥间,
只见山如黛眉,隐隐龙脉姿显;
水似玉环潺流,惬意伶仃岸畔;
草木在晨光里,把清新酿就香甜。
凤凰收敛了翅膀,栖落在山水间。
无名的山脉有了名字,叫“凤凰山”
从此,每一层峦,都藏着羽翼的温婉;
每一滴泉水涓淌,都载着神鸟的啼响。
凤凰山的风,带着羽翼的吉祥,
吹绿了千年的梧桐与松岗,
吹活了一方水土的灵秀内涵
吹起了唐家湾的人杰地灵,
吹成了香山文化的悠久绵延。

 枇杷树
枇杷树
□ 蒲光树
那天回家,猛然瞥见那棵光秃秃的枇杷树,我的心为之一紧,这棵枇杷树怎么了?那疏朗的枝呢?那油亮亮的叶呢?那昂首向天的头呢?都到哪里去了?我停下匆匆的脚步,凑上前仔细打量:枇杷树的枝与头都被人砍去了,断裂处整齐光滑,可见砍刀十分锋利,挥刀人下手相当狠,仿佛有深仇大恨,砍了头斩了枝还不解恨,又在枇杷树离地一米处做了环切手术,切除了包裹的皮,切口足足三厘米宽,还在切口处扎进了一颗至少三厘米的铁钉。
我家单元门口左边有棵枇杷树。我喜欢枇杷,以及树。
不说枇杷的果有多甜,花有多美,叶有多绿,单是那名字,就让人喜欢得情不自禁。
叶似琵琶,故名枇杷。古人真有想象力,把一种水果赋予一种乐器的音乐质感。品尝枇杷,仿佛就听见了琵琶语,那缕缕思绪就飘向枇杷树的枝丫间,天籁之音悠然而起,轻叩心弦,婉转悠扬,宁静空灵,纯洁如西泠河畔的甘霖,沐浴其中,整个人便远离了世俗,洗净了凡尘杂音,无论怎么遐想连篇,都再也不想初恋了。朦胧中,头花开了,二花开了,三花也开了,一百多天,枇杷花依序开放,蜜蜂嗡嗡嗡的,枇杷蜜从蜜蜂嘴里淌出来,混在琵琶语里,仿佛“枇杷”的每一笔每一画都又甜又香。吃枇杷果,听琵琶语,好似置身西王母的蟠桃宴。这世上有多少水果与乐器扯在了一起?我孤陋寡闻,只知道有“枇杷”扯上了“琵琶”。
于是,我特别喜欢枇杷。曾经把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篡改成“日啖枇杷三百颗,不辞长做东山人”,让乡镇写成大横幅,横挂在人行道树上。所谓东山,双流的兴隆、永兴、太平、三星、大林一带丘区乡镇。这些乡镇曾经大面积种植枇杷,为助推枇杷销售,还设立了“枇杷节”。那些年,我经常跑这些乡镇,也经常下到地里,看一看枇杷长得好不好,与老百姓聊一聊枇杷种植的话题,推动散落在田间地头的期盼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惠农举措。“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枇杷黄熟时,整个东山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那滋味不亚于过年,只差杀一头肥猪。看枇杷长,品枇杷味,枇杷丰收了,我和老百姓一样的快乐。
后来,我远离了那片叫东山的农田,那一棵棵枇杷树却一直长在我的心头,让我时时念兹在兹那一树青绿。
换个地方居住,尽管容积率不小,楼房外观长相粗陋,场景亮丽指数低,也没什么舒适度,但是小区地段还算好,出门就是公园,方便散步遛弯,还有一米阳光晒着,我身不由己成了这处楼房的业主。收房时偶然发现单元门口一左一右各栽了一棵枇杷树,令我喜出望外。
枇杷树左右相对,续了我对枇杷的念想。左边数枝蜡梅陪伴,枇杷树与蜡梅日复一日深情守望;右边一树芙蓉相偎,不远处还有一棵洋槐和几丛绵竹陪衬。仅三两年时间,枇杷树就长到了三米多高,树干挺直,树型高挑,分出了四层枝丫,虽不甚茂密繁盛,却也疏朗有度,它们都长成了自己的风景。枇杷树长到应有的高度就不再往上长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开花结果,能结多少就结多少,一点也不含糊。槐花落尽,芙蓉含笑,枇杷二花刚开,蜡梅即含苞待放,绵竹则不声不响地静候枇杷三花迎春,花和花加持,香与香缠绕着,爱的长度只在四季间轮回。枇杷三花开过,几场春雨润泽,几日暖阳照耀,枇杷果一天天膨胀,由青变黄,橄榄球一样高高地挂在枝头,又像散落的星星,招摇着,众人路过都情不自禁抬头翘望,想象着枇杷的滋味。芙蓉、蜡梅、绵竹簇拥着枇杷树,还有我叫不出名的那些花花草草们都走出了自己的内心,相互加持,挨挨挤挤,争着向天空探出头去,不为浮云,只为多晒一晒红彤彤的太阳。它们在各得其所的宿命里,翻新着我家单元门前的四季韵味,美了我们的日子,也长出了我们的快乐,从枇杷树下经过,我的脚步仿佛也轻快了许多。
流年似水,日子习以为常,我总是步履匆匆走过,似乎不曾有一丝丝感激,也很少为它们特意停留一时半会儿。
自苗圃来到这个小区,栽树的人随意挖个坑,枇杷树就在我家单元门口落地生根。每天清晨,枇杷树醒来,揉揉惺忪的眼睛,打量着进进出出的人们,他们一个个穿戴得整整齐齐,包裹得严严实实,和自己一样好看,间或有人朝自己瞟一瞟,眼睛里好像也充满了善意。枇杷树感到很踏实,也很欣慰,那个栽树的人随便挖个坑,就为自己的一生选择了一处好风水。几年来,枇杷树卖力生长,一茎一脉,等身长头一般默默向上,只为快快长高,长得枝繁叶茂,让头顶上那片天空不空,让周遭的空气更加清新甜润,让粗粝的墙体幻化成一幅婉约的画,让滴翠的枝叶为人们送上满眼青绿,遮挡一星半点阳光。

□ 彭 健
学诗
行医之余妄学诗,
工夫深浅惟自知。
炼字熔句搜枯肠,
始是沉吟初成时。
疏狂
李杜诗篇曜银河,
余亦飘零自此过。
拟把疏狂付弦歌,
星月陶然从天落。
礼仪
礼仪之大故称夏,
服章之美谓之华。
明是非,正性情,
踵事增华经国家。
聆听
大音希声邈寂静,
虚空无垠惊雷闻。
侧听山水弥琮琤,
林间飞鸟啁啾鸣。
花开草长自低吟,
响浃肌髓诗乐音。
澄怀观道聆真淳,
箴言语重抵人心。

□ 龙志球
夫人在金湾开了一家棋院,我偶尔过去帮忙。碰巧隔壁正在敲敲打打搞装修,我抬头一看,四个大字——穗华书店!
这名字眼熟呀。我问老板:是不是以前前山那个穗华书城?
老板点头。我说:“以前我经常去这家书店看书呢……”
二十多年前,父母在珠海打工。读高中的我,每逢寒暑假就像候鸟一样,从湖南过来团聚。一有空,我就自己坐公交车去逛书店。
那时珠海市区的公交车,普通车收费1元,空调车要2元。为了省1块钱,我宁肯多等也要坐普通车,即便一上车就热得大汗淋漓。我对自己说:没事,到书店就好了。
从翠景工业区出发,有时坐5路车或15路车去南坑。南坑市场对面的新一佳超市人气很旺。我不逛超市,直奔二楼的凤凰书城。书城虽不算大,但一摞一摞的书足够你看了。有时坐8路车去拱北,华润万家超市地下,有一个超级大书店——文华书城。说实话,单从规模来看,凤凰书城其实还算不上“城”,叫“书店”更准确,文华书城那规模才配得上这个“城”字。在里面一排排逛,光是选择就得耗费不少时间,看这本还是读那本呢?那时囊中羞涩,买得少,一般都是就地坐下“蹭”书看。但售货员经常来回巡逻,喊你起来,让我想起挤火车时,那熟悉的“瓜子可乐矿泉水”。免费看个书,不容易!
当然,人家做生意也不容易。不过,我这个人还是讲原则的,不管去哪个店,至少买一本书。买得最多的,是年度小说选(短篇或者中篇);也买文具,比如笔记本——那时我每天写日记。前山的穗华书城,其实我去得不多,但确实在那买过好几个精美笔记本。
去得最多的,是吉大的新华书店,也就是珠海书城。这当然是珠海最大的书店了。每天,我也像个上班族,吃了早餐就去挤40路公交车,到新华书店“上班”。一般在二楼或三楼,选一本喜欢的书——文学或历史类比较多,时政或人物传记也喜欢,找个拐角僻静的地方“躲”起来,席地而坐。吹着空调,安安静静地读书,多美的时光!但新华书店的店员也非常称职,走来走去地喊“起来哈起来哈”,把一众像我一样“蹭知识”的人搞得像打游击似的。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部分的书都套了一层塑料膜,非买勿拆!这可怎么办?顾客问:你这书打不开,我都不晓得写得好不好,怎么敢买呢?书店觉得有道理,于是每种书都拆开一本——类似卖糕点的人,切些小块让你免费试吃,好吃了再买。于是那本拆开的样书,往往被我这样的人翻得“饱经沧桑”。
然而话说回来,一本书要是没人翻,它干干净净地立在书架上,又有什么意义呢?
看了一上午,肚子饿了。我也“下班”,到对面一家桂林米粉店吃碗粉。吃饱了,我是不午休的——也没条件呀。于是又回到新华书店,继续席地而坐“蹭”书看。中午店员也困,我这边反而可以专心致志了——就是空调开得有点低,经常冷得要左右手互相“摩擦生热”。夜色阑珊时,我也赶公交车“下班”,回家去了。
等参加工作,生了娃,于是又带娃一起逛书店。这些年,我们在日月贝新华书店书笙馆搞过沙龙,在优特汇西西弗书店买过珍藏版四大名著,在扬名广场文华书城买过老乡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在无界书店看过博洛尼亚插画展,在北山停云书房买过生肖陶瓷杯……
最夸张的一次,我一个人带5个小孩去香山公园对面的阅潮书店读绘本,孩子们特别喜欢躺在墙壁凹进去的圆形座位上,优哉游哉地翻书。
最难忘的一次,是在吉大新华书店一个僻静的角落,发现了一本写近现代名人逸闻趣事的《野史记》,忍不住发朋友圈:“在成千上万堆书中,淘到它全靠运气,有趣还有所思有所得,一本好书碰到了有缘人!”
当然还有幸运的事。2020年某个周末,我在北师大珠海校区加班干活,无意中听说梁鸿来无界书店,于是赶过去听她讲梁庄人的故事,买了《出梁庄记》。2021年某天,我去华发商都阅潮书店参加刘震云《一日三秋》分享会,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我拿之前买过他的几本小说一并请他签名。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还一起合了影。
最意难平的一次,是去年3月,在会同村举行《湾韵》创刊2周年纪念活动后,蒋子龙、潘军、田瑛等著名作家闲逛时,我热情地向他们推介旁边古色古香的阅潮书店,结果走到那里才发现,书店关门了。我忍不住一声长叹,一段文坛佳话就此完美错过,可惜!
二十多年来,能够静下心来读书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书店的经营自然也越发举步维艰。2019年,拱北文华书城关停,但比起消失的凤凰书城,它算幸运的,最起码它依然存在。
时代的脚步仿佛正在俯冲,它自带加速度,裹挟着我们个个行色匆匆。然而万物运转,也需动静调和。那么,不妨偶尔找个空隙,躲进某个书店:偷得浮生半日闲,遨游书海赛神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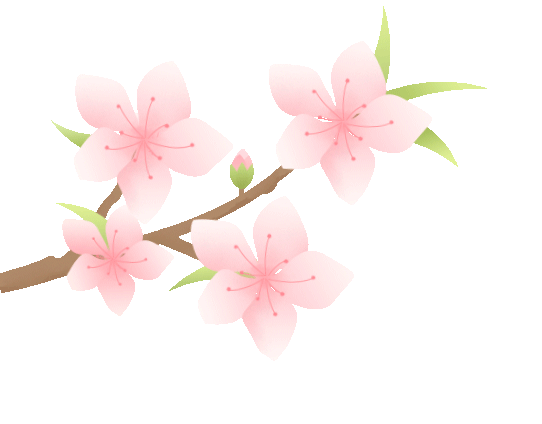
□ 赵同江
日历轻轻一翻,冬便悄然而至了。
窗外的风,果然换了一副腔调,从高楼的窗缝里挤进来,吹得小北屋的窗格子微微作响,带着些凛冽的、不容分说的冬的声音。可这寒意,偏偏是叫人清醒的;透过玻璃望去,绿意消失,它将天地间纷繁的杂色一并收拾了去,只剩下疏朗的枝干,与高而远的、铅灰色的天空。
儿时的冬,人坐在屋里,守着红泥小炉上咕嘟着的茶,那热气袅袅地升腾起来,混着茶香,便觉得那窗外的寒,倒成了这室内暖的一种陪衬了。呷一口暖茶,与三五故人,说些闲话,也无非是桑麻收成、旧年光景。这光阴,真是快得吓人,像一只飞得决绝的鸟儿,倏忽间,便只剩个小小的影儿了。
这般想着,心里便不由得盘桓起“冬”的意味来。这“冬”,又何尝只是时令上的呢?
人生的路途上,谁不曾走过自己的“冬”呢?那青涩年华里,揣着一颗滚烫的心,在陌生的城池里奔走,尝过多少冷眼,碰过多少壁。那为着一个前程,点灯熬夜的酸楚;那为一个机会,赔尽小心的卑微;那眼看努力付诸东流,心头泛起的苦涩……这一切,都像是人生里一场又一场的寒风,砭人肌骨。创业的艰辛,更是如此了。那是一条少有人走的、布满荆棘的路。资金的窘迫,如同数九的冰;市场的莫测,好似突来的雪;同行的倾轧,又像刺骨的霜。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无边的暗夜里,独自守着一点不肯熄灭的星火,那滋味,是真正的寒冬。
还有那情爱里的“冬”,怕是最叫人断肠的。也像是公式和方程,这样被人们遵循着,由起初的炽热,到后来的猜疑、怨怼,终至分离。那爱里的恨,舍中的痛,离别的哀,都积在心里,冻成一块沉甸甸的、永不融化的冰。每每想起,便是一阵彻骨的凉意,仿佛生命里最明媚的一段春光,被硬生生地夺了去,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若将眼光再放得开阔些,我们脚下这片古老的土地,又何尝不是从漫长的“冬”里跋涉出来的呢?我仿佛还能从史书的字缝里,听见那百年来的苦难与悲歌。战争的烽火,灼伤了她的肌肤;贫穷的枷锁,禁锢了她的脚步;还有那些内里的危机与外来的欺侮,像一层又一层的坚冰,将她紧紧封冻。那是一段多么漫长而酷烈的严冬啊,山河呜咽,天地同悲。
然而,你且看——
那行路的人,虽在寒风中瑟缩,却总将衣领竖得更高,脚步踩得更实;那创业的灯火,在深夜里,反而燃得更亮,更旺;那颗受过伤的心,在无尽的冬日里,默默地积蓄着、修复着,等待着下一次勇敢地跳动。而我们这多难兴邦的国家,更是在这严寒里,迸发出最惊人的热力。一代代人,怀着那伟大复兴的梦想,胼手胝足,奋力前行。这梦想,便如冬日里一轮不落的太阳,光芒虽不炽烈,却源源不断地供给着温暖与希望。于是,冻土松动了,生机萌发了,一条崭新的、洒满晨光的路,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
炉上的茶,又滚了一回。那“咕嘟咕嘟”的声音,听着就叫人心里踏实。窗外的天色,似乎也不那么阴沉了,云层后面,隐隐透出些光来。
是的,还带着数字中国的风,冬天既已堂堂正正地来了,那么,那莺飞草长、春暖花开的日子,难道还会远吗?

□ 陈毅艺
凯旋门般的树荫
每次经过老香洲的桃园路,都被路两旁粗生粗长的大叶榕树与绿意所震撼;被她双向对弯成凯旋门般的姿势与绿荫所敬仰。
每当看着那浓浓的绿,在四季的守候中依然不改容颜,哪怕台风袭来,她也坚韧地在风中沉默对抗风的肆虐。
我想起那不太遥远的1979年,想起南疆木棉花怒放的那个三月底,踏着硝烟凯旋的子弟兵,走在欢呼鲜花凯旋门那一望无际的沾满征尘的绿军装中!
那长成凯旋门般的树荫,是大自然馈赠的杰作。那沉默的绿荫,每天为夏日献出她清凉的爱。她得到行人的声声赞美,也获取走过此路游人一瞥羡慕的眼光。
冬天将至,她绿荫依旧,她一年四季都在绿色中成长。她在岁月的暗夜里酝酿绿意,在黎明之后她释放爱的绿荫。
她是城市里一抹永恒的颜色,每次经过这条路,都仿如走进一幅画、一首散文诗……
鸡山半湾沙滩
有空,你真应往那个地方走走看看。半山半海半村庄的鸡山村,其外滩是珠海情侣路北段最美最大的一个半湾。若说情侣路是城市的裙裾,那这半湾就是镶嵌在裙边最闪亮的那块珠片。
潮涨潮退,褪不去的是海湾四季迷人的美景。风来风去,吹不走的是美人踩在沙滩上的风情。云聚云散,看湾区五大机场客机云上的翱翔。
多羡慕那些栖居半湾海边的人啊,白天能眺望鸥飞鹭翔,静夜可一揽万千星辉,头枕海水轻漫上岸来,倾听潮声飒飒,在梦中与浅海那点点隐约渔火相拥入眠……
鸡山半湾沙滩,也是有待你寄给远方一封情书上的那枚邮票。
十字门两岸
不见当年的硝烟与拼杀!
不闻当年的战鼓与呐喊!
伫立十字门岸边,水道海面不再现南宋覆灭的最后惨烈一战。那千艘沿海一路苦难鏖战的船舶,在交战中早已樯橹灰飞烟灭……如今的海上古战场,四岸崛起座座宏伟的建筑,宛如当年威风凛凛,迎面而来的艘艘战船。
我静静凝望沉思,我凭吊737年前由此至崖山的南宋与元军终极一战!在此历经四场血火大海战,一代宋朝宁死明志不降,用尸山筑我大宋民族之威武,用血海抒写我堂堂大朝之浩气!
我凭栏眺望,水道潮涌崖门缓缓而去,平静的海水呢喃诉说昔日宋元大战的风云,那沉没海底的战船没有静卧岁月的海床,更迭的历史风暴,一次次把它从大海深处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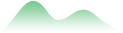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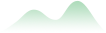
□ 赵艳芬
北方的凤凰,携着一缕清凉,
掠过南海的碧波,
抵达这方港湾——
绿草如茵,山水相伴。
四季如春,海色云天。
那是一只怎样的凤凰?
羽翅驮着星月的光,尾翎轻过云端。
惊鸿一瞥间,
只见山如黛眉,隐隐龙脉姿显;
水似玉环潺流,惬意伶仃岸畔;
草木在晨光里,把清新酿就香甜。
凤凰收敛了翅膀,栖落在山水间。
无名的山脉有了名字,叫“凤凰山”
从此,每一层峦,都藏着羽翼的温婉;
每一滴泉水涓淌,都载着神鸟的啼响。
凤凰山的风,带着羽翼的吉祥,
吹绿了千年的梧桐与松岗,
吹活了一方水土的灵秀内涵
吹起了唐家湾的人杰地灵,
吹成了香山文化的悠久绵延。

-我已经到底线啦-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