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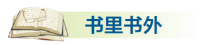
梦中的水声 |
| ——读卢锡铭散文集《枕水听涛》 |
□范若丁
近日,我常常似梦似幻地听到水声。有大江大海相拥掀起的激越巨浪,有灌溉千顷良田的涓涓清流,有渔舟唱晚的桨橹,有孩子们嬉水的喧闹,我正迷惑这些或悲壮或柔和或欢快的声音由何而来,忽然看到身旁一部书稿——作家卢锡铭的新作散文集《枕水听涛》。
卢锡铭的故乡在虎门,一个从历史到现实都非常有名的地方,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前后有天壤的变化。人们对故乡大都有一种依恋之情,这不仅因为故乡的风光,而且有他少年生活的记忆。卢锡铭的《枕水听涛》是写故乡虎门,而且多是写虎门的水。虎门为珠江八个出海口之首,它靠江靠海,也有大岭山、象山、三台山、眼眉山、钓鱼岗等起伏的山岗和万顷良田,但水是它最美最让人难忘的地方。
我是外乡人,其实我与虎门老早就有缘分,1954年我到过那里。当时国家要对烟酒实行专卖,我和几位参加筹建广东专卖事业管理局的同事到各地调查情况,给筹建工作提供依据。现代的人们很难想象,当时我是坐单车去的。从广州乘火车先到石龙,石龙离太平(虎门)还有几十公里,就只有去乘单车了,那时候珠江三角洲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单车。后来我再去时,就坐花尾渡船。就像卢锡铭文中所说,花尾渡是一种靠火船拉动的巨大客船,有两三层高,白色,每次拉动像一只在水中滑行的白天鹅。沿途每到一个码头,岸上就会有清脆的钟声飘过来,随后上来几个乘客。随着时代的变化,交通工具也有变化,到了上世纪90年代,广州到虎门已经有了水上飞翼船和高速公路的公共汽车,现在就乘高铁和城轨了。交通便利了,人民的生活更是日新月异。作家卢锡铭虽然出外工作数十年,但对故乡却念念不忘。2008年,他让我联系几位作家到他家乡走一趟,采访和参观,写一部反映虎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报告文学集。于是金敬迈、章以武、左多夫、伊始、艾云、张梅、郭玉山和我就随卢锡铭走进虎门。
我负责采访南栅村,蒋光鼐的故居就在这条村。它位于广济河口,古代河道口设置栅栏,缉查私盐,派兵驻守。这鱼米之乡,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民只能在地里刨食,一年三造还填不饱肚子。改革开放大潮冲开这栅门,翻起滔天的巨浪,这条村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采访当年已实现全区人均收入14535元,如今的南栅更是工厂林立,街道纵横,昔日的农村嬗变成一个繁华的小镇。虎门更是气象万千,比内地一个中等城市还要兴旺。历史的嬗变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今后的样子也难以猜想。
卢锡铭的散文新作,有其鲜明的特点:即写真情实感。真情实感是普通的,人人有之,但非人皆用之。通过真情实感书写,透视社会前进的履痕,更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文章写得再美,空空如也,也只是一纸彩色废纸而已。这本书稿最感人的就是动真情抒实感,思驰千载,下笔神助,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烟火味浓,浪涛声高。非一般乡愁文章可比。我骤然明白,这水声,扣动的是时代的浪潮。
我读老卢的文章,每个细节都会在我心里响动,如那岭南水乡女人爱穿的木屐在石板路敲出的踢踏声,常在我心内回旋,这就是他的成功之处。
啊!枕着水韵入梦,听见时代涛声。
(作者系花城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花城》杂志原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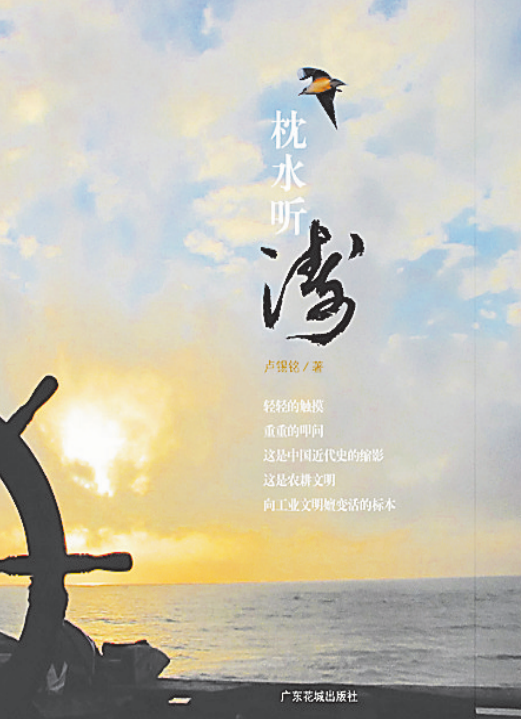 《枕水听涛》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枕水听涛》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顽强的小草 |
| ——序毛岸琴作品集《岸芷汀兰》 |
□钟建平
毛岸琴,湖南长沙人。来珠海有些年头了,一直在打拼。正应了那句赞扬潮州人的歌词——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为工作,为家庭,为爱好,岸琴恰似一棵小草,看上去很平凡,却折射出一种昂扬向上且不屈不挠的精神。
岸琴在一家幼儿园工作近二十年,勤恳,踏实,有爱心,富文采,颇得赞誉。尽管工作持家养娃非常辛苦和劳累,岸琴依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苦苦追求。事实上,她出道很早,1996年就在家乡的《望城报》发表作品。2011年《精彩》创刊以来,尤其是2014年《精彩诗报》创办以来,经常可见岸琴忙碌的身影,参加诗歌沙龙,登台珠港澳诗会,流连大湾区诗歌论坛,蜜蜂采蜜般地吸取营养,或采风、或创作、或交流、或切磋,三年一小台阶,五年一大台阶。佳作迭出,散文有《香樟树下的母亲》《父爱如山》《星星点灯》;激情喷涌,诗作不断,如《公交到站》《石溪感怀》《疼痛并未消失》《春的召唤》等,引人关注。在文友师长们的鼓励下,就拿出第一本作品集来了。可喜,可贺!
岸琴的诗写得比散文好,有感而发,接地气,体会深,用词精炼,留白到位,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公交到站》体现得淋漓尽致:提拐/伸手/摸索/抬脚/迈步/小步丈量了距离/大步跨过了障碍/车轮动/声音和眼神聚焦/陌生的臂膀/拦住下滑的拐杖/公交再到站/车厢/一时塞满/拐杖笃笃/霎时/闪出一条道/相扶下车/回望/渐行渐远/拐杖笃笃/血色的黄昏/仿若晨曦。岸琴的诗既能找到传统的影子,又有现代的手法和技巧,给人比较广阔的想象空间。读完《公交到站》,你可以感觉到上公交车的残障人士至少有两个,甚至三个四个。他们之间互相提携,而车上的人也主动帮忙引导或让道,寥寥数笔,小中见大。岸琴工作生活的珠海,那人与人之间暖暖的温情,通过这么一件小事就弥漫开来了,让人动容。
她的《春的召唤》异曲同工:春天/有温暖的味道/窗前/落叶自由飘过/眼神/在没有自由的窗棂边游离/一个小小的脑袋/探出渴望的眼神/多想/像树叶般/至少可以触摸到/春的温柔/痴痴凝望窗外/不曾清洗的小手/在空中划过/他想握住父母/离开时的影子。读完这首诗,我立刻就想到二十多年前让无数中国人揪心甚至落泪的“希望工程招贴画”——小女孩那大大的忧郁的闪着晶莹泪光的眼睛。岸琴的诗让人将心又沉重一次——关注留守儿童。这是岸琴写作上的一次升华,她已走出小我,关注大我了。2017年是中国新诗一百年,从胡适、鲁迅到徐志摩,再到舒婷、海子……几代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今年是新诗第二个一百年的头一年,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岸琴出书了,这本身就是对新诗百年最好的纪念。
祝愿岸琴能在风风雨雨中,经受住生活的磨难,仍能坚守初心,像一棵顽强的小草,活出自己的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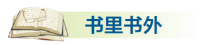
梦中的水声 |
| ——读卢锡铭散文集《枕水听涛》 |
□范若丁
近日,我常常似梦似幻地听到水声。有大江大海相拥掀起的激越巨浪,有灌溉千顷良田的涓涓清流,有渔舟唱晚的桨橹,有孩子们嬉水的喧闹,我正迷惑这些或悲壮或柔和或欢快的声音由何而来,忽然看到身旁一部书稿——作家卢锡铭的新作散文集《枕水听涛》。
卢锡铭的故乡在虎门,一个从历史到现实都非常有名的地方,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前后有天壤的变化。人们对故乡大都有一种依恋之情,这不仅因为故乡的风光,而且有他少年生活的记忆。卢锡铭的《枕水听涛》是写故乡虎门,而且多是写虎门的水。虎门为珠江八个出海口之首,它靠江靠海,也有大岭山、象山、三台山、眼眉山、钓鱼岗等起伏的山岗和万顷良田,但水是它最美最让人难忘的地方。
我是外乡人,其实我与虎门老早就有缘分,1954年我到过那里。当时国家要对烟酒实行专卖,我和几位参加筹建广东专卖事业管理局的同事到各地调查情况,给筹建工作提供依据。现代的人们很难想象,当时我是坐单车去的。从广州乘火车先到石龙,石龙离太平(虎门)还有几十公里,就只有去乘单车了,那时候珠江三角洲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单车。后来我再去时,就坐花尾渡船。就像卢锡铭文中所说,花尾渡是一种靠火船拉动的巨大客船,有两三层高,白色,每次拉动像一只在水中滑行的白天鹅。沿途每到一个码头,岸上就会有清脆的钟声飘过来,随后上来几个乘客。随着时代的变化,交通工具也有变化,到了上世纪90年代,广州到虎门已经有了水上飞翼船和高速公路的公共汽车,现在就乘高铁和城轨了。交通便利了,人民的生活更是日新月异。作家卢锡铭虽然出外工作数十年,但对故乡却念念不忘。2008年,他让我联系几位作家到他家乡走一趟,采访和参观,写一部反映虎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报告文学集。于是金敬迈、章以武、左多夫、伊始、艾云、张梅、郭玉山和我就随卢锡铭走进虎门。
我负责采访南栅村,蒋光鼐的故居就在这条村。它位于广济河口,古代河道口设置栅栏,缉查私盐,派兵驻守。这鱼米之乡,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民只能在地里刨食,一年三造还填不饱肚子。改革开放大潮冲开这栅门,翻起滔天的巨浪,这条村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采访当年已实现全区人均收入14535元,如今的南栅更是工厂林立,街道纵横,昔日的农村嬗变成一个繁华的小镇。虎门更是气象万千,比内地一个中等城市还要兴旺。历史的嬗变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今后的样子也难以猜想。
卢锡铭的散文新作,有其鲜明的特点:即写真情实感。真情实感是普通的,人人有之,但非人皆用之。通过真情实感书写,透视社会前进的履痕,更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文章写得再美,空空如也,也只是一纸彩色废纸而已。这本书稿最感人的就是动真情抒实感,思驰千载,下笔神助,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烟火味浓,浪涛声高。非一般乡愁文章可比。我骤然明白,这水声,扣动的是时代的浪潮。
我读老卢的文章,每个细节都会在我心里响动,如那岭南水乡女人爱穿的木屐在石板路敲出的踢踏声,常在我心内回旋,这就是他的成功之处。
啊!枕着水韵入梦,听见时代涛声。
(作者系花城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花城》杂志原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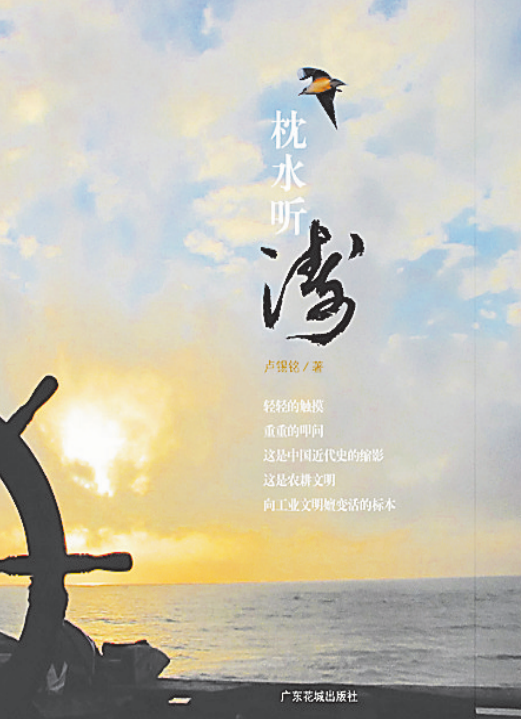 《枕水听涛》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枕水听涛》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顽强的小草 |
| ——序毛岸琴作品集《岸芷汀兰》 |
□钟建平
毛岸琴,湖南长沙人。来珠海有些年头了,一直在打拼。正应了那句赞扬潮州人的歌词——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为工作,为家庭,为爱好,岸琴恰似一棵小草,看上去很平凡,却折射出一种昂扬向上且不屈不挠的精神。
岸琴在一家幼儿园工作近二十年,勤恳,踏实,有爱心,富文采,颇得赞誉。尽管工作持家养娃非常辛苦和劳累,岸琴依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苦苦追求。事实上,她出道很早,1996年就在家乡的《望城报》发表作品。2011年《精彩》创刊以来,尤其是2014年《精彩诗报》创办以来,经常可见岸琴忙碌的身影,参加诗歌沙龙,登台珠港澳诗会,流连大湾区诗歌论坛,蜜蜂采蜜般地吸取营养,或采风、或创作、或交流、或切磋,三年一小台阶,五年一大台阶。佳作迭出,散文有《香樟树下的母亲》《父爱如山》《星星点灯》;激情喷涌,诗作不断,如《公交到站》《石溪感怀》《疼痛并未消失》《春的召唤》等,引人关注。在文友师长们的鼓励下,就拿出第一本作品集来了。可喜,可贺!
岸琴的诗写得比散文好,有感而发,接地气,体会深,用词精炼,留白到位,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公交到站》体现得淋漓尽致:提拐/伸手/摸索/抬脚/迈步/小步丈量了距离/大步跨过了障碍/车轮动/声音和眼神聚焦/陌生的臂膀/拦住下滑的拐杖/公交再到站/车厢/一时塞满/拐杖笃笃/霎时/闪出一条道/相扶下车/回望/渐行渐远/拐杖笃笃/血色的黄昏/仿若晨曦。岸琴的诗既能找到传统的影子,又有现代的手法和技巧,给人比较广阔的想象空间。读完《公交到站》,你可以感觉到上公交车的残障人士至少有两个,甚至三个四个。他们之间互相提携,而车上的人也主动帮忙引导或让道,寥寥数笔,小中见大。岸琴工作生活的珠海,那人与人之间暖暖的温情,通过这么一件小事就弥漫开来了,让人动容。
她的《春的召唤》异曲同工:春天/有温暖的味道/窗前/落叶自由飘过/眼神/在没有自由的窗棂边游离/一个小小的脑袋/探出渴望的眼神/多想/像树叶般/至少可以触摸到/春的温柔/痴痴凝望窗外/不曾清洗的小手/在空中划过/他想握住父母/离开时的影子。读完这首诗,我立刻就想到二十多年前让无数中国人揪心甚至落泪的“希望工程招贴画”——小女孩那大大的忧郁的闪着晶莹泪光的眼睛。岸琴的诗让人将心又沉重一次——关注留守儿童。这是岸琴写作上的一次升华,她已走出小我,关注大我了。2017年是中国新诗一百年,从胡适、鲁迅到徐志摩,再到舒婷、海子……几代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今年是新诗第二个一百年的头一年,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岸琴出书了,这本身就是对新诗百年最好的纪念。
祝愿岸琴能在风风雨雨中,经受住生活的磨难,仍能坚守初心,像一棵顽强的小草,活出自己的精彩。

-我已经到底线啦-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