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赵 丹
正是盛夏时节,窗外的植物长得正旺。我所在的考场,正对着操场边的那一架炮仗花。初夏已过,那些热烈绚烂的花儿早已凋谢落尽了。那些绿色的叶子层层叠叠,挨挨挤挤,沿着花架攀援而上,一路铺开而去,像极了一股绿色的热烈的生命之流,铺满整个花架,形成一道天然的绿色凉棚。
考场里,学生正埋头答题,我仔细瞧了,有一道题是:写出关于“花中四君子”的一句古诗。我抬头望向窗外,不禁莞尔,那葱葱茏茏的炮仗花藤下,不正悬挂着这些诗句吗?此刻,在那些抓耳挠腮的孩子中,不知哪个有心的人能发现这个秘密?
“不行啦,毛虫太多了,这架子得拆了。”两个月前,有人说。我不禁感慨,这一架长得正旺的绿色瀑布,命不久矣。暑期马上就要到了,我知道,我得与它们告别了。
园林师傅拿起修长的园林剪,把那些伸得太长的不听话的藤蔓剪掉了,地上已堆起被剪掉的绿色枝叶。我倒是喜欢看它们自在舒展的样子,它们不理会烈日的灼晒,不理会喧闹的孩童,在夏日的光阴里,自由任性地舒展着。细长的藤蔓在阳光中划出一条条优美的弧线,自由地垂着,在微风中摇曳。如果有人走过凉棚,它们便轻抚过行人的脸颊、肩头。在这些稚嫩的翠绿的藤蔓里,透过它们背后的阳光,我似乎看到,那里面流淌着最鲜活最灵动的绿色生命之流,像血液在血管里流动,像药液在输液管里滴淌。不错的,那就是它们的血液,它们的乳汁,它们的寄托,同时也饱含着最卑微也最执着的希望之光。
它们,是活的。
这是一座老校,园里的建筑也老,植物也跟着老。犹记得几年前,校园外的小路两旁生长着高大浓密的小叶榕,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几可蔽日。清晨,我踏着星星点点的光影走进学校,似乎也浸染了它们的生命之光,顿觉神清气爽,舒适自在。后来,街道改建,这些树被剪断了枝叶,连根拔起,整条街道便曝晒于烈日之下。我还记得那日的惨状:满街的碎叶折枝,裸露在外的树根,一截一截的树桩挤满了每一辆卡车。自那以后,我走在这条路上,少了些闲情逸致,更不忍那烈日的曝晒,却是脚步匆匆了。
此刻,窗外的那些绿色,似乎与路边的榕树有着同样的命运。就在顷刻间,窗外那些线条被师傅修剪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师傅满意地点点头,收拾起地上的残枝败叶。然而,生命仍在继续。对于这些可爱的绿色,我似乎不能做些什么,唯有不舍罢了,唯有怀念罢了。在夏日的微风中,飘来一丝淡淡的青草香,倏地,又随风飘散去了。

□ 肖景文
在零丁洋的浩渺呼啸间
海浪翻涌 似白花绽放
港珠澳大桥 飞架如虹霞
巨龙蜿蜒 串起三地繁华
车影匆匆 穿梭于雾霭之下
心随远方 向着无垠天涯
涛声悠悠 弹奏清嘉的韵华
这千秋的伟大功业
如明珠 璀璨耀中华
转身来到白浪滩的夜畔
渔歌晚唱 声声不断
红霞在潮涨中舒展 翻卷
明月洒下清辉 潜入深蓝
文艺的旋律 如灵动的弦
在沙滩上 悠悠地弹
晴夜之下 铁花四溅
飞舟破浪 击破烟波
爽风轻拂 沉醉了这个夏天
似神仙 逍遥在天地间
千浪涌起 涛光闪闪
游客的欢笑 回荡在海边



□ 彭 健
东风
东风溥天浩荡情,大地生机绚彩竞。
鱼龙吹浪海潮迎,无限希冀乘春兴。
朔风
呼啸怒号天地摇,裹挟西北冰雪刀。
凛冽刺骨胆气寒,进一退三行镳镳。
西风
枫落菊残秋无多,谁唤西风泪婆娑?
花神吹恨入星河,檀英无奈冷香何。
夏雨
南国夏雨漫水涨,风似拔山怒欲狂。
雨如决河倒川江,卷地飚来忽震泱。
墨云飘去天苍苍,海面夜月光翻浪。
舟行帆扬复荡漾,鸥鸣鹭飞旋徜徉。
片云
天上有云心更闲,因风伴月到人间。
萦绕高树滞远山,裴回漠漠又空还。


□ 崔 云
时值阳春三月,繁花似锦,绿柳如烟,莺啼燕舞,处处皆是盎然春意。趁着这大好春光,我特地前往石溪亦兰亭,去寻访百年前的摩崖石刻群。
提及石溪,不得不先说一说鲍俊。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是清代岭南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他25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曾以殿试“书法冠场”得御批殊荣。鲍俊曾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刑部山西司主事。1831年,因不满官场倾轧,年仅34岁的他辞官归隐,从此在广州与故乡香山县山场村(今珠海香洲山场村)两地往返。褪去朝服的鲍俊,执笔如剑,在石溪的山水间重筑精神家园。因仰慕王羲之,他便在山场石牛岭溪流旁修建了“亦兰亭”,并效仿兰亭雅集,经常邀请岭南名士在此吟诗作赋,挥毫泼墨,畅叙幽情。兴之所至,乃勒石于涧,留墨迹三十余处。想一想他们纵情山水、曲水流觞的欢乐场景,不禁有些心驰神往,那是何等畅快淋漓,何等洒脱惬意啊!鲍俊的真性情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
行至珠海山场,沿着古元美术馆右侧的小径,循着溪流而上,泉水在耳畔叮咚作响,清脆的鸟鸣此起彼伏,互相应和,山林因此显得十分喧闹,极富生机。溪水自凤凰山南脉蜿蜒而下,在嶙峋怪石间跌宕成韵。沿途翠竹树木交互缠绕,郁郁葱葱,玉堂春、紫荆花、簕杜鹃等花开正盛,蜂飞蝶舞,春风拂面,暖意盈怀。
溯溪前行约200米,便进入了被列为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溪摩崖石刻群。
“石龙溅雪”是进入石溪亦兰亭的第一道景观。在丰水期,山泉喷薄而下,十分壮观,那是山与水的伟力。蓄势而发,一鸣惊人!
抬头左望,一块巨石上镌刻的两个红色大字“莲岛”格外醒目,乃鲍俊所书,字体柔美,温和圆润,与周围的绿意相映成趣。原来这是石溪八景之一的“旷石观莲”。我心中疑惑:山中哪来的莲花呢?细一打量,原来那块题字巨石,经过风雨的雕琢,露出层层叠叠的纹路,真是像极了盛开的硕大莲花。我不禁为古人的智慧暗暗叫绝。
岁月的冲刷,山泉和雨水的侵蚀,使得那些或横卧或矗立或凌空的巨石千疮百孔,颜色呈现红褐色或深黑色。有些石头因靠近路边,经常被行人踩踏或抚摸,变得溜光圆滑。有些大石上的题诗题字,因岁月的剥蚀,已模糊不清,却依然挡不住人们探寻的目光。石头们沉默不语,躬身肃立,仿佛阅尽世间沧桑的老者,宁静淡然。
正当我艰难前行时,迎面一块巨石上“石溪”二字赫然映入眼帘,这是鲍俊的手迹,刚劲有力,潇洒飘逸。相对而立的另一块巨石上,有两首题诗,洋洋洒洒写满了半块石头。两块巨石分别向后侧延伸,犹如燕子展翅,动感十足,因此景点得名“石燕迎风”,极为形象。只是这只石燕千百年来岿然不动,神情自如,任人抚摸打量,显得憨态十足。
行至众多溪流汇聚成的方形池塘边,但见一块刻有“激湍”二字的石头卧于池内,字迹一半浸在水中,一半露出水面。现在雨水不多,没有激流冲刷的石头静如处子。池塘正上方,巍然矗立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四角亭,绿色的“亦兰亭”三字令人心神为之一振,亭柱上的撰联颇有深意:到处有玄机,流水高山随俯仰;此间无俗客,方中野服即神仙。实乃高妙!人一下子仿佛穿越到了远古,去赴一场文人的盛会。
在亦兰亭周围,有斗大的一笔“鹅”奇书和“砥柱”“琴泉”“枕流”“观澜”“流觞”“茂林修竹”等石刻。亦兰亭后方,“惜字社”遗址地基和仅存的几截断墙被妥善保护,可以想象当年名士们雅集的盛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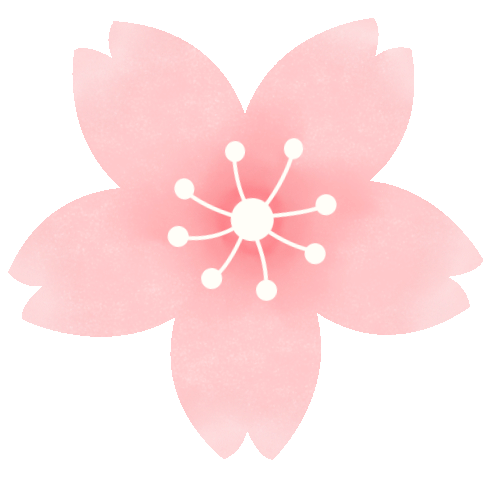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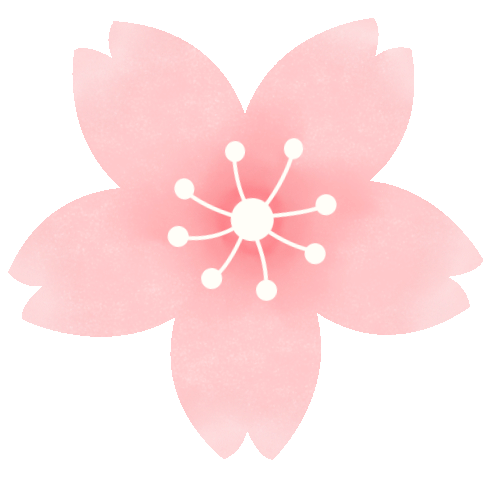
□ 夏太锋
一个双休日,夏周强邀我见面,送我一本广东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新课程理念下的数学教学与评价》。米黄色封面,油墨芳香缠绕鼻尖。轻轻翻开,章节赫然入目。
我与周强是校友,师范毕业后入同一所学校任教,我教语文,周强教数学。
周强任过小学、中学、教师进修学校教师,后评聘为数学高级讲师。年轻时的周强高且单瘦,圆脸,额头宽阔光洁,发际线比普通人高,风流倜傥,英姿勃发。一双深眸常作沉思状,颇有学者风范,后来果然成了小学数学教学领域名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周强从中央团校进修结业归校,担任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同时向学校申请教小学一年级数学。这一届学生为五年制,周强一直教到毕业。其间,周强孜孜矻矻,焚膏继晷,边教学边摸索,寻找规律,积累经验。
一次,我回乡下探望父母,归校几近深夜,校园阒无一人,寂静无声。我俩同住校门口平房,路过廊檐,瞧见周强房里亮着灯,透过窗玻璃望去,办公桌上码着厚厚的作业本和书籍,周强正在挑灯夜战,奋笔疾书,撰写文稿。我至今记得,每周语、数老师轮番辅导学生早自习,轮到周强值日,腋下夹着厚厚的作业本,从宿舍沿着铺了煤渣的跑道前行,肩膀一边下垂一边上耸,走一会下垂的肩膀向上一提,避免作业本掉落。到达教学楼,缓缓爬上三楼,8点准时走进教室,讲解题目,查漏补缺。当年他的住房前有两个高约一米的花坛,红砖浆砌,栽着两棵桂花树。放学后,总有三五个基础较差的学生坐在花坛边做作业。
后来,我们先后离开了学校,周强去了珠海,先后担任珠海市香洲区数学教研员、教师发展中心教研室主任、广东教育学会数学专业委员会理事。特区先进的教学理念、优越的教学条件,为周强搭建了施展才能的舞台。
积沙成塔,集腋成裘。多年的教育教学工作,让周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几年,他在省级以上教育报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教学录像带、教学评价软件、教学光盘各一套。

□ 曾继文
卖酒的女孩
这串号码,被酒洗过
铮亮
像那个卖酒的女孩
银铃般的歌声飘在杯里
她说,酒里有山风
有泥土,有五谷
蜜蜂采的蜜
酿在酒中
我闻到了酒中
天地日月的味道
听到了卖酒女孩
酒窝里盛满的笑声
大雨前的蚂蚁
一只疲惫不堪的蚂蚁
望着天说,明天有大雨
路人说,不怕
我有一把大伞
蚂蚁没有伞
它们要赶紧搬家
从一座山翻到另一座山
寻找一个天晴的家
我们和蚂蚁并没有两样
它们矮小
我们也不高大
都在土地上寻找温暖
一只鸟的祝福
一只鸟,一只干净的鸟
猛然飞过我的头顶
然后飞上电线杆的顶端
每次开车走过前山河大桥
这只鸟总会扇扇翅膀
清脆地叫我几声
我听不懂它说什么
它是不是在说,开慢点
生活不是急来的
窗外
很多年了,窗外的泥土与石头
混杂在一起
光秃秃的
偶尔有群鸟在这玩一会儿
然后又叽叽喳喳飞走
暴雨来了
把窗外的一切冲洗了一遍
一片片凋零的落叶
飘在记忆的风中
远处,一条河
从西往东不停地流
浪花,像白鹭展翅飞翔
月光落在纸上的声音
惊醒了我纸上做梦的词语
这天清晨,太阳还没出来
一阵风推开窗户
石头与泥水间
长出了一片绿草
你提着露珠,向我走来
写给天空
凝眸天空
你把自己交给了一朵白云
树叶上哭泣的小鸟
好想与你唱支悲伤的歌
你一身红裙准备远征
留下昨夜未喝完的半壶酒
雪花悄悄开了
春风在掌心上发芽
两片绿叶重逢
互相说着树的青绿
一个人的念想太小
两个人的念想才是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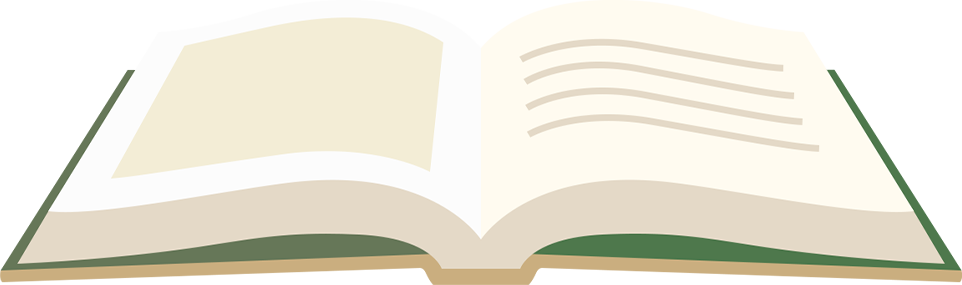
——读方嘉雯《濠涌记忆》
□ 邓翠群
认识方嘉雯老师,源于一次广东散文诗学会组织的采风活动。互加微信后,她说,原来你是我们的资深作者,知你的乡土散文写得很好。虽是一句客套话,但对我来说,是鞭策和鼓励,也证明我们有缘。得知她出了新书,竟有一睹为快的冲动。
掀开扉页,著名作家、书画家刘斯奋先生题写的自然大气、雍容遒健的“濠涌记忆”几字赫然在目。翻阅《濠涌记忆》(全名《濠涌记忆:六百年香山隆都古村的前尘往事》),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油然而生。不仅因它有16开328页(近26万字、200多幅插图)的分量,更因书中记叙的濠涌村有着六百多年历史,厚重悠长。全书分四篇十一章,以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濠涌村方氏家族六百多年历史为主要线索,从姓氏来源、人口迁徙、择地定居、群族关系、繁衍生息、文化遗存、乡音方言、海内名人等方面展开,勾勒出濠涌村数百年的发展历史。
方老师出生在濠涌村,大学毕业后进入报社工作,多年媒体记者、报刊编辑的经历,使她对本地文化有了更多元的视觉。一次她采写的两篇本土文化报道获得中国城市党报新闻奖一等奖。令她意想不到的是,这两份报纸得到海外侨胞的珍藏。侨胞们对乡土历史的珍视,让她萌发了撰写族史的意愿。后来,机缘之下,与当时中山日报社社长方炳焯等人组成工作组,并确立了“跳出村子看村子”的写作定位——从历史的纵深挖掘村庄的故事。
以族氏为中心,把与方氏家族有关的人、事、物勾连起来,四散辐射,等于在窗口里叠加了望远镜,照相机有了广角镜头,视野便豁然开朗。于是,风光旖旎的自然景观,厚重深远的人文历史,寂然无声的古建风物,喧腾热闹的街市景象,以及风味小食、方言俚语、异国风情……如滚滚波涛,奔涌笔端;从香山隆都走出去的方日英、方少穆、方人定、方作标、方宇文等海内外先贤俊彦的身影,一一浮现。
经过十年耕耘,丰富多元、图文并茂的《濠涌记忆》终于得以面世。一部具体而微的族史背后,是恢弘的香山地区甚至是半个岭南的地方史,堪称“以小见大”的典型。
为了呈现真实、客观、全面的族史,她不仅查阅了诸多史料文献,还和工作组成员到实地采访考察,足迹遍布中山市数个镇街、国内多个省市,甚至延伸到国外,那份执着,孜孜以求,只有热爱家乡的人才能做到。例如,她从族谱得知香山的方氏一世祖方道盛是宋度宗长女信安公主的驸马(崖山海战失败后,他带着妻儿逃到新会古冈,后来他的后代迁居沙溪濠涌)后,亲自到崖山海战的遗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官冲村,深入采访和考察,搜集素材。
文采斐然是书的另一亮点。祠堂、庙宇、码头、炮台、古屋、街市、古树等等,成为方老师的精神原乡,她用灵动的笔触深情抒写。
写昔日竹林街景:“大街上一头体型硕大的公猪,一颤一颤地走过,发出‘哼哧哼哧’的喘气声。公猪被牵猪郎一手用绳子牵着,一手提着竹鞭,赶着去打种。”寥寥几笔,勾勒出牵猪郎赶猪去配种的精彩情形。
写故乡景物:“曾经一望无垠的山林,阡陌纵横的田畴沃野,鱼翔浅底的小溪,随风翻滚的稻浪,鸡犬相闻的街巷,蜿蜒曲折的石板街,历史悠久的古建……一帧帧画面,拼成了记忆中的故乡。”字里行间洋溢着浓浓的乡愁。
像这样精妙的语句俯拾皆是,不一一罗列。
美国作家海明威说过:“乡村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灵魂所在。”族史像村志一样,是村的灵魂之书,是乡愁的栖身之所,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通过它,可以感受乡村的脉动,聆听历史的回响,赓续文化的根脉,也为未来的发展汲取智慧和力量。
《濠涌记忆》是我所见到的内容丰富、厚重大气的族史村史杰作,诚如为此书写序的江冰老师所言:“读之亦成精神洗礼。”

□ 赵 丹
正是盛夏时节,窗外的植物长得正旺。我所在的考场,正对着操场边的那一架炮仗花。初夏已过,那些热烈绚烂的花儿早已凋谢落尽了。那些绿色的叶子层层叠叠,挨挨挤挤,沿着花架攀援而上,一路铺开而去,像极了一股绿色的热烈的生命之流,铺满整个花架,形成一道天然的绿色凉棚。
考场里,学生正埋头答题,我仔细瞧了,有一道题是:写出关于“花中四君子”的一句古诗。我抬头望向窗外,不禁莞尔,那葱葱茏茏的炮仗花藤下,不正悬挂着这些诗句吗?此刻,在那些抓耳挠腮的孩子中,不知哪个有心的人能发现这个秘密?
“不行啦,毛虫太多了,这架子得拆了。”两个月前,有人说。我不禁感慨,这一架长得正旺的绿色瀑布,命不久矣。暑期马上就要到了,我知道,我得与它们告别了。
园林师傅拿起修长的园林剪,把那些伸得太长的不听话的藤蔓剪掉了,地上已堆起被剪掉的绿色枝叶。我倒是喜欢看它们自在舒展的样子,它们不理会烈日的灼晒,不理会喧闹的孩童,在夏日的光阴里,自由任性地舒展着。细长的藤蔓在阳光中划出一条条优美的弧线,自由地垂着,在微风中摇曳。如果有人走过凉棚,它们便轻抚过行人的脸颊、肩头。在这些稚嫩的翠绿的藤蔓里,透过它们背后的阳光,我似乎看到,那里面流淌着最鲜活最灵动的绿色生命之流,像血液在血管里流动,像药液在输液管里滴淌。不错的,那就是它们的血液,它们的乳汁,它们的寄托,同时也饱含着最卑微也最执着的希望之光。
它们,是活的。
这是一座老校,园里的建筑也老,植物也跟着老。犹记得几年前,校园外的小路两旁生长着高大浓密的小叶榕,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几可蔽日。清晨,我踏着星星点点的光影走进学校,似乎也浸染了它们的生命之光,顿觉神清气爽,舒适自在。后来,街道改建,这些树被剪断了枝叶,连根拔起,整条街道便曝晒于烈日之下。我还记得那日的惨状:满街的碎叶折枝,裸露在外的树根,一截一截的树桩挤满了每一辆卡车。自那以后,我走在这条路上,少了些闲情逸致,更不忍那烈日的曝晒,却是脚步匆匆了。
此刻,窗外的那些绿色,似乎与路边的榕树有着同样的命运。就在顷刻间,窗外那些线条被师傅修剪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师傅满意地点点头,收拾起地上的残枝败叶。然而,生命仍在继续。对于这些可爱的绿色,我似乎不能做些什么,唯有不舍罢了,唯有怀念罢了。在夏日的微风中,飘来一丝淡淡的青草香,倏地,又随风飘散去了。

□ 肖景文
在零丁洋的浩渺呼啸间
海浪翻涌 似白花绽放
港珠澳大桥 飞架如虹霞
巨龙蜿蜒 串起三地繁华
车影匆匆 穿梭于雾霭之下
心随远方 向着无垠天涯
涛声悠悠 弹奏清嘉的韵华
这千秋的伟大功业
如明珠 璀璨耀中华
转身来到白浪滩的夜畔
渔歌晚唱 声声不断
红霞在潮涨中舒展 翻卷
明月洒下清辉 潜入深蓝
文艺的旋律 如灵动的弦
在沙滩上 悠悠地弹
晴夜之下 铁花四溅
飞舟破浪 击破烟波
爽风轻拂 沉醉了这个夏天
似神仙 逍遥在天地间
千浪涌起 涛光闪闪
游客的欢笑 回荡在海边



□ 彭 健
东风
东风溥天浩荡情,大地生机绚彩竞。
鱼龙吹浪海潮迎,无限希冀乘春兴。
朔风
呼啸怒号天地摇,裹挟西北冰雪刀。
凛冽刺骨胆气寒,进一退三行镳镳。
西风
枫落菊残秋无多,谁唤西风泪婆娑?
花神吹恨入星河,檀英无奈冷香何。
夏雨
南国夏雨漫水涨,风似拔山怒欲狂。
雨如决河倒川江,卷地飚来忽震泱。
墨云飘去天苍苍,海面夜月光翻浪。
舟行帆扬复荡漾,鸥鸣鹭飞旋徜徉。
片云
天上有云心更闲,因风伴月到人间。
萦绕高树滞远山,裴回漠漠又空还。


□ 崔 云
时值阳春三月,繁花似锦,绿柳如烟,莺啼燕舞,处处皆是盎然春意。趁着这大好春光,我特地前往石溪亦兰亭,去寻访百年前的摩崖石刻群。
提及石溪,不得不先说一说鲍俊。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是清代岭南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他25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曾以殿试“书法冠场”得御批殊荣。鲍俊曾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刑部山西司主事。1831年,因不满官场倾轧,年仅34岁的他辞官归隐,从此在广州与故乡香山县山场村(今珠海香洲山场村)两地往返。褪去朝服的鲍俊,执笔如剑,在石溪的山水间重筑精神家园。因仰慕王羲之,他便在山场石牛岭溪流旁修建了“亦兰亭”,并效仿兰亭雅集,经常邀请岭南名士在此吟诗作赋,挥毫泼墨,畅叙幽情。兴之所至,乃勒石于涧,留墨迹三十余处。想一想他们纵情山水、曲水流觞的欢乐场景,不禁有些心驰神往,那是何等畅快淋漓,何等洒脱惬意啊!鲍俊的真性情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
行至珠海山场,沿着古元美术馆右侧的小径,循着溪流而上,泉水在耳畔叮咚作响,清脆的鸟鸣此起彼伏,互相应和,山林因此显得十分喧闹,极富生机。溪水自凤凰山南脉蜿蜒而下,在嶙峋怪石间跌宕成韵。沿途翠竹树木交互缠绕,郁郁葱葱,玉堂春、紫荆花、簕杜鹃等花开正盛,蜂飞蝶舞,春风拂面,暖意盈怀。
溯溪前行约200米,便进入了被列为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溪摩崖石刻群。
“石龙溅雪”是进入石溪亦兰亭的第一道景观。在丰水期,山泉喷薄而下,十分壮观,那是山与水的伟力。蓄势而发,一鸣惊人!
抬头左望,一块巨石上镌刻的两个红色大字“莲岛”格外醒目,乃鲍俊所书,字体柔美,温和圆润,与周围的绿意相映成趣。原来这是石溪八景之一的“旷石观莲”。我心中疑惑:山中哪来的莲花呢?细一打量,原来那块题字巨石,经过风雨的雕琢,露出层层叠叠的纹路,真是像极了盛开的硕大莲花。我不禁为古人的智慧暗暗叫绝。
岁月的冲刷,山泉和雨水的侵蚀,使得那些或横卧或矗立或凌空的巨石千疮百孔,颜色呈现红褐色或深黑色。有些石头因靠近路边,经常被行人踩踏或抚摸,变得溜光圆滑。有些大石上的题诗题字,因岁月的剥蚀,已模糊不清,却依然挡不住人们探寻的目光。石头们沉默不语,躬身肃立,仿佛阅尽世间沧桑的老者,宁静淡然。
正当我艰难前行时,迎面一块巨石上“石溪”二字赫然映入眼帘,这是鲍俊的手迹,刚劲有力,潇洒飘逸。相对而立的另一块巨石上,有两首题诗,洋洋洒洒写满了半块石头。两块巨石分别向后侧延伸,犹如燕子展翅,动感十足,因此景点得名“石燕迎风”,极为形象。只是这只石燕千百年来岿然不动,神情自如,任人抚摸打量,显得憨态十足。
行至众多溪流汇聚成的方形池塘边,但见一块刻有“激湍”二字的石头卧于池内,字迹一半浸在水中,一半露出水面。现在雨水不多,没有激流冲刷的石头静如处子。池塘正上方,巍然矗立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四角亭,绿色的“亦兰亭”三字令人心神为之一振,亭柱上的撰联颇有深意:到处有玄机,流水高山随俯仰;此间无俗客,方中野服即神仙。实乃高妙!人一下子仿佛穿越到了远古,去赴一场文人的盛会。
在亦兰亭周围,有斗大的一笔“鹅”奇书和“砥柱”“琴泉”“枕流”“观澜”“流觞”“茂林修竹”等石刻。亦兰亭后方,“惜字社”遗址地基和仅存的几截断墙被妥善保护,可以想象当年名士们雅集的盛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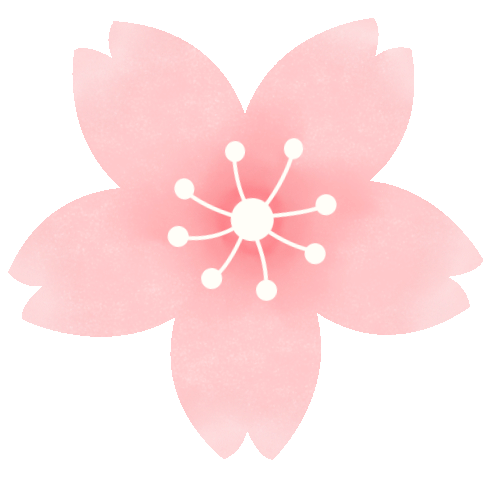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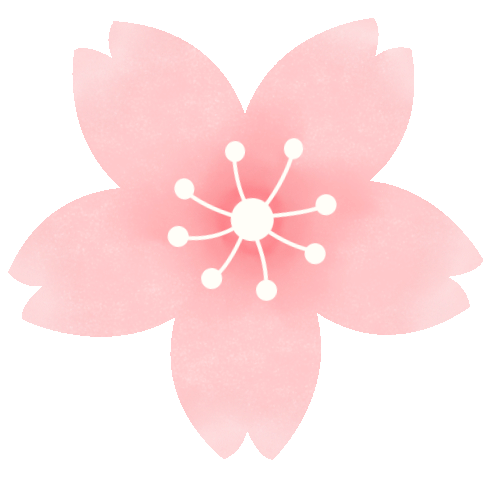
□ 夏太锋
一个双休日,夏周强邀我见面,送我一本广东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新课程理念下的数学教学与评价》。米黄色封面,油墨芳香缠绕鼻尖。轻轻翻开,章节赫然入目。
我与周强是校友,师范毕业后入同一所学校任教,我教语文,周强教数学。
周强任过小学、中学、教师进修学校教师,后评聘为数学高级讲师。年轻时的周强高且单瘦,圆脸,额头宽阔光洁,发际线比普通人高,风流倜傥,英姿勃发。一双深眸常作沉思状,颇有学者风范,后来果然成了小学数学教学领域名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周强从中央团校进修结业归校,担任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同时向学校申请教小学一年级数学。这一届学生为五年制,周强一直教到毕业。其间,周强孜孜矻矻,焚膏继晷,边教学边摸索,寻找规律,积累经验。
一次,我回乡下探望父母,归校几近深夜,校园阒无一人,寂静无声。我俩同住校门口平房,路过廊檐,瞧见周强房里亮着灯,透过窗玻璃望去,办公桌上码着厚厚的作业本和书籍,周强正在挑灯夜战,奋笔疾书,撰写文稿。我至今记得,每周语、数老师轮番辅导学生早自习,轮到周强值日,腋下夹着厚厚的作业本,从宿舍沿着铺了煤渣的跑道前行,肩膀一边下垂一边上耸,走一会下垂的肩膀向上一提,避免作业本掉落。到达教学楼,缓缓爬上三楼,8点准时走进教室,讲解题目,查漏补缺。当年他的住房前有两个高约一米的花坛,红砖浆砌,栽着两棵桂花树。放学后,总有三五个基础较差的学生坐在花坛边做作业。
后来,我们先后离开了学校,周强去了珠海,先后担任珠海市香洲区数学教研员、教师发展中心教研室主任、广东教育学会数学专业委员会理事。特区先进的教学理念、优越的教学条件,为周强搭建了施展才能的舞台。
积沙成塔,集腋成裘。多年的教育教学工作,让周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几年,他在省级以上教育报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教学录像带、教学评价软件、教学光盘各一套。

□ 曾继文
卖酒的女孩
这串号码,被酒洗过
铮亮
像那个卖酒的女孩
银铃般的歌声飘在杯里
她说,酒里有山风
有泥土,有五谷
蜜蜂采的蜜
酿在酒中
我闻到了酒中
天地日月的味道
听到了卖酒女孩
酒窝里盛满的笑声
大雨前的蚂蚁
一只疲惫不堪的蚂蚁
望着天说,明天有大雨
路人说,不怕
我有一把大伞
蚂蚁没有伞
它们要赶紧搬家
从一座山翻到另一座山
寻找一个天晴的家
我们和蚂蚁并没有两样
它们矮小
我们也不高大
都在土地上寻找温暖
一只鸟的祝福
一只鸟,一只干净的鸟
猛然飞过我的头顶
然后飞上电线杆的顶端
每次开车走过前山河大桥
这只鸟总会扇扇翅膀
清脆地叫我几声
我听不懂它说什么
它是不是在说,开慢点
生活不是急来的
窗外
很多年了,窗外的泥土与石头
混杂在一起
光秃秃的
偶尔有群鸟在这玩一会儿
然后又叽叽喳喳飞走
暴雨来了
把窗外的一切冲洗了一遍
一片片凋零的落叶
飘在记忆的风中
远处,一条河
从西往东不停地流
浪花,像白鹭展翅飞翔
月光落在纸上的声音
惊醒了我纸上做梦的词语
这天清晨,太阳还没出来
一阵风推开窗户
石头与泥水间
长出了一片绿草
你提着露珠,向我走来
写给天空
凝眸天空
你把自己交给了一朵白云
树叶上哭泣的小鸟
好想与你唱支悲伤的歌
你一身红裙准备远征
留下昨夜未喝完的半壶酒
雪花悄悄开了
春风在掌心上发芽
两片绿叶重逢
互相说着树的青绿
一个人的念想太小
两个人的念想才是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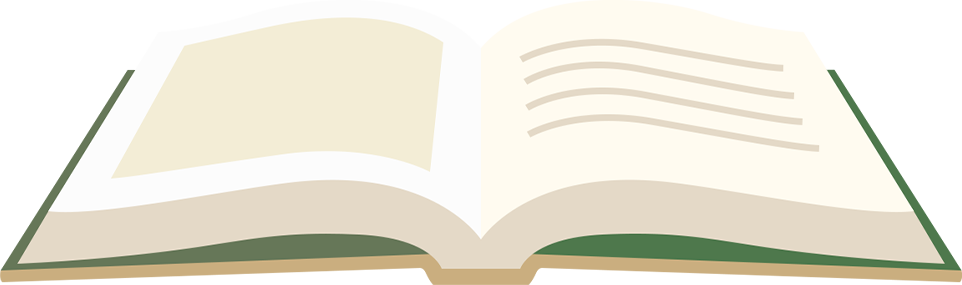
——读方嘉雯《濠涌记忆》
□ 邓翠群
认识方嘉雯老师,源于一次广东散文诗学会组织的采风活动。互加微信后,她说,原来你是我们的资深作者,知你的乡土散文写得很好。虽是一句客套话,但对我来说,是鞭策和鼓励,也证明我们有缘。得知她出了新书,竟有一睹为快的冲动。
掀开扉页,著名作家、书画家刘斯奋先生题写的自然大气、雍容遒健的“濠涌记忆”几字赫然在目。翻阅《濠涌记忆》(全名《濠涌记忆:六百年香山隆都古村的前尘往事》),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油然而生。不仅因它有16开328页(近26万字、200多幅插图)的分量,更因书中记叙的濠涌村有着六百多年历史,厚重悠长。全书分四篇十一章,以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濠涌村方氏家族六百多年历史为主要线索,从姓氏来源、人口迁徙、择地定居、群族关系、繁衍生息、文化遗存、乡音方言、海内名人等方面展开,勾勒出濠涌村数百年的发展历史。
方老师出生在濠涌村,大学毕业后进入报社工作,多年媒体记者、报刊编辑的经历,使她对本地文化有了更多元的视觉。一次她采写的两篇本土文化报道获得中国城市党报新闻奖一等奖。令她意想不到的是,这两份报纸得到海外侨胞的珍藏。侨胞们对乡土历史的珍视,让她萌发了撰写族史的意愿。后来,机缘之下,与当时中山日报社社长方炳焯等人组成工作组,并确立了“跳出村子看村子”的写作定位——从历史的纵深挖掘村庄的故事。
以族氏为中心,把与方氏家族有关的人、事、物勾连起来,四散辐射,等于在窗口里叠加了望远镜,照相机有了广角镜头,视野便豁然开朗。于是,风光旖旎的自然景观,厚重深远的人文历史,寂然无声的古建风物,喧腾热闹的街市景象,以及风味小食、方言俚语、异国风情……如滚滚波涛,奔涌笔端;从香山隆都走出去的方日英、方少穆、方人定、方作标、方宇文等海内外先贤俊彦的身影,一一浮现。
经过十年耕耘,丰富多元、图文并茂的《濠涌记忆》终于得以面世。一部具体而微的族史背后,是恢弘的香山地区甚至是半个岭南的地方史,堪称“以小见大”的典型。
为了呈现真实、客观、全面的族史,她不仅查阅了诸多史料文献,还和工作组成员到实地采访考察,足迹遍布中山市数个镇街、国内多个省市,甚至延伸到国外,那份执着,孜孜以求,只有热爱家乡的人才能做到。例如,她从族谱得知香山的方氏一世祖方道盛是宋度宗长女信安公主的驸马(崖山海战失败后,他带着妻儿逃到新会古冈,后来他的后代迁居沙溪濠涌)后,亲自到崖山海战的遗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官冲村,深入采访和考察,搜集素材。
文采斐然是书的另一亮点。祠堂、庙宇、码头、炮台、古屋、街市、古树等等,成为方老师的精神原乡,她用灵动的笔触深情抒写。
写昔日竹林街景:“大街上一头体型硕大的公猪,一颤一颤地走过,发出‘哼哧哼哧’的喘气声。公猪被牵猪郎一手用绳子牵着,一手提着竹鞭,赶着去打种。”寥寥几笔,勾勒出牵猪郎赶猪去配种的精彩情形。
写故乡景物:“曾经一望无垠的山林,阡陌纵横的田畴沃野,鱼翔浅底的小溪,随风翻滚的稻浪,鸡犬相闻的街巷,蜿蜒曲折的石板街,历史悠久的古建……一帧帧画面,拼成了记忆中的故乡。”字里行间洋溢着浓浓的乡愁。
像这样精妙的语句俯拾皆是,不一一罗列。
美国作家海明威说过:“乡村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灵魂所在。”族史像村志一样,是村的灵魂之书,是乡愁的栖身之所,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通过它,可以感受乡村的脉动,聆听历史的回响,赓续文化的根脉,也为未来的发展汲取智慧和力量。
《濠涌记忆》是我所见到的内容丰富、厚重大气的族史村史杰作,诚如为此书写序的江冰老师所言:“读之亦成精神洗礼。”

-我已经到底线啦-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