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 维
2025-08-04 02:30
施 维
2025-08-04 0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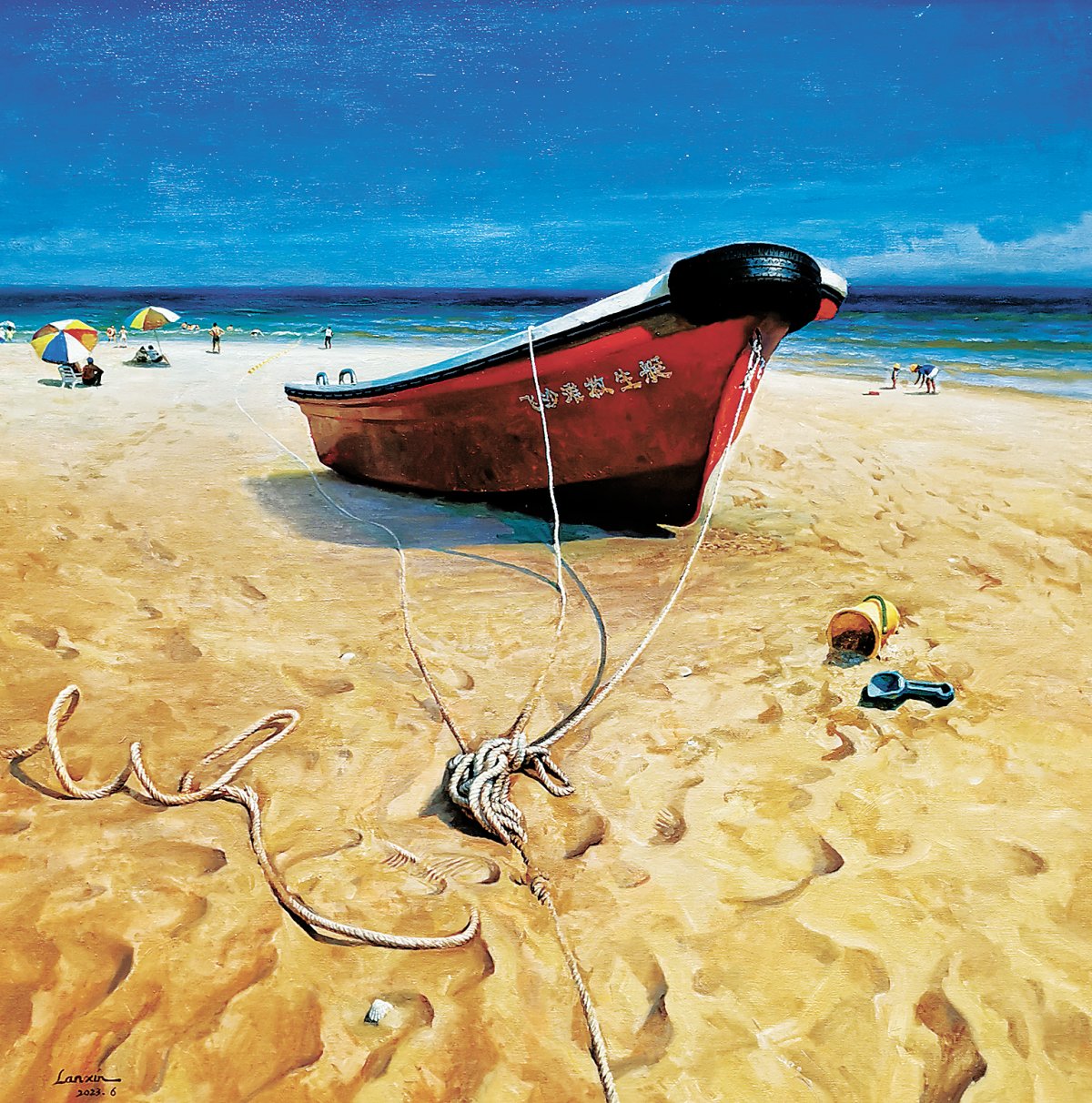
诗人艾青曾说:“诗是人类向未来寄发的信息,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对困境的凝视与对光明的追寻,在罗春柏的诗歌《韦帕》与《记忆》中得到了深刻印证。前者以台风“韦帕”为切口,展开自然暴力对现实世界的撕裂与重构;后者借“记忆”为载体,呈现时间长河中情感碎片的沉淀与反刍。两首诗看似主题迥异,实则共同构建了一个关于“困境”的精神场域,诗人始终以诗意的笔触在黑暗里打捞光的形状,完成对生命韧性的诗性确证。
《韦帕》的开端便以极具冲击力的意象撕开现实的伤口:“挣脱镣铐的狂人/率性地施暴/用铁鞭抽打七月的大地”。这里的“韦帕”已超越台风的自然属性,被赋予“狂人”的人格化特征——“挣脱镣铐”的野性、“率性施暴”的无度、“铁鞭抽打”的暴烈,共同构建出自然力对人类秩序的颠覆图景。诗人将抽象灾难具象化的手法,强化了视觉冲击,更暗示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从“和谐共生”滑向“对抗撕裂”。
诗人并未停留在破坏场景的铺陈,而是以“花园成了废墟”“残垣断壁间”的白描,将灾难的破坏性延伸至空间与人心的双重维度。当“行人驱不散心头惊魂”时,自然暴力已从物理层面渗透到精神领域,形成对生存安全感的根本动摇。诗人以“你”代指所有受灾者,将个体经验升华为群体记忆,在灾难的废墟上立起了生命韧性的坐标。
如果说《韦帕》聚焦自然暴力对现实的冲击,《记忆》则转向时间对情感的侵蚀。诗中“褪色的胶片/在脑海里播放”的开头,以“胶片”这个物质载体隐喻记忆的易逝性——“褪色”“斑驳”“模糊”等修饰词,共同构建出记忆的“雾态”:既非彻底消散,亦非清晰可触,而是以若即若离的姿态存在于意识深处。诗人对记忆质感的精准捕捉,使诗歌一开始便笼罩着温柔的怅惘。
诗人并未沉溺于记忆的模糊性,而是以具体场景的回溯激活情感的温度:“曾在村口的广场/一起放飞风筝/说过的誓言/随风飘向远方”。“村口广场”“风筝”“誓言”等意象,共同勾勒出一段鲜活的过往——广场是公共记忆的场域,风筝是自由与联结的象征,誓言则是情感的契约。然而“随风飘向远方”的转折,将记忆的美好与流失并置,形成情感的张力。
诗的后半段转向对记忆的主动审视:“在时间流水中/寻找你浪迹的远帆/却在涟漪镜面/照见自己的孤单”。“时间流水”的意象呼应“胶片”的流逝感,“寻找远帆”是对记忆的主动打捞,“涟漪镜面”的反射却暴露了“孤单”的本质——当试图在记忆中寻找他人的痕迹时,最终照见的是自我的存在。诗人认知的翻转,将记忆从“对他者的追念”升华为“对自我的观照”。而结尾“摘一朵水花作围巾/擦拭眼睛里的纤尘/原来许多往事/是心空驱不散的浮云”,以“水花作围巾”的诗意动作,完成对记忆的仪式化整理:“擦拭纤尘”是对记忆杂质的过滤,“浮云”的比喻则道破记忆的本质——既非沉重的负累,亦非虚无的幻影,而是心空永恒的存在,以轻盈的姿态参与生命的构成。
从《韦帕》的“寻找晴朗”到《记忆》的“擦拭纤尘”,罗春柏的诗歌完成了一次从外部困境到内部困境、从现实突围到心灵澄明的精神漫游。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是诗人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捕捉,是一个观察者对生命本质的思考——真正的超越,不在于战胜困境,而在于在困境中保持凝视的勇气,让每一道裂痕都成为光照进来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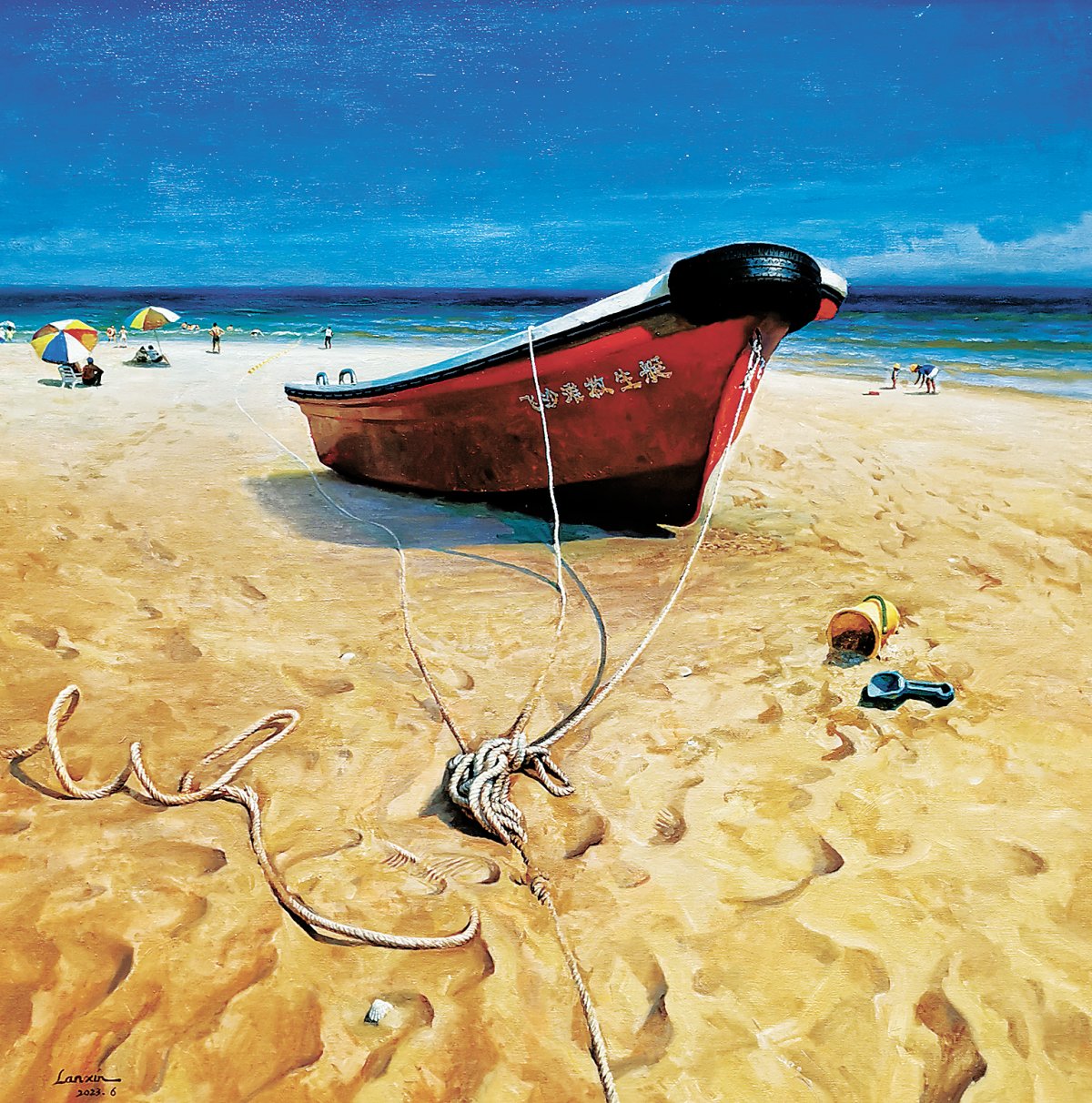
诗人艾青曾说:“诗是人类向未来寄发的信息,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对困境的凝视与对光明的追寻,在罗春柏的诗歌《韦帕》与《记忆》中得到了深刻印证。前者以台风“韦帕”为切口,展开自然暴力对现实世界的撕裂与重构;后者借“记忆”为载体,呈现时间长河中情感碎片的沉淀与反刍。两首诗看似主题迥异,实则共同构建了一个关于“困境”的精神场域,诗人始终以诗意的笔触在黑暗里打捞光的形状,完成对生命韧性的诗性确证。
《韦帕》的开端便以极具冲击力的意象撕开现实的伤口:“挣脱镣铐的狂人/率性地施暴/用铁鞭抽打七月的大地”。这里的“韦帕”已超越台风的自然属性,被赋予“狂人”的人格化特征——“挣脱镣铐”的野性、“率性施暴”的无度、“铁鞭抽打”的暴烈,共同构建出自然力对人类秩序的颠覆图景。诗人将抽象灾难具象化的手法,强化了视觉冲击,更暗示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从“和谐共生”滑向“对抗撕裂”。
诗人并未停留在破坏场景的铺陈,而是以“花园成了废墟”“残垣断壁间”的白描,将灾难的破坏性延伸至空间与人心的双重维度。当“行人驱不散心头惊魂”时,自然暴力已从物理层面渗透到精神领域,形成对生存安全感的根本动摇。诗人以“你”代指所有受灾者,将个体经验升华为群体记忆,在灾难的废墟上立起了生命韧性的坐标。
如果说《韦帕》聚焦自然暴力对现实的冲击,《记忆》则转向时间对情感的侵蚀。诗中“褪色的胶片/在脑海里播放”的开头,以“胶片”这个物质载体隐喻记忆的易逝性——“褪色”“斑驳”“模糊”等修饰词,共同构建出记忆的“雾态”:既非彻底消散,亦非清晰可触,而是以若即若离的姿态存在于意识深处。诗人对记忆质感的精准捕捉,使诗歌一开始便笼罩着温柔的怅惘。
诗人并未沉溺于记忆的模糊性,而是以具体场景的回溯激活情感的温度:“曾在村口的广场/一起放飞风筝/说过的誓言/随风飘向远方”。“村口广场”“风筝”“誓言”等意象,共同勾勒出一段鲜活的过往——广场是公共记忆的场域,风筝是自由与联结的象征,誓言则是情感的契约。然而“随风飘向远方”的转折,将记忆的美好与流失并置,形成情感的张力。
诗的后半段转向对记忆的主动审视:“在时间流水中/寻找你浪迹的远帆/却在涟漪镜面/照见自己的孤单”。“时间流水”的意象呼应“胶片”的流逝感,“寻找远帆”是对记忆的主动打捞,“涟漪镜面”的反射却暴露了“孤单”的本质——当试图在记忆中寻找他人的痕迹时,最终照见的是自我的存在。诗人认知的翻转,将记忆从“对他者的追念”升华为“对自我的观照”。而结尾“摘一朵水花作围巾/擦拭眼睛里的纤尘/原来许多往事/是心空驱不散的浮云”,以“水花作围巾”的诗意动作,完成对记忆的仪式化整理:“擦拭纤尘”是对记忆杂质的过滤,“浮云”的比喻则道破记忆的本质——既非沉重的负累,亦非虚无的幻影,而是心空永恒的存在,以轻盈的姿态参与生命的构成。
从《韦帕》的“寻找晴朗”到《记忆》的“擦拭纤尘”,罗春柏的诗歌完成了一次从外部困境到内部困境、从现实突围到心灵澄明的精神漫游。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是诗人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捕捉,是一个观察者对生命本质的思考——真正的超越,不在于战胜困境,而在于在困境中保持凝视的勇气,让每一道裂痕都成为光照进来的方向。

-我已经到底线啦-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