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的支点
——《忘年四十咏》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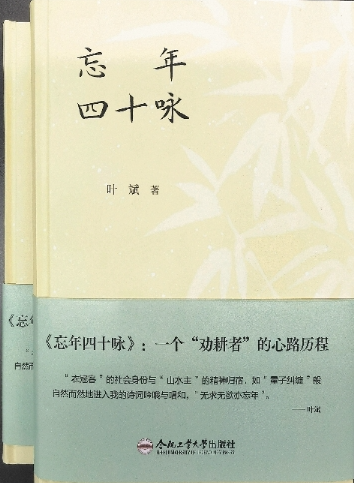
□ 潘 军
叶斌同学《忘年四十咏》即将付梓,嘱我作跋,于是就把我拽到了四十几年前的安徽大学校园。自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这些原本与大学无缘的人得以相继考入,成为当代中国历史巨变的见证者。转眼间,我们又都相继退休了,每每想起,总有一种恍然若梦的感觉。中文系自77级始,至78级、79级,这“新三届”似乎有一个传统——临近退休之际,都会有人自觉投入格律诗词的创作。往下却很罕见。除了安徽大学,我发现省内外的高校中文系大都如此,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格律诗词在当代文化领域日渐式微,而“新三届”的同学却乐此不疲,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叶斌是79级的,晚我一年,在校期间我们虽同住一栋宿舍楼,却从未有过接触。我们的交往也是在退休之际开始的。丁酉年是我的本命年,我离开了生活二十年的京城,回到了故乡安庆。我在长江边上新置一宅,以“泊心堂”作为斋号——这些年走南闯北,我早已厌倦了都市的喧嚣和浮躁,向往的是一份内心的安宁。以前就说过,这一生以六十岁为分界线,之前舞文,之后弄墨,舞文弄墨即我今生的规划。曾有记者问,书画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说:这一刻生命的最佳支点,此一生精神的最后家园。生命是需要支点的,我选择了书画,而叶斌则执着于诗词。我对格律诗词的兴趣,又发端于我的书画创作。中国所谓“文人画”,并非指作者的文人身份,而是一个专有名词,要求的是在一幅画中有诗情,有哲思,有意境,有格调,同时在形式上能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于是作画之余也偶尔填写几首。叶斌便与我有了唱和,这种老式做派看似有悖时尚,却为我所看重。叶斌是“泊心堂”的常客,每次他来安庆,都会来此喝茶畅聊。我去合肥,只要他在,照例也得小聚。这种同学、朋友之间的交往淳朴而美好,让我难忘。正如此一刻,我在东京的寓所里写这篇小文,往昔和叶斌的交往便犹如目下。
收录在《忘年四十咏》的作品,都是叶斌的近作。叶斌对格律诗词的研究很深入,写作也勤奋,近年来所作诗词竟达两千余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公差旅途所得,或触景生情,或怀古咏志,或思念亲朋,或读书心得,不乏精品力作,可圈可点。然而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叶斌的生命找到了一个支点。正是这样的支点,使退而不休的他有更多的时间亲近天地自然、山水田间,俨然一个孤勇行者,一个田园诗人。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便建筑于此,这也是我欣然答应写下这段话的理由。
中国历史上某些艺术门类,如格律诗词,如书法,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后人可以继承,却难以超越。那么,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此呢?不能说只是个人的兴趣爱好,至少,在我看来它必定成为一种情怀的寄托方式,从而体现了一个人的精神气质。它会让你觉得,自己还像一个读书人的样子。格律诗词的妙与难,就在于一种限制。尤其是小令,区区几十个字,却要营造大的格局和美的境界,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挑战。唐诗宋词之所以不朽,就在于前人达到的高度后人难以企及。或许正是这样的一种诱惑,造就了像叶斌这样的追随者。我钦佩他们,更希望叶斌永不停歇地追随下去,保持一个读书人应有的样子。
是为跋。

站在十字路口的长篇小说
□ 曹元勇
在所有文学门类中,长篇小说因其体裁的特殊性,无疑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成就的重要标杆之一。新世纪以来,原创长篇小说已经取得的辉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优秀作家们给这个时代贡献了很多称得上艺术质量上乘、为广大读者喜欢的长篇佳作。然而,随着二十一世纪走过四分之一,随着科技不断革新,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随着读者群体的代际变化和阅读方式的显著转变,随着传统纸质图书市场的逐年萎缩,长篇小说创作如同我们的文学出版一样,走到了一个生态环境格外复杂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十分艰难的抉择。
读者阅读方式、阅读趣味的巨大变化,数字化技术的无情冲击,图书市场的剧烈振荡等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变化无疑都会影响到长篇小说的创作和生产。但是从文学创作的本质来看,决定创作结果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身上。从这个角度观察,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一些作家进行创作的动机和节奏比较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出版市场的需求、各种评奖评优的风向、各种资金扶持项目的召唤,以及读者情绪价值的吁求,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这些作家创作中的重要驱动力。多数出版机构常常把“冲奖夺杯”当作原创文学出版的第一目标,甚至是硬性任务;题材先行、主题先行,以及作家的写作方式是不是现实主义,也都因此成为出版方选择作家作品的重要依据。如果说出版社重视“冲奖夺杯”尚情有可原,那么作家若也把“冲奖夺杯”当作创作的最大目标,就免不了有舍本逐末之嫌。获奖当然可以是作家的梦想之一,但比获奖更重要的还是文学本身,比获奖更值得追求的还是创作出一代代读者喜欢阅读的优秀作品。
大约二十年前,一位旅居美国的华人作家曾经提出“伟大的中国小说”概念。在他看来,“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应当深刻、丰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我们可能不会完全同意这位作家对“伟大的中国小说”内涵的界定,但毫无疑问,每一位有抱负的中国作家都应该怀有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的理想,都应该把追求卓越、攀登高峰作为自己创作的根本遵循。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做到“用写几本书的精力去写一本书”,而不是急功近利地“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去写几本书”。
二、每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可谓成千上万,但是很多作品停留在对种种表象经验的表达,而缺乏对时代生活、历史生活,以及具体人物生活的深层问题、深层冲突、深层真实的挖掘、体悟和表现,缺乏对不同个体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和精神状态的精准刻画,缺乏对不同世界观、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共存与冲突的深刻想象和探究。很多作者急功近利地抢占题材和素材,满足于对所书写对象——人物、事件、社会、地方史——浮光掠影式的观察、了解和认知,而不能真正沉潜到所书写对象的内部,与所书写对象同频共振、产生共情。这种创作状态产生的结果是:作品的语言往往缺乏个性、张力和想象力,作品本身普遍缺乏精神和情感上的感染力,作品的价值和成就也不是体现在艺术上的成熟和创新,而是体现在作品所追踪、所反映的时代素材和表层现实经验上面。实际上,优秀作品的原始素材往往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需要经过作家独具个性和创造力的想象的孕育,才能最终转化为比较理想的创作构思和创作成果。
三、改变和影响人类现代社会生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些因素不仅给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而且潜移默化地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早已习惯、甚至熟视无睹的东西,比如许多领域的科学,比如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技术手段,等等。用阿来先生这几年经常提到的一个观念来说,就是: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科学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创作不应该停滞在传统的人文、伦理、情感经验和个人感知的书写上面,而是应该打破传统文学经验的局限,融入更多科学的维度,对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的科学和技术,对影响和改变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的诸多事物做出回应。在这些方面,长篇小说创作还有非常巨大的空间可以突破,可以探索。国际上已经有作家在这方面做出了成果显著的探索,比如英国作家萨曼莎·哈维描写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遥望地球的小说《轨道》;我们期待着中国作家也能写出同样具有突破性的作品。
四、可能是受根深蒂固的严肃文学观念的束缚,近几年,比较严肃的长篇小说在类型上显得路数单调、不够丰富,写作题材、写作方式、叙事技巧也常常呈现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同质化和雷同化尴尬;许多作家似乎缺乏打破所谓严肃文学与其他类型文学(如科幻小说、犯罪小说、穿越小说等)之间界限和壁垒的勇气,缺乏开拓具有创造性的小说样式的探索精神。这种现象与读者阅读兴趣的多元化之间当然是有矛盾的。在国际上,跨越严肃文学与类型文学界限的杰出作品并不鲜见,杜仑马特、阿特伍德、萨拉马戈、石黑一雄、托卡尔丘克、大卫·米切尔等作家,也都因此而奠定了他们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新世纪以来,随着人工智能的狂飙突进,随着高端科技的不断涌现,随着经济富足带来的两性疏离,文学创作除了探索和表达已知的世界、已知的历史,除了探索和表达具体人的复杂内心与情感世界,也需要关心人类的未来,关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无垠宇宙中的未来。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家也可以解放文学观念,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与具有丰富科学含量的“天问”结合起来,与关于其他社会形态、关于未来世界、关于太空和外太空世界的超越性想象结合起来,从而创作出引领国际文学潮流的新文学样式和新文学精品。
五、任何一部作品在创作完成之后,都会有如何面对读者、面对市场的问题。在“Z时代读者”成为文学阅读主要群体的背景下,作家和专业评论家也需要适应时代变化,更新交流方式,学会与读者面对面,学会在交流中满足读者的情绪价值,进而通过拉近作家个人与读者的关系,来拉近作品与读者的关系。

马勒之悲悯 拉赫之轻盈
□ 桑 子
现场听马勒的艺术歌曲,终于在本届澳门国际音乐节上得偿夙愿。七旬男中音托马斯·汉普森演绎了18首曲目,其中钢琴版《少年魔号》乐谱由他编辑出版(源自马勒原乐谱),并题献给已故的伯恩斯坦。
曾看过一则实况录像:大约是1987年前后,托马斯在金色大厅唱《流浪者之歌》,伯恩斯坦指挥,维也纳爱乐伴奏,三十出头的歌者英姿勃发,却能将一个学徒在爱与伤痛旅途上的挣扎撕裂,唱得哀而不伤、悲而不戚。据说此曲乃马勒“第一次认真恋爱”的自况,由一老一少美国音乐人如此传递,大厅内掌声如潮,是嘉许。
德国艺术歌曲源起19世纪,由贝多芬、舒伯特等开创,融合诗歌与音乐以叙述故事,延续至马勒,则谱出最迷人最特异的一组作品——从童谣、情歌、讽刺到饥馑、战争、死亡;从民歌旋律到舞曲节奏;从简单伴奏到管弦厚重,马勒堪称将德国艺术歌曲从庙堂拽到乡土、从优美滑向怪诞,“爱与伤痛,世界与梦”是其不变的主题,也是其灵魂与艺术的自白。
“我的艺术生涯与马勒的艺术歌曲紧密相连。”此番澳门舞台上的托马斯早已不是那个被大师连声诘问弄得不知所措的毛头小伙,鬓已霜,容颜已改,歌声里的马勒世界多了些从容自信,多了些沧桑况味。
托马斯从1987年开始受伯恩斯坦亲自调教,频繁合作4年,“马勒艺术歌曲”是关键词,“我觉得我对马勒音乐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我对音乐的语言有了新的理解——这是一种讲述着我们生命的语言,它不仅仅是用来演出的,更多的是我们作为人类个体的心灵之旅。这是他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东西。”
不懂德语,并不妨碍现场聆听感受托马斯的马勒,音乐会始末,这句话一直在脑海里打转儿:“我怎么能够幸福,如果在这世界上还有一个生命在受苦。”
本届澳门国际音乐节的重头戏,非“拉赫马拉松”莫属:钢琴大师普莱特涅夫(昵称“普神”)携乐团连续两夜呈现全套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协奏曲。
我的重头是听第三钢琴协奏曲(简称“拉三”)。它采用精彩的华彩、浓密的复调织体、轻快机敏的断音、大量宏大的和弦等钢琴技法,拥有丰富的色彩效果,历来被誉为“钢琴协奏曲之王”。
5年前也是此时、此舞台,王羽佳与维也纳爱乐合作“拉三”,她的演奏的确充满旋风式力量,驾驭多样复杂的钢琴技巧如御龙穿越熊熊火圈,以浓烈的情感表达强悍的俄罗斯精神。
那么,“普神”呢?
一身缁衣软鞋上台,五官绵软松垮、毫无表情,这位68岁俄罗斯老头倒像一个随时逛菜市场的中国老婆婆,毫无“神性”可言。
然而,从他触键那一瞬开始,“拉三”以迥异于他人的方式徐徐展开,拉氏本尊自嘲的“大象之作”忽然变得灵动、轻盈起来,40分钟整曲完结之际,他坐在琴凳上气定神闲,弹“拉三”好比铲十吨煤的趔趄、困顿,于他而言只是一个坊间笑谈。
发音清亮透彻,乐曲行进干净利落,乐句处理细致而不做作,整体结构呈现均衡平稳,演奏有激情但无任何身体夸张,细部处理看似轻触键却千变万化,极为困难的技巧片段在他手下皆翩若惊鸿,优雅非凡。
是的,不温不火的“拉三”,四两拨千斤的“拉三”,颇具20世纪初“黄金时代”钢琴大师遗风的“拉三”!“普神”为此曲勾摹的神性光辉,几度令人恍觉琴前那个隔空对话的身影,与拉氏合二为一。
13岁入莫斯科音乐学院,20岁夺柴赛金奖,被霍洛维茨赞誉“有恶魔技巧和诗人之心”,引领当今俄罗斯钢琴学派,66岁开启“拉赫马拉松”至今……
还有机会见证“普神”的神迹吗?毕竟,真正的令人屏住呼吸等待灵感和奇迹浑然一体的古典音乐现场,几稀矣!

浩瀚历史烟云的诗意撷取
——读蔡新华的《诗话中国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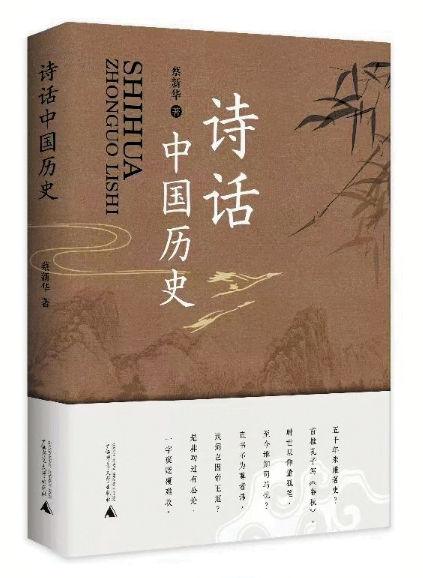
□ 林小兵
在中国史学著作中,以文字铺陈历史的典籍浩如烟海,而蔡新华的《诗话中国历史》则另辟蹊径,以七言古体诗为笔,以历史人事兴衰为墨,在数千年中国时光长卷上勾勒出独特的文化图景。在我看来,这部兼具文学性与知识性的作品,打破了传统史书的刻板叙事,规避了诗歌创作中历史细节的模糊地带,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以诗读史、以史解诗”的窗口。
从内容架构来看,《诗话中国历史》的选材颇具匠心。作者并未贪多求全地覆盖所有的历史节点,而是经过审慎的取舍,选择聚焦100个历史人物、50件历史大事与50项世界遗产,最终形成了“人物-事件-遗产”三位一体的叙事体系。这些遴选对象可以说都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既有商鞅变法、安史之乱等左右历史走向的关键事件,也有孔子、李白、苏轼等贯穿千年的文化先贤,更不乏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等凝结古人智慧的遗产佳构。这种少而精的选材特点,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历史功底,避免了通史类著作广而不深的局限,让读者在有限的篇幅内能够快速把握中国历史核心脉络,堪称一部浓缩版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
七言八句诗体的选择,是本书最鲜明的特色,也是较难驾驭的挑战。正如学者于丹在本书序言中所言:“作诗难,人物诗传更难,以诗记史尤难。”历史诗歌创作的困境在于,不光要遵守“平仄协调、对仗工整”的格律要求,还要在短短八句之内承载复杂的历史信息。我们欣喜地看到,蔡新华在书中将这种“难”,化为了自己作品的亮点:写孔子“杏坛讲学传儒道,列国周游觅大同”,以简练诗句概括其一生核心事迹;吟咏长城“万里长龙横塞北,千年雄魄镇边关”,用生动意象展现其雄伟气势,以精准的笔触勾勒出文化遗产的精髓。尽管从传统格律的角度来看,这些诗句的平仄仍有推敲进步的空间,但我宁愿理解为这是作者不去因律害意而折中为之的手法。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并未止步于单纯的历史诗歌创作,而是为每首诗配上了翔实的史料注解。这些少则数百字、多则近千字的注解,既是对诗歌内容的补充,也是对历史背景的延伸。作者解读商鞅变法时,不仅说明变法的具体措施,还分析其对秦国统一六国的深远影响;在介绍苏轼时,既提及他的文学成就,也兼顾其仕途起伏与人生态度;描述苏州园林时,既讲解造园艺术的特点,也追溯其历史演变与文化内涵。这种“诗+注”的形式,很好地平衡了作品的可读性与普及性,让那些即使是对历史了解不多的普通读者,也能借助注解理解到诗歌背后的历史逻辑,达到“在吟诵中感知历史,在解读中读懂文化”的效果。
纵览全书,作者蔡新华对历史文化的赤诚之心跃然纸上。就像书中所述,“这部作品是超越功利的发心,是忠于内心兴趣的事情”,这种治学为人的态度,让全书褪去了学术著作的晦涩与商业书籍的浮躁,多了一份文人的纯粹坚守。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许多人对历史认知只停留在碎片化的信息片段中,而《诗话中国历史》以诗为介,让浩瀚的历史烟云由此而变得可感、可读、可记。一册读完,我最大的感受是,在浓浓诗意中感受到了历史的壮阔,在翔实的注解中触摸到了文化的细节。
对于想要快速了解中国历史的读者或是诗歌与传统文化的爱好者,《诗话中国历史》不失为值得一读的一部佳作。蔡新华诗意撷取浩瀚历史烟云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历史从未远离我们,当它与诗歌相遇,便能在新时代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纽带。

生命的支点
——《忘年四十咏》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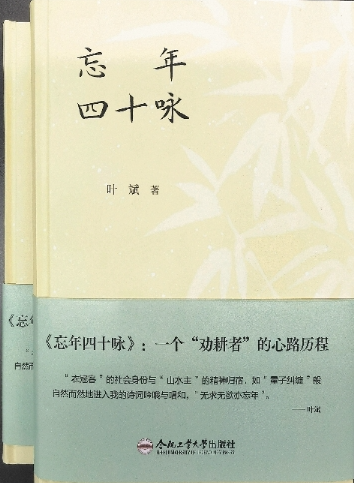
□ 潘 军
叶斌同学《忘年四十咏》即将付梓,嘱我作跋,于是就把我拽到了四十几年前的安徽大学校园。自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这些原本与大学无缘的人得以相继考入,成为当代中国历史巨变的见证者。转眼间,我们又都相继退休了,每每想起,总有一种恍然若梦的感觉。中文系自77级始,至78级、79级,这“新三届”似乎有一个传统——临近退休之际,都会有人自觉投入格律诗词的创作。往下却很罕见。除了安徽大学,我发现省内外的高校中文系大都如此,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格律诗词在当代文化领域日渐式微,而“新三届”的同学却乐此不疲,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叶斌是79级的,晚我一年,在校期间我们虽同住一栋宿舍楼,却从未有过接触。我们的交往也是在退休之际开始的。丁酉年是我的本命年,我离开了生活二十年的京城,回到了故乡安庆。我在长江边上新置一宅,以“泊心堂”作为斋号——这些年走南闯北,我早已厌倦了都市的喧嚣和浮躁,向往的是一份内心的安宁。以前就说过,这一生以六十岁为分界线,之前舞文,之后弄墨,舞文弄墨即我今生的规划。曾有记者问,书画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说:这一刻生命的最佳支点,此一生精神的最后家园。生命是需要支点的,我选择了书画,而叶斌则执着于诗词。我对格律诗词的兴趣,又发端于我的书画创作。中国所谓“文人画”,并非指作者的文人身份,而是一个专有名词,要求的是在一幅画中有诗情,有哲思,有意境,有格调,同时在形式上能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于是作画之余也偶尔填写几首。叶斌便与我有了唱和,这种老式做派看似有悖时尚,却为我所看重。叶斌是“泊心堂”的常客,每次他来安庆,都会来此喝茶畅聊。我去合肥,只要他在,照例也得小聚。这种同学、朋友之间的交往淳朴而美好,让我难忘。正如此一刻,我在东京的寓所里写这篇小文,往昔和叶斌的交往便犹如目下。
收录在《忘年四十咏》的作品,都是叶斌的近作。叶斌对格律诗词的研究很深入,写作也勤奋,近年来所作诗词竟达两千余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公差旅途所得,或触景生情,或怀古咏志,或思念亲朋,或读书心得,不乏精品力作,可圈可点。然而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叶斌的生命找到了一个支点。正是这样的支点,使退而不休的他有更多的时间亲近天地自然、山水田间,俨然一个孤勇行者,一个田园诗人。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便建筑于此,这也是我欣然答应写下这段话的理由。
中国历史上某些艺术门类,如格律诗词,如书法,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后人可以继承,却难以超越。那么,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此呢?不能说只是个人的兴趣爱好,至少,在我看来它必定成为一种情怀的寄托方式,从而体现了一个人的精神气质。它会让你觉得,自己还像一个读书人的样子。格律诗词的妙与难,就在于一种限制。尤其是小令,区区几十个字,却要营造大的格局和美的境界,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挑战。唐诗宋词之所以不朽,就在于前人达到的高度后人难以企及。或许正是这样的一种诱惑,造就了像叶斌这样的追随者。我钦佩他们,更希望叶斌永不停歇地追随下去,保持一个读书人应有的样子。
是为跋。

站在十字路口的长篇小说
□ 曹元勇
在所有文学门类中,长篇小说因其体裁的特殊性,无疑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成就的重要标杆之一。新世纪以来,原创长篇小说已经取得的辉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优秀作家们给这个时代贡献了很多称得上艺术质量上乘、为广大读者喜欢的长篇佳作。然而,随着二十一世纪走过四分之一,随着科技不断革新,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随着读者群体的代际变化和阅读方式的显著转变,随着传统纸质图书市场的逐年萎缩,长篇小说创作如同我们的文学出版一样,走到了一个生态环境格外复杂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十分艰难的抉择。
读者阅读方式、阅读趣味的巨大变化,数字化技术的无情冲击,图书市场的剧烈振荡等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变化无疑都会影响到长篇小说的创作和生产。但是从文学创作的本质来看,决定创作结果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身上。从这个角度观察,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一些作家进行创作的动机和节奏比较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出版市场的需求、各种评奖评优的风向、各种资金扶持项目的召唤,以及读者情绪价值的吁求,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这些作家创作中的重要驱动力。多数出版机构常常把“冲奖夺杯”当作原创文学出版的第一目标,甚至是硬性任务;题材先行、主题先行,以及作家的写作方式是不是现实主义,也都因此成为出版方选择作家作品的重要依据。如果说出版社重视“冲奖夺杯”尚情有可原,那么作家若也把“冲奖夺杯”当作创作的最大目标,就免不了有舍本逐末之嫌。获奖当然可以是作家的梦想之一,但比获奖更重要的还是文学本身,比获奖更值得追求的还是创作出一代代读者喜欢阅读的优秀作品。
大约二十年前,一位旅居美国的华人作家曾经提出“伟大的中国小说”概念。在他看来,“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应当深刻、丰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我们可能不会完全同意这位作家对“伟大的中国小说”内涵的界定,但毫无疑问,每一位有抱负的中国作家都应该怀有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的理想,都应该把追求卓越、攀登高峰作为自己创作的根本遵循。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做到“用写几本书的精力去写一本书”,而不是急功近利地“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去写几本书”。
二、每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可谓成千上万,但是很多作品停留在对种种表象经验的表达,而缺乏对时代生活、历史生活,以及具体人物生活的深层问题、深层冲突、深层真实的挖掘、体悟和表现,缺乏对不同个体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和精神状态的精准刻画,缺乏对不同世界观、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共存与冲突的深刻想象和探究。很多作者急功近利地抢占题材和素材,满足于对所书写对象——人物、事件、社会、地方史——浮光掠影式的观察、了解和认知,而不能真正沉潜到所书写对象的内部,与所书写对象同频共振、产生共情。这种创作状态产生的结果是:作品的语言往往缺乏个性、张力和想象力,作品本身普遍缺乏精神和情感上的感染力,作品的价值和成就也不是体现在艺术上的成熟和创新,而是体现在作品所追踪、所反映的时代素材和表层现实经验上面。实际上,优秀作品的原始素材往往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需要经过作家独具个性和创造力的想象的孕育,才能最终转化为比较理想的创作构思和创作成果。
三、改变和影响人类现代社会生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些因素不仅给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而且潜移默化地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早已习惯、甚至熟视无睹的东西,比如许多领域的科学,比如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技术手段,等等。用阿来先生这几年经常提到的一个观念来说,就是: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科学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创作不应该停滞在传统的人文、伦理、情感经验和个人感知的书写上面,而是应该打破传统文学经验的局限,融入更多科学的维度,对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的科学和技术,对影响和改变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的诸多事物做出回应。在这些方面,长篇小说创作还有非常巨大的空间可以突破,可以探索。国际上已经有作家在这方面做出了成果显著的探索,比如英国作家萨曼莎·哈维描写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遥望地球的小说《轨道》;我们期待着中国作家也能写出同样具有突破性的作品。
四、可能是受根深蒂固的严肃文学观念的束缚,近几年,比较严肃的长篇小说在类型上显得路数单调、不够丰富,写作题材、写作方式、叙事技巧也常常呈现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同质化和雷同化尴尬;许多作家似乎缺乏打破所谓严肃文学与其他类型文学(如科幻小说、犯罪小说、穿越小说等)之间界限和壁垒的勇气,缺乏开拓具有创造性的小说样式的探索精神。这种现象与读者阅读兴趣的多元化之间当然是有矛盾的。在国际上,跨越严肃文学与类型文学界限的杰出作品并不鲜见,杜仑马特、阿特伍德、萨拉马戈、石黑一雄、托卡尔丘克、大卫·米切尔等作家,也都因此而奠定了他们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新世纪以来,随着人工智能的狂飙突进,随着高端科技的不断涌现,随着经济富足带来的两性疏离,文学创作除了探索和表达已知的世界、已知的历史,除了探索和表达具体人的复杂内心与情感世界,也需要关心人类的未来,关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无垠宇宙中的未来。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家也可以解放文学观念,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与具有丰富科学含量的“天问”结合起来,与关于其他社会形态、关于未来世界、关于太空和外太空世界的超越性想象结合起来,从而创作出引领国际文学潮流的新文学样式和新文学精品。
五、任何一部作品在创作完成之后,都会有如何面对读者、面对市场的问题。在“Z时代读者”成为文学阅读主要群体的背景下,作家和专业评论家也需要适应时代变化,更新交流方式,学会与读者面对面,学会在交流中满足读者的情绪价值,进而通过拉近作家个人与读者的关系,来拉近作品与读者的关系。

马勒之悲悯 拉赫之轻盈
□ 桑 子
现场听马勒的艺术歌曲,终于在本届澳门国际音乐节上得偿夙愿。七旬男中音托马斯·汉普森演绎了18首曲目,其中钢琴版《少年魔号》乐谱由他编辑出版(源自马勒原乐谱),并题献给已故的伯恩斯坦。
曾看过一则实况录像:大约是1987年前后,托马斯在金色大厅唱《流浪者之歌》,伯恩斯坦指挥,维也纳爱乐伴奏,三十出头的歌者英姿勃发,却能将一个学徒在爱与伤痛旅途上的挣扎撕裂,唱得哀而不伤、悲而不戚。据说此曲乃马勒“第一次认真恋爱”的自况,由一老一少美国音乐人如此传递,大厅内掌声如潮,是嘉许。
德国艺术歌曲源起19世纪,由贝多芬、舒伯特等开创,融合诗歌与音乐以叙述故事,延续至马勒,则谱出最迷人最特异的一组作品——从童谣、情歌、讽刺到饥馑、战争、死亡;从民歌旋律到舞曲节奏;从简单伴奏到管弦厚重,马勒堪称将德国艺术歌曲从庙堂拽到乡土、从优美滑向怪诞,“爱与伤痛,世界与梦”是其不变的主题,也是其灵魂与艺术的自白。
“我的艺术生涯与马勒的艺术歌曲紧密相连。”此番澳门舞台上的托马斯早已不是那个被大师连声诘问弄得不知所措的毛头小伙,鬓已霜,容颜已改,歌声里的马勒世界多了些从容自信,多了些沧桑况味。
托马斯从1987年开始受伯恩斯坦亲自调教,频繁合作4年,“马勒艺术歌曲”是关键词,“我觉得我对马勒音乐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我对音乐的语言有了新的理解——这是一种讲述着我们生命的语言,它不仅仅是用来演出的,更多的是我们作为人类个体的心灵之旅。这是他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东西。”
不懂德语,并不妨碍现场聆听感受托马斯的马勒,音乐会始末,这句话一直在脑海里打转儿:“我怎么能够幸福,如果在这世界上还有一个生命在受苦。”
本届澳门国际音乐节的重头戏,非“拉赫马拉松”莫属:钢琴大师普莱特涅夫(昵称“普神”)携乐团连续两夜呈现全套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协奏曲。
我的重头是听第三钢琴协奏曲(简称“拉三”)。它采用精彩的华彩、浓密的复调织体、轻快机敏的断音、大量宏大的和弦等钢琴技法,拥有丰富的色彩效果,历来被誉为“钢琴协奏曲之王”。
5年前也是此时、此舞台,王羽佳与维也纳爱乐合作“拉三”,她的演奏的确充满旋风式力量,驾驭多样复杂的钢琴技巧如御龙穿越熊熊火圈,以浓烈的情感表达强悍的俄罗斯精神。
那么,“普神”呢?
一身缁衣软鞋上台,五官绵软松垮、毫无表情,这位68岁俄罗斯老头倒像一个随时逛菜市场的中国老婆婆,毫无“神性”可言。
然而,从他触键那一瞬开始,“拉三”以迥异于他人的方式徐徐展开,拉氏本尊自嘲的“大象之作”忽然变得灵动、轻盈起来,40分钟整曲完结之际,他坐在琴凳上气定神闲,弹“拉三”好比铲十吨煤的趔趄、困顿,于他而言只是一个坊间笑谈。
发音清亮透彻,乐曲行进干净利落,乐句处理细致而不做作,整体结构呈现均衡平稳,演奏有激情但无任何身体夸张,细部处理看似轻触键却千变万化,极为困难的技巧片段在他手下皆翩若惊鸿,优雅非凡。
是的,不温不火的“拉三”,四两拨千斤的“拉三”,颇具20世纪初“黄金时代”钢琴大师遗风的“拉三”!“普神”为此曲勾摹的神性光辉,几度令人恍觉琴前那个隔空对话的身影,与拉氏合二为一。
13岁入莫斯科音乐学院,20岁夺柴赛金奖,被霍洛维茨赞誉“有恶魔技巧和诗人之心”,引领当今俄罗斯钢琴学派,66岁开启“拉赫马拉松”至今……
还有机会见证“普神”的神迹吗?毕竟,真正的令人屏住呼吸等待灵感和奇迹浑然一体的古典音乐现场,几稀矣!

浩瀚历史烟云的诗意撷取
——读蔡新华的《诗话中国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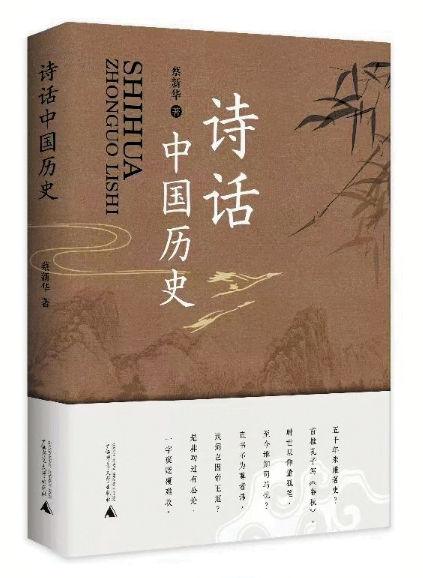
□ 林小兵
在中国史学著作中,以文字铺陈历史的典籍浩如烟海,而蔡新华的《诗话中国历史》则另辟蹊径,以七言古体诗为笔,以历史人事兴衰为墨,在数千年中国时光长卷上勾勒出独特的文化图景。在我看来,这部兼具文学性与知识性的作品,打破了传统史书的刻板叙事,规避了诗歌创作中历史细节的模糊地带,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以诗读史、以史解诗”的窗口。
从内容架构来看,《诗话中国历史》的选材颇具匠心。作者并未贪多求全地覆盖所有的历史节点,而是经过审慎的取舍,选择聚焦100个历史人物、50件历史大事与50项世界遗产,最终形成了“人物-事件-遗产”三位一体的叙事体系。这些遴选对象可以说都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既有商鞅变法、安史之乱等左右历史走向的关键事件,也有孔子、李白、苏轼等贯穿千年的文化先贤,更不乏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等凝结古人智慧的遗产佳构。这种少而精的选材特点,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历史功底,避免了通史类著作广而不深的局限,让读者在有限的篇幅内能够快速把握中国历史核心脉络,堪称一部浓缩版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
七言八句诗体的选择,是本书最鲜明的特色,也是较难驾驭的挑战。正如学者于丹在本书序言中所言:“作诗难,人物诗传更难,以诗记史尤难。”历史诗歌创作的困境在于,不光要遵守“平仄协调、对仗工整”的格律要求,还要在短短八句之内承载复杂的历史信息。我们欣喜地看到,蔡新华在书中将这种“难”,化为了自己作品的亮点:写孔子“杏坛讲学传儒道,列国周游觅大同”,以简练诗句概括其一生核心事迹;吟咏长城“万里长龙横塞北,千年雄魄镇边关”,用生动意象展现其雄伟气势,以精准的笔触勾勒出文化遗产的精髓。尽管从传统格律的角度来看,这些诗句的平仄仍有推敲进步的空间,但我宁愿理解为这是作者不去因律害意而折中为之的手法。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并未止步于单纯的历史诗歌创作,而是为每首诗配上了翔实的史料注解。这些少则数百字、多则近千字的注解,既是对诗歌内容的补充,也是对历史背景的延伸。作者解读商鞅变法时,不仅说明变法的具体措施,还分析其对秦国统一六国的深远影响;在介绍苏轼时,既提及他的文学成就,也兼顾其仕途起伏与人生态度;描述苏州园林时,既讲解造园艺术的特点,也追溯其历史演变与文化内涵。这种“诗+注”的形式,很好地平衡了作品的可读性与普及性,让那些即使是对历史了解不多的普通读者,也能借助注解理解到诗歌背后的历史逻辑,达到“在吟诵中感知历史,在解读中读懂文化”的效果。
纵览全书,作者蔡新华对历史文化的赤诚之心跃然纸上。就像书中所述,“这部作品是超越功利的发心,是忠于内心兴趣的事情”,这种治学为人的态度,让全书褪去了学术著作的晦涩与商业书籍的浮躁,多了一份文人的纯粹坚守。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许多人对历史认知只停留在碎片化的信息片段中,而《诗话中国历史》以诗为介,让浩瀚的历史烟云由此而变得可感、可读、可记。一册读完,我最大的感受是,在浓浓诗意中感受到了历史的壮阔,在翔实的注解中触摸到了文化的细节。
对于想要快速了解中国历史的读者或是诗歌与传统文化的爱好者,《诗话中国历史》不失为值得一读的一部佳作。蔡新华诗意撷取浩瀚历史烟云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历史从未远离我们,当它与诗歌相遇,便能在新时代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纽带。

-我已经到底线啦-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