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 军
2025-11-24 01:56
潘 军
2025-11-24 0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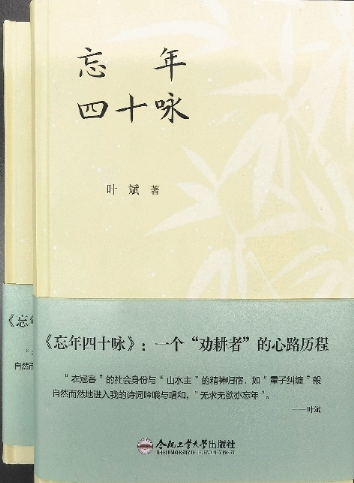
叶斌同学《忘年四十咏》即将付梓,嘱我作跋,于是就把我拽到了四十几年前的安徽大学校园。自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这些原本与大学无缘的人得以相继考入,成为当代中国历史巨变的见证者。转眼间,我们又都相继退休了,每每想起,总有一种恍然若梦的感觉。中文系自77级始,至78级、79级,这“新三届”似乎有一个传统——临近退休之际,都会有人自觉投入格律诗词的创作。往下却很罕见。除了安徽大学,我发现省内外的高校中文系大都如此,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格律诗词在当代文化领域日渐式微,而“新三届”的同学却乐此不疲,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叶斌是79级的,晚我一年,在校期间我们虽同住一栋宿舍楼,却从未有过接触。我们的交往也是在退休之际开始的。丁酉年是我的本命年,我离开了生活二十年的京城,回到了故乡安庆。我在长江边上新置一宅,以“泊心堂”作为斋号——这些年走南闯北,我早已厌倦了都市的喧嚣和浮躁,向往的是一份内心的安宁。以前就说过,这一生以六十岁为分界线,之前舞文,之后弄墨,舞文弄墨即我今生的规划。曾有记者问,书画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说:这一刻生命的最佳支点,此一生精神的最后家园。生命是需要支点的,我选择了书画,而叶斌则执着于诗词。我对格律诗词的兴趣,又发端于我的书画创作。中国所谓“文人画”,并非指作者的文人身份,而是一个专有名词,要求的是在一幅画中有诗情,有哲思,有意境,有格调,同时在形式上能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于是作画之余也偶尔填写几首。叶斌便与我有了唱和,这种老式做派看似有悖时尚,却为我所看重。叶斌是“泊心堂”的常客,每次他来安庆,都会来此喝茶畅聊。我去合肥,只要他在,照例也得小聚。这种同学、朋友之间的交往淳朴而美好,让我难忘。正如此一刻,我在东京的寓所里写这篇小文,往昔和叶斌的交往便犹如目下。
收录在《忘年四十咏》的作品,都是叶斌的近作。叶斌对格律诗词的研究很深入,写作也勤奋,近年来所作诗词竟达两千余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公差旅途所得,或触景生情,或怀古咏志,或思念亲朋,或读书心得,不乏精品力作,可圈可点。然而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叶斌的生命找到了一个支点。正是这样的支点,使退而不休的他有更多的时间亲近天地自然、山水田间,俨然一个孤勇行者,一个田园诗人。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便建筑于此,这也是我欣然答应写下这段话的理由。
中国历史上某些艺术门类,如格律诗词,如书法,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后人可以继承,却难以超越。那么,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此呢?不能说只是个人的兴趣爱好,至少,在我看来它必定成为一种情怀的寄托方式,从而体现了一个人的精神气质。它会让你觉得,自己还像一个读书人的样子。格律诗词的妙与难,就在于一种限制。尤其是小令,区区几十个字,却要营造大的格局和美的境界,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挑战。唐诗宋词之所以不朽,就在于前人达到的高度后人难以企及。或许正是这样的一种诱惑,造就了像叶斌这样的追随者。我钦佩他们,更希望叶斌永不停歇地追随下去,保持一个读书人应有的样子。
是为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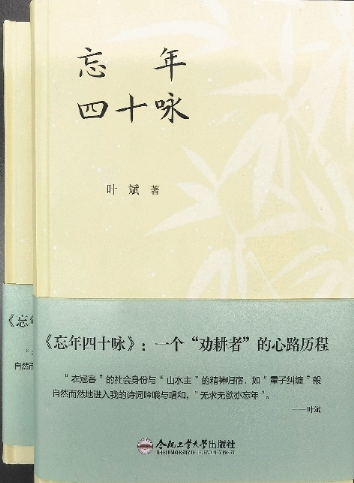
叶斌同学《忘年四十咏》即将付梓,嘱我作跋,于是就把我拽到了四十几年前的安徽大学校园。自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这些原本与大学无缘的人得以相继考入,成为当代中国历史巨变的见证者。转眼间,我们又都相继退休了,每每想起,总有一种恍然若梦的感觉。中文系自77级始,至78级、79级,这“新三届”似乎有一个传统——临近退休之际,都会有人自觉投入格律诗词的创作。往下却很罕见。除了安徽大学,我发现省内外的高校中文系大都如此,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格律诗词在当代文化领域日渐式微,而“新三届”的同学却乐此不疲,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叶斌是79级的,晚我一年,在校期间我们虽同住一栋宿舍楼,却从未有过接触。我们的交往也是在退休之际开始的。丁酉年是我的本命年,我离开了生活二十年的京城,回到了故乡安庆。我在长江边上新置一宅,以“泊心堂”作为斋号——这些年走南闯北,我早已厌倦了都市的喧嚣和浮躁,向往的是一份内心的安宁。以前就说过,这一生以六十岁为分界线,之前舞文,之后弄墨,舞文弄墨即我今生的规划。曾有记者问,书画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说:这一刻生命的最佳支点,此一生精神的最后家园。生命是需要支点的,我选择了书画,而叶斌则执着于诗词。我对格律诗词的兴趣,又发端于我的书画创作。中国所谓“文人画”,并非指作者的文人身份,而是一个专有名词,要求的是在一幅画中有诗情,有哲思,有意境,有格调,同时在形式上能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于是作画之余也偶尔填写几首。叶斌便与我有了唱和,这种老式做派看似有悖时尚,却为我所看重。叶斌是“泊心堂”的常客,每次他来安庆,都会来此喝茶畅聊。我去合肥,只要他在,照例也得小聚。这种同学、朋友之间的交往淳朴而美好,让我难忘。正如此一刻,我在东京的寓所里写这篇小文,往昔和叶斌的交往便犹如目下。
收录在《忘年四十咏》的作品,都是叶斌的近作。叶斌对格律诗词的研究很深入,写作也勤奋,近年来所作诗词竟达两千余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公差旅途所得,或触景生情,或怀古咏志,或思念亲朋,或读书心得,不乏精品力作,可圈可点。然而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叶斌的生命找到了一个支点。正是这样的支点,使退而不休的他有更多的时间亲近天地自然、山水田间,俨然一个孤勇行者,一个田园诗人。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便建筑于此,这也是我欣然答应写下这段话的理由。
中国历史上某些艺术门类,如格律诗词,如书法,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后人可以继承,却难以超越。那么,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此呢?不能说只是个人的兴趣爱好,至少,在我看来它必定成为一种情怀的寄托方式,从而体现了一个人的精神气质。它会让你觉得,自己还像一个读书人的样子。格律诗词的妙与难,就在于一种限制。尤其是小令,区区几十个字,却要营造大的格局和美的境界,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挑战。唐诗宋词之所以不朽,就在于前人达到的高度后人难以企及。或许正是这样的一种诱惑,造就了像叶斌这样的追随者。我钦佩他们,更希望叶斌永不停歇地追随下去,保持一个读书人应有的样子。
是为跋。

-我已经到底线啦-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