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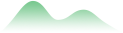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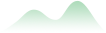
□ 余丛
深秋时节,收到友人育邦从南京寄来最新出版的诗集,叫《草木深》。每天清晨,我便带着他的书散步于仙湖植物园内,一边读一边感受诗中的意境。特别是途经弘法寺时,刚好读到《光孝寺之路》诗中的“晨光熹微,我便起身/拾起这片树叶/忘却那棵树/就像轻轻提起自己冒昧的一生”,那也是格外应景。南方的秋天,草木并未萧条,反而越发郁郁葱葱,我也人过中年,内心的荒芜与落寞,仿佛在“草木深”处获得无尽慰藉。
与育邦的交往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南京渡江纪念馆任职的时候,后来又从《青春》杂志社调到《雨花》杂志社,转眼间已经二十余年。我们既是来往密切的诗友,又是来自苏北连云港的同乡,我比他虚长几岁,在学养上他却是让我仰视的读书人。他博览群书,总是先人一步;他视野开阔,对世界文学更是如数家珍。近年来,育邦还专门写过两部这方面的著作,一部叫《从乔伊斯到马尔克斯》,另一部书叫《从海明威到昆德拉》,光看书名就已经令人瞠目结舌,敬佩不已。
言归正传,回到《草木深》这部诗集,作为“70后”代表诗人之一的育邦,显然已形成自己清新典雅而意象超拔的诗歌面目。写诗至今,育邦陆续出版了诗集《忆故人》《伐桐》《止酒》《归来》,一路走来对诗的探索从未止步,他用一支深刻而敏感的笔,写下了许多意味深长的名篇佳作。通读可见,育邦的诗无论是抒情言志,还是行吟唱和,内容上大致分为应景和怀古两类。看似触景生情的自然人文,如《司空山》《白鹭洲》《过元好问墓》等,却处处尽显灵魂游走的痕迹;看似托物感怀的凭吊怀古,如《晨起读苏轼》《空亭——为倪云林而作》《豹隐——读陈寅恪先生》等,却在重构内心深处的精神家园。他以现代人的情怀,或眺望于山水之间,或照会于前人古迹,或深思于现实处境,始终是诗带给他生命的一份天真和自如。
育邦的诗歌,简洁节制,不见晦涩繁复;含蓄凝练,又别具寓意。细细品味,常给人一种虚实相间的直觉,尤其是《我认出了我的父亲》《寂静邮局》《对饮》《止酒》等常被提及的诸多诗作,似梦非梦,又真实可感。诗中看似有我,却不像似我,看似无我,我又在其中。只不过,后一个我已非前一个我,好像将诗外的我邀请入内。其实,这就是育邦的高明之处,他能将所见所闻的感悟,通过想象和虚构,以化境之笔,写出情韵兼至的文采。貌似通过语言、形象和节奏的层层叠进而浑然天成,其实是作者本自俱足的技艺、智识和远见的融会贯通所得。每一首诗成形前被一再修剪,仿若诗人的情感、信仰和执念的枝条,而言语的贫乏造就了诗意心声,并以此回应一个时代的精神困境。
在汉语的一招一式中,育邦正在创造自己的诗歌范式,那是接驳传统的古典韵味又在拓展现代诗性边界的一条诗学道路。当“草木深”这一意象在为一部诗集命名时,自然的时序也随之更替,而这一切似乎也在为汉语新诗实践着新的可能。育邦说:“有了草木葳蕤,世界才充满生机。”显然,诗人就是“草木深”处捕捉诗意的猎手,时刻准备语言长矛的猛然一击,将四处逃窜的诗歌灵兽捉拿归案。我想,育邦的理想也莫过于成为这样的猎手,不过他潜伏于人间的“草木”丛林,却将入世的修行和出世的智慧置入文字的庇护之所。正如他在诗中所言:“在汉语中,我安下一座隐秘的家……不可言说的/皆密封于塔,深埋于地”。
落笔至此,我想说出那不经意间诗人的平常之处,或更能体现他的心性喜好,而这在他的诗中已不成为秘密。育邦有一首诗叫《庄子,或维特根斯坦》,我以为这就是混合在育邦身上的“气质”,有时候他是庄子,有时候他是维特根斯坦,有时候又游离于二者之间。而那个真实的育邦,就在诗集《草木深》中蛰居,就在他未来诗篇里渐次隐身,他将始终是人群中的众人,却又是自我的异类。
(《草木深》育邦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5年9月版)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读凸凹非虚构作品《龙泉山传》

□ 盛红
作家凸凹非虚构作品《龙泉山传》用82.5万字的体量,讲述龙泉山脉的前世今生。对这部沉甸甸的大书,我需要用虔诚的双手才能用力捧起,而更多的人则用一个又一个的转发与传递来表达他们的喜欢和在意。正如凸凹在后记中所写:“对于这条从没人首尾拉通写过的山,我的难度是,如何于有限的时间,只用几十万字的文学性体量,将一切尽数拿下,而又有几分意思至少读得下去……”于是,“顺应山脉的生发、结构、组织与衍变,《龙泉山传》跟着有了总述、侧重、专题和分述的架构,具体则由‘我叫龙泉山’‘主峰’‘中段’‘北段’和‘南段’五个区间作背书式呈现。实操为让一些事体呈线性集束,跋山涉水在山脉的时间轴上;让一些事体呈非线性发散,团身聚合于山脉之区块界域。”
这既是作者构思上的巧妙又绝非取巧,如果没有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文字驾驭能力,没有凸凹自20世纪90年代初落脚龙泉驿后,一直不断地对这方地域的调查、研究、走访以及书写,尤其是深深的热爱和全身心的付出,哪有此刻的巧思和妙笔?也正是这无处不在的巧妙布局和拆分,才将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龙泉山拉网式地全景呈现在读者面前,才有机会让以为熟悉此山的人得以重新认识它,让不熟悉此山的人了解它爱上它,让一座看似无名却早已有名的山,不只有桃花的妖艳,农家乐的偷闲,更有今日城市森林公园的无限生机,以及你未曾看见的延伸出去的一路文脉和精神根系。
为一座山立传,除了独特的视角外,如何让这“庞然大物”可亲可近可读?作者凸凹用他一贯流畅如丝滑般的叙述语言,以纪实文体的方式,又兼具了一个诗人对文字独特的组合运用,在《龙泉山传》中通过人物、故事、典籍以及诗情画意,全面呈现了龙泉山脉的生态与人文,挖掘了包括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在内的文旅资源,为读者呈现了一场山水与人文交相共情的文化和文字的盛宴。书中不仅详细记录了龙泉山脉的自然地理特征,还通过实地踏勘和采访,展现了其丰富的动植物种类和独特的地质特征。关于山中独特植物物种的些微点拨,关于曾经隐于山中的三线建设基地,前者是我尤其喜欢的部分,后者是勾连三线情结的线头,一旦挑起就波光潋滟。他让我看到,那些同样深藏于山里的秘密,它们悄悄地生长,默默地发光,并不动声色,却将大地和人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书里类似的章节,比如延伸出去的《北段》和《南段》,在我过去的记忆里,都只是单个片段,是个体的存在,当作者凸凹将其打通之后,才发现他们都在龙泉山脉的脉系中,承一脉山水,得一脉风骨。还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一面熟悉,一面陌生,熟悉的只是A面,陌生的则是表面背后我们所不知的B面。
作者对文字的掌控和把玩,游刃有余地在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之间转换,让原本看起来比较枯燥的对一座山的文本阅读变得十分轻松愉悦,这是非一般史记作家或传记作家所能企及的。看到凸凹端出如此厚重的对这座山的文字表意,将他几十年来在山前山后、山里山外的足迹、心迹和墨迹,全方位地融入对龙泉山的书写中,首先我以为,唯有跟龙泉山有着这么深的渊源和深情的人,才可以去完成它的前世今生,唯凸凹是天选之人。
龙泉山脉不仅是成都平原与川中丘陵的自然分界线,也是岷江与涪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它纵贯五市28个区市县,全长300公里,是四川省内重要的地理和文化标志。此外,沿着龙泉山的走势,珠串般联结着无数的文人墨客,他们像吸石般逐渐沿山靠拢,让客场变主场,于有形与无形间,将龙泉山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旅游资源和文化体验。作家凸凹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在这瞬息万变的新时代,以一部《龙泉山传》的方式著书立说,为龙泉山脉的生态多样性、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今天的人文景观,使其成为备受关注的旅游和研究热点提供了宝贵的范本。

□ 方寸玉
捧读蔡旭先生散文诗集《一路生花》,脑海里油然冒出一个文艺人类学概念:艺术家生命向力,即作家艺术家出于喜爱乃至崇敬,将自己的精神能量、情感体验和生命感悟,转化为艺术作品的内驱力;此力不垂青实用,也无涉功名,只推动文艺家敞开心扉,向往真善美,确证人间的正道,探寻世界的本原存在。
中国当代散文诗蔚为大观。我在柯蓝、郭风和刘再复等大家的创作中,强烈感受到他们的生命向力,推动其关注国运和民生,反抗虚无与平庸,将创作通向广阔丰盈的精神世界,进而外化为风格独特、情思饱满和意象鲜活的美学结晶。在此过程中,生命向力强健的诗人们,往往会构型出两种动人心魄的意象群或意象系列。一是大气磅礴,宏阔渊深,挟带着时代、社会、人生与自然的大命题,一如惊涛骇浪奔涌到你的面前。刘再复《读沧海》《榕树,生命进行曲》《大河,永远的奔流》《高山,永远的巍峨》等,堪称这一样貌的典范。诗人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情满于山并溢于海,思结千载且眺未来,化为一行行发烫的诗句,热烈赞美着太阳、土地、沧海、人、爱,深切反思着历史与传统,不懈追寻着真理和生命价值。刘再复虽一再自谦其散文诗的创作,比鲁迅所蕴藏着心灵岩浆的《野草》差距甚大,但作为震撼人心的时代强音,《观沧海》诸作,今天仍鸣响在我的心中。
《观沧海》一类力作,需要大开大合时代的激荡,方可扶摇直上审美的碧空;在庸常的日子里,生命向力则主要外显为作家健康长寿且感觉纤敏,创作频仍多造诣精深,且以角度独特、描述质朴、抒情不动声色,议论平中奇而见长。此风格虽少了些震撼力冲击波,但更“能给人发现喜悦与美的回味。”散文诗意象创造的这一种构型,以获“中国当代优秀散文诗作家”十佳称号、退休后寓居珠海的蔡旭先生为代表。2025年,适逢从事散文诗创作60周年之际,79岁的老诗人出版了他的第39本散文诗集《一路生花》,此前还有随笔短论等10部作品问世;仅观写作时长和出版数量,我不知散文诗界还有谁能与之比肩;况且,越进入老境,他的创作越是旺盛, 2015年至2025年十一年间,他就密集出版了14本散文诗集和两本散文诗创作短论集。在一如既往地写身边熟悉的人、事、物、景的时候,他将笔触伸向更远更深处:以爷爷身份来到“婴国”,畅享天伦之乐,礼赞元初生命的美与力,亦用婴儿双眼里澄澈的清泉,洗涤俗世的尘埃和疲惫。诗人悠游自然,带着新奇,怀着大爱,步入古树花丛,走进动物王国,遥望历史烟尘……写作题材的大拓展,以及由此而来的诗意、新意与深意,不正是老诗人生命向力勃郁而焕然的征象吗?
揽阅蔡旭的散文诗,你能鲜明感受到,他于平淡琐屑中,发现并捕捉新意和深意的敏锐力,是多么的不同寻常。在被多位评家称道的《筷子》中,他赋予这一餐具以多重意蕴,其中柴米夫妻“一起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相依为命;一起风花雪月,风雨兼程;一起青春,一起慢慢变老”的抒写, 特别温暖、尤为肯綮。《海加山等于更美》告诉我们:新意和深意的发现与赋形,还需要深厚的知解力和强劲的想象力:“一座有海又有山的风景名城,珠海,真是太美了。还可以更美吗?珠海说,当然可以,把海与山加起来就是了。无敌海景有海滨公园,仙境山色有石景山。可惜多少年来,它们之间被两幢旧楼房阻隔着。把挡住眼界的障碍物挪开,不就豁然开朗了吗?就这样,海与山连了起来。海滨公园与石景山亲密地握起了手。从云飞雾绕的石景山,可以走到碧海银滩,同作为城徽的珠海渔女合影,在20公里长的情侣路尽情浪漫。从浪涛拍岸的海滩,也可以徒步登上石景山,同奇形怪状的石头相认,乘索道穿越白云清风。在山与海相接的山坡,建了一座城市阳台,就是一条眺山望海的阶梯与纽带。海加山,等于更美。是的,美的愿望是无限的,美的追求与创造也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把遮住望眼的障碍移开就可以了,只要把蒙住想象的迷雾拨开就可以了。”其令人感怀又发人深思之处,既在于诗人用极简的文字,描绘了改建后的香炉湾,山海一体所独具的疏朗、开阔之美,更在于诗人关于美的追求与创造的前提:把遮住望眼的障碍物移开的深刻顿悟;其浓郁的哲理象征意味,从美学领域自然而逍遥地逸出,飘洒到个体的心里,便不会再有堵得慌的忧闷,从而笑口常开;弥散在人际关系中,便不会作茧自缚,从而通达随和知交多多;上升到民族国家的层面,定然会冲破闭关锁国的牢笼,走向改革开放……
我对充满生命活力与艺术张力的《一路生花》,还有一些心领神会,限于篇幅,不再叨叨了。唯愿上苍助我,像蔡旭先生那样也活成诗,跟读他散文诗第七、第八、第九个十年作品选!
向下生长的光芒
□ 浩二
在中国当代诗歌的星空中,卢卫平以他独特的“向下”视角照亮了那些常被忽视的角落。当多数诗人习惯性仰望星空或沉溺于内心迷宫时,卢卫平却弯腰俯身,将目光投向那些“向下生长的枝条”,倾听“异乡的老鼠”在黑暗中的细语。卢卫平的诗歌世界是一个倒置的宇宙——光芒来自下方,力量源于卑微,意义在坠落中重生。通过关注底层生命与边缘存在,卢卫平构建了一种独特的诗歌伦理学,在当代诗歌谱系中开辟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地理。
卢卫平的“向下”首先是一种视角选择。在《向下生长的枝条》中,他写道:“所有向上的路都已堵死/唯有向下,向深处/向无人问津的黑暗/伸展触须。”这里的“向下”不是沉沦,而是另一种生长;不是放弃,而是更执着地坚持。这种倒置的生长学构成了卢卫平诗歌的核心隐喻——真正的生命力量往往源自那些被压抑、被忽视、被遮蔽的存在。对卢卫平诗歌的持续阅读,人们会发现,“向下”不只是视角,更是一种坚定的立场。他为自己确立选材范围、叙述原则和语义准度、情感深度。《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中,那些接受城市挑选的最优秀的苹果,成为城市底层生命的绝妙喻体。苹果的沉默与被动,恰恰映射出那些失去话语权的群体的生存状态。卢卫平赋予这些静默之物以声音,让它们在诗歌中获得第二次生命。
对边缘生命的关注,使卢卫平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卑微者诗学”。他诗歌中的主角往往是那些被主流视野排除的存在:流浪者、打工者、小贩、老鼠甚至静物。在《异乡的老鼠》中,老鼠成为异乡人的替身:“它和我一样/在别人的城市里偷生”。通过这种身份认同的转移,卢卫平打破了物种与阶层的界限,建立起一种基于生存困境的生命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不是自上而下的怜悯,而是发自内部的共情。当诗人说“我就是那只老鼠”时,便彻底消解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等级关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视。
卢卫平的诗歌版图上,“异乡”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坐标。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位移,更是精神层面的悬置状态。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双重浪潮中,现代人普遍体验着“异乡感”——与环境疏离,与他人隔膜,与自我陌生。卢卫平的异乡书写捕捉到这种现代性困境,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不在异乡中寻找返乡之路,而是将异乡本身作为家园来建构。《异乡的老鼠》结尾处写道:“终于,它停下,朝我张望/仿佛两个异乡人/在辨认彼此身上的故乡气味。”这里出现了一种惊人的逆转:异乡不再是被逃离的对象,而成为可能产生新认同的空间;故乡不再是地理上的坐标原点,而是流动的关系与瞬间的识别。情感的浓烈注入,让故乡与异乡呈某种量子纠缠的状态。
卢卫平擅长赋予日常之物以惊人的隐喻力量。在他的诗歌中,苹果不只是水果,而是“一群被迫圆滑的真理”;枝条不只是植物器官,而是“倒立的闪电,向下击穿”;老鼠不只是啮齿动物,而是“夜色的核心,黑暗中最黑的部分”。这些意象的转换如此自然又如此颠覆,使读者在熟悉的表象下发现陌生的真相。卢卫平的意象体系具有明显的“向下”特质:他偏爱那些贴近地面、隐藏于暗处、被人轻视的意象。这种意象选择与他的价值立场完全一致,形成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在语言风格上,卢卫平追求一种“克制的抒情”。他的诗句简洁而精准,避免夸张的修辞和泛滥的情感。但这种克制之下涌动着一股暗流,那是被压抑的愤怒、被掩藏的悲悯、被萃取的乡愁。在谈到《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这首诗的写作缘起时,他说:“这些乡下来的苹果,它们不会喊痛,不会流血,只会慢慢地,从内部开始,将甜转化为酸,将光亮转化为暗影。”他诗中这种平静的叙述比任何直接的指控都更有力量,因为它揭示了暴力如何以日常的、自然的、无可指摘的方式实施。卢卫平的诗歌语言就像他笔下的枝条——向下生长,却暗中积蓄着向上的力量。
在当代诗歌日益精英化、抽象化、内向化的趋势中,卢卫平坚持的“向下”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平衡力量。他的诗歌提醒我们:诗歌不仅可以向上触及形而上学的天空,也应该向下触摸生活粗糙的地表;不仅可以向内探索意识的迷宫,也应该向外关注他者的生存。这种平衡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对诗歌本质的深刻理解——诗歌最终是关于生命的艺术,而生命既存在于高处,也存在于低处;既体现于光明,也隐藏于黑暗。
卢卫平的诗歌如同一束向下照射的光,照亮了那些被遗忘的角落,让沉默者发声,让卑微者显形,让异乡成为另一种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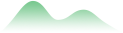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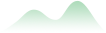
□ 余丛
深秋时节,收到友人育邦从南京寄来最新出版的诗集,叫《草木深》。每天清晨,我便带着他的书散步于仙湖植物园内,一边读一边感受诗中的意境。特别是途经弘法寺时,刚好读到《光孝寺之路》诗中的“晨光熹微,我便起身/拾起这片树叶/忘却那棵树/就像轻轻提起自己冒昧的一生”,那也是格外应景。南方的秋天,草木并未萧条,反而越发郁郁葱葱,我也人过中年,内心的荒芜与落寞,仿佛在“草木深”处获得无尽慰藉。
与育邦的交往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南京渡江纪念馆任职的时候,后来又从《青春》杂志社调到《雨花》杂志社,转眼间已经二十余年。我们既是来往密切的诗友,又是来自苏北连云港的同乡,我比他虚长几岁,在学养上他却是让我仰视的读书人。他博览群书,总是先人一步;他视野开阔,对世界文学更是如数家珍。近年来,育邦还专门写过两部这方面的著作,一部叫《从乔伊斯到马尔克斯》,另一部书叫《从海明威到昆德拉》,光看书名就已经令人瞠目结舌,敬佩不已。
言归正传,回到《草木深》这部诗集,作为“70后”代表诗人之一的育邦,显然已形成自己清新典雅而意象超拔的诗歌面目。写诗至今,育邦陆续出版了诗集《忆故人》《伐桐》《止酒》《归来》,一路走来对诗的探索从未止步,他用一支深刻而敏感的笔,写下了许多意味深长的名篇佳作。通读可见,育邦的诗无论是抒情言志,还是行吟唱和,内容上大致分为应景和怀古两类。看似触景生情的自然人文,如《司空山》《白鹭洲》《过元好问墓》等,却处处尽显灵魂游走的痕迹;看似托物感怀的凭吊怀古,如《晨起读苏轼》《空亭——为倪云林而作》《豹隐——读陈寅恪先生》等,却在重构内心深处的精神家园。他以现代人的情怀,或眺望于山水之间,或照会于前人古迹,或深思于现实处境,始终是诗带给他生命的一份天真和自如。
育邦的诗歌,简洁节制,不见晦涩繁复;含蓄凝练,又别具寓意。细细品味,常给人一种虚实相间的直觉,尤其是《我认出了我的父亲》《寂静邮局》《对饮》《止酒》等常被提及的诸多诗作,似梦非梦,又真实可感。诗中看似有我,却不像似我,看似无我,我又在其中。只不过,后一个我已非前一个我,好像将诗外的我邀请入内。其实,这就是育邦的高明之处,他能将所见所闻的感悟,通过想象和虚构,以化境之笔,写出情韵兼至的文采。貌似通过语言、形象和节奏的层层叠进而浑然天成,其实是作者本自俱足的技艺、智识和远见的融会贯通所得。每一首诗成形前被一再修剪,仿若诗人的情感、信仰和执念的枝条,而言语的贫乏造就了诗意心声,并以此回应一个时代的精神困境。
在汉语的一招一式中,育邦正在创造自己的诗歌范式,那是接驳传统的古典韵味又在拓展现代诗性边界的一条诗学道路。当“草木深”这一意象在为一部诗集命名时,自然的时序也随之更替,而这一切似乎也在为汉语新诗实践着新的可能。育邦说:“有了草木葳蕤,世界才充满生机。”显然,诗人就是“草木深”处捕捉诗意的猎手,时刻准备语言长矛的猛然一击,将四处逃窜的诗歌灵兽捉拿归案。我想,育邦的理想也莫过于成为这样的猎手,不过他潜伏于人间的“草木”丛林,却将入世的修行和出世的智慧置入文字的庇护之所。正如他在诗中所言:“在汉语中,我安下一座隐秘的家……不可言说的/皆密封于塔,深埋于地”。
落笔至此,我想说出那不经意间诗人的平常之处,或更能体现他的心性喜好,而这在他的诗中已不成为秘密。育邦有一首诗叫《庄子,或维特根斯坦》,我以为这就是混合在育邦身上的“气质”,有时候他是庄子,有时候他是维特根斯坦,有时候又游离于二者之间。而那个真实的育邦,就在诗集《草木深》中蛰居,就在他未来诗篇里渐次隐身,他将始终是人群中的众人,却又是自我的异类。
(《草木深》育邦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5年9月版)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读凸凹非虚构作品《龙泉山传》

□ 盛红
作家凸凹非虚构作品《龙泉山传》用82.5万字的体量,讲述龙泉山脉的前世今生。对这部沉甸甸的大书,我需要用虔诚的双手才能用力捧起,而更多的人则用一个又一个的转发与传递来表达他们的喜欢和在意。正如凸凹在后记中所写:“对于这条从没人首尾拉通写过的山,我的难度是,如何于有限的时间,只用几十万字的文学性体量,将一切尽数拿下,而又有几分意思至少读得下去……”于是,“顺应山脉的生发、结构、组织与衍变,《龙泉山传》跟着有了总述、侧重、专题和分述的架构,具体则由‘我叫龙泉山’‘主峰’‘中段’‘北段’和‘南段’五个区间作背书式呈现。实操为让一些事体呈线性集束,跋山涉水在山脉的时间轴上;让一些事体呈非线性发散,团身聚合于山脉之区块界域。”
这既是作者构思上的巧妙又绝非取巧,如果没有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文字驾驭能力,没有凸凹自20世纪90年代初落脚龙泉驿后,一直不断地对这方地域的调查、研究、走访以及书写,尤其是深深的热爱和全身心的付出,哪有此刻的巧思和妙笔?也正是这无处不在的巧妙布局和拆分,才将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龙泉山拉网式地全景呈现在读者面前,才有机会让以为熟悉此山的人得以重新认识它,让不熟悉此山的人了解它爱上它,让一座看似无名却早已有名的山,不只有桃花的妖艳,农家乐的偷闲,更有今日城市森林公园的无限生机,以及你未曾看见的延伸出去的一路文脉和精神根系。
为一座山立传,除了独特的视角外,如何让这“庞然大物”可亲可近可读?作者凸凹用他一贯流畅如丝滑般的叙述语言,以纪实文体的方式,又兼具了一个诗人对文字独特的组合运用,在《龙泉山传》中通过人物、故事、典籍以及诗情画意,全面呈现了龙泉山脉的生态与人文,挖掘了包括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在内的文旅资源,为读者呈现了一场山水与人文交相共情的文化和文字的盛宴。书中不仅详细记录了龙泉山脉的自然地理特征,还通过实地踏勘和采访,展现了其丰富的动植物种类和独特的地质特征。关于山中独特植物物种的些微点拨,关于曾经隐于山中的三线建设基地,前者是我尤其喜欢的部分,后者是勾连三线情结的线头,一旦挑起就波光潋滟。他让我看到,那些同样深藏于山里的秘密,它们悄悄地生长,默默地发光,并不动声色,却将大地和人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书里类似的章节,比如延伸出去的《北段》和《南段》,在我过去的记忆里,都只是单个片段,是个体的存在,当作者凸凹将其打通之后,才发现他们都在龙泉山脉的脉系中,承一脉山水,得一脉风骨。还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一面熟悉,一面陌生,熟悉的只是A面,陌生的则是表面背后我们所不知的B面。
作者对文字的掌控和把玩,游刃有余地在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之间转换,让原本看起来比较枯燥的对一座山的文本阅读变得十分轻松愉悦,这是非一般史记作家或传记作家所能企及的。看到凸凹端出如此厚重的对这座山的文字表意,将他几十年来在山前山后、山里山外的足迹、心迹和墨迹,全方位地融入对龙泉山的书写中,首先我以为,唯有跟龙泉山有着这么深的渊源和深情的人,才可以去完成它的前世今生,唯凸凹是天选之人。
龙泉山脉不仅是成都平原与川中丘陵的自然分界线,也是岷江与涪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它纵贯五市28个区市县,全长300公里,是四川省内重要的地理和文化标志。此外,沿着龙泉山的走势,珠串般联结着无数的文人墨客,他们像吸石般逐渐沿山靠拢,让客场变主场,于有形与无形间,将龙泉山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旅游资源和文化体验。作家凸凹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在这瞬息万变的新时代,以一部《龙泉山传》的方式著书立说,为龙泉山脉的生态多样性、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今天的人文景观,使其成为备受关注的旅游和研究热点提供了宝贵的范本。

□ 方寸玉
捧读蔡旭先生散文诗集《一路生花》,脑海里油然冒出一个文艺人类学概念:艺术家生命向力,即作家艺术家出于喜爱乃至崇敬,将自己的精神能量、情感体验和生命感悟,转化为艺术作品的内驱力;此力不垂青实用,也无涉功名,只推动文艺家敞开心扉,向往真善美,确证人间的正道,探寻世界的本原存在。
中国当代散文诗蔚为大观。我在柯蓝、郭风和刘再复等大家的创作中,强烈感受到他们的生命向力,推动其关注国运和民生,反抗虚无与平庸,将创作通向广阔丰盈的精神世界,进而外化为风格独特、情思饱满和意象鲜活的美学结晶。在此过程中,生命向力强健的诗人们,往往会构型出两种动人心魄的意象群或意象系列。一是大气磅礴,宏阔渊深,挟带着时代、社会、人生与自然的大命题,一如惊涛骇浪奔涌到你的面前。刘再复《读沧海》《榕树,生命进行曲》《大河,永远的奔流》《高山,永远的巍峨》等,堪称这一样貌的典范。诗人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情满于山并溢于海,思结千载且眺未来,化为一行行发烫的诗句,热烈赞美着太阳、土地、沧海、人、爱,深切反思着历史与传统,不懈追寻着真理和生命价值。刘再复虽一再自谦其散文诗的创作,比鲁迅所蕴藏着心灵岩浆的《野草》差距甚大,但作为震撼人心的时代强音,《观沧海》诸作,今天仍鸣响在我的心中。
《观沧海》一类力作,需要大开大合时代的激荡,方可扶摇直上审美的碧空;在庸常的日子里,生命向力则主要外显为作家健康长寿且感觉纤敏,创作频仍多造诣精深,且以角度独特、描述质朴、抒情不动声色,议论平中奇而见长。此风格虽少了些震撼力冲击波,但更“能给人发现喜悦与美的回味。”散文诗意象创造的这一种构型,以获“中国当代优秀散文诗作家”十佳称号、退休后寓居珠海的蔡旭先生为代表。2025年,适逢从事散文诗创作60周年之际,79岁的老诗人出版了他的第39本散文诗集《一路生花》,此前还有随笔短论等10部作品问世;仅观写作时长和出版数量,我不知散文诗界还有谁能与之比肩;况且,越进入老境,他的创作越是旺盛, 2015年至2025年十一年间,他就密集出版了14本散文诗集和两本散文诗创作短论集。在一如既往地写身边熟悉的人、事、物、景的时候,他将笔触伸向更远更深处:以爷爷身份来到“婴国”,畅享天伦之乐,礼赞元初生命的美与力,亦用婴儿双眼里澄澈的清泉,洗涤俗世的尘埃和疲惫。诗人悠游自然,带着新奇,怀着大爱,步入古树花丛,走进动物王国,遥望历史烟尘……写作题材的大拓展,以及由此而来的诗意、新意与深意,不正是老诗人生命向力勃郁而焕然的征象吗?
揽阅蔡旭的散文诗,你能鲜明感受到,他于平淡琐屑中,发现并捕捉新意和深意的敏锐力,是多么的不同寻常。在被多位评家称道的《筷子》中,他赋予这一餐具以多重意蕴,其中柴米夫妻“一起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相依为命;一起风花雪月,风雨兼程;一起青春,一起慢慢变老”的抒写, 特别温暖、尤为肯綮。《海加山等于更美》告诉我们:新意和深意的发现与赋形,还需要深厚的知解力和强劲的想象力:“一座有海又有山的风景名城,珠海,真是太美了。还可以更美吗?珠海说,当然可以,把海与山加起来就是了。无敌海景有海滨公园,仙境山色有石景山。可惜多少年来,它们之间被两幢旧楼房阻隔着。把挡住眼界的障碍物挪开,不就豁然开朗了吗?就这样,海与山连了起来。海滨公园与石景山亲密地握起了手。从云飞雾绕的石景山,可以走到碧海银滩,同作为城徽的珠海渔女合影,在20公里长的情侣路尽情浪漫。从浪涛拍岸的海滩,也可以徒步登上石景山,同奇形怪状的石头相认,乘索道穿越白云清风。在山与海相接的山坡,建了一座城市阳台,就是一条眺山望海的阶梯与纽带。海加山,等于更美。是的,美的愿望是无限的,美的追求与创造也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把遮住望眼的障碍移开就可以了,只要把蒙住想象的迷雾拨开就可以了。”其令人感怀又发人深思之处,既在于诗人用极简的文字,描绘了改建后的香炉湾,山海一体所独具的疏朗、开阔之美,更在于诗人关于美的追求与创造的前提:把遮住望眼的障碍物移开的深刻顿悟;其浓郁的哲理象征意味,从美学领域自然而逍遥地逸出,飘洒到个体的心里,便不会再有堵得慌的忧闷,从而笑口常开;弥散在人际关系中,便不会作茧自缚,从而通达随和知交多多;上升到民族国家的层面,定然会冲破闭关锁国的牢笼,走向改革开放……
我对充满生命活力与艺术张力的《一路生花》,还有一些心领神会,限于篇幅,不再叨叨了。唯愿上苍助我,像蔡旭先生那样也活成诗,跟读他散文诗第七、第八、第九个十年作品选!
向下生长的光芒
□ 浩二
在中国当代诗歌的星空中,卢卫平以他独特的“向下”视角照亮了那些常被忽视的角落。当多数诗人习惯性仰望星空或沉溺于内心迷宫时,卢卫平却弯腰俯身,将目光投向那些“向下生长的枝条”,倾听“异乡的老鼠”在黑暗中的细语。卢卫平的诗歌世界是一个倒置的宇宙——光芒来自下方,力量源于卑微,意义在坠落中重生。通过关注底层生命与边缘存在,卢卫平构建了一种独特的诗歌伦理学,在当代诗歌谱系中开辟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地理。
卢卫平的“向下”首先是一种视角选择。在《向下生长的枝条》中,他写道:“所有向上的路都已堵死/唯有向下,向深处/向无人问津的黑暗/伸展触须。”这里的“向下”不是沉沦,而是另一种生长;不是放弃,而是更执着地坚持。这种倒置的生长学构成了卢卫平诗歌的核心隐喻——真正的生命力量往往源自那些被压抑、被忽视、被遮蔽的存在。对卢卫平诗歌的持续阅读,人们会发现,“向下”不只是视角,更是一种坚定的立场。他为自己确立选材范围、叙述原则和语义准度、情感深度。《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中,那些接受城市挑选的最优秀的苹果,成为城市底层生命的绝妙喻体。苹果的沉默与被动,恰恰映射出那些失去话语权的群体的生存状态。卢卫平赋予这些静默之物以声音,让它们在诗歌中获得第二次生命。
对边缘生命的关注,使卢卫平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卑微者诗学”。他诗歌中的主角往往是那些被主流视野排除的存在:流浪者、打工者、小贩、老鼠甚至静物。在《异乡的老鼠》中,老鼠成为异乡人的替身:“它和我一样/在别人的城市里偷生”。通过这种身份认同的转移,卢卫平打破了物种与阶层的界限,建立起一种基于生存困境的生命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不是自上而下的怜悯,而是发自内部的共情。当诗人说“我就是那只老鼠”时,便彻底消解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等级关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视。
卢卫平的诗歌版图上,“异乡”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坐标。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位移,更是精神层面的悬置状态。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双重浪潮中,现代人普遍体验着“异乡感”——与环境疏离,与他人隔膜,与自我陌生。卢卫平的异乡书写捕捉到这种现代性困境,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不在异乡中寻找返乡之路,而是将异乡本身作为家园来建构。《异乡的老鼠》结尾处写道:“终于,它停下,朝我张望/仿佛两个异乡人/在辨认彼此身上的故乡气味。”这里出现了一种惊人的逆转:异乡不再是被逃离的对象,而成为可能产生新认同的空间;故乡不再是地理上的坐标原点,而是流动的关系与瞬间的识别。情感的浓烈注入,让故乡与异乡呈某种量子纠缠的状态。
卢卫平擅长赋予日常之物以惊人的隐喻力量。在他的诗歌中,苹果不只是水果,而是“一群被迫圆滑的真理”;枝条不只是植物器官,而是“倒立的闪电,向下击穿”;老鼠不只是啮齿动物,而是“夜色的核心,黑暗中最黑的部分”。这些意象的转换如此自然又如此颠覆,使读者在熟悉的表象下发现陌生的真相。卢卫平的意象体系具有明显的“向下”特质:他偏爱那些贴近地面、隐藏于暗处、被人轻视的意象。这种意象选择与他的价值立场完全一致,形成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在语言风格上,卢卫平追求一种“克制的抒情”。他的诗句简洁而精准,避免夸张的修辞和泛滥的情感。但这种克制之下涌动着一股暗流,那是被压抑的愤怒、被掩藏的悲悯、被萃取的乡愁。在谈到《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这首诗的写作缘起时,他说:“这些乡下来的苹果,它们不会喊痛,不会流血,只会慢慢地,从内部开始,将甜转化为酸,将光亮转化为暗影。”他诗中这种平静的叙述比任何直接的指控都更有力量,因为它揭示了暴力如何以日常的、自然的、无可指摘的方式实施。卢卫平的诗歌语言就像他笔下的枝条——向下生长,却暗中积蓄着向上的力量。
在当代诗歌日益精英化、抽象化、内向化的趋势中,卢卫平坚持的“向下”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平衡力量。他的诗歌提醒我们:诗歌不仅可以向上触及形而上学的天空,也应该向下触摸生活粗糙的地表;不仅可以向内探索意识的迷宫,也应该向外关注他者的生存。这种平衡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对诗歌本质的深刻理解——诗歌最终是关于生命的艺术,而生命既存在于高处,也存在于低处;既体现于光明,也隐藏于黑暗。
卢卫平的诗歌如同一束向下照射的光,照亮了那些被遗忘的角落,让沉默者发声,让卑微者显形,让异乡成为另一种故乡。

-我已经到底线啦-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