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合军 庞惊涛 刘诗哲
2024-10-25 00:47
刘合军 庞惊涛 刘诗哲
2024-10-25 00: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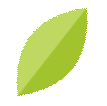
——读罗春柏诗集《记忆的绳子》有感
□ 刘合军
南国初秋,红霞日暮,有幸又一次与诗人罗春柏先生雅聚,并获赠诗人新著《记忆的绳子》,借着明灿的灯光,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书的封面庄重而又厚重色调,以及一轮朝红隐入淡淡山川与河流所酝造出的一幅智慧图案,接下来的是雄鹰展翅翱翔在云水之间,这仿若植入灵魂而又动感的场景首先对我有了磁的吸力。
我的思想之悟是随着——静、禅、爱,而跌落华夏文字的浩瀚与无垠中的,这是一种生命与智慧,阅历与思考,内心与繁杂,希望与焦虑“外与内”互为修行的“无我”精神状态,一个人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做到排除外部环境的干扰,剔除繁杂而静卧流水风声,在冥想的世界去沉淀自己的思想,用有限的空间去营造一个更广义的、脱俗的豁达之心去对待和发现平凡中的一切事物,这就是一种境界。七情六欲是每一个人的人初共性,诗人也不例外,爱是人间之大善,有父母之爱,子女之爱,友人和对万物悲悯之爱,也有对他人予以关怀与培养之爱,诗人罗春柏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大善之爱,而感染了身边太多的文学爱好者,用文学之爱温暖和激励了更多身边的新人。
我轻轻漫步于《天容海色本澄明》叶延滨老师为《记忆的绳子》新著之序,更进一步地品尝到了诗人创作之风、之气、之爱与之禅,感受文字与诗品的高雅和人性探求之大美与大善,读到语境中那份对名与利的淡泊,就像诗人语录“一个人/一支笔/洗尽铅华的清绝。”也读到了诗人澄澈的精彩世界与风轻云淡的恬静,安祥之高远。
随晨风吹开的页面,我静静打开诗人宝藏,扑面而来的是《沸动的春天》,就找到了阳光的密钥读到诗歌与意境的美感,“温柔的风、轻轻的雨”共同营造出宁静而美好的氛围。雨滋润着玫瑰种子,使其萌发,展现出大自然的生命力。“那片土地拂动/春天的旖旎”,让人仿佛看到了春天里生机勃勃、色彩斑斓的景象,这种语言的美感像春风一样吹拂和浸润着心灵的明亮。进而诗人将活力复苏沉睡的江河,流水奔涌,带来了玫瑰色的阳光和燕子的双翅。这里既有江河复苏的动态感,又有阳光和燕子带来的温暖与生机。“你款款而来,歌声/在青青的田野飘逸”,为整个画面增添了一份灵动和诗意,让人感受到一种美好的期待。通过这两节的赏读,让读者充分感受到艺术,意象与语言的运用,读到风、雨、玫瑰种子、江河、阳光、燕子等来自大自然丰富的意象,这些意象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玫瑰种子象征着希望和美好,江河象征着生命的流动,阳光和燕子则带来了温暖的生动活力。“滋润”“萌发”“拂动”“奔涌”“飘逸”“玫瑰色的阳光”为诗歌增添了一抹温暖而浪漫的色彩。上述动词的运用,使诗歌更加生动形象,增强了更灵动的画面感。通过对自然与景象的描绘,传达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让人感受到诗人内心的澄明和对生活中的美好与希望。
诗歌是聆听心声酝酿神思引燃的火线,他在自己特定的环境与状态下引爆和炸响,发现是一种闪电内燃“材料”,存在与表达是对自然与万物变化的敏锐观察,这“材料”就是语言与灵魂的赋物。读《太阳与海》,它是一首充满了强烈的画面感和对比感的隐喻与述说作品,其手法贯以雄浑与宁静:诗的前半部分描绘了一万头雄狮在咆哮和撕咬的场景,充满了力量和狂暴,给人一种仿佛世界即将被吞噬的压迫感。而后半部分则转向头上那轮不慌不忙的太阳,它投下一缕缕光,轻抚大地和疲惫的海浪,营造出一种宁静而温暖的氛围。这种强烈的对比使诗歌的意境更加丰富和深刻。诗人通过自然的力量,雄狮代表着自然的强大,它们的咆哮和撕咬展现出大自然的狂野一面。而太阳则象征着温暖和希望,它的光轻抚大地和海浪,体现了大自然的温柔与慈爱。这种对自然不同面的描绘,让人感受到自然的复杂与神秘,诗人拟用艺术夸张与对比手法,同时,与太阳的不慌不忙形成鲜明对比,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太阳和海是两个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意象。太阳代表着光明、温暖和希望,海则象征着广阔、深邃和神秘。它们的组合使诗歌具有了更广阔的内涵和更深的情感,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和赞美之情。通过对雄狮和太阳的描写,诗人展现了自然的强大力量和温柔之美,让人感受到自然的伟大和神秘。同时,诗歌也传达出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让人在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也能从中汲取力量和勇气。
珠海乃山水秀美、诗意灵动的诗者栖居之地,它不但孕育了一方水土,也孕育了历史与现代诗歌文化,读先生的诗会使人心思愉悦敞亮。读到山与海那些奔腾的语言,《外伶仃岛》,写外伶仃岛的诗人有一万种写法,罗春柏的伶仃岛除了湛蓝,还有摇晃的天和摇晃的海,这里不但刻录下乘舟驾浪画面感,也刻画出此境此情之“白浪/远方”。读《雾锁金台寺》,就是读他的禅意,读木然于世的石阶,读“烟云”与香火,读扬幡于钟声的一场又一场法事和众生冀望的艳阳。读《在抚仙湖致徐霞客》,是少女与雾霭遮掩下的纱巾,荡漾的一个一个故事,陈砖旧瓦展开的马鞭花和多情风喂暖的“醉”游人。读《凭吊》,你能读到埋藏于野的一部史书,读征人的悲壮与离愁,硝烟与惊雷遗落在云天与雾雨的他处。
诗是牵引灵魂的圣物,每一字都是呼唤生命中的语言与“真情”,写诗既可以是神旨的陈述,也是烟火与尘土传承,现代生活中,我们需要在物欲与喧嚣中发现或找到寄养灵魂的一块静地,找到另一个自己,那就是写诗和读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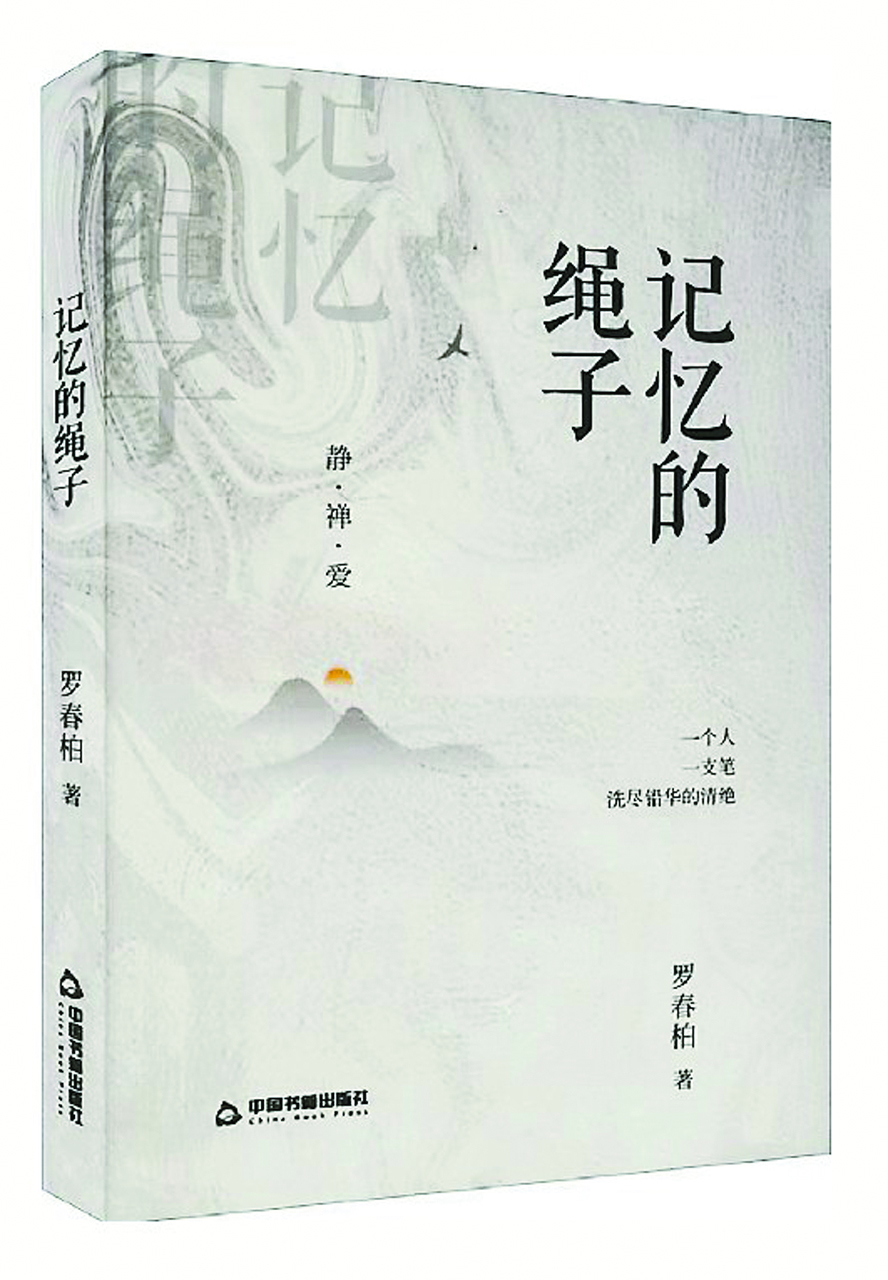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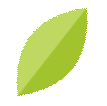
——雍也《从诗经出发》的三个学理维度
□ 庞惊涛
作家雍也继《回望诗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年6月)之后,深研细磨,纵横比较,再一次推出了《从诗经出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这部《诗经》研究的开创性力作。其综合调度的比较哲学、比较神学和比较美学三个维度,将《诗经》研究置于更深广的时空关系之中,不失为借经典向海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
比较哲学:天命观的问题意识
雍也在《从诗经出发》中用力最勤、体虑精深的一篇,即全书第一篇:《天命观》。此篇系于该书的上篇,总名之为“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当然指向中西之间《诗经》研究璀璨若锦的喻意。“天命观”问题的发现和提出,是我认为雍也这部作品里最显理论功力的代表和集大成。从方法论上看,显然是借助于传统文学的入口,而用了比较哲学的解法,最后达成问题的初步解决。
剖析其问题意识的形成和结论的形成,我大约可以梳理其比较哲学形成的理路:
一是《诗经》篇目的连类。雅颂诸篇中的政治属性,历来容易被普通读者忽略。但雍也却敏感地注意到这些篇目中的表述,“像散落在草丛里熠熠生辉的花朵,带着周人赋予的特别的气息。”将这些篇目连类,他发现了周人天命观的三重意涵。
二是对近世以来中国哲学家对周人天命观的幽光灼见进行了列举。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他们几乎就是在西方比较哲学概念提出的同时,对《诗经》中雅颂诸篇中的东方哲学“天命观”进行了深入的探析。这是雍也为最终驾驭比较哲学这个手段,为他的结论服务的理论关键和理论基础。
三是由此及彼、由内而外的理论推演。当《诗经》天命观的来源和形成愈益清晰,其意义的探求已然完成,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东西方天命观比较及其结论的形成,就是水到渠成之势。“西方也有天命一说。”看似波澜不惊的一句,其实是比较哲学在本篇中最为动人的一次桥接。基于此,柏拉图、希罗多德等西哲的哲学思想被拿来作为《诗经》天命观的阐释和比较对象,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比较哲学必然要指向哲学思想的异同之处。“中西两种天命观有一个共同点:人都受命于天,为其主宰。”但更多的还在于差异。所谓差异,或许也可以理解为雍也比较哲学的结论:“西方天命观较之中国天命观,宿命论色彩重得多,而中国天命观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强得多。”此外,“二者建立的情感基础不同”“追求路径也不同”。这些不同,虽然属于典型的“拿来主义”,但谁又能否认,雍也在比较哲学视野下,“发现”的价值呢?
比较神学:咒语何以产生魔力?
相较于比较哲学的成熟,比较神学在学术上还显“稚嫩”,或者说“年轻”,也因此显出其特别的朝气。雍也在《从诗经出发》里,看似无意、实则有心地从《诗经》中一些比较不为人注意的篇目研究出发,通过爱情、美人等易于公众接受的话题探析,从而带领读者进入到比较神学的“年轻”学术之境,深得通俗引向雅致的学问探求和普及传播之法。
雍也引出的小诗,是《东方之日》。在主流观念里,此诗“刺衰”,写“男女淫奔”,故不宜大众传播。但雍也却在此诗中看到了爱情,或者更直接地说,是爱情咒。在印度《阿达婆吠陀》里,“要你爱我,永不离分”岂不就是《东方之日》里“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的爱情咒语?为此,他引用任乃强先生对“发”本意的阐释,认为不是历史上几成定论的“行也”或“言蹑我而行去也”,而是“猎人捕兽之机栝,践之则机发”,换言之,有“机关”意,这就更有“咒语”意味了。他还引证叶舒宪对南太平洋原始民族民歌,来考证这咒语中近乎巫术的部分。在日本学者白川静看来,“歌谣源于撼动神明,祈祷神灵的语言”,所以,这样的神性咒语,大约脱不开神学的范畴。与之具有同样性质的,还有《何人斯》《巷伯》中这样的咒语。既然《诗经》中有咒语诗,那么,就存在爱情咒的可能。更进一步,这样的爱情咒,就能在世俗社会里产生感染人和影响人的魔力。
只是稍微遗憾的是,如果印度和日本的咒语诗和《诗经》里的爱情咒语,都指向神秘的东方的话,那么,比较神学的范畴,大概还缺失了美西从神话时代向传说时代过渡时代的咒语诗——它们大概率上应归结于神学范畴。
在另一篇题为《一个绝代佳人引发的“国际风云”》的作品里,雍也用同样基于比较神学的手法,来进行中西比较——当然,鉴于神话学和神学本质的差异,此处用神话学似乎更准确一些。雍也引用《诗经》中的作品,也是一篇不太为大众所熟知的《株林》,其指向可能更接近于半信史时代和信史时代之间的神话学。夏姬的故事未保真有,但也不能说全是神话,和《伊利亚特》中的海伦一样,模糊的文字,往往塑造出一个个清晰的美人。夏姬其时,华夏民族正处于自由无羁、天性无束的童年时期。两个美人的比较,其实是两种文化的比较,她们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都清晰地指向她们背后的时代、社会和世俗认知。
这样的比较视野,不仅让枯燥的“解经”妙趣横生,也能帮助我们通过借助《诗经》的阐释,抵向更开阔的文化空间。一言以蔽之,《诗经》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自我的过往,也帮助我们看到“他者”的过往。在“自我”和“他者”之间,诗歌怎样作为桥梁,如何帮助我们缩短了历史的时空。
比较美学:战争的大义与悲伤
如同一个圆满的环,《从诗经出发》开篇阐释比较哲学,其终篇则指向比较美学。作为一种美学思潮,比较美学从20世纪初开始确立,并受比较哲学等比较学科的影响而得到发展。雍也将《诗经》中关于战争的篇目拈出,并与《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进行比较,从而提炼出了中西大异其趣的战争美学,颇具手眼的同时,也从“血与痛”“歌与哭”的主题昭示中,显示了自己具有诗人气质的大义立场和人文关怀。
在雍也看来,《诗经》中对特定战争行为即正义战争的歌颂与认同的篇目,不仅代表统治阶层的价值观,同时也理应受到广大群众阶层的理解和支持。其称颂战争的道德之美、军阵之美、人格之美和情怀之美与人性之美,都是大义或者正义战争的东方美学构成。和《荷马史诗》中的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的“暴力美学”颇为不同。在雍也看来,“化悲痛为悲哀,化悲痛为悲壮,这正是《诗经》与《荷马史诗》呈现出来最大的美学之异。”
在指出中西战争美学的不同之后,雍也对《诗经》中这些关于战争的篇目的阐释,以及随后进行的美学比较,显然还需要指向一个更具体和深刻的思辨维度。在这部以学理性见长的著作里,我每每为雍也跳出逻辑严密的论证和推演,而发出基于比较视野下的哲思和提示而拍案——比较美学作为一种方法,终极的价值,正是这样超越一般性解经的哲思和提示——尽管它偏于强烈的个人旨趣,但我能想象,这样的个人旨趣,会引发相当多的共鸣。这大约就是借助于比较美学让我们提升对《诗经》文本认知的最好的阐释。
杜甫说,“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在这样的比较视野下,《诗经》的研究和传播可以引入更为广大的文化天地。雍也借助对《诗经》的阐释,或者说“从诗经出发”的真正命意,是倡导一种宽广的文化胸怀和历史眼光,从而让《诗经》带着我们,到达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多元文化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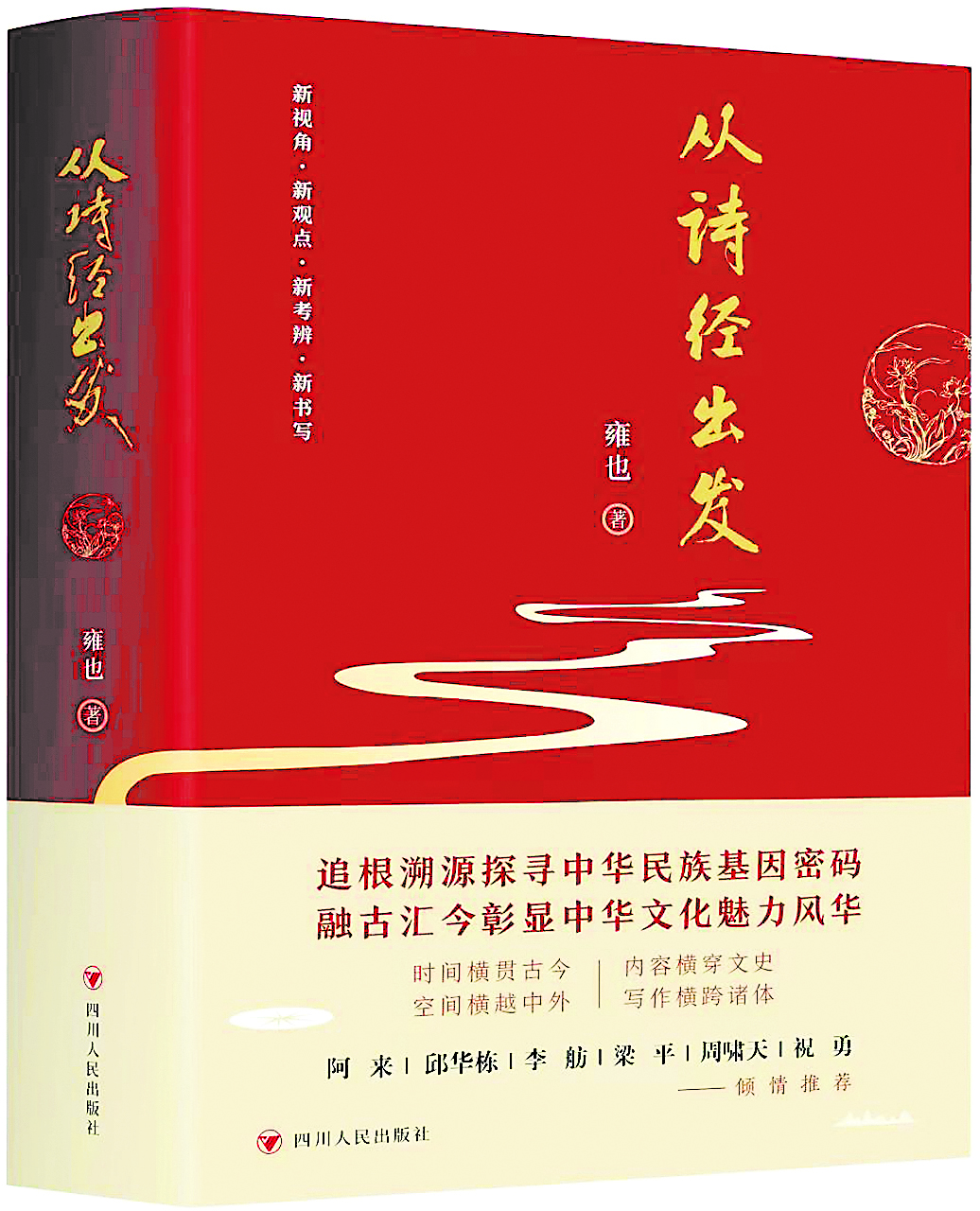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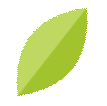
——读《隐衷》
□ 刘诗哲
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回到童年的老房子,试图理解三十年前在这里上演的悲剧。“我不知道是哪根线把我又拉回到这里。”小说就此展开。一个暗含疑问的陈述句,显示一个路标:读者期待的一切答案从这里开始寻找吧!
这部书名《隐衷》的小说,是法国新小说作家吉塞勒·富尼耶著,方颂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3月出品的“午夜文丛”系列作品之一。吉塞勒·富尼耶生于1953年,曾在巴黎从事金融分析工作多年,后定居日内瓦,致力于写作。《隐衷》是她第一部小说,其法文版2000年由法国午夜出版社出版。
翻开这部小说素雅的封面之前,书名就引起我的猜测:会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是探讨人物内心世界、秘密情感或者不为人知的想法的释疑之作,还是围绕人物复杂心理、人际关系的微妙或者私生活中难言之隐展开的故事?我预感到它将带给我阅读的欣喜。
阅读完小说第一节,我最初认定,这是一部“我”(玛蒂尔德)通过追忆构成的小说。但很快发现,我犯了经验主义错误。玛蒂尔德只不过是率先出场的那一个。一个引子。接着出场的人物:托马、蕾阿、卡米耶、不忠的母亲丽莎,甚至是死去的父亲莱昂斯都成了“我”,都是叙事、回忆与内心独白的主人公。他们站在各自的立场和各自的视角进行叙说,让每一件事都找到各自意义,各归其位,共同描绘和编织一个立体杂驳又内涵丰富的玛蒂尔德的童年。这让人想到中国成语“盲人摸象”,每个盲人能说出自己摸到的那个部分,所有人加在一起,就是一头完整的大象。
小说的人物关系并不复杂,而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令人咋舌。小说将人性的幽微:复杂、微妙与难以捉摸,多面性与深不可测揭示得淋漓尽致。而每个人内心独白又像是在密室里向神忏悔,从而揭示出那些隐藏得很深又涵泳在因果之中的隐衷。
蕾阿阿姨的隐衷应该有两个:一是因家道中落无力维持生活,而设计招赘成为妹妹卡米耶丈夫的、前佃户之子托马,让他成为一个好劳动力。二是自己初恋、因某种缘故成为自己妹夫、最终死于猎枪(尽管作者含糊其辞,故设迷阵,但读者还是读出了死于自杀)的莱昂斯。
对于托马,他并没真正爱过自己妻子卡米耶,甚至一点都不喜欢她。“但只有通过婚姻这条唯一的途径,我才能回到这片土地,让它结出硕果,我还想成为它的主人。”这是托马的隐衷。当他知道妻妹丽莎对自己产生兴趣时,不但不采取任何举动加以阻止,还任凭事情往下发展,“借此机会,报复这两个为钱坑我的女人(蕾阿和卡米耶)”,这不过是“一次小小的反击。”
卡米耶面对丈夫与妹妹的奸情隐而不发,除了怕撕破脸皮彻底失去丈夫,还想将这件事当做手里一种说不定哪天可使用的秘密武器。她还有一个不可示人的隐衷:通过跟踪偷窥还有想象,让自己得到某个方面的满足。
小说人物中最可怜的人物莫过于“我”的父亲莱昂斯。一个死于非命的人,有情人未成眷属,草率结婚的妻子又红杏出墙,自己一味忍气吞声,佯装不知情以保全颜面,当女儿遭受托马猥亵告诉他时,他不但不出头为她申张正义,还责怪女儿胡思乱想。中国有句老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可怜又可恨之人,最终颜面无存时,只好选择死这种永远的麻木形式。
至于“我”——玛蒂尔德,这么多年过去了,何苦又回来?“因为近来,又或许是长久以来,我内心里存在着一种渴望,一种迫切的需求,想知道事情的原委。”我想,玛蒂尔德想弄清楚童年生活里的每个人的隐衷,就是自己的隐衷吧。“所有这些隐衷,我从来都没搞明白。”小说最后一个小节里,她如是说。事情果真如比吗?显然,聪慧的读者已从阅读得到很多答案。
“我”,沉浸在夏日午后的颓唐里,“我”的回忆是它唯一鲜活的部分。最终,“我”来到一个岔路口,选定一条狭窄、蜿蜒的小路,“我顺着路继续开了下去”。就小说艺术来说,一种未完成的开放结局,往往是最迷人的!
作为新小说之一种,这部小说并不“疯狂”,走得也不算太远,故事相对完整,也好理解。吉塞勒·富尼耶根据各自回忆(甚至根据需要让死去的莱昂斯也参与进来)“过去”来进行叙事,并与“现实”的叙述相对照而共同产生心理上的“厚度”,叙事的时间线有些错乱,但叙述逻辑不错乱。唯一要求读者专心致志的是,应时刻弄明白自己的目光与思绪正搭在哪一位主人公的情感线上,才能从纷繁复杂的交叉叙事中不至于迷失方向,并时刻准备随着作者笔锋转向而迅速拐入另一个主人公的另一条道路。
一个夏日午后,是一根风中飘着的无形的线,连着过往,又通往未来,成全一个没有让读者失望的小说。在此多说一句:《隐衷》译者方颂华先生的译笔很好,译文通顺晓畅,典雅优美,读之如饮醇醪,齿颊生津。遗憾的是,方先生于2020年辞世,令人惋惜。借此文向方先生致敬。
结束这篇短文时,突然想起诗人聂沛一首长诗的诗题:下午是一条远逝的河。这首诗的题记引用了蒙田名句:“我们的世界刚寻找到另一个世界,一个未必不更辽阔、更广博、更充满生灵的世界。当我们走出光明之际,那一个世界则进入了光明。”这也是我想对新小说讲的题外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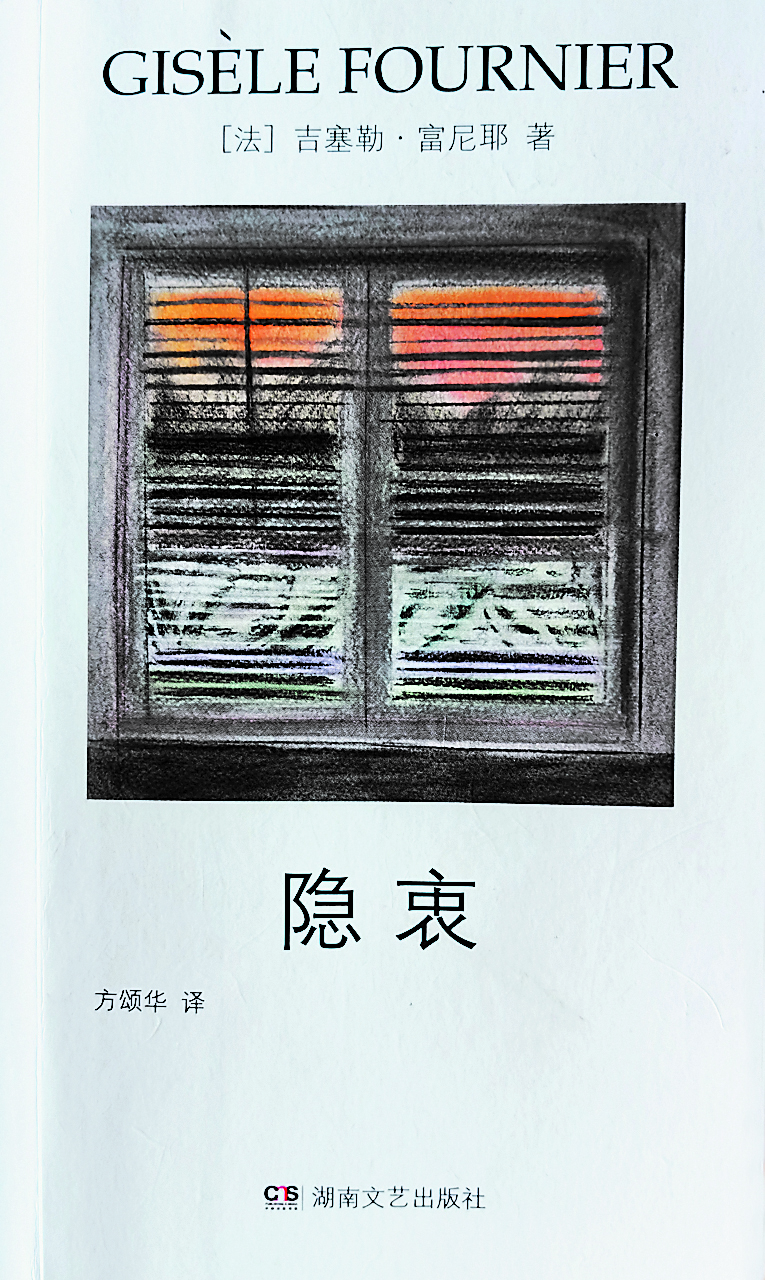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文字:刘合军 庞惊涛 刘诗哲 编辑:莫海晖 责任编辑:吴颖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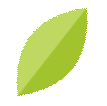
——读罗春柏诗集《记忆的绳子》有感
□ 刘合军
南国初秋,红霞日暮,有幸又一次与诗人罗春柏先生雅聚,并获赠诗人新著《记忆的绳子》,借着明灿的灯光,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书的封面庄重而又厚重色调,以及一轮朝红隐入淡淡山川与河流所酝造出的一幅智慧图案,接下来的是雄鹰展翅翱翔在云水之间,这仿若植入灵魂而又动感的场景首先对我有了磁的吸力。
我的思想之悟是随着——静、禅、爱,而跌落华夏文字的浩瀚与无垠中的,这是一种生命与智慧,阅历与思考,内心与繁杂,希望与焦虑“外与内”互为修行的“无我”精神状态,一个人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做到排除外部环境的干扰,剔除繁杂而静卧流水风声,在冥想的世界去沉淀自己的思想,用有限的空间去营造一个更广义的、脱俗的豁达之心去对待和发现平凡中的一切事物,这就是一种境界。七情六欲是每一个人的人初共性,诗人也不例外,爱是人间之大善,有父母之爱,子女之爱,友人和对万物悲悯之爱,也有对他人予以关怀与培养之爱,诗人罗春柏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大善之爱,而感染了身边太多的文学爱好者,用文学之爱温暖和激励了更多身边的新人。
我轻轻漫步于《天容海色本澄明》叶延滨老师为《记忆的绳子》新著之序,更进一步地品尝到了诗人创作之风、之气、之爱与之禅,感受文字与诗品的高雅和人性探求之大美与大善,读到语境中那份对名与利的淡泊,就像诗人语录“一个人/一支笔/洗尽铅华的清绝。”也读到了诗人澄澈的精彩世界与风轻云淡的恬静,安祥之高远。
随晨风吹开的页面,我静静打开诗人宝藏,扑面而来的是《沸动的春天》,就找到了阳光的密钥读到诗歌与意境的美感,“温柔的风、轻轻的雨”共同营造出宁静而美好的氛围。雨滋润着玫瑰种子,使其萌发,展现出大自然的生命力。“那片土地拂动/春天的旖旎”,让人仿佛看到了春天里生机勃勃、色彩斑斓的景象,这种语言的美感像春风一样吹拂和浸润着心灵的明亮。进而诗人将活力复苏沉睡的江河,流水奔涌,带来了玫瑰色的阳光和燕子的双翅。这里既有江河复苏的动态感,又有阳光和燕子带来的温暖与生机。“你款款而来,歌声/在青青的田野飘逸”,为整个画面增添了一份灵动和诗意,让人感受到一种美好的期待。通过这两节的赏读,让读者充分感受到艺术,意象与语言的运用,读到风、雨、玫瑰种子、江河、阳光、燕子等来自大自然丰富的意象,这些意象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玫瑰种子象征着希望和美好,江河象征着生命的流动,阳光和燕子则带来了温暖的生动活力。“滋润”“萌发”“拂动”“奔涌”“飘逸”“玫瑰色的阳光”为诗歌增添了一抹温暖而浪漫的色彩。上述动词的运用,使诗歌更加生动形象,增强了更灵动的画面感。通过对自然与景象的描绘,传达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让人感受到诗人内心的澄明和对生活中的美好与希望。
诗歌是聆听心声酝酿神思引燃的火线,他在自己特定的环境与状态下引爆和炸响,发现是一种闪电内燃“材料”,存在与表达是对自然与万物变化的敏锐观察,这“材料”就是语言与灵魂的赋物。读《太阳与海》,它是一首充满了强烈的画面感和对比感的隐喻与述说作品,其手法贯以雄浑与宁静:诗的前半部分描绘了一万头雄狮在咆哮和撕咬的场景,充满了力量和狂暴,给人一种仿佛世界即将被吞噬的压迫感。而后半部分则转向头上那轮不慌不忙的太阳,它投下一缕缕光,轻抚大地和疲惫的海浪,营造出一种宁静而温暖的氛围。这种强烈的对比使诗歌的意境更加丰富和深刻。诗人通过自然的力量,雄狮代表着自然的强大,它们的咆哮和撕咬展现出大自然的狂野一面。而太阳则象征着温暖和希望,它的光轻抚大地和海浪,体现了大自然的温柔与慈爱。这种对自然不同面的描绘,让人感受到自然的复杂与神秘,诗人拟用艺术夸张与对比手法,同时,与太阳的不慌不忙形成鲜明对比,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太阳和海是两个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意象。太阳代表着光明、温暖和希望,海则象征着广阔、深邃和神秘。它们的组合使诗歌具有了更广阔的内涵和更深的情感,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和赞美之情。通过对雄狮和太阳的描写,诗人展现了自然的强大力量和温柔之美,让人感受到自然的伟大和神秘。同时,诗歌也传达出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让人在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也能从中汲取力量和勇气。
珠海乃山水秀美、诗意灵动的诗者栖居之地,它不但孕育了一方水土,也孕育了历史与现代诗歌文化,读先生的诗会使人心思愉悦敞亮。读到山与海那些奔腾的语言,《外伶仃岛》,写外伶仃岛的诗人有一万种写法,罗春柏的伶仃岛除了湛蓝,还有摇晃的天和摇晃的海,这里不但刻录下乘舟驾浪画面感,也刻画出此境此情之“白浪/远方”。读《雾锁金台寺》,就是读他的禅意,读木然于世的石阶,读“烟云”与香火,读扬幡于钟声的一场又一场法事和众生冀望的艳阳。读《在抚仙湖致徐霞客》,是少女与雾霭遮掩下的纱巾,荡漾的一个一个故事,陈砖旧瓦展开的马鞭花和多情风喂暖的“醉”游人。读《凭吊》,你能读到埋藏于野的一部史书,读征人的悲壮与离愁,硝烟与惊雷遗落在云天与雾雨的他处。
诗是牵引灵魂的圣物,每一字都是呼唤生命中的语言与“真情”,写诗既可以是神旨的陈述,也是烟火与尘土传承,现代生活中,我们需要在物欲与喧嚣中发现或找到寄养灵魂的一块静地,找到另一个自己,那就是写诗和读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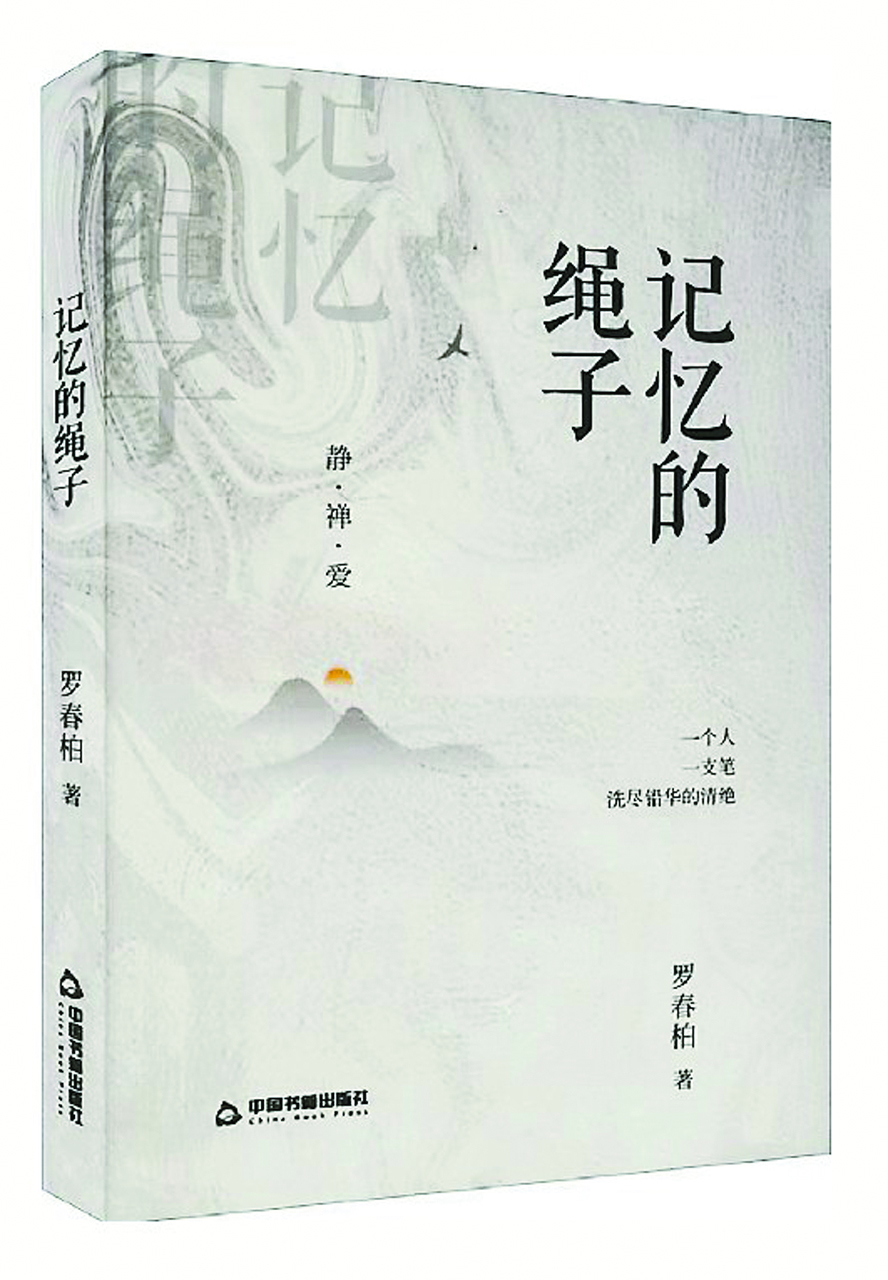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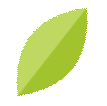
——雍也《从诗经出发》的三个学理维度
□ 庞惊涛
作家雍也继《回望诗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年6月)之后,深研细磨,纵横比较,再一次推出了《从诗经出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这部《诗经》研究的开创性力作。其综合调度的比较哲学、比较神学和比较美学三个维度,将《诗经》研究置于更深广的时空关系之中,不失为借经典向海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
比较哲学:天命观的问题意识
雍也在《从诗经出发》中用力最勤、体虑精深的一篇,即全书第一篇:《天命观》。此篇系于该书的上篇,总名之为“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当然指向中西之间《诗经》研究璀璨若锦的喻意。“天命观”问题的发现和提出,是我认为雍也这部作品里最显理论功力的代表和集大成。从方法论上看,显然是借助于传统文学的入口,而用了比较哲学的解法,最后达成问题的初步解决。
剖析其问题意识的形成和结论的形成,我大约可以梳理其比较哲学形成的理路:
一是《诗经》篇目的连类。雅颂诸篇中的政治属性,历来容易被普通读者忽略。但雍也却敏感地注意到这些篇目中的表述,“像散落在草丛里熠熠生辉的花朵,带着周人赋予的特别的气息。”将这些篇目连类,他发现了周人天命观的三重意涵。
二是对近世以来中国哲学家对周人天命观的幽光灼见进行了列举。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他们几乎就是在西方比较哲学概念提出的同时,对《诗经》中雅颂诸篇中的东方哲学“天命观”进行了深入的探析。这是雍也为最终驾驭比较哲学这个手段,为他的结论服务的理论关键和理论基础。
三是由此及彼、由内而外的理论推演。当《诗经》天命观的来源和形成愈益清晰,其意义的探求已然完成,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东西方天命观比较及其结论的形成,就是水到渠成之势。“西方也有天命一说。”看似波澜不惊的一句,其实是比较哲学在本篇中最为动人的一次桥接。基于此,柏拉图、希罗多德等西哲的哲学思想被拿来作为《诗经》天命观的阐释和比较对象,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比较哲学必然要指向哲学思想的异同之处。“中西两种天命观有一个共同点:人都受命于天,为其主宰。”但更多的还在于差异。所谓差异,或许也可以理解为雍也比较哲学的结论:“西方天命观较之中国天命观,宿命论色彩重得多,而中国天命观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强得多。”此外,“二者建立的情感基础不同”“追求路径也不同”。这些不同,虽然属于典型的“拿来主义”,但谁又能否认,雍也在比较哲学视野下,“发现”的价值呢?
比较神学:咒语何以产生魔力?
相较于比较哲学的成熟,比较神学在学术上还显“稚嫩”,或者说“年轻”,也因此显出其特别的朝气。雍也在《从诗经出发》里,看似无意、实则有心地从《诗经》中一些比较不为人注意的篇目研究出发,通过爱情、美人等易于公众接受的话题探析,从而带领读者进入到比较神学的“年轻”学术之境,深得通俗引向雅致的学问探求和普及传播之法。
雍也引出的小诗,是《东方之日》。在主流观念里,此诗“刺衰”,写“男女淫奔”,故不宜大众传播。但雍也却在此诗中看到了爱情,或者更直接地说,是爱情咒。在印度《阿达婆吠陀》里,“要你爱我,永不离分”岂不就是《东方之日》里“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的爱情咒语?为此,他引用任乃强先生对“发”本意的阐释,认为不是历史上几成定论的“行也”或“言蹑我而行去也”,而是“猎人捕兽之机栝,践之则机发”,换言之,有“机关”意,这就更有“咒语”意味了。他还引证叶舒宪对南太平洋原始民族民歌,来考证这咒语中近乎巫术的部分。在日本学者白川静看来,“歌谣源于撼动神明,祈祷神灵的语言”,所以,这样的神性咒语,大约脱不开神学的范畴。与之具有同样性质的,还有《何人斯》《巷伯》中这样的咒语。既然《诗经》中有咒语诗,那么,就存在爱情咒的可能。更进一步,这样的爱情咒,就能在世俗社会里产生感染人和影响人的魔力。
只是稍微遗憾的是,如果印度和日本的咒语诗和《诗经》里的爱情咒语,都指向神秘的东方的话,那么,比较神学的范畴,大概还缺失了美西从神话时代向传说时代过渡时代的咒语诗——它们大概率上应归结于神学范畴。
在另一篇题为《一个绝代佳人引发的“国际风云”》的作品里,雍也用同样基于比较神学的手法,来进行中西比较——当然,鉴于神话学和神学本质的差异,此处用神话学似乎更准确一些。雍也引用《诗经》中的作品,也是一篇不太为大众所熟知的《株林》,其指向可能更接近于半信史时代和信史时代之间的神话学。夏姬的故事未保真有,但也不能说全是神话,和《伊利亚特》中的海伦一样,模糊的文字,往往塑造出一个个清晰的美人。夏姬其时,华夏民族正处于自由无羁、天性无束的童年时期。两个美人的比较,其实是两种文化的比较,她们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都清晰地指向她们背后的时代、社会和世俗认知。
这样的比较视野,不仅让枯燥的“解经”妙趣横生,也能帮助我们通过借助《诗经》的阐释,抵向更开阔的文化空间。一言以蔽之,《诗经》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自我的过往,也帮助我们看到“他者”的过往。在“自我”和“他者”之间,诗歌怎样作为桥梁,如何帮助我们缩短了历史的时空。
比较美学:战争的大义与悲伤
如同一个圆满的环,《从诗经出发》开篇阐释比较哲学,其终篇则指向比较美学。作为一种美学思潮,比较美学从20世纪初开始确立,并受比较哲学等比较学科的影响而得到发展。雍也将《诗经》中关于战争的篇目拈出,并与《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进行比较,从而提炼出了中西大异其趣的战争美学,颇具手眼的同时,也从“血与痛”“歌与哭”的主题昭示中,显示了自己具有诗人气质的大义立场和人文关怀。
在雍也看来,《诗经》中对特定战争行为即正义战争的歌颂与认同的篇目,不仅代表统治阶层的价值观,同时也理应受到广大群众阶层的理解和支持。其称颂战争的道德之美、军阵之美、人格之美和情怀之美与人性之美,都是大义或者正义战争的东方美学构成。和《荷马史诗》中的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的“暴力美学”颇为不同。在雍也看来,“化悲痛为悲哀,化悲痛为悲壮,这正是《诗经》与《荷马史诗》呈现出来最大的美学之异。”
在指出中西战争美学的不同之后,雍也对《诗经》中这些关于战争的篇目的阐释,以及随后进行的美学比较,显然还需要指向一个更具体和深刻的思辨维度。在这部以学理性见长的著作里,我每每为雍也跳出逻辑严密的论证和推演,而发出基于比较视野下的哲思和提示而拍案——比较美学作为一种方法,终极的价值,正是这样超越一般性解经的哲思和提示——尽管它偏于强烈的个人旨趣,但我能想象,这样的个人旨趣,会引发相当多的共鸣。这大约就是借助于比较美学让我们提升对《诗经》文本认知的最好的阐释。
杜甫说,“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在这样的比较视野下,《诗经》的研究和传播可以引入更为广大的文化天地。雍也借助对《诗经》的阐释,或者说“从诗经出发”的真正命意,是倡导一种宽广的文化胸怀和历史眼光,从而让《诗经》带着我们,到达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多元文化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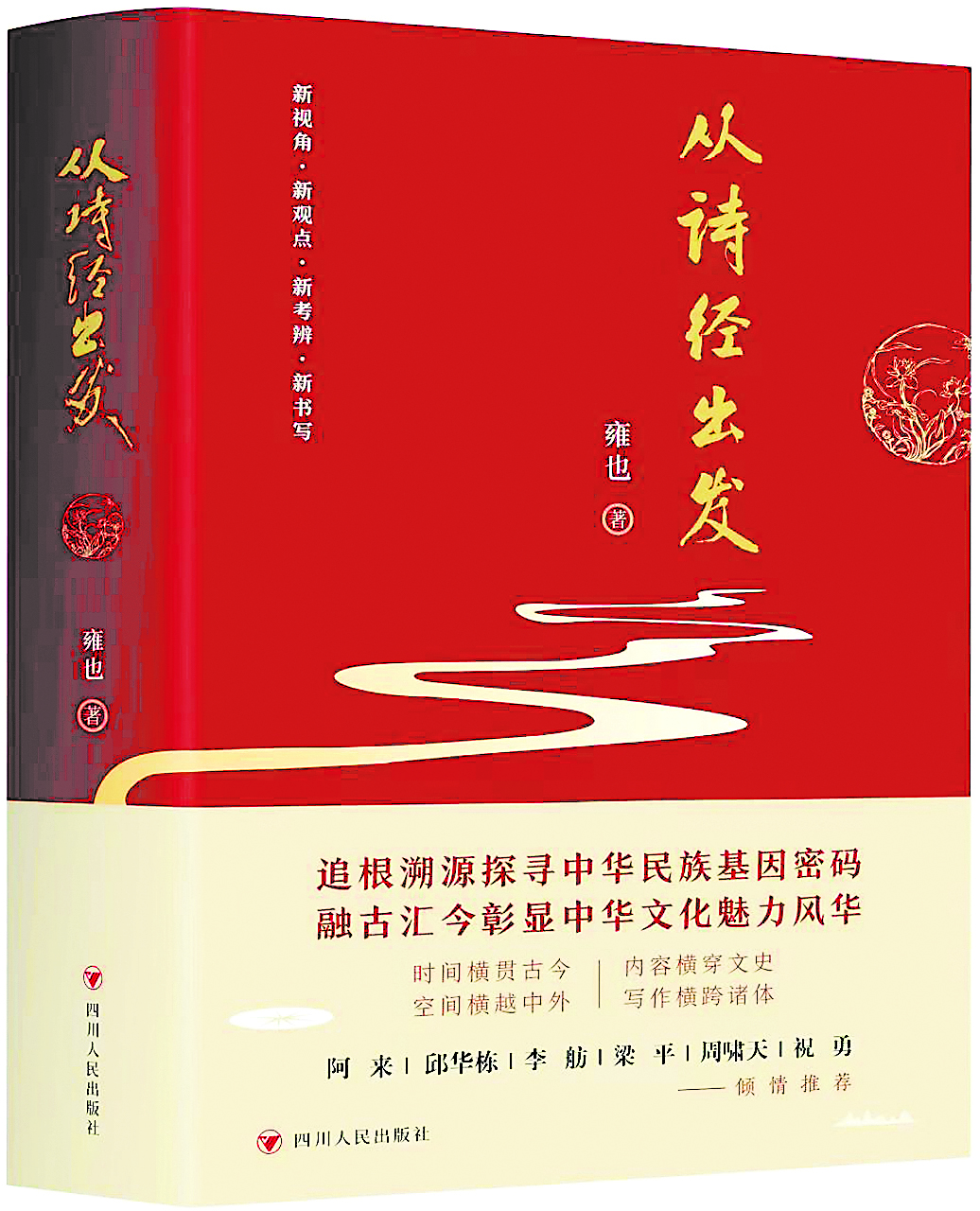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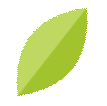
——读《隐衷》
□ 刘诗哲
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回到童年的老房子,试图理解三十年前在这里上演的悲剧。“我不知道是哪根线把我又拉回到这里。”小说就此展开。一个暗含疑问的陈述句,显示一个路标:读者期待的一切答案从这里开始寻找吧!
这部书名《隐衷》的小说,是法国新小说作家吉塞勒·富尼耶著,方颂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3月出品的“午夜文丛”系列作品之一。吉塞勒·富尼耶生于1953年,曾在巴黎从事金融分析工作多年,后定居日内瓦,致力于写作。《隐衷》是她第一部小说,其法文版2000年由法国午夜出版社出版。
翻开这部小说素雅的封面之前,书名就引起我的猜测:会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是探讨人物内心世界、秘密情感或者不为人知的想法的释疑之作,还是围绕人物复杂心理、人际关系的微妙或者私生活中难言之隐展开的故事?我预感到它将带给我阅读的欣喜。
阅读完小说第一节,我最初认定,这是一部“我”(玛蒂尔德)通过追忆构成的小说。但很快发现,我犯了经验主义错误。玛蒂尔德只不过是率先出场的那一个。一个引子。接着出场的人物:托马、蕾阿、卡米耶、不忠的母亲丽莎,甚至是死去的父亲莱昂斯都成了“我”,都是叙事、回忆与内心独白的主人公。他们站在各自的立场和各自的视角进行叙说,让每一件事都找到各自意义,各归其位,共同描绘和编织一个立体杂驳又内涵丰富的玛蒂尔德的童年。这让人想到中国成语“盲人摸象”,每个盲人能说出自己摸到的那个部分,所有人加在一起,就是一头完整的大象。
小说的人物关系并不复杂,而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令人咋舌。小说将人性的幽微:复杂、微妙与难以捉摸,多面性与深不可测揭示得淋漓尽致。而每个人内心独白又像是在密室里向神忏悔,从而揭示出那些隐藏得很深又涵泳在因果之中的隐衷。
蕾阿阿姨的隐衷应该有两个:一是因家道中落无力维持生活,而设计招赘成为妹妹卡米耶丈夫的、前佃户之子托马,让他成为一个好劳动力。二是自己初恋、因某种缘故成为自己妹夫、最终死于猎枪(尽管作者含糊其辞,故设迷阵,但读者还是读出了死于自杀)的莱昂斯。
对于托马,他并没真正爱过自己妻子卡米耶,甚至一点都不喜欢她。“但只有通过婚姻这条唯一的途径,我才能回到这片土地,让它结出硕果,我还想成为它的主人。”这是托马的隐衷。当他知道妻妹丽莎对自己产生兴趣时,不但不采取任何举动加以阻止,还任凭事情往下发展,“借此机会,报复这两个为钱坑我的女人(蕾阿和卡米耶)”,这不过是“一次小小的反击。”
卡米耶面对丈夫与妹妹的奸情隐而不发,除了怕撕破脸皮彻底失去丈夫,还想将这件事当做手里一种说不定哪天可使用的秘密武器。她还有一个不可示人的隐衷:通过跟踪偷窥还有想象,让自己得到某个方面的满足。
小说人物中最可怜的人物莫过于“我”的父亲莱昂斯。一个死于非命的人,有情人未成眷属,草率结婚的妻子又红杏出墙,自己一味忍气吞声,佯装不知情以保全颜面,当女儿遭受托马猥亵告诉他时,他不但不出头为她申张正义,还责怪女儿胡思乱想。中国有句老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可怜又可恨之人,最终颜面无存时,只好选择死这种永远的麻木形式。
至于“我”——玛蒂尔德,这么多年过去了,何苦又回来?“因为近来,又或许是长久以来,我内心里存在着一种渴望,一种迫切的需求,想知道事情的原委。”我想,玛蒂尔德想弄清楚童年生活里的每个人的隐衷,就是自己的隐衷吧。“所有这些隐衷,我从来都没搞明白。”小说最后一个小节里,她如是说。事情果真如比吗?显然,聪慧的读者已从阅读得到很多答案。
“我”,沉浸在夏日午后的颓唐里,“我”的回忆是它唯一鲜活的部分。最终,“我”来到一个岔路口,选定一条狭窄、蜿蜒的小路,“我顺着路继续开了下去”。就小说艺术来说,一种未完成的开放结局,往往是最迷人的!
作为新小说之一种,这部小说并不“疯狂”,走得也不算太远,故事相对完整,也好理解。吉塞勒·富尼耶根据各自回忆(甚至根据需要让死去的莱昂斯也参与进来)“过去”来进行叙事,并与“现实”的叙述相对照而共同产生心理上的“厚度”,叙事的时间线有些错乱,但叙述逻辑不错乱。唯一要求读者专心致志的是,应时刻弄明白自己的目光与思绪正搭在哪一位主人公的情感线上,才能从纷繁复杂的交叉叙事中不至于迷失方向,并时刻准备随着作者笔锋转向而迅速拐入另一个主人公的另一条道路。
一个夏日午后,是一根风中飘着的无形的线,连着过往,又通往未来,成全一个没有让读者失望的小说。在此多说一句:《隐衷》译者方颂华先生的译笔很好,译文通顺晓畅,典雅优美,读之如饮醇醪,齿颊生津。遗憾的是,方先生于2020年辞世,令人惋惜。借此文向方先生致敬。
结束这篇短文时,突然想起诗人聂沛一首长诗的诗题:下午是一条远逝的河。这首诗的题记引用了蒙田名句:“我们的世界刚寻找到另一个世界,一个未必不更辽阔、更广博、更充满生灵的世界。当我们走出光明之际,那一个世界则进入了光明。”这也是我想对新小说讲的题外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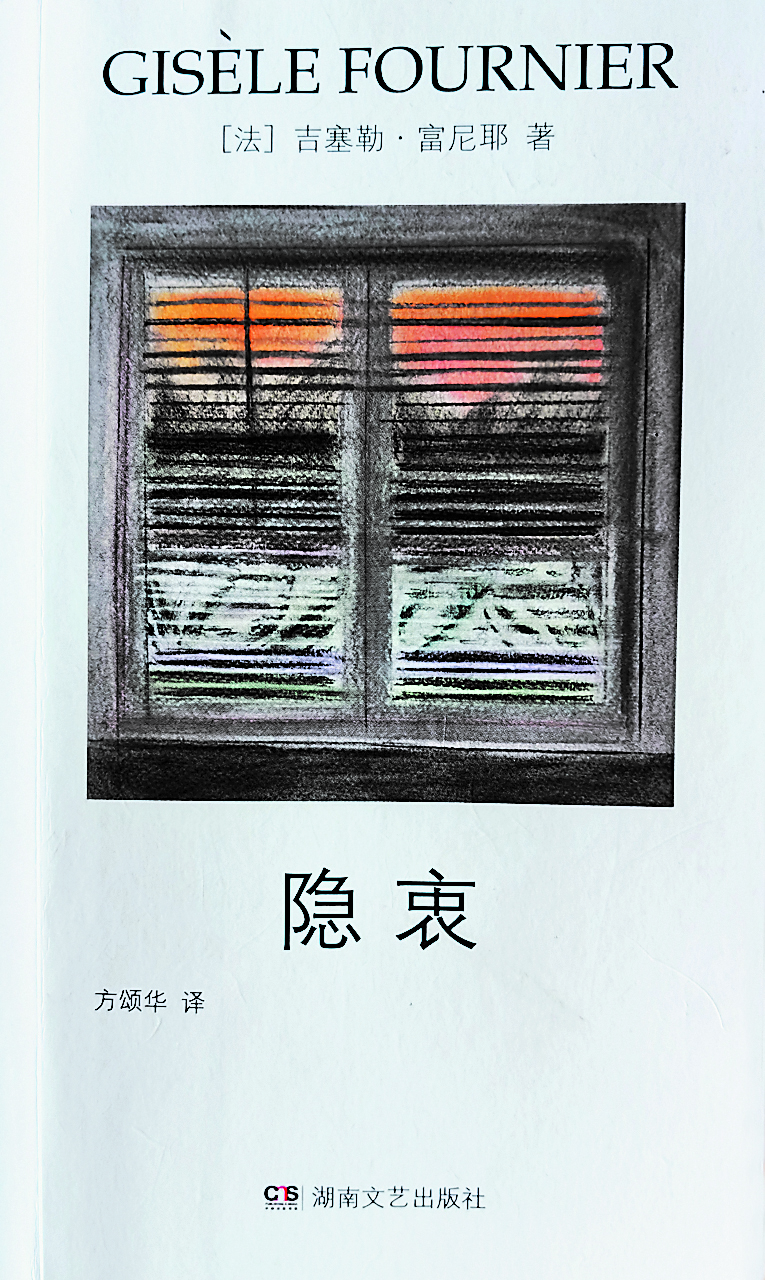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文字:刘合军 庞惊涛 刘诗哲 编辑:莫海晖 责任编辑:吴颖琼

-我已经到底线啦-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