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一安 崔云 智通义 林伟光
2025-09-27 02:04
李一安 崔云 智通义 林伟光
2025-09-27 02:04



□ 李一安
我最原生态、最本真的文化名片是编辑,自认“小作家、老编辑”,自诩当编辑还有点慧根。编辑的职业毛病是手痒难耐,常常鸡一嘴鸭一嘴地对过手的书稿品评几句,朋友们称之为点评,究其实,也就类似在岗时的审读意见或曰编辑手记。套用秦晖教授一句话,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就是后人眼中的历史;我们现在所讲的历史,就是前人留下的作品——兹事体大。
一
祝贺林小兵获苏曼殊文学奖暨他的散文集列入曼殊文丛出版。这是第一次由珠海市作家协会和珠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袂为他——一个业余作者召开的研讨会!
匆匆浏览了小兵的散文集《点点灯火》,有两个感触,一是从作品中感受到了作者深厚的人文情怀,他用自己人文情怀的点点灯火照亮他周围的人、事、物、景,也照亮自己的人生历练。从身边从警的同事到桂北山区支教、帮助脱贫攻坚的战友甚至万里之外奋战在边关的巾帼英雄,他给予关心关爱和敬佩敬重,并热情歌赞,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好人好事;对家乡吴阳镇点点滴滴的记叙,父亲的单车背,放牛的故事,过年的传统仪式感,海难的悲凉,同村清道光年间的状元林召棠,乃至北上读大学时藏在身上的6000元钱……也不仅仅是家长里短的记忆碎片。这些点点灯火照亮的点点滴滴读来真实真切,启迪心智,人文情怀的因子就弥漫于这些细节,温暖中不乏酸涩和沉思。二是小兵的文学语言已经到了比较纯熟的程度,高出一般业余作者很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鹏凯初次接触小兵的作品就觉得他语感不错,小兵自己也认为他对语言的敏感来自日记的锻炼和情书的写作。他的语言朴实无华,不堆砌、不造作,不掉书袋,低调务实,但在平朴的叙事中寥寥几句描绘景物、天气的所谓闲笔,却很见功力。小兵认定他找到了散文这种他认为最好的文学形式,他的散文写作也超越了一般业余作者的水平,如果有时间,建议小兵可以扩大阅读面,比如读读西部军旅作家周涛的散文和茅奖得主刘亮程的散文,如果还有探讨的兴趣,可以看看石耿立教授关于散文创作“拒绝合唱”的学术论文,避免散文创作同质化,以提升自己的认知高度和开拓自己的创作视野。希望小兵随着观察、阅读、思考的深入和年岁的渐长,由文学小兵成长为文学大兵,最终能成长为一个硕果累累的文坛老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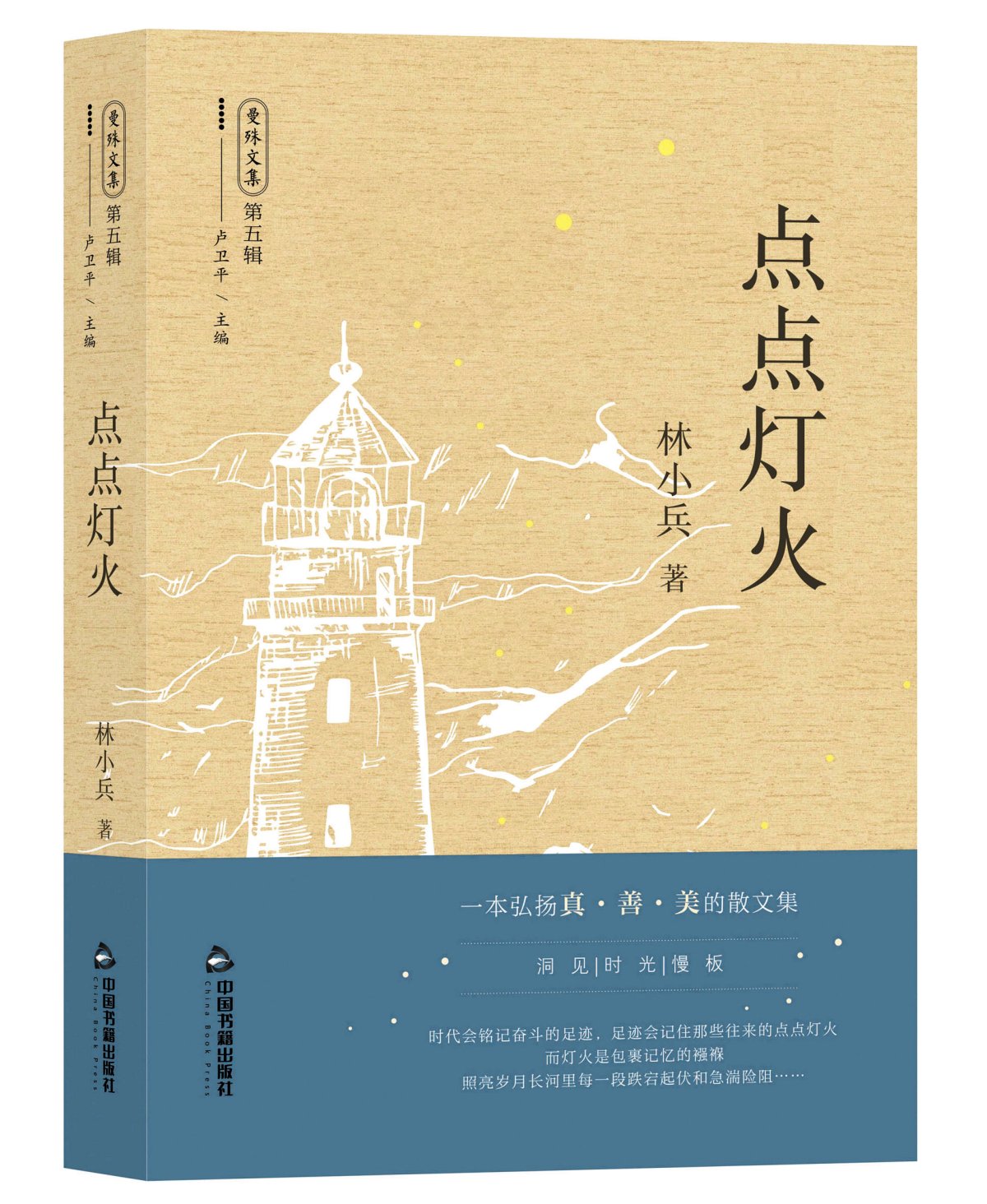
二
中篇小说《枪手》,作者杨晓升,载《芙蓉》2024年第6期。遇见“枪手”,此“枪手”不是彼“枪手”。此“枪手”大略有点类似旧时的刀笔吏,刀笔吏又称讼师,替人捉刀,代写讼案,不具其名,换点银两;今天的枪手则替人捉刀,代写文案,没有名分,酬劳丰厚。作品中的凃文贵便是一名代写电视连续剧的“枪手”。作者杨晓升用白描的手法、平朴的语言,将笔触直捣“钱眼”,在金钱的“诱惑”下,在以金钱为故事核心的外壳包裹下,一步步将读者引入亢奋,一步步将在小说创作上斩获颇丰而生活相对窘迫的凃文贵“逼”着走上了争取财务自由的奋斗之路。凃文贵成功了!凃文贵成功了吗?这是一个悬念,这是一篇“好看小说”。杨晓升现实主义的笔法几近原生态反映出现实生活中的二律悖反,凃文贵从重名轻利到重利轻名的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的嬗变,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命题,人生目标的选择,生活方式的选择,其实是一种社会生存哲学的驱动,因此,《枪手》的社会学意义也挣脱故事的桎梏横空出世,给人联想,发人深省。于是,我就揣摩着,晓升兄久有凌云志,执念于文学情结,或者说怀有文学梦想,与他笔下的人物凃文贵一样近年佳作迭出,已在小说界声名鹊起,那么,他是否会像凃文贵一样“华丽转身”充当“枪手”,捉刀炮制影视剧集,然后暴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呢?
三
长篇小说《躁动》是年近九秩的老作家陈伯坚先生耗时26年反复思考、打磨、殚精竭虑的精品力作。《躁动》是心的躁动,情的躁动,性的躁动,人的生命意识在躁动中复苏,在复苏中滋长蔓延,在蔓延中激活原创力。伯坚先生笔名陈年酒,《躁动》正是伯坚先生捧上的一坛浓香馥郁、醇厚绵长的陈年佳酿。
小说以珠水先暖的改革开放时代为背景,以与澳门一水之隔的大锅岛为舞台,以马头山“神水”的开发为核心,演绎出一部历史活剧,高扬着对“人本主义”的礼赞。小说围绕马头山“神水”的开发,在人性的复归、人性的勃发和理性自控的矛盾过程中发展,最终对“欲”的野蛮生长之“度”的思悟,把社会学的现象推升至一个哲学命题的高度,从而给《躁动》赋予了思想活力和精神魅力,为大湾区文学长廊增添了一抹崭新的色彩。
四
数年前邂逅罗春柏,我尊一声“罗书记”。他自诩为一介布衣,大隐于市,平实低调。书记者,古已有之,用以指称记事的书写文字,三国曹丕的《与吴质书》中“元瑜书记翩翩”即指章、表、书、疏等类文体,近些年,罗书记诗誉盛传:获广东省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第四本诗集《记忆的绳子》在诗者们的殷殷期盼下付梓出版、其个人诗歌创作研讨会在碧波万顷的伶仃洋簇拥下盛装登场……罗书记以静水深流的诗意逻辑抒情愫,抒遐思,抒禅悟,抒清绝,以及对山水田园、一草一木的细微体察。人如其文也好,文如其人也罢,他的诗没有金戈铁马,没有大开大阖,整体呈现内敛沉静的阴柔美,诗语修辞绵密、圆润温婉,有的诗句切入中国文字奥妙的肌理,如甘草橄榄,让人咀嚼良久,意味悠长。
五
梁冬霓,一个音韵平和的名字,一个点缀冬的淡妆和霓虹玫瑰蕴藉着诗意的名字,一个在文字间恣意徜徉的客家妹,携着她的散文集《时光倒影》出现在一场文学盛宴上。翻阅这些文字,使我讶异的是,她对文学的热爱,对文学的追求,甚至对文学的膜拜都迥异于一般作家——有人在文字间寻梦,有人在文字间刷存在感,有人凭借文字的排列组合展露才华谋取物欲……这都没问题,都无可厚非,而冬霓却自以为幸运地认为“文学让我找到灵魂的皈依”,她深知“文学对于我的意义更多的是安放灵魂,修正内心,传递真善美,在生命的渡河中,为自己,为他人,做一个摆渡者,从荒莽的此岸,渡到花开的彼岸。我相信,文学会让痛苦成为一种救赎,让幸福成为一盏明灯”。这种特立独行,这种孤高,这种清越,这种对文学敬畏的情结和精神力量使人感佩,也许这就是她自我价值的文化密码以及经营文字的控制模板吧。因此她从自己的文学世界出发,抵达现实世界的各个角落,乡情、友情、亲情,生活的斑斓多彩和五味杂陈都涌现笔端。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用两支笔写作,一支笔写散文,一支笔写评论,两支笔互为伯仲,用自己的才情和慧眼游走于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之间。
不可或缺的是,黄龙汉先生的序言堪称字字珠玑,给《时光倒影》精准地勾勒出一道绚丽的光影,彰显着提携、奖掖文学后进的伯乐胸襟和人文情怀。
朋友们,坐下来,静下来,读读《时光倒影》,读读梁冬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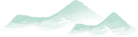
为凡人而歌
——散文集《照见》自序

□ 崔 云
写作在我看来,犹如春蚕吐丝,丝丝缕缕,持续不懈,最终织就一幅完美的图案。蚕儿之所以能源源不断地吐丝,在于它摄入了足够多的桑叶,汲取了足够多的能量。同理,写作也需要作者不断汲取生活的养分,拥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与体验,才能写出有血有肉、能够打动人心的文字。
我一直坚信,好文章是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发乎心而为文,只有当写作者的情感、智慧与思想真诚地融入文字之中,作品才会散发出温暖与力量。渴望通过文字抚慰读者的心灵,这是我作为写作者的最大心愿,并一直为此努力着。
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人总给我最多感动。也许是出生于农村的缘故,我平时喜欢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身边的普通百姓,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质朴善良,他们努力奋斗的样子,都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着我的心怀,并鼓舞和鞭策着我,让我情不自禁拿起手中的笔。小区里的保安、办公楼的保洁员、菜市场的小商小贩、流水线上的打工者、花艺市场的花农,在城市里奔忙的的士司机、快递小哥及家政人员,还有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建筑工人、田野里辛勤劳作的农民等,他们都是我笔下的主人公,他们虽身处社会底层,却都在尽力发着光和热。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的世界才变得更加干净、舒适与便捷。他们的笑容、泪水、汗水,都是那么真实而感人。他们积极阳光的心态和努力生活的样子真的很美,是他们教会了我更加热爱生命、珍惜当下。
2001年的金秋十月,我怀揣梦想从荆楚大地来到经济特区珠海,一转眼已是25个年头。由于从事社团工作的缘故,20多年来,我打交道最多的群体是民营企业家,他们是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更是慈善事业的“领头雁”。他们身上那种坚韧顽强、拼搏创新、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让我深深为之折服。对于家国情怀,他们比一般人的理解更为透彻,那就是慎始如终地认真践行。顺境逆境、成功失败、荣辱得失,他们的领悟比一般人要真切而深刻。创业、创新、创富,是每一位有追求有梦想的民营企业家的使命,他们驰而不息,乐此不疲。在商海中搏击,可谓惊涛骇浪,瞬息万变,凶险难料。从风光无限到一无所有,有时可能只是一个错误的决策,或是一场意外的天灾人祸。我常常感叹,没有强大的心脏,是难以承受如此重压的。面对各种风险和不确定的因素,他们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无怨无悔。正是这些平凡的民营企业家,给了无数人就业的机会,给了无数个家庭安稳与幸福。因而我常常会将钦佩的目光投向他们,写他们艰辛的创业历程和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写他们的大爱善举和追梦故事,传递人性的善良与美好。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是一场寻找自我的旅程。终其一生,都是为了抵达自己,与更好的自己相遇。写作如此,干其他工作亦如此。对于我来说,故乡始终是我心灵的归宿。不管走多远,不管离开多久,它总牵引着我的视线,令我魂牵梦萦,也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那方水土那方人,故乡的一草一木和田野里长出的故事一直在我笔下流淌——年少时最爱逛的乡村集市和说书场、最爱看的村戏和乡下电影,最爱去的小竹林和小池塘,还有那淳朴善良、勤劳勇敢的乡亲……每次写故乡的风土人情,都是一次与故乡的精神重逢,让我欣喜与感伤。那熟悉的土地和人们总能激发我无尽的创作灵感。乡亲们那家长里短背后隐藏着的生活智慧、闲聊时的情感碰撞,都散发着泥土的芬芳,让我心生感动,情不自禁地拿起了手中的笔,定格下乡音、乡情。
如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我,亲见亲历了太多人间的生离死别和悲欢离合,更加深刻地领会到生命的无常和生活的真义。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只是希望能够通过我的文字,传递出某种情感和力量,让读者朋友能从他人的经历、感受或故事中得到启发,找到心的出口和前行的方向,人生多一些快乐与幸福。
在我看来,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他们是生活中最美的风景,也是我创作的不竭动力与源泉。
写作不仅是一种表达,更是一种探索。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或许我们都渴望找到一个宁静的角落,聆听来自心底的声音。而我,愿意用手中的笔,为那些普通但不平凡的人们歌唱,让他们的故事恒久流传……

寻常咏物 意蕴深远
——赏析当代诗人叶宝林的“赋律”
□ 智通义
当代诗人叶宝林一组题为《赋律》的七律作品,读后令人耳目一新,心有所动。这34首以“赋”冠名、以“物”为题的律诗,看似寻常咏物,实则意蕴深远,展现出作者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力与独特的哲思艺术风格。从蚂蚁、蜉蝣、蝼蛄等微小生灵,到扇子、雨伞、拐杖等日常器物,叶宝林以“小物”为切入点,借物抒怀,托物言志,将个体生命体验、社会现实观察与宇宙人生哲理融为一体,构建出一种“小物大思”的独特创作格局。其诗不仅在艺术上达到情景交融、意境悠远之境,更在思想层面体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易经》《道德经》等经典哲思的深刻体悟与创造性转化。
叶宝林的创作思想核心,可归结为“以物观道”。他并非止步于对物象的形貌描摹,而是将每一物视为“道”的具象载体,通过对其形态、习性、命运的细腻刻画,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生命哲理与宇宙法则。物即道,道寓于物,二者互为表里,浑然一体。如《山泉赋》:“辞高一去归溟底,利世芸芸道未争”,以山泉自高处奔流而下、润泽万物却不争功名的品性,暗合《道德经》“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核心思想。山泉之行,即“道”之行;山泉之德,即“道”之德。又如《水酒赋》,写酒体的水火相融,假杯中之物,揭示了《易经》里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理。
叶宝林的写作风格,呈现出“寓庄于谐、以小见大、虚实相生”的鲜明特色,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其艺术魅力的基石。
“寓庄于谐”是其智慧的外化。他常以轻松、诙谐甚至略带调侃的笔调,书写严肃深刻的社会批判与人生思考。如《苍蝇赋》中“屏风正欲观虫画,借点青蝇构墨图”,化用“误点成蝇”的典故,将苍蝇之“污”与画壁之“洁”形成强烈反差,讽喻现实中某些“污点人物”对清正环境的破坏,语言机智,讽刺犀利,令人会心之余又不禁使人警醒。《南郭赋》则借“滥竽充数”之典,直指当下人才评价机制中的形式主义与虚伪风气,“人才不抵伪人精”一语,直击要害,发人深省。这种“谐”并非轻佻,而是智者冷眼观世的幽默,是诗人对现实清醒而深刻的洞察。
“以小见大”是其最突出的艺术手法。他从不直接书写宏大主题,而是以最微小、最平凡、最易被忽视的物象为切口,从中开掘出广阔的思想空间。《蝼蛄赋》写地下之虫,“平生忏悔赎苗祸,舍与鸡虫兑蛋香”,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观察看待一个微小的生灵,既有批判的角度写其危害性,又有褒扬的角度赞其功用性,不仅可以松耕土地,更可舍身喂鸡换来“蛋香”,把一个无知的小虫,升华为一个知道“忏悔”有着“救赎”心态的“悟者”,充满了幡然醒悟的禅智。这种从“小”中见“大”的写法,使诗歌既有现实关怀的锐度,又有人文温馨的厚度,更蕴含文化反思的深度。
“虚实相生”则体现在其意象营造与意境构建的高超技艺上。叶宝林善于将具体物象与抽象哲理、历史典故与当下现实、自然景观与心灵世界巧妙融合,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审美空间。《红莲赋》通篇以“空”字贯穿,“内外皆空色与同”“红莲出水清空立”“藕眼虚心洞洞空”,创造出一个空灵澄澈、禅意盎然的艺术境界。《白云赋》写“远世离尘嫁与风,南浮北往任西东”,以白云的飘忽无定,喻示老子“无中生有”的宇宙观,其“心舒漫卷无还有,影去形消色去空”之句,更将物象的消逝升华为对存在本质的玄思。
叶宝林“赋律”作品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其对古典诗词格律的精深掌握与创造性运用。作为长期研究《周易》与诗词格律关系的学者,他深谙平仄、对仗、用韵之法度,作品严谨工整,音韵和谐。然而,他并不为格律所缚,而是在规范中求变,在传统中出新。
从对当代诗词创作的启示来看,叶宝林的“赋律”系列提供了宝贵的借鉴。首先,它证明了古典诗词这一古老文体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创作者能否赋予其新的思想内涵与时代精神。其次,它启示我们,诗词创作不必追求宏大叙事或华丽辞藻,从身边之物、日常之景入手,同样可以写出深刻之作。“以小见大”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观照世界的方式。再次,它强调了诗人应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与独立的思想品格。叶宝林的诗之所以能“小中见大”,正源于他对《易经》《道德经》《庄子》等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最后,它展示了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既尊重格律,又不拘泥于格律;既运用典故,又能翻出新意;既扎根传统,又能吸纳现代科学概念。这种“守正创新”的态度,正是当代诗词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 林伟光
读书,并不仅仅读而已,还有一个访书的过程,有的人说淘书,都是一种情牵不已的境界。
人性喜其新而厌其旧,唯有书却不怕其旧,我的几千册旧书,有不少都还没有读过,正好借此闲岁月以读,遣此有涯之生啊。
启功先生暮年有句:饮余有兴频添酒,读日无多慎买书。这份顺生心态,很好。我不善饮,偶尔的半杯已经脸红心跳,“频添酒”的佳兴,只好存于梦境,而这“慎买书”却恰如警语,故心有所触动,取此句而成俚语曰:回回梦里缥缃架,读日无多慎买书。苦暑思风茶伴我,新翻旧籍云卷舒。
最近,友人赠一本《知堂回想录》手稿本。此书我藏有好几个版本,却没有认真通读过,这回借着欣赏手稿,正好读它一过。知堂手迹,一直想收藏,终于如愿。
鲁迅的手稿集,自己也收有,虽不全,却是他晚年写“且介亭杂文”的一些原稿。鲁迅手稿,显出功力,他是钞过碑的,这份风骨在不经意中就流露出来,却也温润,令人赏心悦目。可以看出,他写作时的愉悦,从容的笔致中,蕴含郁郁的风情。那么泼辣的文字,可是笔下却是从容而舒徐的。而知堂的手笔,就不能跟乃兄相比拟了。虽然在娴熟的书写中,也有文气氤氲;不过,骨力却是没有的,只是一些拖泥带水的味道。
二周的文章,我都喜欢,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并且各成高峰。一是浓到极致,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一是淡到极致,总努力剔除情绪,在不动声色中行文。有的人总在讨论他们失和的原因,其实,所有的这或那的原因,通通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而已,他们都不可能退让的。
人老了,阅历多了,早已失却了风花雪月的心,只想喝一杯苦茶,故心境渐近于知堂。那么,已没有激情了吗?也不然。知堂文字虽好,却总嫌有些隔膜,离得远,就不如鲁迅的入世,有不少文章犹如写当下。可见这世界凡是人性,总归古今变化不大的。除非我们不去关心世态,变诸多的看不惯为司空见惯,或者才可以淡看。
读书,有时也读前人的往事与往思,觉得日光之下无新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杞忧也真的大可不必。这就是读书的好处,世事洞明之后,渐渐人情练达,可以一切只当浮云看了。



□ 李一安
我最原生态、最本真的文化名片是编辑,自认“小作家、老编辑”,自诩当编辑还有点慧根。编辑的职业毛病是手痒难耐,常常鸡一嘴鸭一嘴地对过手的书稿品评几句,朋友们称之为点评,究其实,也就类似在岗时的审读意见或曰编辑手记。套用秦晖教授一句话,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就是后人眼中的历史;我们现在所讲的历史,就是前人留下的作品——兹事体大。
一
祝贺林小兵获苏曼殊文学奖暨他的散文集列入曼殊文丛出版。这是第一次由珠海市作家协会和珠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袂为他——一个业余作者召开的研讨会!
匆匆浏览了小兵的散文集《点点灯火》,有两个感触,一是从作品中感受到了作者深厚的人文情怀,他用自己人文情怀的点点灯火照亮他周围的人、事、物、景,也照亮自己的人生历练。从身边从警的同事到桂北山区支教、帮助脱贫攻坚的战友甚至万里之外奋战在边关的巾帼英雄,他给予关心关爱和敬佩敬重,并热情歌赞,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好人好事;对家乡吴阳镇点点滴滴的记叙,父亲的单车背,放牛的故事,过年的传统仪式感,海难的悲凉,同村清道光年间的状元林召棠,乃至北上读大学时藏在身上的6000元钱……也不仅仅是家长里短的记忆碎片。这些点点灯火照亮的点点滴滴读来真实真切,启迪心智,人文情怀的因子就弥漫于这些细节,温暖中不乏酸涩和沉思。二是小兵的文学语言已经到了比较纯熟的程度,高出一般业余作者很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鹏凯初次接触小兵的作品就觉得他语感不错,小兵自己也认为他对语言的敏感来自日记的锻炼和情书的写作。他的语言朴实无华,不堆砌、不造作,不掉书袋,低调务实,但在平朴的叙事中寥寥几句描绘景物、天气的所谓闲笔,却很见功力。小兵认定他找到了散文这种他认为最好的文学形式,他的散文写作也超越了一般业余作者的水平,如果有时间,建议小兵可以扩大阅读面,比如读读西部军旅作家周涛的散文和茅奖得主刘亮程的散文,如果还有探讨的兴趣,可以看看石耿立教授关于散文创作“拒绝合唱”的学术论文,避免散文创作同质化,以提升自己的认知高度和开拓自己的创作视野。希望小兵随着观察、阅读、思考的深入和年岁的渐长,由文学小兵成长为文学大兵,最终能成长为一个硕果累累的文坛老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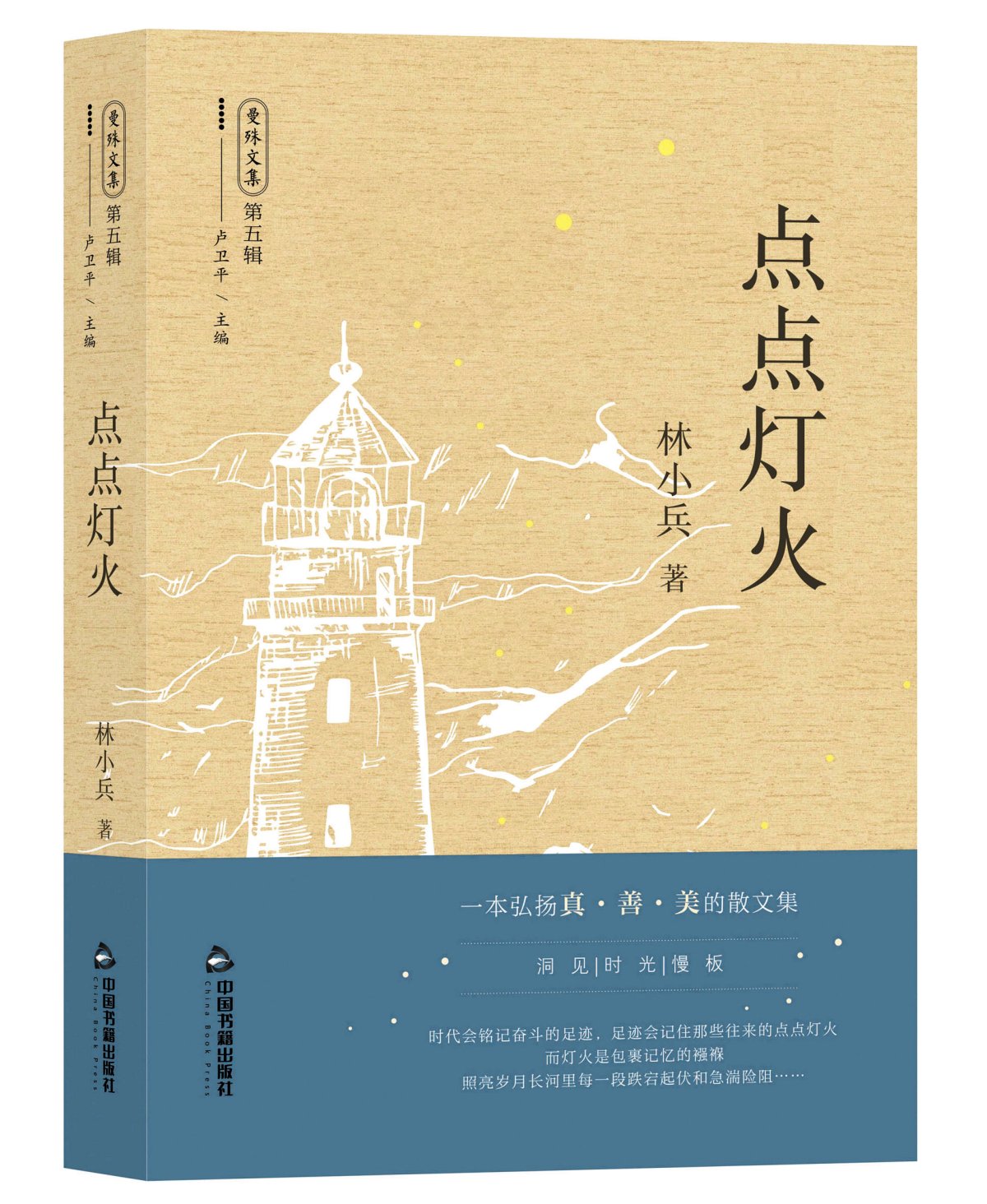
二
中篇小说《枪手》,作者杨晓升,载《芙蓉》2024年第6期。遇见“枪手”,此“枪手”不是彼“枪手”。此“枪手”大略有点类似旧时的刀笔吏,刀笔吏又称讼师,替人捉刀,代写讼案,不具其名,换点银两;今天的枪手则替人捉刀,代写文案,没有名分,酬劳丰厚。作品中的凃文贵便是一名代写电视连续剧的“枪手”。作者杨晓升用白描的手法、平朴的语言,将笔触直捣“钱眼”,在金钱的“诱惑”下,在以金钱为故事核心的外壳包裹下,一步步将读者引入亢奋,一步步将在小说创作上斩获颇丰而生活相对窘迫的凃文贵“逼”着走上了争取财务自由的奋斗之路。凃文贵成功了!凃文贵成功了吗?这是一个悬念,这是一篇“好看小说”。杨晓升现实主义的笔法几近原生态反映出现实生活中的二律悖反,凃文贵从重名轻利到重利轻名的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的嬗变,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命题,人生目标的选择,生活方式的选择,其实是一种社会生存哲学的驱动,因此,《枪手》的社会学意义也挣脱故事的桎梏横空出世,给人联想,发人深省。于是,我就揣摩着,晓升兄久有凌云志,执念于文学情结,或者说怀有文学梦想,与他笔下的人物凃文贵一样近年佳作迭出,已在小说界声名鹊起,那么,他是否会像凃文贵一样“华丽转身”充当“枪手”,捉刀炮制影视剧集,然后暴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呢?
三
长篇小说《躁动》是年近九秩的老作家陈伯坚先生耗时26年反复思考、打磨、殚精竭虑的精品力作。《躁动》是心的躁动,情的躁动,性的躁动,人的生命意识在躁动中复苏,在复苏中滋长蔓延,在蔓延中激活原创力。伯坚先生笔名陈年酒,《躁动》正是伯坚先生捧上的一坛浓香馥郁、醇厚绵长的陈年佳酿。
小说以珠水先暖的改革开放时代为背景,以与澳门一水之隔的大锅岛为舞台,以马头山“神水”的开发为核心,演绎出一部历史活剧,高扬着对“人本主义”的礼赞。小说围绕马头山“神水”的开发,在人性的复归、人性的勃发和理性自控的矛盾过程中发展,最终对“欲”的野蛮生长之“度”的思悟,把社会学的现象推升至一个哲学命题的高度,从而给《躁动》赋予了思想活力和精神魅力,为大湾区文学长廊增添了一抹崭新的色彩。
四
数年前邂逅罗春柏,我尊一声“罗书记”。他自诩为一介布衣,大隐于市,平实低调。书记者,古已有之,用以指称记事的书写文字,三国曹丕的《与吴质书》中“元瑜书记翩翩”即指章、表、书、疏等类文体,近些年,罗书记诗誉盛传:获广东省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第四本诗集《记忆的绳子》在诗者们的殷殷期盼下付梓出版、其个人诗歌创作研讨会在碧波万顷的伶仃洋簇拥下盛装登场……罗书记以静水深流的诗意逻辑抒情愫,抒遐思,抒禅悟,抒清绝,以及对山水田园、一草一木的细微体察。人如其文也好,文如其人也罢,他的诗没有金戈铁马,没有大开大阖,整体呈现内敛沉静的阴柔美,诗语修辞绵密、圆润温婉,有的诗句切入中国文字奥妙的肌理,如甘草橄榄,让人咀嚼良久,意味悠长。
五
梁冬霓,一个音韵平和的名字,一个点缀冬的淡妆和霓虹玫瑰蕴藉着诗意的名字,一个在文字间恣意徜徉的客家妹,携着她的散文集《时光倒影》出现在一场文学盛宴上。翻阅这些文字,使我讶异的是,她对文学的热爱,对文学的追求,甚至对文学的膜拜都迥异于一般作家——有人在文字间寻梦,有人在文字间刷存在感,有人凭借文字的排列组合展露才华谋取物欲……这都没问题,都无可厚非,而冬霓却自以为幸运地认为“文学让我找到灵魂的皈依”,她深知“文学对于我的意义更多的是安放灵魂,修正内心,传递真善美,在生命的渡河中,为自己,为他人,做一个摆渡者,从荒莽的此岸,渡到花开的彼岸。我相信,文学会让痛苦成为一种救赎,让幸福成为一盏明灯”。这种特立独行,这种孤高,这种清越,这种对文学敬畏的情结和精神力量使人感佩,也许这就是她自我价值的文化密码以及经营文字的控制模板吧。因此她从自己的文学世界出发,抵达现实世界的各个角落,乡情、友情、亲情,生活的斑斓多彩和五味杂陈都涌现笔端。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用两支笔写作,一支笔写散文,一支笔写评论,两支笔互为伯仲,用自己的才情和慧眼游走于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之间。
不可或缺的是,黄龙汉先生的序言堪称字字珠玑,给《时光倒影》精准地勾勒出一道绚丽的光影,彰显着提携、奖掖文学后进的伯乐胸襟和人文情怀。
朋友们,坐下来,静下来,读读《时光倒影》,读读梁冬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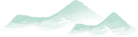
为凡人而歌
——散文集《照见》自序

□ 崔 云
写作在我看来,犹如春蚕吐丝,丝丝缕缕,持续不懈,最终织就一幅完美的图案。蚕儿之所以能源源不断地吐丝,在于它摄入了足够多的桑叶,汲取了足够多的能量。同理,写作也需要作者不断汲取生活的养分,拥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与体验,才能写出有血有肉、能够打动人心的文字。
我一直坚信,好文章是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发乎心而为文,只有当写作者的情感、智慧与思想真诚地融入文字之中,作品才会散发出温暖与力量。渴望通过文字抚慰读者的心灵,这是我作为写作者的最大心愿,并一直为此努力着。
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人总给我最多感动。也许是出生于农村的缘故,我平时喜欢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身边的普通百姓,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质朴善良,他们努力奋斗的样子,都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着我的心怀,并鼓舞和鞭策着我,让我情不自禁拿起手中的笔。小区里的保安、办公楼的保洁员、菜市场的小商小贩、流水线上的打工者、花艺市场的花农,在城市里奔忙的的士司机、快递小哥及家政人员,还有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建筑工人、田野里辛勤劳作的农民等,他们都是我笔下的主人公,他们虽身处社会底层,却都在尽力发着光和热。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的世界才变得更加干净、舒适与便捷。他们的笑容、泪水、汗水,都是那么真实而感人。他们积极阳光的心态和努力生活的样子真的很美,是他们教会了我更加热爱生命、珍惜当下。
2001年的金秋十月,我怀揣梦想从荆楚大地来到经济特区珠海,一转眼已是25个年头。由于从事社团工作的缘故,20多年来,我打交道最多的群体是民营企业家,他们是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更是慈善事业的“领头雁”。他们身上那种坚韧顽强、拼搏创新、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让我深深为之折服。对于家国情怀,他们比一般人的理解更为透彻,那就是慎始如终地认真践行。顺境逆境、成功失败、荣辱得失,他们的领悟比一般人要真切而深刻。创业、创新、创富,是每一位有追求有梦想的民营企业家的使命,他们驰而不息,乐此不疲。在商海中搏击,可谓惊涛骇浪,瞬息万变,凶险难料。从风光无限到一无所有,有时可能只是一个错误的决策,或是一场意外的天灾人祸。我常常感叹,没有强大的心脏,是难以承受如此重压的。面对各种风险和不确定的因素,他们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无怨无悔。正是这些平凡的民营企业家,给了无数人就业的机会,给了无数个家庭安稳与幸福。因而我常常会将钦佩的目光投向他们,写他们艰辛的创业历程和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写他们的大爱善举和追梦故事,传递人性的善良与美好。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是一场寻找自我的旅程。终其一生,都是为了抵达自己,与更好的自己相遇。写作如此,干其他工作亦如此。对于我来说,故乡始终是我心灵的归宿。不管走多远,不管离开多久,它总牵引着我的视线,令我魂牵梦萦,也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那方水土那方人,故乡的一草一木和田野里长出的故事一直在我笔下流淌——年少时最爱逛的乡村集市和说书场、最爱看的村戏和乡下电影,最爱去的小竹林和小池塘,还有那淳朴善良、勤劳勇敢的乡亲……每次写故乡的风土人情,都是一次与故乡的精神重逢,让我欣喜与感伤。那熟悉的土地和人们总能激发我无尽的创作灵感。乡亲们那家长里短背后隐藏着的生活智慧、闲聊时的情感碰撞,都散发着泥土的芬芳,让我心生感动,情不自禁地拿起了手中的笔,定格下乡音、乡情。
如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我,亲见亲历了太多人间的生离死别和悲欢离合,更加深刻地领会到生命的无常和生活的真义。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只是希望能够通过我的文字,传递出某种情感和力量,让读者朋友能从他人的经历、感受或故事中得到启发,找到心的出口和前行的方向,人生多一些快乐与幸福。
在我看来,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他们是生活中最美的风景,也是我创作的不竭动力与源泉。
写作不仅是一种表达,更是一种探索。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或许我们都渴望找到一个宁静的角落,聆听来自心底的声音。而我,愿意用手中的笔,为那些普通但不平凡的人们歌唱,让他们的故事恒久流传……

寻常咏物 意蕴深远
——赏析当代诗人叶宝林的“赋律”
□ 智通义
当代诗人叶宝林一组题为《赋律》的七律作品,读后令人耳目一新,心有所动。这34首以“赋”冠名、以“物”为题的律诗,看似寻常咏物,实则意蕴深远,展现出作者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力与独特的哲思艺术风格。从蚂蚁、蜉蝣、蝼蛄等微小生灵,到扇子、雨伞、拐杖等日常器物,叶宝林以“小物”为切入点,借物抒怀,托物言志,将个体生命体验、社会现实观察与宇宙人生哲理融为一体,构建出一种“小物大思”的独特创作格局。其诗不仅在艺术上达到情景交融、意境悠远之境,更在思想层面体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易经》《道德经》等经典哲思的深刻体悟与创造性转化。
叶宝林的创作思想核心,可归结为“以物观道”。他并非止步于对物象的形貌描摹,而是将每一物视为“道”的具象载体,通过对其形态、习性、命运的细腻刻画,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生命哲理与宇宙法则。物即道,道寓于物,二者互为表里,浑然一体。如《山泉赋》:“辞高一去归溟底,利世芸芸道未争”,以山泉自高处奔流而下、润泽万物却不争功名的品性,暗合《道德经》“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核心思想。山泉之行,即“道”之行;山泉之德,即“道”之德。又如《水酒赋》,写酒体的水火相融,假杯中之物,揭示了《易经》里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理。
叶宝林的写作风格,呈现出“寓庄于谐、以小见大、虚实相生”的鲜明特色,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其艺术魅力的基石。
“寓庄于谐”是其智慧的外化。他常以轻松、诙谐甚至略带调侃的笔调,书写严肃深刻的社会批判与人生思考。如《苍蝇赋》中“屏风正欲观虫画,借点青蝇构墨图”,化用“误点成蝇”的典故,将苍蝇之“污”与画壁之“洁”形成强烈反差,讽喻现实中某些“污点人物”对清正环境的破坏,语言机智,讽刺犀利,令人会心之余又不禁使人警醒。《南郭赋》则借“滥竽充数”之典,直指当下人才评价机制中的形式主义与虚伪风气,“人才不抵伪人精”一语,直击要害,发人深省。这种“谐”并非轻佻,而是智者冷眼观世的幽默,是诗人对现实清醒而深刻的洞察。
“以小见大”是其最突出的艺术手法。他从不直接书写宏大主题,而是以最微小、最平凡、最易被忽视的物象为切口,从中开掘出广阔的思想空间。《蝼蛄赋》写地下之虫,“平生忏悔赎苗祸,舍与鸡虫兑蛋香”,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观察看待一个微小的生灵,既有批判的角度写其危害性,又有褒扬的角度赞其功用性,不仅可以松耕土地,更可舍身喂鸡换来“蛋香”,把一个无知的小虫,升华为一个知道“忏悔”有着“救赎”心态的“悟者”,充满了幡然醒悟的禅智。这种从“小”中见“大”的写法,使诗歌既有现实关怀的锐度,又有人文温馨的厚度,更蕴含文化反思的深度。
“虚实相生”则体现在其意象营造与意境构建的高超技艺上。叶宝林善于将具体物象与抽象哲理、历史典故与当下现实、自然景观与心灵世界巧妙融合,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审美空间。《红莲赋》通篇以“空”字贯穿,“内外皆空色与同”“红莲出水清空立”“藕眼虚心洞洞空”,创造出一个空灵澄澈、禅意盎然的艺术境界。《白云赋》写“远世离尘嫁与风,南浮北往任西东”,以白云的飘忽无定,喻示老子“无中生有”的宇宙观,其“心舒漫卷无还有,影去形消色去空”之句,更将物象的消逝升华为对存在本质的玄思。
叶宝林“赋律”作品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其对古典诗词格律的精深掌握与创造性运用。作为长期研究《周易》与诗词格律关系的学者,他深谙平仄、对仗、用韵之法度,作品严谨工整,音韵和谐。然而,他并不为格律所缚,而是在规范中求变,在传统中出新。
从对当代诗词创作的启示来看,叶宝林的“赋律”系列提供了宝贵的借鉴。首先,它证明了古典诗词这一古老文体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创作者能否赋予其新的思想内涵与时代精神。其次,它启示我们,诗词创作不必追求宏大叙事或华丽辞藻,从身边之物、日常之景入手,同样可以写出深刻之作。“以小见大”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观照世界的方式。再次,它强调了诗人应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与独立的思想品格。叶宝林的诗之所以能“小中见大”,正源于他对《易经》《道德经》《庄子》等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最后,它展示了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既尊重格律,又不拘泥于格律;既运用典故,又能翻出新意;既扎根传统,又能吸纳现代科学概念。这种“守正创新”的态度,正是当代诗词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 林伟光
读书,并不仅仅读而已,还有一个访书的过程,有的人说淘书,都是一种情牵不已的境界。
人性喜其新而厌其旧,唯有书却不怕其旧,我的几千册旧书,有不少都还没有读过,正好借此闲岁月以读,遣此有涯之生啊。
启功先生暮年有句:饮余有兴频添酒,读日无多慎买书。这份顺生心态,很好。我不善饮,偶尔的半杯已经脸红心跳,“频添酒”的佳兴,只好存于梦境,而这“慎买书”却恰如警语,故心有所触动,取此句而成俚语曰:回回梦里缥缃架,读日无多慎买书。苦暑思风茶伴我,新翻旧籍云卷舒。
最近,友人赠一本《知堂回想录》手稿本。此书我藏有好几个版本,却没有认真通读过,这回借着欣赏手稿,正好读它一过。知堂手迹,一直想收藏,终于如愿。
鲁迅的手稿集,自己也收有,虽不全,却是他晚年写“且介亭杂文”的一些原稿。鲁迅手稿,显出功力,他是钞过碑的,这份风骨在不经意中就流露出来,却也温润,令人赏心悦目。可以看出,他写作时的愉悦,从容的笔致中,蕴含郁郁的风情。那么泼辣的文字,可是笔下却是从容而舒徐的。而知堂的手笔,就不能跟乃兄相比拟了。虽然在娴熟的书写中,也有文气氤氲;不过,骨力却是没有的,只是一些拖泥带水的味道。
二周的文章,我都喜欢,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并且各成高峰。一是浓到极致,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一是淡到极致,总努力剔除情绪,在不动声色中行文。有的人总在讨论他们失和的原因,其实,所有的这或那的原因,通通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而已,他们都不可能退让的。
人老了,阅历多了,早已失却了风花雪月的心,只想喝一杯苦茶,故心境渐近于知堂。那么,已没有激情了吗?也不然。知堂文字虽好,却总嫌有些隔膜,离得远,就不如鲁迅的入世,有不少文章犹如写当下。可见这世界凡是人性,总归古今变化不大的。除非我们不去关心世态,变诸多的看不惯为司空见惯,或者才可以淡看。
读书,有时也读前人的往事与往思,觉得日光之下无新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杞忧也真的大可不必。这就是读书的好处,世事洞明之后,渐渐人情练达,可以一切只当浮云看了。

-我已经到底线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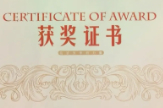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