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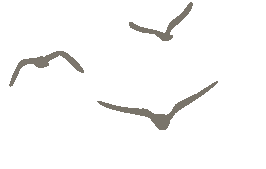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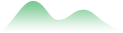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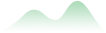
□ 梁冬霓
一阵豪雨,让夏日的凌人气势矮了三分。荔枝树叶在雨中绿得更加真切,石块垒砌的树池经雨水的洗涤,像抹了一层光。我们撑着伞躲在黄皮树下,望着白墙黛瓦的民宿,和在雨中摆动的红灯笼,恍惚间好像来到了烟雨江南。
但这里不是江南,而是曾经留下我足迹的斗门石龙村。
清康熙年间,石龙村先祖周姓从中原远道而来,在这个五指山以东、顺流河以西的地方,垦山开岭,开拓田园。涔涔汗水洇染了晨昏,一个村庄就此落成。岁月流转,何氏、赵氏后来相继迁入,从此村庄三姓交融,烟火渐盛。2005年,由原来的石龙村和三湾村合并成一个村庄,统一叫石龙村。
古老的村庄已从陈旧的岁月中挣脱出来,而一路的民宿,却用木门青瓦、白墙院落、迎风花草,点染了一番旧时韵味,像典雅的词句随意铺陈了一首现代诗,诗中落满古风。岁月匆匆,浮躁的心若能在这里栖息片刻,看东山月起,听夏虫唧唧,在安宁中窥见内心所想、所求,也不失为一件快事。
这里的民宿,都是村内空置房盘活所用。离开故土的村民自愿把房屋腾给村里打造,足见他们的拳拳之心。多年前我来到这里,那时只有石板路和整齐的青瓦白墙,而现在,墙边有了花草,休闲院落有了诱人的果香,还有独享早晨与黄昏的观景平台,更彰显了古朴的田园诗意。想想在院子里卸下尘世生活带来的疲惫,静听天地与自己的呼吸,是何其美妙。
城市酒店给旅人带来的也许是现代环境的舒适与物质的享受,而石龙村的民宿给游客带来的却更像是精神的回归。在这里,你来到一个返璞归真的天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会进一步思考,追求浮华名利与寻一片心中净土,回归自我,这种生活方式或许更有意义。
在一个院子里,我们坐在茶几旁听雨,一个在此管理民宿的女士说起了十年间民宿从打造到现在的路途。有过艰辛,也有很多的收获,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虽然目前经济形势比不上早些年,但还是有络绎不绝的游人。此时雨越下越大,人生与自然界一样,必定要经历风雨,一个村庄的发展亦然。我相信石龙村民宿会带着她浓郁的诗韵走向更远的岁月。
除了民宿街,石龙村更广阔的画卷在“岭南大地”,景区的核心区域就位于石龙村。“百草园”“花田喜地”“岭南风情水街”……这些景点映入眼帘,仿佛自己也成为花草的一部分,在大自然中进入无我的境界。
“百草园”中橱窗里的每一剂草药都仿佛来自《诗经》,有田园的气息,有治病救人的美德,有安放心灵的清香。在这个以中医药文化为主题的馆内,我们了解到了阴阳平衡、天人同源等中药文化的内涵。在“百草园”内开展的“望、闻、问、切”的研学活动,和中药的“寻、辨、识、采、制”的科普,也使得中医文化在这里得到传播。
除了精心打造的景点,石龙村的底色离不开葱葱郁郁的花木产业。发展旅游业前,石龙村依托了莲洲镇的花木产业,从一个普通村庄变成花木村。各种花木从小苗开始,经几年时间,才长成荫浓花盛的大树。草木是有情的,它们的情,就是以绿叶花香回赠农人,以告别故园的方式增加农人的收入。而葱茏的花木,无意中营造了自然景观,它们在呼吸吐纳之间制造的负离子,又为石龙村发展生态旅游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个旅游村庄除了发展生态,还需文化的传承与体验。已入选珠海市非遗文化名录的莲洲地色,起源于莲洲镇的文锋村,如今的传承人就在石龙村。地色与飘色相对,飘色中表演的人物是脱离地面,展现凌空之美,而地色的表演人物是在地上,手持道具且可与观众即兴互动。
“八仙过海”的民间传说,在这里已表演了多年。身背药葫芦的铁拐李,手持芭蕉扇的汉钟离,骑纸驴的张果老,手捧莲花的何仙姑……八仙们活灵活现地出现在非遗节目表演中,引来众多喝彩声与欢呼声。沸腾的街上,演员们穿着粉衣、蓝衣、黄衣等颜色的古代服饰,戴着各种头饰,飘逸中带着极强的喜感,让人觉得神仙就在身边,不再遥远。各显神通的才能,风调雨顺的愿望,都在演员们的神态、动作中呈现。石龙文化墙,把莲洲地色的缤纷、趣味、内涵,在我们面前逐一展现。
离开石龙村时,夏雨初晴,天空湛蓝如洗。我相信石龙村的发展,必定有过阵痛,但石龙村经风雨洗练的温润之光,正散发在雨后清新的空气中。



□ 蔡 旭
我知道你五年级刚读过“清泉石上流”的诗句。我对孙子说。
可是你未见过这样的场景吧。其实许多人也没见过。这种美景不是到处都有的。珠海的石溪公园才有。见多了从石山上飞下来的瀑布,这个不算。它只能算“山上流”。
现在来到刻着“石溪”的大石头旁边,诗境就在那一片平坦的石板上出现了。溪水从石板上舒展地漫过来,像一面透明的玻璃铺在石面上。只见一匹柔软的丝绸,深情地吻过石板坚硬的胸膛。
泉水很静。不急着走路的它,轻轻抚过岩面细密的肌理。泉水很净。可以看到藏在水下的石头上那些美丽的波纹。安静的石头,任由清泉在它的胸膛上写着流动的诗。
温暖的阳光,用水面上的碎金点缀着依依不舍的情意。偶有落花漂过,奏响一曲华彩的乐章,整个山谷都轻晃了起来。飞鸟衔着云影,也来加入这场如诗如画的聚会。
我和孙子静静地看着,默默地想着,慢慢地品味着。想当年,唐朝的王维也没来过珠海的石溪。那时这里还是大海上的荒山。我们太幸运了,我们太有福了。我对孙子说。
竟可以身临其境,把自己摆进王维的诗情画意中……

□ 朱先进
昨晚打开《古文观止》,翻到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读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时,倏地想到了小学、初中、高中时教过我语文的几位先生。
第一位是小学的袁老师。四十多岁,个子高挑,身材微胖,脸上隐隐约约有一些麻子。她是插队到我们村的城里人,丈夫是大学生,据说是教高中的老师。袁老师教我们一年级,很细心,一点儿也不凶。我们背地里总是偷偷地叫她“袁麻子”,好多时候,我们童言无忌地叫着,其实与她的距离并不远,我想她一定是听到了的。不过,袁老师从不生气。
当时的办学条件不好,坐在教室里,往往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一到雨天,课桌左挪右移,就是为了避开漏雨。有一次,我挤在角落,就是避不开,只好冒雨写作业。袁老师见了,赶快拿来她的油纸伞,撑开替我遮雨。几乎一整节课,她就这样撑着伞。搞得我很不好意思,那节课,我的字写得特别好。
一年级下学期的最后一个月,袁老师生病了,没来学校,换了一个小姐姐为我们上课(是学校“戴帽初中”的女学生)。我们好不容易盼到上二年级,终于又见到袁老师,大家脸上都绽放着笑容。奇怪的是,再也没有同学叫他“袁麻子”了,而是恭恭敬敬地叫“袁老师”。袁老师对学习抓得很紧,只要没有完成当天的学习任务,她就会先让我们背《明日歌》,再留堂。若学生家远的,她还会塞点小零食让其带回家。
我记得,我留过几次堂,但为时很短。回家时,在土路上会边跑边扯着嗓子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陀螺(蹉跎)……”
第二位是初中时的陈老师。陈老师当时三十多岁,妥妥的帅哥一枚,而且写得一手宋体字,据说以前还做过赤脚医生。教课时激情澎湃,语言生动,表情丰富,学识渊博。有一次,陈老师外出学习了一个多月,再次返校见到我们时很激动,谈了很多在外学习的收获。他说学到了一种“蒙太奇”的写作方法,尤其是“特写镜头”的写作法。也许是被陈老师唾沫四溅的激情感染,我居然把“蒙太奇”和“特写镜头”记得特深。
后来在一次作文中,我尝试着用到了。
那是写晨读的一个场景。我们学校里有几个大池塘,塘坝上种了很多柳树,因时间颇长,粗壮茂盛,柳条依依,像挂了长长的一道门帘子。晨读时,学生可以去那里自由朗读。我在习作中写道:“晨风吹拂,在依依的柳条中,微微露出一张嘴,一张一翕,一翕一张,发出琅琅的读书声……”
过了几天,陈老师拎着一叠作文本来讲评,对我大加夸赞。什么“拍案叫绝”“要修改后拿去发表”之类的话,搅得我心里乐开了花!我感觉到同学们不时投来羡慕的目光。
正因陈老师的鼓励,我更加喜欢写作文了。
几十年后,我把这个经历讲给我的学生听,竟然也有让我“拍案叫绝”的文章。上届初三的一个同学,写跑步——“体育中考的那一刻,鲜红的跑道上,两只白色的球鞋,一上一下,一下一上,急速交替,奋力奔向终点……”这或许就是一种传承吧。
第三位是高中的李老师。他是位老先生,高一教了我一年。班上的学生坐得满满的,李老师年纪大了,有学生悄悄进出教室,常常也顾及不到。但是,每节语文课,他都工工整整板书,娓娓道来,毫不敷衍。
印象最深的是——讲评学生的作文。他批阅学生习作,一边批注,一边写到自己的讲义上。每次讲评,他都是捧着厚厚的一叠稿纸在那里点评。有时,他那老花镜都滑落到鼻尖上了,颇有点像叶圣陶先生写的《多收了三五斗》中的米行账房先生。
记得我的一篇习作《除夕》,受到李老师的表扬——“除夕的第一声鞭炮响,就像莱克星顿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他说这句比喻很大气,能学科融通,文史本就不分嘛。(那时还没有“跨学科学习”的说法。)这又给我学习写作添了一盆旺火。
教师节到来之际,忽然想起我的这几位先生,心里暖暖的。先生们的风范,永远值得我学习。更希望,我在我的学生心中亦复如是。
□ 李 皓
秋水伊人
只一汪秋水
便让我目睹了
爱情的整个过程
从混沌到清澈
从青翠到红润
从消瘦到丰腴
你以一枚果实的面容
泊于我视野中央
当萧瑟秋风无所不在
你是唯一的善良
当真爱雁过高天
你是最后的淑女
在水一方
采黄花缀于你梦的衣裳
插茱萸伴你登那
高过神灵的重阳
九月,你做我的新娘
秋日还乡
那落光了叶子的树,是在
向故乡举手投降么?
那无法克制的山一程,水一程
无非是想把自己归还
在一条路的尽头
在一棵树的根部
除了一枚飘零的落叶
除了一个虚晃的身影
比晨雾还淡,比炊烟还轻
比初恋还可有可无
那收割后的田野空空荡荡
那被遗弃的秸秆无人收场
相比于一枚落叶,它们
更加容易被人遗忘
因为它们不曾拥有一个
朗朗上口的乳名
而村口的三叔二大爷
稍作打量,轻易就认出了我——
呵呵,这不是秋生回来了么?
在肇东过生日
接受一群诗人的起哄
是司空见惯的
接受一群诗人的祝福
是危险的
他们无疑是一群肇事者
他们吟诵着旧爱
掺和着新欢
他们释放着野性,豪情
却难以掩饰善良和软弱
他们把我的内心搅得鸡犬不宁
而我甘愿撇家舍业来与他们相逢
一起密谋一个感伤的夜晚
一起吐真言,一起酒后失忆
当一个女诗人,说我
穿白衬衫的样子很帅的时候
我的秋天开始了,看来在肇东
我必须留下足够的蛛丝马迹
立秋小记
老虎站了起来
天空被抬高了三尺
神明的昨夜非线性失忆
从一杯接一杯的红酒里
挤出汗水,挤出肝胆
挤出欲念,挤出波浪
理屈词穷的早晨
一只蝉在窗棂上高喊
命,命,命
蒲石河的枫叶
红了的,是你鲜艳的
红围巾
在我的内心
留下你狠狠的牙痕
未红或正在红的
是背道而驰的欢愉
是歧途
不曾抵达的美
流水无情
石头波澜不惊
蒲石河有不动声色的口德
而赛马小镇
根本看不到一匹马
它枣红色的身子
像极了惊鸿的背影
□ 陈继文
暑假里,几次打开家里那台快成摆设的电视,想给孩子找些假期常播的老少皆宜的连续剧,可遥控器来回换台,愣是没找着。盯着略显陌生的画面,心里忽然空落落的,像丢了什么,又说不清是什么。
小时候,每次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永远是扯着嗓子喊妈妈。她在,一切安好,问这说那,好不自在;她不在,六神无主,呆若木鸡,心里空落落的。
年龄稍大,渐渐懂得了读书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不二出路,坚信付出总有回报,盼着一朝金榜题名,挑灯夜读,不敢懈怠。忽略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每次成绩出来,总超不过想超越的人,之后总有那么几天,心里空落落的。
初入社会,褪不尽一身书生气,只顾埋首业务不管其它,盼着早点站稳脚跟,甚至想成为单位的栋梁。忽略了领导的叮咛和有些人身后若有若无的 “关系”,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或根本抓不住。当结果事与愿违,那种无能为力,瞬间化成心里的空落落。
后来成家,有了小窝,也有人管了。钱花得不合妻子意,要被唠叨,之后买东西先问一句;喝酒失态,免不了数落,出门先请示,不然怕是要睡客厅。柴米油盐就这样积累着幸福,可某天她出差或回娘家,家里静得陌生,思来想去,竟想念她的唠叨——原来少了妻子的絮叨,心里也空落落的。
空落落,空落落,人生几度空落落?
同窗、战友数载,一朝分别,空落落;千里探亲,见父母鬓白佝偻,短暂相聚后再远行,空落落;独当一面,没了师傅、领导的批评指点,反倒不知所措,空落落;失恋、失败时心里空落落,父母老了、走了心里会空落落,孩子长大离家了,也会空落落…… 人生一路,走着走着,好像啥都能让人空落落。我们光着身子来,空着双手走,兜转一圈回到原点,谁都躲不过空落落。
可是,那些风雨后所见过的彩虹,始终在记忆中泛着粼光;那些翻山越岭邂逅的风景,叫人久久流连;那些一路同行、并肩而立的人,始终屹立心间;那些打动心灵的故事,从未随岁月褪色。心里的空落落,或许只是一时,而所有难得的过程、真切的经历,那些人、那些事,终究会穿越所有空落落的瞬间,成为一世的珍藏!
□ 叶宝林
珠海冬雨
小雪封严令入冬,时来珠海遇春风。
开门叶茂芭蕉绿,对月花繁木槿红。
鸟语枝头晨雾里,蛙鸣夜半水塘中。
京都白絮迷天地,梦卧香洲雨万重。
过濂溪书院
老院凡门过鸟音,三人栈道探篁林。
萧郎索句云铺雪,邓女填词水抚琴。
影入花间同粉面,身移竹下共青襟。
黄昏无语山溪语,古井波明看月心。

□ 彭 健
汉字
天上一轮才捧出,当惊世界殊甲骨。
天雨粟,鬼夜哭,仓颉造字窥四目。
智慧岂被机器阻,五笔输入神工斧。
形音义妙耀始祖,历久弥新昭今古。
家书
见字如面母亲好,久未尽孝犹害臊。
事业有成聊以慰,寸草春晖终难报。
罔极之恩思悠邈,企盼慈颜永不老。
母亲高寿家至宝,子嗣感念共祈祷。
新八股
摹仿成风泛身影,废话套话僵化文。
模式化何谓创新,标签化了无真情。
写作倚人工智能,新八股困机器病。
临文不苟劳罄心,辞达为本风骨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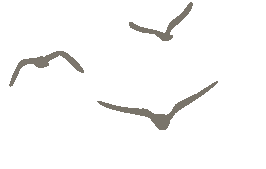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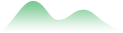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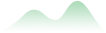
□ 梁冬霓
一阵豪雨,让夏日的凌人气势矮了三分。荔枝树叶在雨中绿得更加真切,石块垒砌的树池经雨水的洗涤,像抹了一层光。我们撑着伞躲在黄皮树下,望着白墙黛瓦的民宿,和在雨中摆动的红灯笼,恍惚间好像来到了烟雨江南。
但这里不是江南,而是曾经留下我足迹的斗门石龙村。
清康熙年间,石龙村先祖周姓从中原远道而来,在这个五指山以东、顺流河以西的地方,垦山开岭,开拓田园。涔涔汗水洇染了晨昏,一个村庄就此落成。岁月流转,何氏、赵氏后来相继迁入,从此村庄三姓交融,烟火渐盛。2005年,由原来的石龙村和三湾村合并成一个村庄,统一叫石龙村。
古老的村庄已从陈旧的岁月中挣脱出来,而一路的民宿,却用木门青瓦、白墙院落、迎风花草,点染了一番旧时韵味,像典雅的词句随意铺陈了一首现代诗,诗中落满古风。岁月匆匆,浮躁的心若能在这里栖息片刻,看东山月起,听夏虫唧唧,在安宁中窥见内心所想、所求,也不失为一件快事。
这里的民宿,都是村内空置房盘活所用。离开故土的村民自愿把房屋腾给村里打造,足见他们的拳拳之心。多年前我来到这里,那时只有石板路和整齐的青瓦白墙,而现在,墙边有了花草,休闲院落有了诱人的果香,还有独享早晨与黄昏的观景平台,更彰显了古朴的田园诗意。想想在院子里卸下尘世生活带来的疲惫,静听天地与自己的呼吸,是何其美妙。
城市酒店给旅人带来的也许是现代环境的舒适与物质的享受,而石龙村的民宿给游客带来的却更像是精神的回归。在这里,你来到一个返璞归真的天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会进一步思考,追求浮华名利与寻一片心中净土,回归自我,这种生活方式或许更有意义。
在一个院子里,我们坐在茶几旁听雨,一个在此管理民宿的女士说起了十年间民宿从打造到现在的路途。有过艰辛,也有很多的收获,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虽然目前经济形势比不上早些年,但还是有络绎不绝的游人。此时雨越下越大,人生与自然界一样,必定要经历风雨,一个村庄的发展亦然。我相信石龙村民宿会带着她浓郁的诗韵走向更远的岁月。
除了民宿街,石龙村更广阔的画卷在“岭南大地”,景区的核心区域就位于石龙村。“百草园”“花田喜地”“岭南风情水街”……这些景点映入眼帘,仿佛自己也成为花草的一部分,在大自然中进入无我的境界。
“百草园”中橱窗里的每一剂草药都仿佛来自《诗经》,有田园的气息,有治病救人的美德,有安放心灵的清香。在这个以中医药文化为主题的馆内,我们了解到了阴阳平衡、天人同源等中药文化的内涵。在“百草园”内开展的“望、闻、问、切”的研学活动,和中药的“寻、辨、识、采、制”的科普,也使得中医文化在这里得到传播。
除了精心打造的景点,石龙村的底色离不开葱葱郁郁的花木产业。发展旅游业前,石龙村依托了莲洲镇的花木产业,从一个普通村庄变成花木村。各种花木从小苗开始,经几年时间,才长成荫浓花盛的大树。草木是有情的,它们的情,就是以绿叶花香回赠农人,以告别故园的方式增加农人的收入。而葱茏的花木,无意中营造了自然景观,它们在呼吸吐纳之间制造的负离子,又为石龙村发展生态旅游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个旅游村庄除了发展生态,还需文化的传承与体验。已入选珠海市非遗文化名录的莲洲地色,起源于莲洲镇的文锋村,如今的传承人就在石龙村。地色与飘色相对,飘色中表演的人物是脱离地面,展现凌空之美,而地色的表演人物是在地上,手持道具且可与观众即兴互动。
“八仙过海”的民间传说,在这里已表演了多年。身背药葫芦的铁拐李,手持芭蕉扇的汉钟离,骑纸驴的张果老,手捧莲花的何仙姑……八仙们活灵活现地出现在非遗节目表演中,引来众多喝彩声与欢呼声。沸腾的街上,演员们穿着粉衣、蓝衣、黄衣等颜色的古代服饰,戴着各种头饰,飘逸中带着极强的喜感,让人觉得神仙就在身边,不再遥远。各显神通的才能,风调雨顺的愿望,都在演员们的神态、动作中呈现。石龙文化墙,把莲洲地色的缤纷、趣味、内涵,在我们面前逐一展现。
离开石龙村时,夏雨初晴,天空湛蓝如洗。我相信石龙村的发展,必定有过阵痛,但石龙村经风雨洗练的温润之光,正散发在雨后清新的空气中。



□ 蔡 旭
我知道你五年级刚读过“清泉石上流”的诗句。我对孙子说。
可是你未见过这样的场景吧。其实许多人也没见过。这种美景不是到处都有的。珠海的石溪公园才有。见多了从石山上飞下来的瀑布,这个不算。它只能算“山上流”。
现在来到刻着“石溪”的大石头旁边,诗境就在那一片平坦的石板上出现了。溪水从石板上舒展地漫过来,像一面透明的玻璃铺在石面上。只见一匹柔软的丝绸,深情地吻过石板坚硬的胸膛。
泉水很静。不急着走路的它,轻轻抚过岩面细密的肌理。泉水很净。可以看到藏在水下的石头上那些美丽的波纹。安静的石头,任由清泉在它的胸膛上写着流动的诗。
温暖的阳光,用水面上的碎金点缀着依依不舍的情意。偶有落花漂过,奏响一曲华彩的乐章,整个山谷都轻晃了起来。飞鸟衔着云影,也来加入这场如诗如画的聚会。
我和孙子静静地看着,默默地想着,慢慢地品味着。想当年,唐朝的王维也没来过珠海的石溪。那时这里还是大海上的荒山。我们太幸运了,我们太有福了。我对孙子说。
竟可以身临其境,把自己摆进王维的诗情画意中……

□ 朱先进
昨晚打开《古文观止》,翻到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读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时,倏地想到了小学、初中、高中时教过我语文的几位先生。
第一位是小学的袁老师。四十多岁,个子高挑,身材微胖,脸上隐隐约约有一些麻子。她是插队到我们村的城里人,丈夫是大学生,据说是教高中的老师。袁老师教我们一年级,很细心,一点儿也不凶。我们背地里总是偷偷地叫她“袁麻子”,好多时候,我们童言无忌地叫着,其实与她的距离并不远,我想她一定是听到了的。不过,袁老师从不生气。
当时的办学条件不好,坐在教室里,往往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一到雨天,课桌左挪右移,就是为了避开漏雨。有一次,我挤在角落,就是避不开,只好冒雨写作业。袁老师见了,赶快拿来她的油纸伞,撑开替我遮雨。几乎一整节课,她就这样撑着伞。搞得我很不好意思,那节课,我的字写得特别好。
一年级下学期的最后一个月,袁老师生病了,没来学校,换了一个小姐姐为我们上课(是学校“戴帽初中”的女学生)。我们好不容易盼到上二年级,终于又见到袁老师,大家脸上都绽放着笑容。奇怪的是,再也没有同学叫他“袁麻子”了,而是恭恭敬敬地叫“袁老师”。袁老师对学习抓得很紧,只要没有完成当天的学习任务,她就会先让我们背《明日歌》,再留堂。若学生家远的,她还会塞点小零食让其带回家。
我记得,我留过几次堂,但为时很短。回家时,在土路上会边跑边扯着嗓子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陀螺(蹉跎)……”
第二位是初中时的陈老师。陈老师当时三十多岁,妥妥的帅哥一枚,而且写得一手宋体字,据说以前还做过赤脚医生。教课时激情澎湃,语言生动,表情丰富,学识渊博。有一次,陈老师外出学习了一个多月,再次返校见到我们时很激动,谈了很多在外学习的收获。他说学到了一种“蒙太奇”的写作方法,尤其是“特写镜头”的写作法。也许是被陈老师唾沫四溅的激情感染,我居然把“蒙太奇”和“特写镜头”记得特深。
后来在一次作文中,我尝试着用到了。
那是写晨读的一个场景。我们学校里有几个大池塘,塘坝上种了很多柳树,因时间颇长,粗壮茂盛,柳条依依,像挂了长长的一道门帘子。晨读时,学生可以去那里自由朗读。我在习作中写道:“晨风吹拂,在依依的柳条中,微微露出一张嘴,一张一翕,一翕一张,发出琅琅的读书声……”
过了几天,陈老师拎着一叠作文本来讲评,对我大加夸赞。什么“拍案叫绝”“要修改后拿去发表”之类的话,搅得我心里乐开了花!我感觉到同学们不时投来羡慕的目光。
正因陈老师的鼓励,我更加喜欢写作文了。
几十年后,我把这个经历讲给我的学生听,竟然也有让我“拍案叫绝”的文章。上届初三的一个同学,写跑步——“体育中考的那一刻,鲜红的跑道上,两只白色的球鞋,一上一下,一下一上,急速交替,奋力奔向终点……”这或许就是一种传承吧。
第三位是高中的李老师。他是位老先生,高一教了我一年。班上的学生坐得满满的,李老师年纪大了,有学生悄悄进出教室,常常也顾及不到。但是,每节语文课,他都工工整整板书,娓娓道来,毫不敷衍。
印象最深的是——讲评学生的作文。他批阅学生习作,一边批注,一边写到自己的讲义上。每次讲评,他都是捧着厚厚的一叠稿纸在那里点评。有时,他那老花镜都滑落到鼻尖上了,颇有点像叶圣陶先生写的《多收了三五斗》中的米行账房先生。
记得我的一篇习作《除夕》,受到李老师的表扬——“除夕的第一声鞭炮响,就像莱克星顿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他说这句比喻很大气,能学科融通,文史本就不分嘛。(那时还没有“跨学科学习”的说法。)这又给我学习写作添了一盆旺火。
教师节到来之际,忽然想起我的这几位先生,心里暖暖的。先生们的风范,永远值得我学习。更希望,我在我的学生心中亦复如是。
□ 李 皓
秋水伊人
只一汪秋水
便让我目睹了
爱情的整个过程
从混沌到清澈
从青翠到红润
从消瘦到丰腴
你以一枚果实的面容
泊于我视野中央
当萧瑟秋风无所不在
你是唯一的善良
当真爱雁过高天
你是最后的淑女
在水一方
采黄花缀于你梦的衣裳
插茱萸伴你登那
高过神灵的重阳
九月,你做我的新娘
秋日还乡
那落光了叶子的树,是在
向故乡举手投降么?
那无法克制的山一程,水一程
无非是想把自己归还
在一条路的尽头
在一棵树的根部
除了一枚飘零的落叶
除了一个虚晃的身影
比晨雾还淡,比炊烟还轻
比初恋还可有可无
那收割后的田野空空荡荡
那被遗弃的秸秆无人收场
相比于一枚落叶,它们
更加容易被人遗忘
因为它们不曾拥有一个
朗朗上口的乳名
而村口的三叔二大爷
稍作打量,轻易就认出了我——
呵呵,这不是秋生回来了么?
在肇东过生日
接受一群诗人的起哄
是司空见惯的
接受一群诗人的祝福
是危险的
他们无疑是一群肇事者
他们吟诵着旧爱
掺和着新欢
他们释放着野性,豪情
却难以掩饰善良和软弱
他们把我的内心搅得鸡犬不宁
而我甘愿撇家舍业来与他们相逢
一起密谋一个感伤的夜晚
一起吐真言,一起酒后失忆
当一个女诗人,说我
穿白衬衫的样子很帅的时候
我的秋天开始了,看来在肇东
我必须留下足够的蛛丝马迹
立秋小记
老虎站了起来
天空被抬高了三尺
神明的昨夜非线性失忆
从一杯接一杯的红酒里
挤出汗水,挤出肝胆
挤出欲念,挤出波浪
理屈词穷的早晨
一只蝉在窗棂上高喊
命,命,命
蒲石河的枫叶
红了的,是你鲜艳的
红围巾
在我的内心
留下你狠狠的牙痕
未红或正在红的
是背道而驰的欢愉
是歧途
不曾抵达的美
流水无情
石头波澜不惊
蒲石河有不动声色的口德
而赛马小镇
根本看不到一匹马
它枣红色的身子
像极了惊鸿的背影
□ 陈继文
暑假里,几次打开家里那台快成摆设的电视,想给孩子找些假期常播的老少皆宜的连续剧,可遥控器来回换台,愣是没找着。盯着略显陌生的画面,心里忽然空落落的,像丢了什么,又说不清是什么。
小时候,每次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永远是扯着嗓子喊妈妈。她在,一切安好,问这说那,好不自在;她不在,六神无主,呆若木鸡,心里空落落的。
年龄稍大,渐渐懂得了读书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不二出路,坚信付出总有回报,盼着一朝金榜题名,挑灯夜读,不敢懈怠。忽略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每次成绩出来,总超不过想超越的人,之后总有那么几天,心里空落落的。
初入社会,褪不尽一身书生气,只顾埋首业务不管其它,盼着早点站稳脚跟,甚至想成为单位的栋梁。忽略了领导的叮咛和有些人身后若有若无的 “关系”,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或根本抓不住。当结果事与愿违,那种无能为力,瞬间化成心里的空落落。
后来成家,有了小窝,也有人管了。钱花得不合妻子意,要被唠叨,之后买东西先问一句;喝酒失态,免不了数落,出门先请示,不然怕是要睡客厅。柴米油盐就这样积累着幸福,可某天她出差或回娘家,家里静得陌生,思来想去,竟想念她的唠叨——原来少了妻子的絮叨,心里也空落落的。
空落落,空落落,人生几度空落落?
同窗、战友数载,一朝分别,空落落;千里探亲,见父母鬓白佝偻,短暂相聚后再远行,空落落;独当一面,没了师傅、领导的批评指点,反倒不知所措,空落落;失恋、失败时心里空落落,父母老了、走了心里会空落落,孩子长大离家了,也会空落落…… 人生一路,走着走着,好像啥都能让人空落落。我们光着身子来,空着双手走,兜转一圈回到原点,谁都躲不过空落落。
可是,那些风雨后所见过的彩虹,始终在记忆中泛着粼光;那些翻山越岭邂逅的风景,叫人久久流连;那些一路同行、并肩而立的人,始终屹立心间;那些打动心灵的故事,从未随岁月褪色。心里的空落落,或许只是一时,而所有难得的过程、真切的经历,那些人、那些事,终究会穿越所有空落落的瞬间,成为一世的珍藏!
□ 叶宝林
珠海冬雨
小雪封严令入冬,时来珠海遇春风。
开门叶茂芭蕉绿,对月花繁木槿红。
鸟语枝头晨雾里,蛙鸣夜半水塘中。
京都白絮迷天地,梦卧香洲雨万重。
过濂溪书院
老院凡门过鸟音,三人栈道探篁林。
萧郎索句云铺雪,邓女填词水抚琴。
影入花间同粉面,身移竹下共青襟。
黄昏无语山溪语,古井波明看月心。

□ 彭 健
汉字
天上一轮才捧出,当惊世界殊甲骨。
天雨粟,鬼夜哭,仓颉造字窥四目。
智慧岂被机器阻,五笔输入神工斧。
形音义妙耀始祖,历久弥新昭今古。
家书
见字如面母亲好,久未尽孝犹害臊。
事业有成聊以慰,寸草春晖终难报。
罔极之恩思悠邈,企盼慈颜永不老。
母亲高寿家至宝,子嗣感念共祈祷。
新八股
摹仿成风泛身影,废话套话僵化文。
模式化何谓创新,标签化了无真情。
写作倚人工智能,新八股困机器病。
临文不苟劳罄心,辞达为本风骨魂。

-我已经到底线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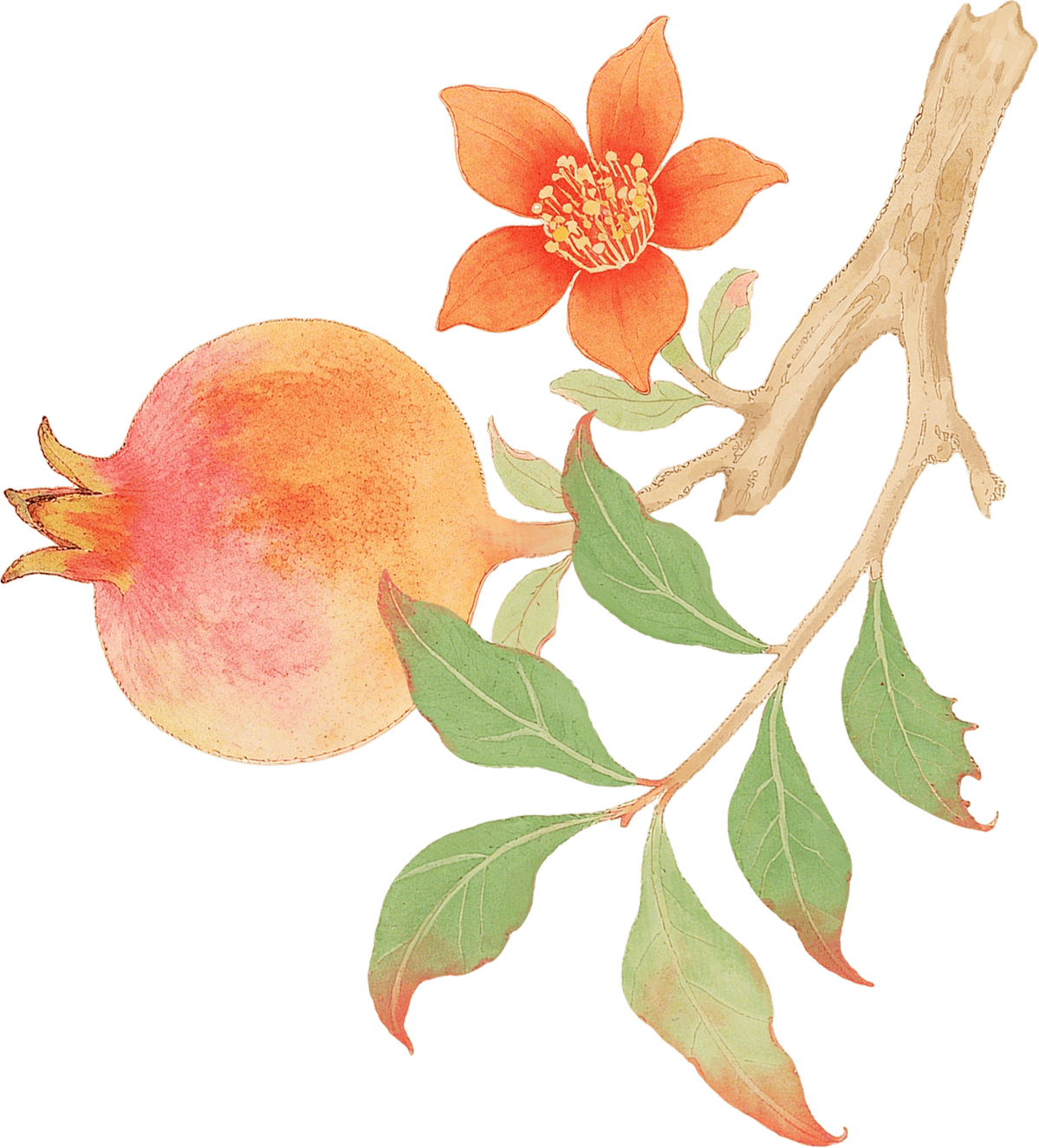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