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徐全庆
周福元突然来电话,让我约几个同学聚一聚,他请客。我的第一感觉是遇到了骗子,赶紧又看一眼来电号码,是周福元的。再仔细辨听声音,确实是周福元。“什么事儿可以先给我透露一下吗?”我问。
他说:“啥事儿没有,就是想大家了。”但语气中掩饰不住一股兴奋之情。
放下电话,我感觉周边的一切都朦朦胧胧的,仿佛置身于一个虚幻的世界中。
周福元是我师专的同学。学校只面向省内招生,我们班阜阳老乡就有七个,周福元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我们学校还包分配,进了校门就等于有了工作,学业相当轻松,远不像现在的学生那么卷,那么苦。除了张亮等少数几个人,大家都不怎么学习,变着花样玩,想把高中时没能玩的时间补回来。周福元喜欢打扑克,一回宿舍就在走廊里大喊“三缺一了”,其实往往还只有他一个人。他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在打扑克中度过的。学习自然是不好的,每个学期都有两三门成绩补考。张亮曾经劝过他:“也不能光玩,学习总要有个差不多,毕竟咱将来要当老师的。”他满不在乎地说:“我这三年学不上,教初中生也绰绰有余。”
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我们七个老乡境遇都差不多,基本上都分配到乡镇中学。起初,我们常常相聚,都是我在市内安排好酒店,大家从不同的县会聚过来。那时候大家都意气风发,大谈将来如何如何,仿佛只要我们愿意,世界就会按照我们的意愿改变。周福元从来不谈这些。大家问他将来如何打算,他总是说:“想将来干啥?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大改变。我通过招考进了一家政府机关,张亮已经成了全市有名的教坛新星,江涛考研去了外地,卢鼎年成了教导主任……只有周福元还像以前一样。
我们的聚会不再像过去一样频繁,往往两三年才聚一次,就这周福元还常常缺席。酒桌上他只闷头喝酒,很少说话,偶尔一张口,就是骂社会不公,骂他们校长欺负老实人。
从他的骂声里,我们知道了他这些年没有任何进步,甚至连中级职称都没有。按他的说法,主要是校长对他有成见。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能沉默。
有一次,卢鼎年问我:“你不是和教育局的人熟吗?”
周福元眼中泛起一道亮光,殷殷地望着我。
我无奈地笑笑:“我只和我们区的教育局熟悉。”
他眼中的亮光迅速消失了,又闷头喝酒。大家都劝他少喝点。他倒了一满杯酒,冲大家举了举杯子,说:“大家不要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我其实挺好的,课不多,有的是时间打牌,不像你们,每天忙得要死。”
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周福元。最近几次同学聚会,他都借口有事没有参加。没想到这次他竟主动约大家见面。
这一次我们聚得很齐,连外地的江涛也回来了。周福元不再像过去那样少言寡语,他像个高明的主持人一样,牢牢把握着话题方向,而且不时地插科打诨,活跃着现场气氛。
我们都惊讶他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这谜团很快由他自己解开了,他当了校总务处主任。
我们一起举杯敬他酒说:“周主任好。”语气半是戏谑半是真诚。
他连连摆手说:“我还只是代理,正式文件还没下呢。”他这样说时,嘴角翘得老高,掩饰不住兴奋。
他接着说,虽然只代理了短短一段时间,新校长对他的管理能力很是欣赏。“以前都被教学耽误了,我要是早走上管理岗位……”下面的话他没说完,但意思我们都明白。
酒足饭饱,他把钱包拍在服务员手中:“帮我把账结了,别忘了开张发票。”
几个同学羡慕地望着他。当了多年副校长的卢鼎年在我耳边悄悄说:“要发票也没用,一个总务主任,应该报不掉。”
分手的时候,大家都依依不舍。周福元逐个握着大家的手说:“有时间到我那里去,我在县城安排。”
之后又没了他的消息。打他的电话,居然成了空号。发微信也不回。我问其他几个同学他怎么了,大家和我一样茫然。
他在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
有一次,我开车恰好路过他的学校,便去找他。门卫问我找谁,我说:“你们总务主任周福元。”
“他可不是总务主任。”门卫说,语气中颇有些不屑的味道。
“没当上?”我很吃惊。
“代理了两个月就被拿下来了。”门卫说:“请您登记一下。”
我没有登记,直接离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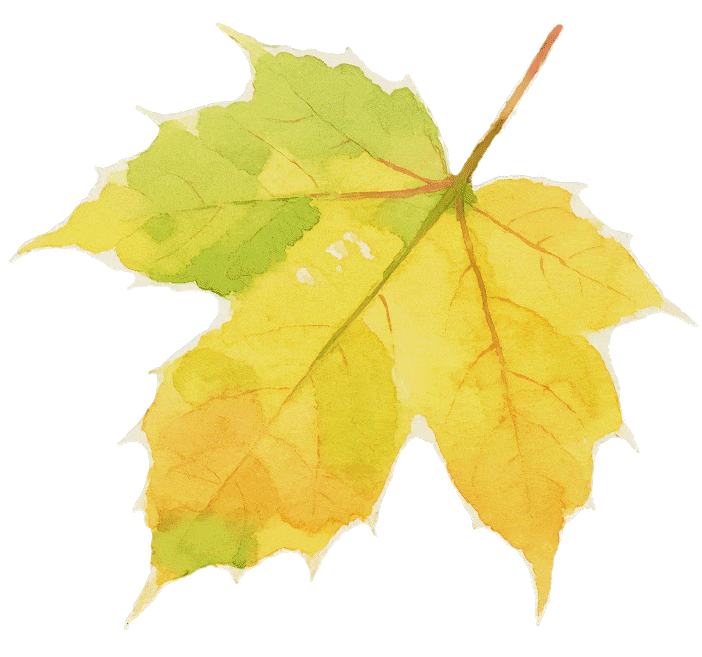
□ 何百源
甜杨桃和酸杨桃是一对孪生兄弟,不但树型、叶子、花极其相似,就是果实也毫无二致,只有当你品尝它时,才能判别出来。为了区别甜杨桃和酸杨桃,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人给酸杨桃另外起了一个名字:三稔。
村子里同时生长着甜杨桃和三稔树,每到果熟时节,甜杨桃树下就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充溢着赞美的话语。
而三稔树呢?果实落了一地而无人问津。不但这样,因为落地的果子招惹虫蚁和其他生物,沤烂了以后又散发出腐朽的气味,因此人们都非常厌恶它。有的人就说,这是棵没用的树,果实不但不能吃,反而污染了环境,不如把它砍伐了吧!
住在三稔树旁的少年小凡好几次在睡梦中听见有人对他说:救救我!小凡从梦中醒来,推开窗,窗外阒无一人。他大声问:谁在求救?无人回应。他想了很久,只有一种可能,三稔树在求救。
怎么救呢?他想,人们之所以要伐倒三稔树,是因为它的果不但不能吃,还污染环境。
要救树,就得将果变废为宝。他找了许多参考书籍研读,并反复试验。
树的基因是无法改变的,那就只有从果实入手。他将三稔果切成一片片,进行腌制,然后晒干,一尝,酸味去掉了,变成了非常可口的零食,且对健康有益。
他将“三稔干”分发众街坊,但没有说明这是什么果品。
大家品尝过后,都啧啧称赞这种果干美味解馋,并询问这果品的来路。
当大家了解了这美味果干的来源之后,都惊奇地将嘴巴张成了“O”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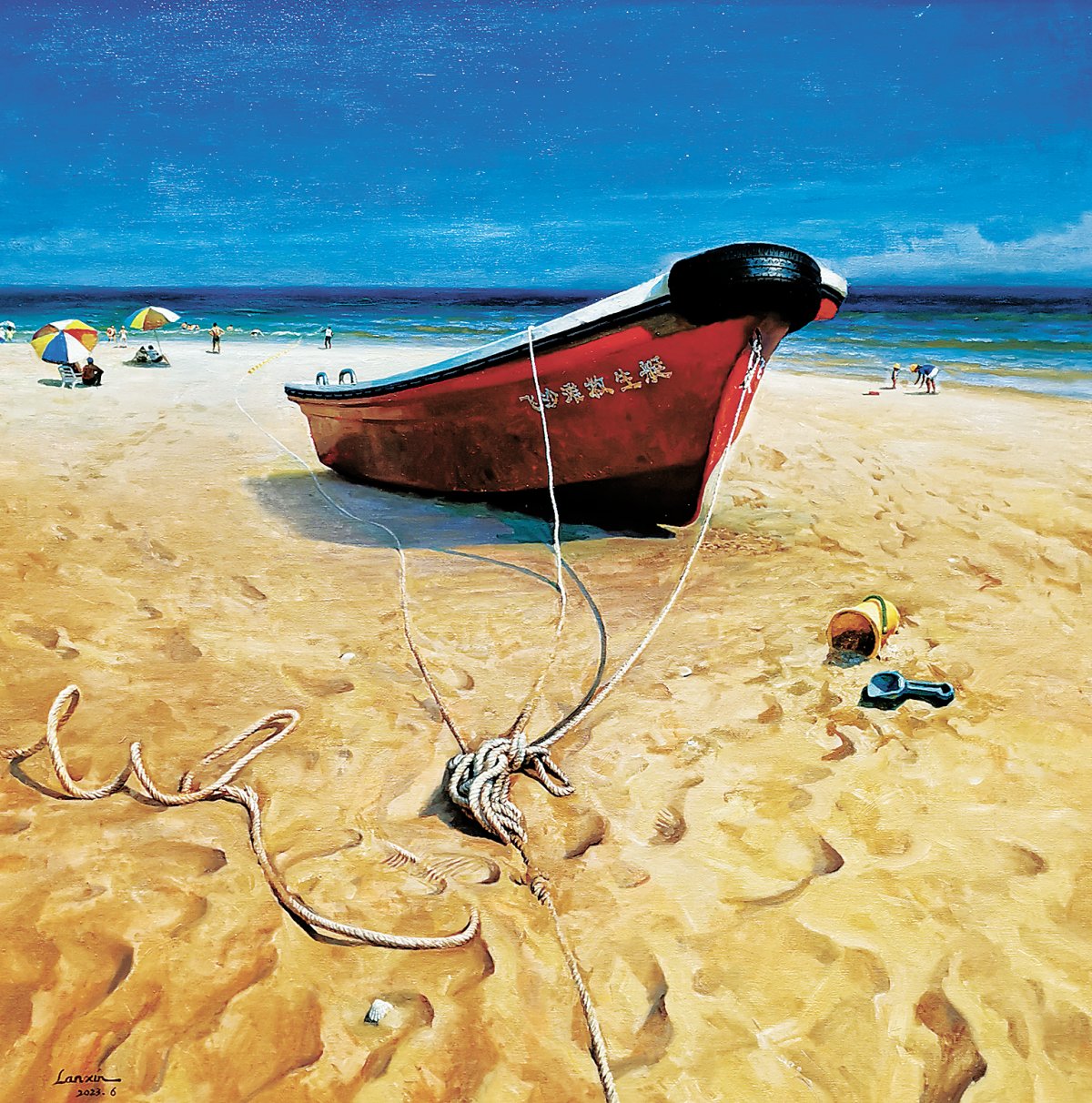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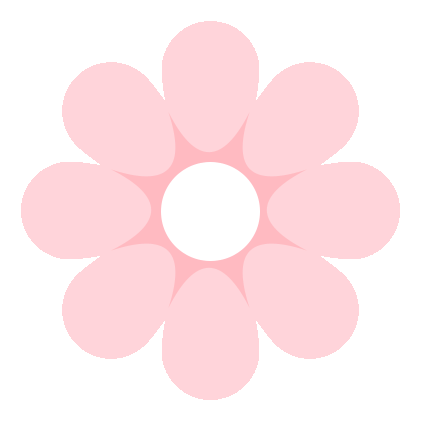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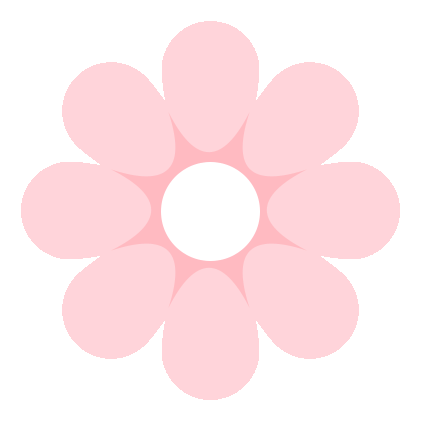
□ 郝 俊
阳台上的两盆杜鹃花,是2024年除夕买的,那天中午吃完团年饭,我下楼散步,看到学校西门对面的花市还没有打烊,就走了进去,发现大多摊位都撤走了,还有少数几个摊主正在收拾,看样子也准备回家过年。只有一个摊位前还有人在买花,走近一看,有十多盆杜鹃花开得火红娇艳,一朵朵花挤在一起,互不相让,着实令人喜欢。
我凑过去看了好一会儿,摊主问我买不买?我才回过神来,我买了两盆,一手一盆提回家,心里美滋滋的。有时候收获惊喜就是这样简单,多一份无关现实利益的喜好,生活也许就多一些乐趣。有句话说得好:“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确,有限的人生总该做一些看似无用的事情,这样可以让生活增添更多的美好。
伺弄花草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把买回来的两盆杜鹃花安置在阳台上,按那位摊主介绍的养护方法,每隔两三天浇一次水,大概两周之后,发现有几朵花的花瓣开始发蔫,我估计是因为光照和气温条件的改变,导致水分消耗比以前要大,于是试着改为每天早上浇一次水,每次大约100毫升,一周之后,那些发蔫的花瓣就重新振作起来了。根据以前的经验,临近春节,在花市买的花,尤其是那种小盆栽种的花卉,花期大多只有半个月,这两盆杜鹃花倒是有些出乎意料,3月上旬的时候,依旧红艳,只是花开得不似先前那般满满当当,直到3月下旬还有零星几朵,愈发令人珍惜。在我看来,近两个月的花期,已经称得上相当“漫长”了。
到了4月上旬,枝叶上只剩下枯萎的花瓣,看上去犹如暗红的疮痂,等全部脱落之后,春日已尽,转眼就到了夏天,褪去红妆的杜鹃换上一身清爽的绿衫,虽没有开花时那么动人,却也十分养眼。我认真观察过它们的叶子,很有层次感,最里面是一个嫩绿的“小尖儿”,等这个“小尖儿”展开之后,就有了叶子的模样,当原来的“小尖儿”变成小叶子,里面又会生出“小尖儿”,叶子就这么一层一层地打开,似乎有一种层出不穷的魔力。从里到外的叶子,其颜色也会发生渐变,从嫩绿变为碧绿,而后深绿。新叶不断长出来的同时,最外面的叶子就会逐渐枯黄,直至凋落,到五六月份的时候,新老叶子基本完成交替,可谓“旧貌换新颜”。
我每天早上洗漱后,就给它们浇水,从不间断,心里期盼它们年底开花,有时候也会对它们念叨一句“冬天记得开花哟”。12月上旬的时候,我发现其中一盆结了一个花苞,看着花苞顶端露出来的一点殷红,如获至宝,情不自禁地大声喊道:“开花了!开花了!”家里人都围过来看。
我相信,每一盆花都有自己的花期,都有自己的际遇,不必催促,不用焦急,只需耐心等待和守候。
今年1月18日,我看到了两个花苞,一周之后,两个花苞已褪去青涩,显出将绽未绽、欲言又止的娇羞之态。都说美人迟暮,到了4月,本以为花期会结束,没想到岁月不败美人,总是有几朵花端坐枝头。一年多来,杜鹃花让我看到了属于它们的美妙和深邃,有时候,我会蹲在它们旁边,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它们,都会为它们的一点小变化感到惊讶和满足。这种奇妙的体验,让我想到《海德格尔文集:从思想的经验而来》一书中的几句话:“匆忙与惊讶……前者经营算计。后者不期而至。前者遵守一个计划。后者拜访一个驻留。”
我以为,看花的时候,就是“驻留”,就是一次忙碌之外的诗意停顿。

□ 施 维
诗人艾青曾说:“诗是人类向未来寄发的信息,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对困境的凝视与对光明的追寻,在罗春柏的诗歌《韦帕》与《记忆》中得到了深刻印证。前者以台风“韦帕”为切口,展开自然暴力对现实世界的撕裂与重构;后者借“记忆”为载体,呈现时间长河中情感碎片的沉淀与反刍。两首诗看似主题迥异,实则共同构建了一个关于“困境”的精神场域,诗人始终以诗意的笔触在黑暗里打捞光的形状,完成对生命韧性的诗性确证。
《韦帕》的开端便以极具冲击力的意象撕开现实的伤口:“挣脱镣铐的狂人/率性地施暴/用铁鞭抽打七月的大地”。这里的“韦帕”已超越台风的自然属性,被赋予“狂人”的人格化特征——“挣脱镣铐”的野性、“率性施暴”的无度、“铁鞭抽打”的暴烈,共同构建出自然力对人类秩序的颠覆图景。诗人将抽象灾难具象化的手法,强化了视觉冲击,更暗示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从“和谐共生”滑向“对抗撕裂”。
诗人并未停留在破坏场景的铺陈,而是以“花园成了废墟”“残垣断壁间”的白描,将灾难的破坏性延伸至空间与人心的双重维度。当“行人驱不散心头惊魂”时,自然暴力已从物理层面渗透到精神领域,形成对生存安全感的根本动摇。诗人以“你”代指所有受灾者,将个体经验升华为群体记忆,在灾难的废墟上立起了生命韧性的坐标。
如果说《韦帕》聚焦自然暴力对现实的冲击,《记忆》则转向时间对情感的侵蚀。诗中“褪色的胶片/在脑海里播放”的开头,以“胶片”这个物质载体隐喻记忆的易逝性——“褪色”“斑驳”“模糊”等修饰词,共同构建出记忆的“雾态”:既非彻底消散,亦非清晰可触,而是以若即若离的姿态存在于意识深处。诗人对记忆质感的精准捕捉,使诗歌一开始便笼罩着温柔的怅惘。
诗人并未沉溺于记忆的模糊性,而是以具体场景的回溯激活情感的温度:“曾在村口的广场/一起放飞风筝/说过的誓言/随风飘向远方”。“村口广场”“风筝”“誓言”等意象,共同勾勒出一段鲜活的过往——广场是公共记忆的场域,风筝是自由与联结的象征,誓言则是情感的契约。然而“随风飘向远方”的转折,将记忆的美好与流失并置,形成情感的张力。
诗的后半段转向对记忆的主动审视:“在时间流水中/寻找你浪迹的远帆/却在涟漪镜面/照见自己的孤单”。“时间流水”的意象呼应“胶片”的流逝感,“寻找远帆”是对记忆的主动打捞,“涟漪镜面”的反射却暴露了“孤单”的本质——当试图在记忆中寻找他人的痕迹时,最终照见的是自我的存在。诗人认知的翻转,将记忆从“对他者的追念”升华为“对自我的观照”。而结尾“摘一朵水花作围巾/擦拭眼睛里的纤尘/原来许多往事/是心空驱不散的浮云”,以“水花作围巾”的诗意动作,完成对记忆的仪式化整理:“擦拭纤尘”是对记忆杂质的过滤,“浮云”的比喻则道破记忆的本质——既非沉重的负累,亦非虚无的幻影,而是心空永恒的存在,以轻盈的姿态参与生命的构成。
从《韦帕》的“寻找晴朗”到《记忆》的“擦拭纤尘”,罗春柏的诗歌完成了一次从外部困境到内部困境、从现实突围到心灵澄明的精神漫游。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是诗人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捕捉,是一个观察者对生命本质的思考——真正的超越,不在于战胜困境,而在于在困境中保持凝视的勇气,让每一道裂痕都成为光照进来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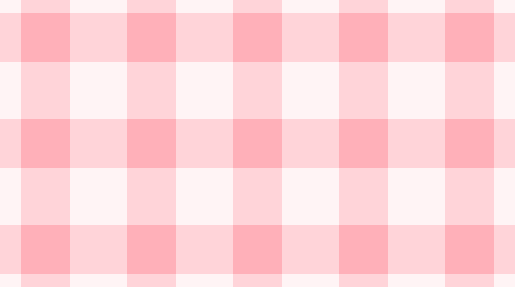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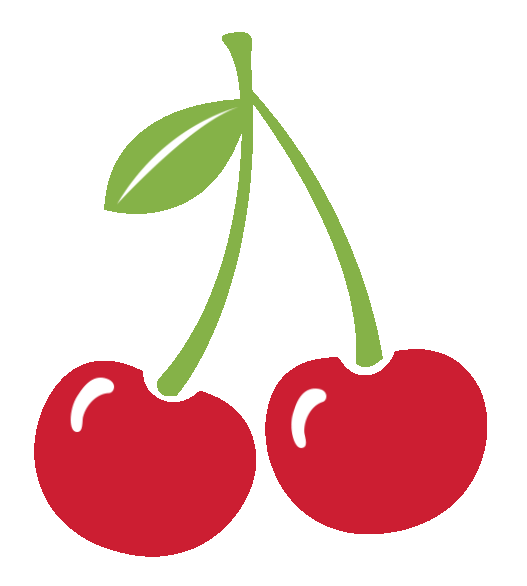
□ 邓 婷
没有亲昵的称呼
和揽入怀里的嬉闹
额头上也没留下吻痕
想不起您笑的模样
让我一度怀疑您和别人的奶奶不一样
有一把用了多年的蒲扇
又大又旧 风却很大
食不言寝不语是铁律
蒲扇的摇摆声伴我入眠
度过了无数个炎热的夜晚
不知道您的手现在还酸不酸痛
如果空调没有坏掉
我会记起那把又大又旧的蒲扇吗
偶尔您又会成为裁判
少有的荔枝蒸鸡蛋
成了是非的源头
昏暗的煤油灯下
严肃表情那么清晰
拄着拐杖坐在我们兄妹之间
防止我碗里的食物被掠夺
印象中没见您享用过
难道您不喜欢甜
如果可以 好想现在问问您
荔枝甜 可是鸡蛋不甜啊
记忆中看到您给我兄长吃食
应该勇敢一点走进去
问问您属于我的那一份
如今 您离开我们已经多年
我终于明白
这也是一种爱
就不会给您贴了二十多年
都不掉色的偏心的标签
安息地
小黄花在微笑
知了在演奏
蝴蝶在舞蹈
鸟儿在觅食
湖光潋滟
鱼儿成双成对
人类是占有的奴隶
当肉体被世俗束缚
灵魂就得不到释放
远看的美好
靠近的污浊
愿用轮回救赎无知
三伏天只有燥热
没有微风带香
天上的云儿在扮怪
尘世的虚伪 罪孽 悲伤
向你汹涌而来
在密林的深处
寻觅轮回通道
仿佛听到
生命成长的另一种声音
□ 钟百超
阳台的空间不算小
我曾在花盆里种过兰花、玫瑰和月季还有许多花花草草
名字已经想不起来了
似乎都是云烟过客
想留也留不住
否则今天的阳台
一定是它们的风景
前年种的木棯去年开花了
收获了十几枚果子
今年又开出了更多的花
从四月底到现在
依然还有许多花苞
等待绽放的妩媚
每一朵花凋谢后就化作一颗果子
花和果是天生的因果循环
但不是每一粒果子
都有幸长成成熟的模样
有些过一段时间就蔫掉
最后变成我口福的
一定和我有着同样顽强的生命意志
让你赏花,还长出果子给你吃
这是何等美妙的事情
在这花里的世界
有我们难以企及的境界
一些植物,比如猪笼草
许下美好的诺言
其实是在布下一个巨大的陷阱
多少心怀善念的虫儿
难免会因果腹而成为猎物

□ 徐全庆
周福元突然来电话,让我约几个同学聚一聚,他请客。我的第一感觉是遇到了骗子,赶紧又看一眼来电号码,是周福元的。再仔细辨听声音,确实是周福元。“什么事儿可以先给我透露一下吗?”我问。
他说:“啥事儿没有,就是想大家了。”但语气中掩饰不住一股兴奋之情。
放下电话,我感觉周边的一切都朦朦胧胧的,仿佛置身于一个虚幻的世界中。
周福元是我师专的同学。学校只面向省内招生,我们班阜阳老乡就有七个,周福元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我们学校还包分配,进了校门就等于有了工作,学业相当轻松,远不像现在的学生那么卷,那么苦。除了张亮等少数几个人,大家都不怎么学习,变着花样玩,想把高中时没能玩的时间补回来。周福元喜欢打扑克,一回宿舍就在走廊里大喊“三缺一了”,其实往往还只有他一个人。他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在打扑克中度过的。学习自然是不好的,每个学期都有两三门成绩补考。张亮曾经劝过他:“也不能光玩,学习总要有个差不多,毕竟咱将来要当老师的。”他满不在乎地说:“我这三年学不上,教初中生也绰绰有余。”
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我们七个老乡境遇都差不多,基本上都分配到乡镇中学。起初,我们常常相聚,都是我在市内安排好酒店,大家从不同的县会聚过来。那时候大家都意气风发,大谈将来如何如何,仿佛只要我们愿意,世界就会按照我们的意愿改变。周福元从来不谈这些。大家问他将来如何打算,他总是说:“想将来干啥?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大改变。我通过招考进了一家政府机关,张亮已经成了全市有名的教坛新星,江涛考研去了外地,卢鼎年成了教导主任……只有周福元还像以前一样。
我们的聚会不再像过去一样频繁,往往两三年才聚一次,就这周福元还常常缺席。酒桌上他只闷头喝酒,很少说话,偶尔一张口,就是骂社会不公,骂他们校长欺负老实人。
从他的骂声里,我们知道了他这些年没有任何进步,甚至连中级职称都没有。按他的说法,主要是校长对他有成见。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能沉默。
有一次,卢鼎年问我:“你不是和教育局的人熟吗?”
周福元眼中泛起一道亮光,殷殷地望着我。
我无奈地笑笑:“我只和我们区的教育局熟悉。”
他眼中的亮光迅速消失了,又闷头喝酒。大家都劝他少喝点。他倒了一满杯酒,冲大家举了举杯子,说:“大家不要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我其实挺好的,课不多,有的是时间打牌,不像你们,每天忙得要死。”
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周福元。最近几次同学聚会,他都借口有事没有参加。没想到这次他竟主动约大家见面。
这一次我们聚得很齐,连外地的江涛也回来了。周福元不再像过去那样少言寡语,他像个高明的主持人一样,牢牢把握着话题方向,而且不时地插科打诨,活跃着现场气氛。
我们都惊讶他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这谜团很快由他自己解开了,他当了校总务处主任。
我们一起举杯敬他酒说:“周主任好。”语气半是戏谑半是真诚。
他连连摆手说:“我还只是代理,正式文件还没下呢。”他这样说时,嘴角翘得老高,掩饰不住兴奋。
他接着说,虽然只代理了短短一段时间,新校长对他的管理能力很是欣赏。“以前都被教学耽误了,我要是早走上管理岗位……”下面的话他没说完,但意思我们都明白。
酒足饭饱,他把钱包拍在服务员手中:“帮我把账结了,别忘了开张发票。”
几个同学羡慕地望着他。当了多年副校长的卢鼎年在我耳边悄悄说:“要发票也没用,一个总务主任,应该报不掉。”
分手的时候,大家都依依不舍。周福元逐个握着大家的手说:“有时间到我那里去,我在县城安排。”
之后又没了他的消息。打他的电话,居然成了空号。发微信也不回。我问其他几个同学他怎么了,大家和我一样茫然。
他在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
有一次,我开车恰好路过他的学校,便去找他。门卫问我找谁,我说:“你们总务主任周福元。”
“他可不是总务主任。”门卫说,语气中颇有些不屑的味道。
“没当上?”我很吃惊。
“代理了两个月就被拿下来了。”门卫说:“请您登记一下。”
我没有登记,直接离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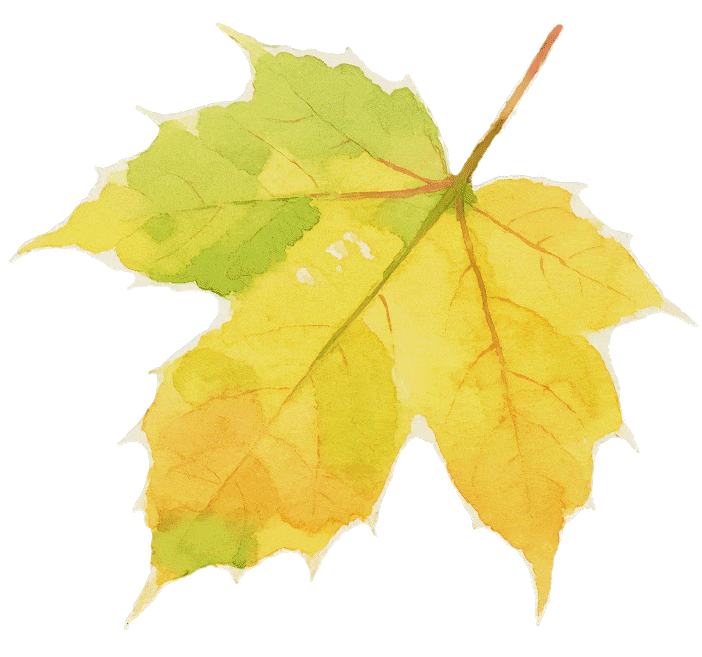
□ 何百源
甜杨桃和酸杨桃是一对孪生兄弟,不但树型、叶子、花极其相似,就是果实也毫无二致,只有当你品尝它时,才能判别出来。为了区别甜杨桃和酸杨桃,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人给酸杨桃另外起了一个名字:三稔。
村子里同时生长着甜杨桃和三稔树,每到果熟时节,甜杨桃树下就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充溢着赞美的话语。
而三稔树呢?果实落了一地而无人问津。不但这样,因为落地的果子招惹虫蚁和其他生物,沤烂了以后又散发出腐朽的气味,因此人们都非常厌恶它。有的人就说,这是棵没用的树,果实不但不能吃,反而污染了环境,不如把它砍伐了吧!
住在三稔树旁的少年小凡好几次在睡梦中听见有人对他说:救救我!小凡从梦中醒来,推开窗,窗外阒无一人。他大声问:谁在求救?无人回应。他想了很久,只有一种可能,三稔树在求救。
怎么救呢?他想,人们之所以要伐倒三稔树,是因为它的果不但不能吃,还污染环境。
要救树,就得将果变废为宝。他找了许多参考书籍研读,并反复试验。
树的基因是无法改变的,那就只有从果实入手。他将三稔果切成一片片,进行腌制,然后晒干,一尝,酸味去掉了,变成了非常可口的零食,且对健康有益。
他将“三稔干”分发众街坊,但没有说明这是什么果品。
大家品尝过后,都啧啧称赞这种果干美味解馋,并询问这果品的来路。
当大家了解了这美味果干的来源之后,都惊奇地将嘴巴张成了“O”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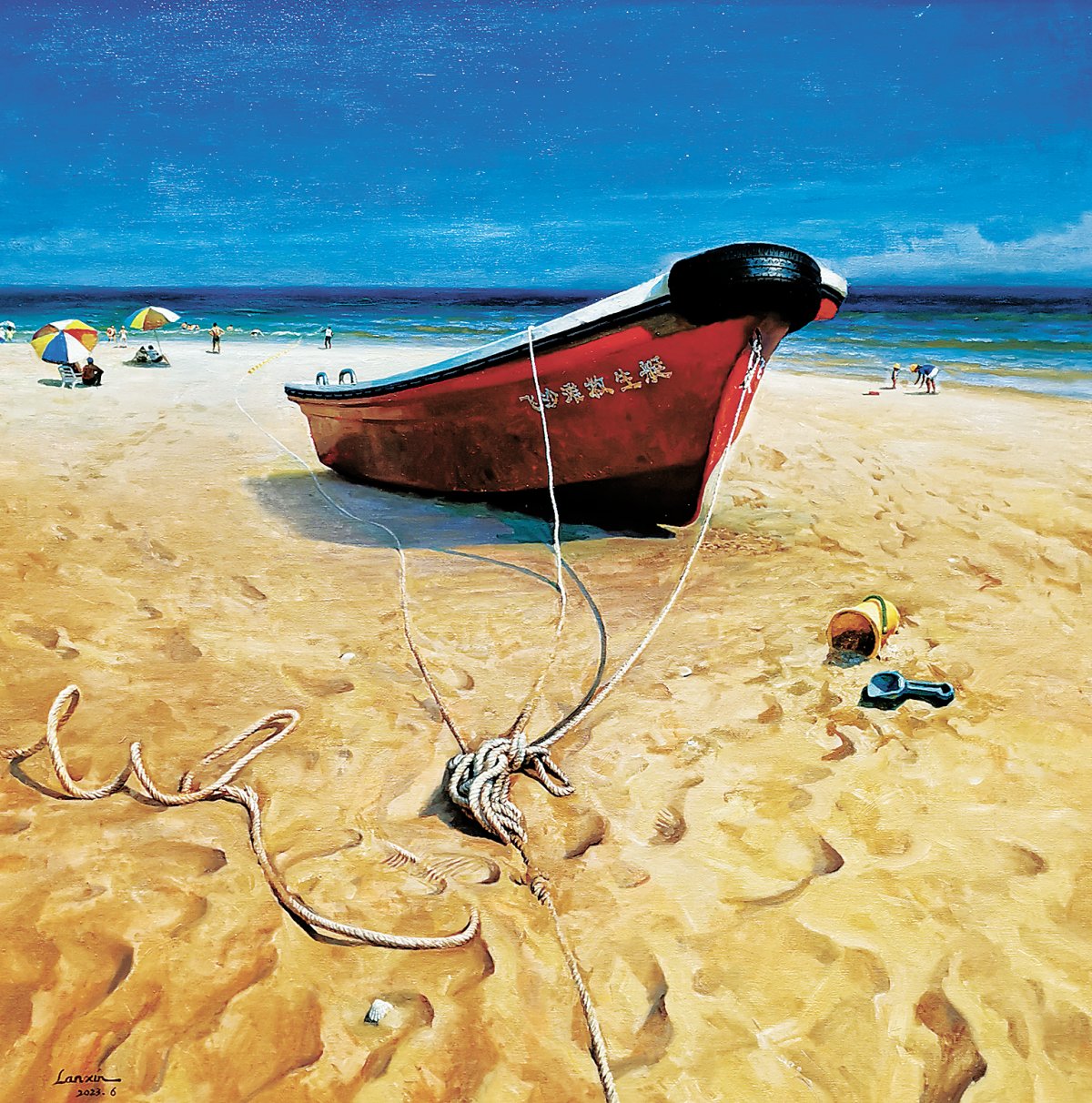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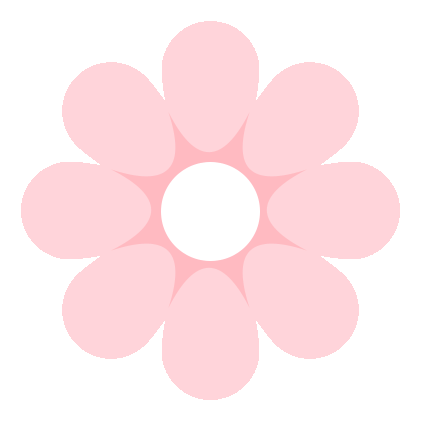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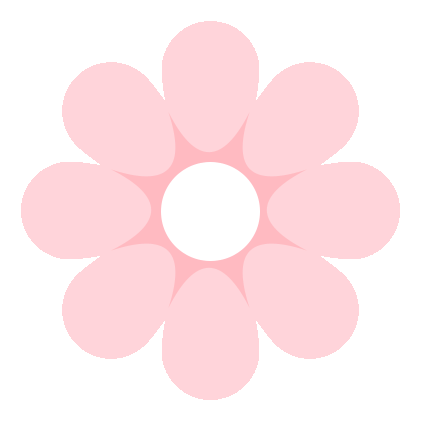
□ 郝 俊
阳台上的两盆杜鹃花,是2024年除夕买的,那天中午吃完团年饭,我下楼散步,看到学校西门对面的花市还没有打烊,就走了进去,发现大多摊位都撤走了,还有少数几个摊主正在收拾,看样子也准备回家过年。只有一个摊位前还有人在买花,走近一看,有十多盆杜鹃花开得火红娇艳,一朵朵花挤在一起,互不相让,着实令人喜欢。
我凑过去看了好一会儿,摊主问我买不买?我才回过神来,我买了两盆,一手一盆提回家,心里美滋滋的。有时候收获惊喜就是这样简单,多一份无关现实利益的喜好,生活也许就多一些乐趣。有句话说得好:“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确,有限的人生总该做一些看似无用的事情,这样可以让生活增添更多的美好。
伺弄花草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把买回来的两盆杜鹃花安置在阳台上,按那位摊主介绍的养护方法,每隔两三天浇一次水,大概两周之后,发现有几朵花的花瓣开始发蔫,我估计是因为光照和气温条件的改变,导致水分消耗比以前要大,于是试着改为每天早上浇一次水,每次大约100毫升,一周之后,那些发蔫的花瓣就重新振作起来了。根据以前的经验,临近春节,在花市买的花,尤其是那种小盆栽种的花卉,花期大多只有半个月,这两盆杜鹃花倒是有些出乎意料,3月上旬的时候,依旧红艳,只是花开得不似先前那般满满当当,直到3月下旬还有零星几朵,愈发令人珍惜。在我看来,近两个月的花期,已经称得上相当“漫长”了。
到了4月上旬,枝叶上只剩下枯萎的花瓣,看上去犹如暗红的疮痂,等全部脱落之后,春日已尽,转眼就到了夏天,褪去红妆的杜鹃换上一身清爽的绿衫,虽没有开花时那么动人,却也十分养眼。我认真观察过它们的叶子,很有层次感,最里面是一个嫩绿的“小尖儿”,等这个“小尖儿”展开之后,就有了叶子的模样,当原来的“小尖儿”变成小叶子,里面又会生出“小尖儿”,叶子就这么一层一层地打开,似乎有一种层出不穷的魔力。从里到外的叶子,其颜色也会发生渐变,从嫩绿变为碧绿,而后深绿。新叶不断长出来的同时,最外面的叶子就会逐渐枯黄,直至凋落,到五六月份的时候,新老叶子基本完成交替,可谓“旧貌换新颜”。
我每天早上洗漱后,就给它们浇水,从不间断,心里期盼它们年底开花,有时候也会对它们念叨一句“冬天记得开花哟”。12月上旬的时候,我发现其中一盆结了一个花苞,看着花苞顶端露出来的一点殷红,如获至宝,情不自禁地大声喊道:“开花了!开花了!”家里人都围过来看。
我相信,每一盆花都有自己的花期,都有自己的际遇,不必催促,不用焦急,只需耐心等待和守候。
今年1月18日,我看到了两个花苞,一周之后,两个花苞已褪去青涩,显出将绽未绽、欲言又止的娇羞之态。都说美人迟暮,到了4月,本以为花期会结束,没想到岁月不败美人,总是有几朵花端坐枝头。一年多来,杜鹃花让我看到了属于它们的美妙和深邃,有时候,我会蹲在它们旁边,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它们,都会为它们的一点小变化感到惊讶和满足。这种奇妙的体验,让我想到《海德格尔文集:从思想的经验而来》一书中的几句话:“匆忙与惊讶……前者经营算计。后者不期而至。前者遵守一个计划。后者拜访一个驻留。”
我以为,看花的时候,就是“驻留”,就是一次忙碌之外的诗意停顿。

□ 施 维
诗人艾青曾说:“诗是人类向未来寄发的信息,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对困境的凝视与对光明的追寻,在罗春柏的诗歌《韦帕》与《记忆》中得到了深刻印证。前者以台风“韦帕”为切口,展开自然暴力对现实世界的撕裂与重构;后者借“记忆”为载体,呈现时间长河中情感碎片的沉淀与反刍。两首诗看似主题迥异,实则共同构建了一个关于“困境”的精神场域,诗人始终以诗意的笔触在黑暗里打捞光的形状,完成对生命韧性的诗性确证。
《韦帕》的开端便以极具冲击力的意象撕开现实的伤口:“挣脱镣铐的狂人/率性地施暴/用铁鞭抽打七月的大地”。这里的“韦帕”已超越台风的自然属性,被赋予“狂人”的人格化特征——“挣脱镣铐”的野性、“率性施暴”的无度、“铁鞭抽打”的暴烈,共同构建出自然力对人类秩序的颠覆图景。诗人将抽象灾难具象化的手法,强化了视觉冲击,更暗示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从“和谐共生”滑向“对抗撕裂”。
诗人并未停留在破坏场景的铺陈,而是以“花园成了废墟”“残垣断壁间”的白描,将灾难的破坏性延伸至空间与人心的双重维度。当“行人驱不散心头惊魂”时,自然暴力已从物理层面渗透到精神领域,形成对生存安全感的根本动摇。诗人以“你”代指所有受灾者,将个体经验升华为群体记忆,在灾难的废墟上立起了生命韧性的坐标。
如果说《韦帕》聚焦自然暴力对现实的冲击,《记忆》则转向时间对情感的侵蚀。诗中“褪色的胶片/在脑海里播放”的开头,以“胶片”这个物质载体隐喻记忆的易逝性——“褪色”“斑驳”“模糊”等修饰词,共同构建出记忆的“雾态”:既非彻底消散,亦非清晰可触,而是以若即若离的姿态存在于意识深处。诗人对记忆质感的精准捕捉,使诗歌一开始便笼罩着温柔的怅惘。
诗人并未沉溺于记忆的模糊性,而是以具体场景的回溯激活情感的温度:“曾在村口的广场/一起放飞风筝/说过的誓言/随风飘向远方”。“村口广场”“风筝”“誓言”等意象,共同勾勒出一段鲜活的过往——广场是公共记忆的场域,风筝是自由与联结的象征,誓言则是情感的契约。然而“随风飘向远方”的转折,将记忆的美好与流失并置,形成情感的张力。
诗的后半段转向对记忆的主动审视:“在时间流水中/寻找你浪迹的远帆/却在涟漪镜面/照见自己的孤单”。“时间流水”的意象呼应“胶片”的流逝感,“寻找远帆”是对记忆的主动打捞,“涟漪镜面”的反射却暴露了“孤单”的本质——当试图在记忆中寻找他人的痕迹时,最终照见的是自我的存在。诗人认知的翻转,将记忆从“对他者的追念”升华为“对自我的观照”。而结尾“摘一朵水花作围巾/擦拭眼睛里的纤尘/原来许多往事/是心空驱不散的浮云”,以“水花作围巾”的诗意动作,完成对记忆的仪式化整理:“擦拭纤尘”是对记忆杂质的过滤,“浮云”的比喻则道破记忆的本质——既非沉重的负累,亦非虚无的幻影,而是心空永恒的存在,以轻盈的姿态参与生命的构成。
从《韦帕》的“寻找晴朗”到《记忆》的“擦拭纤尘”,罗春柏的诗歌完成了一次从外部困境到内部困境、从现实突围到心灵澄明的精神漫游。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是诗人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捕捉,是一个观察者对生命本质的思考——真正的超越,不在于战胜困境,而在于在困境中保持凝视的勇气,让每一道裂痕都成为光照进来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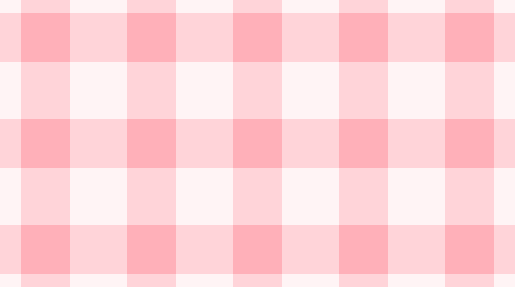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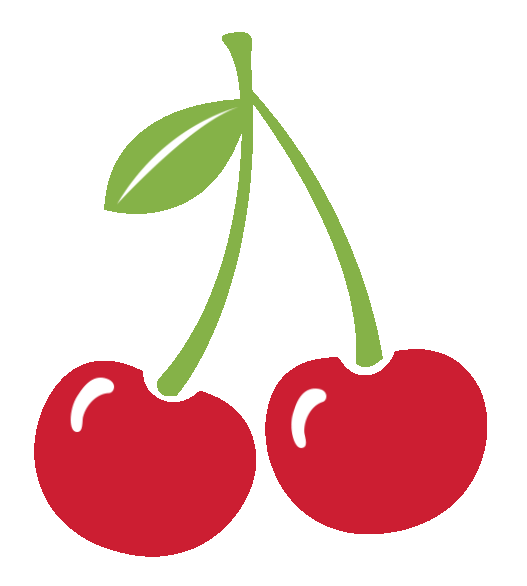
□ 邓 婷
没有亲昵的称呼
和揽入怀里的嬉闹
额头上也没留下吻痕
想不起您笑的模样
让我一度怀疑您和别人的奶奶不一样
有一把用了多年的蒲扇
又大又旧 风却很大
食不言寝不语是铁律
蒲扇的摇摆声伴我入眠
度过了无数个炎热的夜晚
不知道您的手现在还酸不酸痛
如果空调没有坏掉
我会记起那把又大又旧的蒲扇吗
偶尔您又会成为裁判
少有的荔枝蒸鸡蛋
成了是非的源头
昏暗的煤油灯下
严肃表情那么清晰
拄着拐杖坐在我们兄妹之间
防止我碗里的食物被掠夺
印象中没见您享用过
难道您不喜欢甜
如果可以 好想现在问问您
荔枝甜 可是鸡蛋不甜啊
记忆中看到您给我兄长吃食
应该勇敢一点走进去
问问您属于我的那一份
如今 您离开我们已经多年
我终于明白
这也是一种爱
就不会给您贴了二十多年
都不掉色的偏心的标签
安息地
小黄花在微笑
知了在演奏
蝴蝶在舞蹈
鸟儿在觅食
湖光潋滟
鱼儿成双成对
人类是占有的奴隶
当肉体被世俗束缚
灵魂就得不到释放
远看的美好
靠近的污浊
愿用轮回救赎无知
三伏天只有燥热
没有微风带香
天上的云儿在扮怪
尘世的虚伪 罪孽 悲伤
向你汹涌而来
在密林的深处
寻觅轮回通道
仿佛听到
生命成长的另一种声音
□ 钟百超
阳台的空间不算小
我曾在花盆里种过兰花、玫瑰和月季还有许多花花草草
名字已经想不起来了
似乎都是云烟过客
想留也留不住
否则今天的阳台
一定是它们的风景
前年种的木棯去年开花了
收获了十几枚果子
今年又开出了更多的花
从四月底到现在
依然还有许多花苞
等待绽放的妩媚
每一朵花凋谢后就化作一颗果子
花和果是天生的因果循环
但不是每一粒果子
都有幸长成成熟的模样
有些过一段时间就蔫掉
最后变成我口福的
一定和我有着同样顽强的生命意志
让你赏花,还长出果子给你吃
这是何等美妙的事情
在这花里的世界
有我们难以企及的境界
一些植物,比如猪笼草
许下美好的诺言
其实是在布下一个巨大的陷阱
多少心怀善念的虫儿
难免会因果腹而成为猎物

-我已经到底线啦-









暂时没有评论